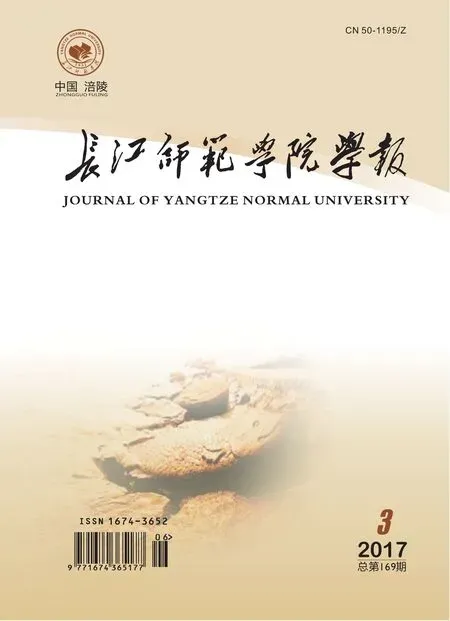移民与重庆城市的跳跃式发展
李禹阶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0047)
□本刊特稿
移民与重庆城市的跳跃式发展
李禹阶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0047)
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历次移民高潮直接推动了古今重庆城市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跳跃式发展,形成重庆民俗“五方杂处”的多元文化格局,并由此奠定了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科技、文化、教育重镇的地位。
移民;重庆;跳跃式;发展
移民与重庆地区发展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重庆地处西南一隅,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及资金、人才资源方面显得十分稀缺。正是因为历史上各次移民高潮,给重庆地区带来的人口、技术、资金、人才优势,直接地推动着重庆城市及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历代移民高潮推动重庆城市的跳跃式发展
重庆地处我国南北部和中西部的交界区,“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虽然重庆被山区环绕,但是水道纵横,境内有长江、嘉陵江、乌江等江河,为本地和外地人口的迁徙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早在夏商时期,从重庆峡江地区走出的巴人鱼凫部,沿长江西上,在川西建立了鱼凫蜀国。秦汉以来,巴地的民众开拓了四通八达的秦巴古道。同时,重庆位扼长江上游要津,系与嘉陵江的汇合处,当时长江中上游能够通航的几大水道,如长江水道、嘉陵江水道、乌江水道等,都与重庆水道直接相关。中国古代的吴越、荆楚与巴、蜀、黔、滇的贯通,重庆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重庆是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人口流动的主要区域。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巴蜀境内向外的交通有两条要道:一条为北向往汉中、关中地区,主要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道为主;另一条则由巴蜀东向,沿长江而下,直抵楚、吴等地。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许多因躲避战争、自然灾害而被迫迁徙的民众,其迁徙路径主要是沿着长江通道,经过三峡地区向上游流动。由于古代民众携家带口的长途远行,加上峡江高峡峻谷,崎岖难行,于是在移民迁徙的过程中,许多适宜生存或者便于就食的地方,都可能成为人们迁徙的居留地。这样,重庆地区尤其是长江沿岸地区,自古以来便成为中国南方、东方及其西南方向移民的重要流动地域。而正是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外来移民潮所形成的动力,直接地推动了重庆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大变化、大发展。
第一次移民高潮及重庆城市的发展是在汉代。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大量的外来移民进入古代巴地,由此促进了古代重庆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当时,来自北方的移民进入巴渝地区生产、生活,使巴地人口急剧增长,成为汉代人口繁盛之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巴郡有158 643户,708 148 人[1]卷28地理志上,1063; 据《后汉书·郡国五》载, 到东汉时有户 310 691 户, 1 086 049 人[2]第23郡国5,3507。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东汉永兴二年(154年)更达到464 780户,人口1 875 535[3]卷1巴志,20,户数较西汉初时增加了近3倍,人口增加了2倍多。两《汉书》所载巴郡人口应该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以汉族为主的编户齐民,而不包括巴地境内难以统计的少数民族“西南夷”。大量移民进入巴地,西汉政府专门在巴郡增设新的行政单位进行管理。由于其时巴郡所增加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汉水(今嘉陵江)、潜水(今渠江)一带,西汉政府就在这些地区新设垫江、安汉、充国、阆中、宕渠5县,其人口占了巴郡人口的2/3左右。这说明当时有许多移民是沿着河流两岸顺流而行,在向西、向北的迁徙、流转中定居或滞留于巴地。
大量移民的进入,加快了古代重庆城市的发展。作为巴郡治所的江州城,就是在人口增长的推动下不断地扩充、发展的。史载秦汉时期江州为郡县治地。秦灭巴蜀后,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11县。张仪筑江州城,为郡治所。两汉时期,随着大量人口进入巴郡,江州城区人口群集,城市也繁荣起来。东汉时期,江州之繁盛,史有所载。《华阳国志·巴志》描写当时郡治江州城是:“地势刚险,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3]卷1巴志,20这虽然说的是江州城的水火灾害,但也说明了当时江州城人烟稠密、重屋累居、屋舍梯级而上的情形。一方都会跃然纸上。
第二次移民高潮是在明清。明清时期,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由于明代末期的战争、灾荒、瘟疫等,使四川、重庆地区人口锐减。政府为了调整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填补战争创伤给四川、重庆造成的人口缺失,于是通过政策性激励办法,鼓励湖广等地民众移民四川。当时,湖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贵州、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移民大量涌入重庆。这些移民的陆续迁入,使战后的重庆人口再次繁盛起来。
大量移民的进入,加快了古代重庆城市的发展。雍正《四川通志》云:“巴县附郭(廓),沿江为池,凿岩为城,天造地设,洵三巴之形胜也。”[4]卷3下重庆府乾隆《四川通志》载:“明洪武(1368-1398年)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二百六十八丈,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之形。”[5]卷24舆地·重庆府,1126当时城区开9门,朝天、东水、太平、储奇、金紫、南纪共6门面临长江,临江、千厮2门临嘉陵江,通远门与陆路相接。其后人口更加密集,重庆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奠定了此后600年重庆城的规模。至清末,重庆城区工商业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光绪五年(1879年)岁末,丁治棠经行重庆时,清晨见“沙岸人立如麻”“商帆集万艘”[6]2、52,极为繁荣。俞陛云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所见的重庆城,人口繁盛,各地商贾云集于此,所谓“居民八万户,楼台灯火,布满一山。滇越行李,江楚舟樯,争惊于其间。”[7]卷下,9
重庆的第三次大发展,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的中央政府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为中央直辖市,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于是,大量国民政府党政机关的军政人员,中国东南部、中部的重要军工企业和科技、文化、艺术机构及其随同人员西迁重庆,致使重庆人口激增。重庆城市的市民结构、工业基础、科技布局、文化层次都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工业基础方面,随大量工厂内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移民,奠定了近代重庆工业经济布局,工业经济在重庆经济中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初步形成重工业、轻工业等配套的工业体系。在城区建设方面,1939年5月3-4日,日寇飞机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此后,日机大轰炸愈为频繁,使得设在市区的部分机关、学校、工厂及所住居民纷纷向郊区疏散。因此,重庆郊区人口迅速增加,郊区地带畸形地繁华起来,出现了一大批人口密集的区域和集镇,如小龙坎、新桥、沙坪坝、石桥铺、歌乐山、青木关等,与旧城一水之隔的江北、南岸等城市的周边区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使重庆市区面积迅速扩大。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抗战”时期的重庆市政府致力于改善市政建设。经过几年城市建设,“在几乎是空白的基础上,市政公用各项事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供电、供水、市区道路,轮渡、公共汽车客运、房地产开发、邮政电讯、医疗机构、慈善事业、难民赈济、环境卫生、防空设施、下水道维修等,从小到大,从简单和结构单一向近现代化发展起来,速度之快,在近现代城市发展史上实为罕见”[8]327,由此奠定了重庆近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地位。在文化、艺术、教育方面,“抗战”时期各地区文化机构及其随迁人员大量涌入重庆,大批的文化、教育、科技、艺术精英也随之云集重庆。重庆集中了当时全国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和许多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如陶行知、晏阳初、张伯苓、喻传鉴等,极大地提升了重庆科技文化水准。尽管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一大批文化精英也随之离开重庆,但经过8年“抗战”的文化熏陶,重庆文化逐渐形成自己多元性、开放性传统,重庆的科技、文化、艺术也得到了跳跃式的发展。
第四次大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0世纪60年代,国家对西部进行“三线”建设。当时我国东部、东南部的大量军工、科技企业,以及随行人员向西部地区内迁,再次使重庆地区云集了许多国家的重要企业、重点工程,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精英。在工厂内迁中,重庆迁建、新建了200多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使重庆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这次大迁移,既是重庆工业结构得到新的调整的契机,初步完善了重庆作为现代工业城市的布局,使重庆成为长江中上游重要的工业城市;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重庆迎来的又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由此促进了重庆人口结构的再次改变。
总而言之,在历史上,由于历次大规模移民,使重庆的经济、文化、教育、艺术也得到一次次跳跃式发展,由此奠定了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政治中心和科技、文化、教育重镇的地位。
二、移民使重庆经济获得质的提升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的丘陵地带,境内江河纵横,土壤肥沃,矿产丰富,有着很好的资源条件。但在历史时期,由于重庆山高水深,交通不便,故其经济、文化以及相关的人才、生产技术等都处于十分落后的局面。秦汉时,随着封建政府对“西南夷”的开发,大量北方移民迁入巴蜀,使这一地区的农、工、商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大量北方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移民人口的进入,大量荒地被开辟出来,农耕面积大大扩充,中原地区新型的铁制农具已经在巴地推广,牛耕普遍使用,水稻在巴郡平坝地区广泛种植,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当时的江州“县北有稻田,出御米”,所产稻米因为质量上乘,被列为贡品。粮食产量也大大增加,并出现粮食外运的情况。在经济作物方面,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书·地理志》对巴蜀地区的繁荣曾经描述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1]卷 28地理志, 1 645
明清时期,重庆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由于外地移民人数增多,开始由平坝深入到广大山地进行农业开垦,形成汉族民众向少数民族分布区延展、推进、开发的局面[9]136。这一时期,农作物种类大大增加。有学者根据文献材料对比先秦、唐宋、明清物产,发现重庆物产结构在唐宋时期与此前差别不大,只是种类、数量有所增加,而明清时期重庆物产的结构和种类则均有重大的变化[10]193-209,表现为结构的不断合理、种类的不断增加。例如,当时除了传统的旱地农作物小麦、燕麦以外,包谷、红薯也大量引进与传播。光绪《奉节县志》载:“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11]卷15物产,286光绪《黔江县志》记黔江除稻谷外,“包谷有数种”,也种有甘藷 (番薯,即红薯)、芋 (洋芋、水芋、旱芋3种)[12]卷3物产,333-335。包谷、红薯都是高产农作物,对种植的环境要求不高。重庆丘陵、山地的复种面积大大增加,成为重庆旱地农业的主角,这对于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经济作物也发展起来。据乾隆《巴县志》卷10《物产》载,当时经济作物种类繁多,产量很大,经济价值可观。其中蔬类有28种,瓜类11种,果属25种,“药属、花属,其类甚广,难以枚举。”[13]卷10物产而麻、水果、桐子树及各类药材等则在经济作物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农业及经济作物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重庆的不少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也引起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道光《重庆府志》卷1《风俗》中就说道:“渝郡土宇则由狭而广,开辟尽也;人民则由寡而众,茲生繁也;土著则由富而贫,习于奢也;物产则由饶而减,竭其力也。”[14]卷1风俗,69
明清时期,重庆的工商业也快速发展。当时,大量土特产品通过重庆及峡江流域,流通于四川、陕西、两湖、福建、贵州、云南、江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商贾云屯(囤),百物萃聚,不取给于土产而无不给也。”“或贩自剑南、西川、蕃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水牵云(运)转,万里贸迁。”[13]卷10物产一方面,由于重庆人口的大量增加,商业城市体系开始形成。重庆、合州、万县、铜梁、南川、涪州、巫山等城市已经开始形成商业网络。重庆城区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东南部地区的中心商业区域,起着远近货物集散的作用。许多货物及土特产等均由重庆城区各码头贩运至沿江各口岸,以至于重庆在粮食贩运上,每年“下楚米石数十万计”[13]卷3课税。乾隆时期(1736-1795年),重庆城的商帮有25个,各业牙行达150多家,城内有街巷240条。广东、浙江、福建、江西、两湖、山西、陕西等省的商贾往来频繁,商船去来如织。再如重庆远郊的铜梁县,“本地人民,粟米布帛,自为贩运……或南贾叙泸,北贾潼郡,所行货以射洪、太和镇生纸为大宗。”[15]卷1地理志·风俗,615就连远在重庆东南部的秀山,也是 “居货成市,竞来商贾,千里奔走,为一都会。其物通行,流衍达乎江汉、河泲、淮海之乡,通有余,补不足。”[16]卷12货殖志,136另一方面,在重庆地区,广大的农村集市也开始形成网络。如酉阳直隶州“市肆既繁”“商贾萃聚,贸迁有无。”[17]卷4规建志·市镇,86集市货物有粮食、布匹、日常用品、生产工具、农副土特产品、药材、茶叶等。这些客商,大部分是明清以来移民。由于大量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开辟,农副业的兴旺,工商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元末明初的衰败气象一扫而光,重庆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并且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了长江中上游及西南地区的重要都市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地。
三、移民形成重庆“五方杂处”的多元文化格局
在重庆历史上,由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浙、陕西、贵州等地移民大量涌入,重庆的特色文化也发展起来。
历史上的重庆移民大都举族迁徙、聚居。一方面,这些家族和宗族聚居、生活在一起,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所属同宗、同族成员不受当地土著的欺负,还通过祖先崇拜,利用血缘关系纽带,加强所属成员的内在凝聚力,使宗族成员在异地他乡仍然有着一种族类归属感。特别是宋元明清以来,大量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安徽、江浙等外省籍移民涌入巴地,在其定居初期基本上按照家族、宗族格局生活,于是一方面是五方习俗杂处、各地方言并存;另一方面是移民信仰的原籍化、多元化。当时,不少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定居重庆,强化了重庆地区的楚、吴、越等地的风俗。宋人苏辙经行忠州时作《竹枝歌》,描述道:“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楚言啁哳安可分,江中明月多风露。”指出巴渝地区与湖广两地语言、文化的近似性。尤其是峡江地区与两湖地区在文化风俗的很多方面几乎相似。端午节本是楚地的节俗,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很多州县与楚地一样也过端午节。如奉节县,以屈原为夔之乡贤,故于端午节馈角黍,并龙舟竞渡,岁以为常。因此有记载认为重庆峡江地区为楚边陲,“接壤荆楚,客籍素多两湖人,风尚所习,由来久矣。”明清以来,以重庆为中心的三峡各个沿江府、州,处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徙路线之要道,因而吸纳了较多的移民,形成了“夔郡土著之民少,荆楚迁居之众多,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的局面。而闽、粤移民迁居进入重庆以后,使重庆的两湖、闽、粤等地文化风俗蔓延,并与本地习俗结合在一起。民国《大足县志》卷2《风俗》记该县“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卒视原籍所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及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各地的这些移民迁居重庆,无疑会加强重庆风俗与楚、吴、越、闽等地文化风俗的融合,从而引起了重庆地方文化习俗的渐变。
自明清以来,重庆地区“方言岛”现象普遍存在。如重庆大足县“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音,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人互话,曰 ‘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与外人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18]卷3政事上·风俗,321又如永川县“五方杂处,语言互异……故郡属城市,均有各省会馆,惟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为多。生聚殷繁,占籍越数十传而土音不改。”[19]卷2风俗,70而有的地区“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其土音有同邑所不尽解者。”重庆荣昌盘龙镇到现在仍然是著名的“方言岛”。这里现有人口8万余人,其中客家4万多人,占50%左右。这里的客家人为了保存客家传统,“宁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这使当地客家人至今仍然有着自己原籍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
近代以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大量政府机构及军政、科技、文化人员移居重庆,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如苏、浙、沪等地的“下江人”和鄂、湘地区的两湖人,这使楚、吴、越各地的文化风俗进一步与重庆的本地文化习俗相融合。在当时重庆一些地区和随迁人员中,源自苏、浙、沪的“下江文化”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下江文化”和巴渝文化相结合,使重庆城区的社会生活氛围与文化风气更加具有苏、浙、沪、楚的多元文化元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三线”建设的大发展,苏、浙、楚、粤、陕、闽,也包括东北、华北地区的大量人员随迁重庆,使重庆文化习俗更加具有多元化特色。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重庆的一些内迁工厂、社区中,“下江文化”、东北习俗都还占着一定的地位,有的甚至成为“下江文化”、东北习俗的“文化孤岛”。这种各地文化习俗的融合,就使重庆的文化风气更加具有着五方杂处的多元化趋向。
与重庆靠近长江沿岸的地理环境相近,重庆特有的码头文化也富于特色。由于过往船只众多,四面八方的客商文化风俗各异,因此这些码头逐渐形成了五方杂处、文化习俗并存的特色文化。例如重庆城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水码头,自古以来,它的建筑就与码头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重庆老城滨江临水,沿着城墙筑有17道城门,9开8闭,以像九宫八卦。如果我们沿着朝天门码头向长江上游数去,有翠微门、东水、太安、太平、仁和、储奇、金紫、凤凰、南纪、金汤等11道城门。沿着嘉陵江向上游数去,有5道城门,即西水门、千厮门、洪崖门、临江门、定远门。
重庆老城沿着长江码头一线,建起了繁华的下半城街区,过去多为过往船帮、客商、纤夫、码头工人服务,至今仍然是重庆城区的主干街道,如解放东路、解放西路、陕西路等。在很多时候,下半城比上半城更加热闹,往来客商、船帮更多。
川剧也是重庆的特色文化。明清时期,湖广等地的大量移民涌向巴蜀地区,各地声腔不同的剧种也随之而来。当时,在巴蜀地区,传统的各地剧种如高腔、昆腔、胡琴、乱弹与灯戏随着各地移民进入到巴蜀地区,并且流行开来。为了适应不同省籍的移民人群,人们就用四川方言与各种外来戏曲同台演出,从而形成共同风格的民间戏曲,统称为川剧。在川剧中,揉和了江西“弋阳腔”的高腔表演特点;具有苏昆传统格律的四川特色的川昆;由湖北汉调发展而来的川剧胡琴戏;由陕西秦腔传入巴蜀演变而成的轻松活泼、抒发感情的乱弹;以短小活泼、乡土风味浓郁为特色的四川民间小调灯戏。这种由各地戏曲与本地曲目杂揉而成的戏剧,就是当时盛极一时的川剧。可见,正是移民文化孕育了川剧这种特色戏剧。
移民大量进入重庆,亦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姓氏文化。现在重庆许多地区的姓氏,都是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迁入重庆的移民家族。重庆本地人的姓氏最早来源于巴人,巴人有白虎与龙蛇两支,其中白虎巴人有5姓:巴、向、瞫、樊、郑,龙蛇巴人有7姓:罗、朴、昝、鄂、庹、夕、龚,这12个姓的族人,可称得上是重庆最早的真正的“土著”。春秋战国时代,大量汉人开始进入四川盆地,其宗族姓氏开始迅速增加。其后各地移民充斥巴蜀地域,百家姓氏几乎覆盖了整个巴蜀地区。现今重庆的许多区县,其姓氏几乎都来自于湖广、闽、赣、浙等地。如1994年新版《忠县志·人口》引用《忠县姓氏志》所载,至1982年在重庆忠县户数人口中,有明清以来迁入的117个姓氏,占1982年全县总姓氏331个的35.3%。又如荣昌盘龙镇,作为一个客家人的集中居住地,客家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左右,分布在盘龙镇12个村4个社区。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李、张、周、黄、颜、马、叶7个大姓。这几个大姓也是盘龙镇自明清以来最大的移民姓氏。人们通过移民姓氏,可以保留客家文化的原脉,寻根归宗,找寻自己的家族渊源,形成对其故乡地域的历史追忆。
另外,明清时期在重庆广泛兴起的会馆建筑,也反映了移民家乡建筑文化的特点。在重庆江津真武场客家聚居地中,过去有着有“九宫十八庙”的移民会馆、公所。在这些移民会馆、公所中,有福建客家移民会馆天上宫、广东客家移民会馆南华宫、江西客家移民会馆万寿宫。另外,有建于20世纪欧式风格民居吴泽俊住宅、建于民国时殖民式风格民居马家洋房子。这些建筑气势雄阔,结构宏伟,特别是马家洋房子更是布局精巧,组合奇特。再以建筑在重庆主城区渝中区的湖广会馆为例。湖广会馆是湖广移民根据本地建筑特点而修建的同籍会馆,该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又加以扩建,总占地面积达8 561m2,坐北朝南,大门面对长江。会馆依山而建,鳞次栉比,气势宏伟。明末清初以前,四川本地的民居很少使用封火墙。随着湖广地区移民大量迁徙入巴蜀,封火墙这种建筑样式也多出现于移民会馆建筑和移民的民居住宅、祠庙建筑中,显示出它们不同于巴蜀传统的建筑风格。如今会馆中,还保存有“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一副对联,反映出客家先民拓荒异乡的创业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这说明移民们的原省籍文化深深融入移民心里,也融合进了移民们的活动场所即会馆建筑之中。
总之,自古以来,各地移民迁徙重庆,使重庆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中国直辖市,长江上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庆,正是在东南西北各地移民的推动下,才有着现在的辉煌。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清]黄廷桂,等.雍正四川通志[M].四库全书本.
[5][清]常明,等.乾隆四川通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6][清]丁治棠.丁治棠纪行四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7][清]俞陛云.蜀輶诗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6.
[8]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9]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0]卢华语.古代重庆经济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1][清]郑王选,等.光绪奉节县志[M].[中国台湾]台北:学生书局,1971.
[12][清]张九章.光绪黔江县志[M].[中国台湾]台北:学生书局,1971.
[13][清]王尔鉴.乾隆巴县志[M].清乾隆(1736-1795 年)本.
[14][清]王梦庚.道光重庆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5][清]韩清桂.光绪铜梁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6][清]李稷勋,等.光绪秀山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7][清]冉崇文,等.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M].成都:巴蜀书社,2009.
[18]郭鸿厚,等.民国重修大足县志[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19][清]许曾荫,等.永川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责任编辑:曾 超]
C922.7
A
1674-3652(2017)03-0001-06
2017-03-22
重庆市政府重大招标项目“重庆移民史”(CQZDZ11)。
李禹阶,男,浙江绍兴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区域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