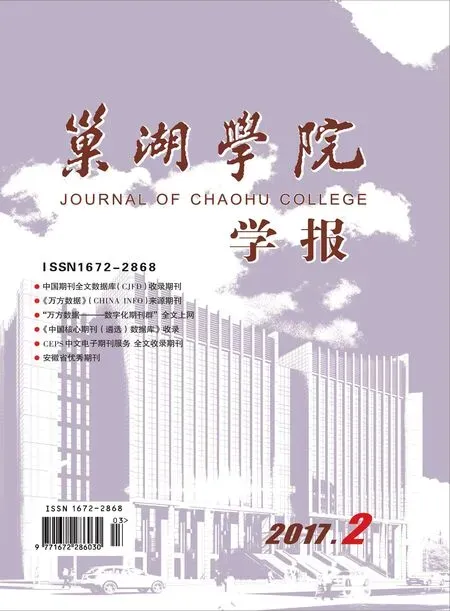养气、循道、净身:水象视阈下的孟子人格思想探析
章亮亮(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0)
养气、循道、净身:水象视阈下的孟子人格思想探析
章亮亮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0)
从湍水之辩到理想人格的六种境界之说,孟子借助水,从自然、社会、精神三个层次上阐述其人格思想,构建由体认本源到固本充盈再到泽被万物的理想人格,最终生成观水以养气、治水以循道、濯水以净身的价值内核。对于孟子人格思想中的水象,历来研究者重宏观之水的积极色彩,轻微观之水的消极意义,缺乏对水功用、流向的探讨。厘清上述问题,对深入理解孟子的人格思想、塑造理想人格、求得当前社会生存焦虑问题的解决之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湍水之辩;六重境界;观水养气;治水循道;濯水净身
孟子在阐述其人格思想时大量运用了水这一意象。在视觉上,水具有宏观、微观两种呈现方式,总体上给人以生命的感召力,个别水象具有消极色彩。在认识上,水依次分为自然、社会、精神三个层次,并逐层转化为孟子理想人格的载体——精神之水,它具有趋下性、前进性、净化性、润泽性四大特性。孟子借由湍水之辩强调,善是人的根本属性,“人之可使为不善”是人性的原始一面,并进一步指出人可以借助善的力量实现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以善为始,以水为本,孟子构建起包含善、信、美、大、圣、神六重境界在内的理想人格体系;进一步借由养气、循道、净身推动个体实现向自身生命的回返,向“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圣”的类主体的聚合,最终达成人与物的和谐共生。
1 孟子人格思想中“水象”的界定
“象”在中华文化系统是一个重要概念,指客观事物的形象和现象,可引申为现象世界的象征[1]。“象”反映了原始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包含了情感、态度等主观因素,并由此逐渐演变为观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取“象”的思维方式。客观与主观之象合为一体,最终构成了象的特有表现形式——符号。原始初民以象形符号反映万物的努力,奠定了以象形为主要造字手法的汉字的基础[1]。探讨孟子人格思想中的水象,不应只局限于江、河、泉、雨等与水直接相关的字词,还需辨析如濯、溺、沐浴、润泽、沟壑等与水间接相关的字词。简要而言,需要关注两点:
其一,《孟子》一书中的水象主要以宏观、微观两种形态呈现,给人带来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体验。孟子将他的生命观融入对水的体察中,通过外在的视觉观察,孟子既真切地描绘了细微之“时雨”捍卫生命权利的生活图景,又思索生命如混混原泉般昼夜流淌、奔涌向前的宏大与壮美。时雨、原泉是有本之水:“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表达了人们对于生命权利的渴望;“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强调了人在充分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应当保有对生命理想的追求。以绵绵细雨与滚滚江水为代表,折射出自然与天地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并直观地揭示了孟子对人格发展的期许:人是具备由自然境界逐渐发展到天地境界的可能性的。此外,孟子认为水有时也会对生命造成压迫,这主要源于对“溺水”的认识。人溺于水,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是自然力对人的伤害[2]。“陷溺其民”“老弱转乎沟壑”虽不至危及生命,但却未能给生命以足够的尊严,这使得孟子对于统治者的暴政、怠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孟子多次使用溺、沟壑等字词,事实上是在为统治者敲响警钟,让他们从流连忘返的迷途中回到理想的彼岸,用仁政找回被放逐的心。
其二,从认识上看,主要有三个层次:自然之水、社会之水、精神之水。孟子借自然之水直观地表达了先民渴望修生养息的基本诉求,揭示出先民对于水的基本态度:对以滋润万物的雨水为代表的水的渴望与感激,如“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若时雨降”“民大悦”;对以横行泛滥的洪水为代表的水的厌恶与恐惧,如“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社会之水强调了水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大禹治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先民对消极水象的恐惧心理。原始先民对水的态度,治水的缘由、方式都浸染了儒家知己与成己的思想,水作为自然之物,在自然生态的形态学意义上,具有道德意义;作为社会之物,在为人类社会所控制或利用的资源的形态学意义上,同样具有道德意义,甚至成为某种超越性之象征[3],最终演化为精神之水。精神之水是孟子理想人格的最终载体,集中地反映了孟子对“水”的两个基本认识:一是在方向上,孟子认为水具有“无有不下”的趋下性与“盈科而后进”的前进性。二是在功用上,孟子认为水具有“濯缨濯足”的净化性与“雨露之所润”的润泽性。四大特性为孟子理想人格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 以水为本育六重境界
在湍水之辩中,孟子取得了胜利,但应当思考:告子关于人性无分于善与不善的结论是基于什么得到的;孟子是否完全否定了告子的观点。为此,应当深入剖析孟告之辩中的“水象”。首先,就观水而言,告子的视野显然要小于孟子的视野,其所言之水也不尽相同。告子所言之水指的是作为水的多种具体形态之一的“湍水”,具有波流萦回之貌。湍水之性任意东西,只是水之诸性的一种。孟子则全面体察了水的各类存在形态,借由理性思辨掌握“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的观水要旨,最终得出“不盈科不行”的结论。“盈科”揭示了水的共性——趋下性,这是水的最根本属性。其次,告子的人性论更接近于卢梭的原始的人性论[4],因而是一种更为真实、不加修饰的、直接的、感性的认识,他借“湍水”,揭示了人性趋利避害的原始一面。最后,“水信无分于东西”事实上部分地肯定了告子的观点,水具有“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的可塑性,“人之可使为不善”意在人性同样可以被塑造,但可塑性都不是二者的根本属性。由此推断,孟告二人关于人性的讨论,并不是观点的绝对对立,而是认识层次的差异。“湍水”“无分东西”是水的自然状态,“决”“搏、跃、激、行”表明水已经被人类所利用,孟子不仅像告子那样看清了水与人的自然性、可塑性,更抓住了二者的根本属性,进而推崇水赋予人的精神力量。深入来看,这是对告子人性论的推进,实现了人性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舜之居深山之中”,虽“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但并没有因此丧失善的本性,这与水可“搏而跃之”“激而行之”依然“无有不下”遥相呼应。孟子认为,向善之心“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个体自身完全可以凭借文明社会之善推动人类永续发展。
由湍水之辩可以梳理出孟子性善论的两条发展路线:一是从人之根本属性出发,人性向善是孟子构建其人格思想的基础。二是由人性的可塑性出发,孟子认为人可以借助善的力量实现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固有之善必将润化“使为不善”。
针对第一条发展路线,孟子借助水象,阐述了养善、扩善,以善润泽万物的观点。孟子言:“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雨又被称为“天水”,它对原始人的生存与生活有决定性作用,人们祈祷着、歌唱着、舞蹈着,同时也赋予雨以生命的性格,雨能听到人们的呐喊与心声[5]。从生存层面看,作为自然之水的雨,可以兴枯槁之苗。苗是植物更是人之善心的物化。“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善心之苗同样需要受到雨的养护,只有经“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才可成长为“参天大树”。雨使枯槁之苗焕发生机,是对善的养护;沛然而下,使苗浡然兴起,是对善的扩充。孟子认为,雨具有两个特性:是有本之水、在空间上具有源源不断的流量,由此进一步说明:人内在拥有善的禀赋,养善、扩善是主体的自觉行为。
由人性本善衍生出的“四端”同样需要“扩而充之矣”,孟子用若“泉之始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过程。泉乃流水之源,它由下至上,喷薄而出。扩充四端的过程犹如泉水喷涌而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充盈全身,而后聚集成“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的浩荡大水,给人以勇往直前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扩充四端不仅需要时间上的积累,更需要主体自发地花费精力,“掘井及泉”。“泉”内存于主体,掘井是主体对信念的持续强化,主体切勿自弃其井、始终向井而掘是至于泉的唯一因素。“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强调不以“能为”为条件的“愿为”,挟太山以超北海之心可以在主体的能动作用下实现自我扩充,并最终外化为“为长者折枝”的具体行为。
当善得到了足够的扩充,就可以由内而外润泽万物。对此,孟子借助了“时雨”这一水象加以阐述。“时雨”强调了善在扩充之后有足够的力量惠及万物,体现了雨的第三个特点:在时间上,蕴含体察万物的关怀,可以顺时而为、应需而降。“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是百姓对安宁祥和的生活的呼唤,时雨恰恰是贤明之君在千里之外对百姓的回应,它及时地将百姓从悲惨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孟子通过“时雨”传递给统治者三个信息:第一,民心如同善心,同样需要大力、及时地呵护;第二,君主若想王天下,必须充盈固有的善,使之具备惠及万民的力量;第三,百姓对雨的呼唤与君主以时雨而降的回应反映了二者有着共同的期许:同归于善。“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所以孟子言“民归之,由水之就下”。百姓并非归于君主,而是与君主同归于善。由此看来:孟子既视雨为本性之善的滋养物,又认为雨具有润泽万物的力量,承载着儒家立己达人的育人思想。
以“善”为原点,孟子最终建立起理想人格的理论体系,可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重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是六境界的基石,“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对于善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内存于心的,这就是“可欲”;在行动中,以固有的善为旨归就构成了信,即“有诸己”:行动的产生来源于善的激发,并不受外力的推动或压迫,孺子将入于井只是给善的外化与释放创设了条件;恻隐之心的发动是行动的最终归宿,救孺子这一行动本身就是结果。于善、信而言,孟子都意在强调有本有原。因此,可以把善、信作为孟子构建理想人格体系的第一个阶段,即水之本源阶段。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水之充盈阶段,包含美、大。美是对善、信的进一步充实,使其达到朱熹所说的“充满积实”的程度,如浩荡大水般“盈科而后进”。只有这样,美才可以无限扩散,以成人之德、助人之业,这就是大。
当一个人具备了“大”的能力,就逐渐向圣、神靠拢。理解圣,首先要从“圣”字本身入手,“圣”即圣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代表。再抓住“化”字,《孟子》全文有五处使用了“化”字,与“大而化之”结构最为相近的只有一处:“有如时雨化之者”。时雨具有善之润泽万物的力量,朱熹以草木的生长为喻,进一步补充:“及此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很显然,化具有“化育”“进化”“演化”的含义。由此可以得出:“圣”即主体充分释放大的能力,润泽万物,推动其变化发展,直至其由初始状态成长为终极的理想状态。这构成了理想人格体系的第三个阶段:水之润泽。
最后来看神,神也属于第三阶段。理由有二:其一,从层次上看,神是对圣的推进,二者没有本质的不同,这符合整个体系的构建逻辑。其二,“圣”已是终极的概念,况且儒家也不存在“神人”一说。那么神与圣的不同点在哪里?关键就在“不可知之”,有学者认为不可知之指“君子所作所为不为一般人了解的情况”,进而指出“神是圣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案,从而达到游刃有余、‘出神入化’境界的意思”[6]。这确实可以用来解释不可知之,但似乎还不够充分,要把握其全部内涵,应当思考两个问题:谁不可知?“之”指什么?按上述观点看,一般百姓、君子的具体行动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百姓愿否、能否知晓君子的具体行动已然不确定,他们看重的是君子的行动能否成就他人,因此从这一角度解释“不可知之”似有疏忽。君主润泽一方,百姓早已渴望并欣然接受,一场“时雨”让黎民百姓发出了“奚为后我”的感叹,于君主而言,已经趋于圣的境界。如若君主消亡,依然可以成就他人,这就离“神”不远了。“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故家遗俗,流风善政是仁君的象征,“圣”历经时间的考验,使百姓在流风余韵下不由自主地被感化,在潜移默化中成就自己的人生,就上升到了神的境界。所以神可以解释为“超越了时空局限后的圣泽被万物,使其在自然和谐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地变化发展,最终达到完满的状态”。围绕对水象认识的层层深入,孟子划定理想人格的六重境界,并逐步建立起由体认本源到固本充盈再到泽被万物的理想人格观。
3 孟子理想人格观的价值内核
延续第二条发展路线,可以发现孟子的理想人格观包含观水以养气、治水以循道、濯水以净身三大价值内核。
首先来看观水以养气。“气”的概念最早见于许慎的《说文解字》:“气:云气①于省吾、李存山、以前川捷三为代表的日本研究人员也都认为:气与云、雨等自然现象密切相关。也,象形。”美国学者艾兰认为“在自然界,气的字义指水的循环往复②李存山先生指出,气具有徐渐、充满之意,可作为循环往复的注解。,溪水下流,上升为雾,下降为雨”[7]。这种循环往复的“气”存在于宇宙之中,统称为自然之气,当其充溢于人体之内,便逐步化为血气③血气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气论”的发端,大致最早可以在《国语·周语》中找到相应表述:“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在此语境中,血气一词已经趋向于志气的精神性概念。,最终形成趋向于志气的精神性概念。这就是孟子“浩然之气”的理论源头。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必定是在观水之澜后于内心深处升腾而起的。对此,朱熹有着更为精微的分析:“浩然之气,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说浩然,便有个广大刚果意思,如长江大河,浩浩而来也。”不足以言之,正如同长江大河浩浩而来,必须抓住至大至刚的特点。正恰恰表明了气充溢于宇宙之中,具有不可超越的终极意义;大是长江大河、混混原泉的波澜壮阔的气势;刚是浩浩而来、盈科后进的毅力。除了至大至刚,也不能忽略浩然之气的另一面:柔。柔与刚并不是相对立的,刚强调气纵向地蒸腾奔涌,自然之血气在运动过程中聚集成精神之志气,具有大水“万折也必东”的前进方向。柔并非是柔弱,而是对“盈科”的推进:柔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使气在上升的同时向四面八方扩展蔓延,最终充溢于整个宇宙。
其次看治水以循道。孟子认为,理想人格能够根植于险恶的生存环境之中。君子成人之道关键在于顺应人之善性。为此,孟子围绕“溺水”问题展开了两个方面的论述:第一,人溺于水。人一旦遭受溺水的困境,求生本能瞬间迸发,如果溺水之人无法获得救援,那么他面临的不仅是身体发肤的消亡,更是心的亡佚。“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虽无性命之忧,但迫使“老稚转乎沟壑”,终将“陷溺其民”“陷溺其心”。百姓的身心陷入不利境地,善的本性就会被蒙蔽,因而“放辟邪侈,无不为已”。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君主也陷入了“溺”的泥潭:
“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饮食若流、流连忘反带给人的都是极其消极的情感体验,是对君主沉溺迷途的生动刻画。百姓陷溺其心,君主流连忘返,亦如“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天下大溺,故孟子言“失其民”“失其心”“载胥及溺”。溺天下是孟子围绕“溺水”问题论述的第二个方面。于君子而言,虽也陷入其中,但依然坚定不移地抱有“志士不忘在沟壑”的恒心,恶湿不居下,“惟士为能”。沟壑意指水停滞于低洼之处,低洼之水无本无原,“其涸也,可立而待”。孟子用“溺”“沟壑”意在强调环境的险恶,并借尧舜禹之口表达了君子应当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如何拯救天下?孟子言:“天下溺,援之以道”。援之以道就是顺应人之善性、还其本来面貌。亦如大禹治水,孟子进一步指出:“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遵循水之就下的根本属性,如若不然,则造成水的逆行。“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水逆行意味着善之本性的扭曲,于君王而言,治理水患、安定天下的关键在于顺水之性,同归于善,“行其所无事”。
最后看濯水以净身。孟子认为水不仅可以泽被万物,还具有归洁其身、涤荡心灵的作用。“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古代先民在祭祀时往往需要穿戴整洁,孟子化用《礼记》上的话说:“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于圣人而言,虽行有不同,但“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如何归洁其身?孟子给出的方法是“沐浴”,“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由清洁身体内化为涤荡心灵,沐浴意味着对自我修养的提升,并且在程度上已经趋于圣的境界。此外,孟子借孔子之口,以沧浪之水为喻,阐述了其清浊观。缨与足在逻辑上无明显对应关系,历代学者对《沧浪歌》的解读也基本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孟子认为清浊之水并没有品性上的高下之分,只是所用之处不同。孟子之言意在君子既可以濯清涟而不妖,也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往来于清浊之间而不失其品格。
当下,世俗所谓锐意进取早已背离了至大至刚的品德追求,异化成一种急功近利,以效率压倒一切的心态。在此种价值取向的裹挟下,个体的生命被不断摧残,精神日趋萎靡。浩然之气中的柔当为一剂良方:柔意味着尊重并善意地接纳、安排[8],它促使个体回归内心固有的善,使其在任何情境下都可以挺立不屈,既不会失去自我,也不会伤及他人,当为则为,反之则止[8]。个体遵循善的本性,就是要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尽最大可能避免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自然而然依生命之节律而行,顺自然之道定夺生命的节拍、考量身外的得失,由“张”而不“弛”到“张”“弛”有序,先净其身,再净其心,逐渐摆脱外物的束缚,实现向自身生命的回返。为生命留出空、让出闲,让身与心在“沐浴”中祛除尘世的繁芜,将个体无限膨胀的欲望与尊严重新置于自然法则的“管辖”之下,审慎运用科技的力量,遵循事物诞生的时空范围与生长路径,依从事物的本来面貌实现人与物的和谐共生。这是孟子理想人格观于当代之永恒意义,更是希望之所在。
在今天,探讨孟子的人格思想依然无法回避人性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我们如何发展都必须要使自身尽快从个人本位提高到类主体形态,并逐步树立起类主体意识,即一种责任意识,一种充分发展了的理性认识[9]。在孟子看来,混混原泉最终“放乎四海”。海之于原泉是类的全体之于个体的关系。“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道德的自律与他律是相统一的,都具有内生性。人通过对自身固有之善的养护、扩充可以无限趋向圣的境界,无数的个体向着类的方向聚拢,最终凝聚成“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圣”的类主体,与自然万物实现和谐共生。上述观点揭示了人类自身螺旋式的发展轨迹,也为个体实现灵根自植,促进个体回归中华民族固有精神家园指明了实践的方向。
[1]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4.
[2]刘雅杰.先秦文学的水意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21-123.
[3]田海平.“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J].江海学刊,2012,(4):6.
[4]王美玲.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J].管子学刊,2012,(1):110.
[5]李云峰.水与中国古代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14-16.
[6]杨泽波.孟子理想人格的思想与践行[J].中国文化研究,1998,(19):36.
[7]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8.
[8]贡华南.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M].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20、139-141.
[9]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26.
IMPROVING CULTIVATION,FOLLOWING REGULARITY,PURIFYING MIND: ANALYSIS OF MENCIUS’PERSONALITY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ATER IMAGE
ZHANG Liang-liang
(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00)
From turbulent water debate to six levels of ideal personality,Mencius uses the water image to elaborate its personality theory from three levels of nature,society and spirit,to construct his personality ideology in self-cognition,self-enhancement and humanistic enlightenment.Eventually,the core values of improving cultivation,following regularity and purifying mind are formed.As for the water image in personality ideology,the researchers in history only focus on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macroscopic water image,but they often neglect the negative significance of microcosmic water image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function of purification and flowing direction.Discussing these problems deeply is very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Mencius’personality ideology,shape its ideal personality,and solv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survival anxiety.
Turbulent water debate;Six levels of personality;Improving cultivation;Following regularity;Purifying mind
B222
A
1672-2868(2017)02-0040-06
责任编辑:杨松水
2017-01-09
章亮亮(1988-),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家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