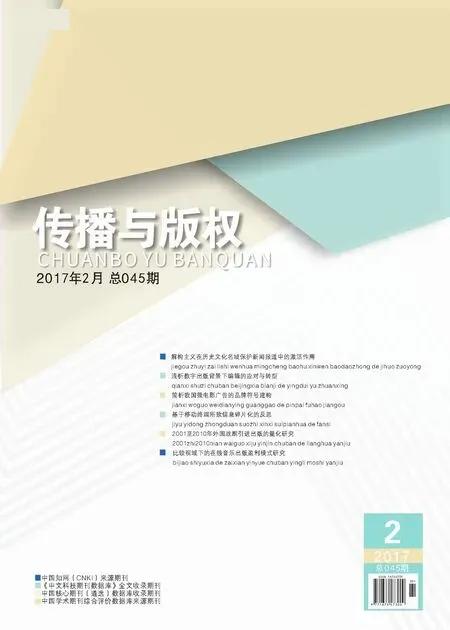基于移动终端所致信息碎片化的反思
吴小飞
基于移动终端所致信息碎片化的反思
吴小飞
通过对时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热门研究点信息碎片化的现象的反思,并对移动终端的两大主要资讯平台APP端和微信公共账号进行分析,认为碎片化的呈现并非意味着负面效应,应该依据碎片化的时代特征,利用碎片、整合碎片。最后,提出在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几点可行性建议。以期在当前的环境下,引发人们对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些思考。
移动互联网;信息碎片化;微信公共账号
[作 者]吴小飞,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迎来了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大众化功能因为移动终端的普及而呈现了便携性和实时性的时代特征。移动终端已经深入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和互动形式,提高了信息获取的速度和便捷性,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近些年来,网络社交工具不断发展和深入人们的生活,我国大陆的主要有腾讯QQ、人人网、YY语音、新浪微博、腾讯微信、陌陌等,其他使用人数较多的主要有推特、脸书、LINE、播客等。在网络平台上社交方式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交生活而且也影响信息的传递方式。由腾讯公司出品的微信自2011年问世以来,以流量的低耗、信息传递方式的多样以及操作程序的“傻瓜化”等诸多优势在短时期内迅速风靡。截止到2013年8月,微信用户已经突破6亿,其中海外用户已经超过1亿。如此强势和快速的吸纳受众引发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关于社交虚拟、移动终端等问题的研究报告也占据各科研杂志的头版。而在这些研究报告中,学者们的陈述充满了人文的忧患。“微信的病毒式传播”“互联网时代的容器人和低头族”“网络信任危机和欺诈现象”等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负面效应成为研究热点。笔者选取“信息碎片化”这一具有较大公约数的认知进行反思,认为碎片化信息传播在当今语境当中不应该成为一种忧思,倡导以有限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思考社会流行元素,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必须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
一、碎片化的内涵
本文所述的碎片化,是特指在当前舆论环境下,完整的信息通过手机、博客、微博等媒介形式的再编辑与传播而呈现的块状,零散的描述形式,从而导致信息、受众与媒体细分化的现象[1]。信息碎片化引发热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微博的广泛流行。以新浪微博为例,每条资讯不得超过140个汉字的限制,以及明星、公知的参与和带动,使微博在短时期内迅速流行,并创造了2010年的“微博元年”,信息传播碎片化也因此进入了普通公众的视野。事实上,碎片化的信息传递方式并非网络环境的独创,根据碎片化的内涵,早已成为历史的电报不失为一个典型代表,并由此催生了报刊消息的“倒金字塔”体。只是当时的信息碎片化传播是以重要性来列次传递,也没有今时今日的普及性和广泛影响力。
碎片化的主要特征是零散化,不具有连贯性。超过一定强度和一定时间长度的碎片化信息接收可能导致人们的阅读趋向于浅层化,情感深度和历史感弱化,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的界限模糊,注意力难以集中,思考能力减弱等一系列不良影响。更有甚者可能会引发焦虑,神经衰弱等生理和心理的亚健康状态。再加上学界和传媒行业对碎片化的过度关注和过度宣传,最终导致“碎片化”在当前语境下是以负面效果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视野。
二、碎片化的“原罪”与“自愈”
(一)碎片化的“原罪”
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凭借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普及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以及原来的实体交易,如学习、购物、各种专业和非专业性质的交流与合作在移动终端的开展。它以其便携性,便易性和实时性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人们现实生活有关的一切资讯似乎都可以在移动终端中获得,代替了原来社会生活中许多真实的社会互动与交流。因此,在各种场合,公开的和非公开的,公共的和私人的,随处可见“低头一族”和“容器人”。更有网友戏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们相隔万里,而是我就在你的身边而你却在玩手机”。
基于上述的种种需求,人们习惯性地去摸手机,当“电子狗”,在一些社交活动中为避免尴尬而划手机,在一些必需的等待时间中浏览资讯,在某些时间空档中“逃避自由”填补目光和思绪的无着落的空白。而微博、网络社交工具、APP,以其短小、实时、趣味、简要等特点,满足了这些需要,用随时随地的优势填补了各种显性、隐性需求的空白,由此而产生的连锁性效果就成为了碎片化的“原罪”。
(二)碎片化“原罪”的“自我治愈”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在阐述他的核心思想“自生自发的经济秩序”中这样叙述:“人及社会的发展过程只是人类长期摸索,不断试错而达至文明进化的过程,是自生自发得到的进步而非设计的结果……社会的进步就是在众人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实现的。”[2]这一思想认识类似于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有无相生”的无为而治。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相伴而生,而被“妖魔化”的碎片化信息时代也同样走在“自我治愈”的道路上。
1.主要移动资讯平台推送信息的“去碎片化”。由于移动终端的新闻资讯类推送平台主要是APP端和微信公共账号。APP端除了各大门户网站还有一些专门的新闻资讯的媒体,如ZAKER、澎湃、品读等。以澎湃新闻客户端为例,其新闻资讯多以时事政治评论为主,单篇资讯少则400到600字,多则几千字。其他各类信息因其内容不同而风格各异。如生活资讯、娱乐八卦较多采用多图片、小视屏、趣味图表、漫画的形式呈现;综合类信息,主要的表达形式还是中长篇文字。而微信公共账号主要有三类:电商、自媒体、传统媒体的平台转移。电商的类别及服务形式与PC端的天猫、京东、亚马逊、易趣之类的大同小异。新闻时政专业性较强的信息则主要依靠传统媒体(报纸、广播)为争取受众抢占市场的平台转移以及资讯类媒体就微信平台的公共账号而进行的文章推送。自媒体大部分都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权威人士、资深人士或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这些自媒体本身的平台和素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推送资讯的可信度和质量。新闻资讯类传统媒体的平台转移,他们在风格上除了语言上口语化,嵌入很多网络流行语以及表现形式更为多样之外大部分与传统方式一致,主要是以“图片+标题+导语式内容概括”的形式,点击后进行深阅读。笔者就2014年10月1日到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和《合肥晚报》进行了追踪观察,前者每日主推文章的点击深阅读最少人数过万次,而后者作为地方都市报在30天里有15日有过万点击量。其他诸如生活资讯服务类的,多是告知式的,功能与广告类似,本身就是浅阅读,不存在“去碎片化”的问题。
新闻资讯类的APP用户端和微信公共账号推送文章完全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有系统、有逻辑、有思想深度的特点,不仅增加了推送资讯的实时性而且提高了人们接受信息时间分配上的灵活度,同时也回归了理性阅读应具备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长阅读的表达在移动终端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微信公共账号的推送是在用户订阅的前提下展开,在后台数据和信息分析(即可根据用户的年龄,区域,兴趣等有选择性的推送文章)后进行一对一的推送,保障了信息100%的到达率,这也是系统性阅读在数量上的到达。上述种种,都是在打破碎片化,回归长阅读的深度和系统连贯性。
2.碎片化的时间需要碎片化的资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空白的小时间段,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十分钟。如等车、排队、如厕、学习和工作的间隙等,这些短小的时间段不适合开展深度阅读,如果在这些时间段里非要进行长阅读反而会破坏一篇文章的逻辑脉络,因为不断地被打断而破坏文章的连贯性。伴随微阅读时代而生的微小说、微电影、微博,以及微信、贴吧、论坛等,为那些短小精悍、风趣幽默、简明扼要的微资讯提供了平台,适应了这种需要。这其中比较优质和成功的案例就是TED大讲堂。TED的宗旨是“好的思想值得人类共享”,内容多是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在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的顿悟或者思维的创新,时长一般在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内容往往融思想性、趣味性和创造性于一体,独具特色。TED有效利用了碎片化时间,使每一个观点都得到了相对完整的表达,高效地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简单的陈述之后引发的除了喝彩还有人们的深思。
从另一个层面上,微言大义、言简义丰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一直所倡导的。有些内容通过某一个片段或者简答的语句往往能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时间的多少和内容的长短不能作为衡量一条资讯的信息量以及内容深度的唯一标准。某些碎片的认定是相对的,在碎片化的内部有其内部的微系统性,碎片化与非逻辑性、缺乏系统性之间不能完全画等号。碎片化的时间只适合碎片化的资讯,人们在合适的时间做适合的事,这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逻辑所在。简言之:让系统的归于系统,碎片的归于碎片。
3.在碎片中整合,让碎片归于系统。大众媒体所称的完整传播,多数只是指作为新闻作品的完整性,是在一个狭隘、封闭的认知框架内语义上的完整,文本上的完整[3]。因为在整个宏观层面上,任何目之所及、脑中所思,都是片面的。碎片和系统都是相对的。新闻报道中的系列报道和深度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某一具体事件的开始和结束的整个过程中,每一篇报道都是完整的文本,而对于整个事件来说却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就算是事件结束后的深度报道以及整个系列报道也不能保证完全呈现了事实的全部,那么我们就要整合碎片,在碎片中寻找系统,让碎片归于系统。这种碎片整合常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个是自发,一个是自觉。前者的典型就是“人肉搜索”。“表哥”杨达才的落马,就得益于网友在各个范围内寻找到的其佩戴名表的图片最终整合出几十块名表,让只有公务员这一职业收入的贪官面对铁证难以辩驳。自觉的案例在媒体中很普遍。《人民日报》在2014年11月12日推送了一篇软新闻《会过日子的女人:看彭丽媛多少套衣服一衣多穿》,展开图集是彭丽媛在各个公开场合几套衣服不同搭配的图片,这就是一种从碎片中整合,从而得出一个系统性的认识。就新闻报道本身而言,多个碎片化也是一种多元呈现,这有利于报道的平衡以及最大限度的还原事实。而且,很多单个碎片化资讯彼此之间是互相补充的,整合后更加能够系统、全面地看待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这也是碎片化回归系统性的“自我治愈”。
三、用有限的理性思维看待碎片化
(一)过分理性的实质是一种非理性
碎片化是这个多元世界的一元,信息碎片化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时代特征,碎片化的呈现是这个时代自生自发的产物,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现象的能指,其所指并非象征着混乱不系统的思维和肤浅片段化的阅读。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在一种意见成为多数意见时,它已不再是最优的意见,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些人的观点可能已经发展到超过多数所能达到的水平[2]。过度的渲染基于移动终端信息传递的碎片化,在一种过度理性思维的指导下去唱衰某一行业或者鼓吹某种警示预言,这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言:从目的的合理性立场出发,价值合理性总是非理性的,而且它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价值,它就越是非理性的。因为对它来说,越是无条件的仅仅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它就越不考虑行为的后果[2]。我们倡导一种有限的理性思维去对社会现象做出批判性的和建设性的思考,以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太多的情感和情绪在分析或者解决现实问题面前则显得苍白无力。
(二)碎片化的问题往往是有深刻渊源的社会问题
当下所呈现的碎片化问题,如:沉溺于移动终端的人们成为自私、冷漠、不愿意接纳外部世界的“容器人”;碎片化的呈现导致真假难辨和网络欺诈横行;意见的多元呈现,网络水军庞大,人们在海量信息面前因为没有权威和中心而失去平衡变得迷茫;移动终端运营市场缺乏与之同步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引发了一些社会伦理问题等,究其根本,这些碎片化之罪往往是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社会矛盾由隐性变为显性,碎片化只是一个矛盾爆发的突破口。没有任何矛盾是由单一因素引发在短时期内完成的,这往往连接着历史,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矛盾的运动过程中或隐性或显性的呈现。所谓个人主义膨胀、社会诚信或者伦理问题则是由来已久的常在问题,并非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更不是碎片化之罪。任何器物,形式都是工具性的,它们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倾向。
四、移动终端应用主体的媒介素养培育的思考
移动互联网已经融入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其应用主体无论在年龄层次还是职业分类都是社会再生产的主力。他们对新媒体的参与和使用能力是科技产品服务社会的最终检验,如何让应用主体更好地利用和驾驭新技术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社会意义,即媒介素养培育。在我们看得见的过去以及可预知的未来的近百年时间内,科技已经成为应然之物,所以当下的媒介素养培育必须呈现出两种状态:参与性学习和终身教育。首先,媒介的使用与主体的参与紧密相关,它不是供后人瞻仰的历史的故事或者哲学的深思,它更强调在一种理性思维的指导下对媒介呈现的熟练操作和认知驾驭,参与科技创造的本身。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没有任何一项技能是一劳永逸的。那么这种媒介素养的培育也必须是与时俱进、常在常新的一个终身学习过程。我国大陆的传统媒体信息生产的运营模式积重难返,在资本利益和新技术的冲击下,他们以相对民主的形态(相对自由开放的言论平台和思想平台),隐蔽的生存着,这比传统信息环境下的情况更加具备“虚伪性”[4]。我们的媒介素养培育除了认清自身的媒介环境和了解公民的媒介素养水平外,还应该借鉴一些在这方面取得较好效果的经验。
作为典型代表的美国,他们的媒介素养培育的主要力量是教育机构,培养的核心是受众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也就是一种解构能力。所谓解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分解媒体信息、操作、流程、机构及影响的具体构成,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这种教育工作,让受众成为具有媒体批判意识的人,而非单纯强加其对媒介信息的抗拒思想[5]。例如,教师会在课堂上展示风格不同的读物让学生们选择,通过选择结果来告诉他们这些书是如何生产、包装以及出版商是如何进行风格设计和产品营销来吸引读者的。同样的方式也会被用来分析媒体资讯以及影视作品。通过参与式的互动来解读信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打破媒介呈现的神秘性,从而培养学生的辨别力的预测力,提高媒介使用的自由度和驾驭能力。同时他们还特别注意针对不同群体进行特色教育,如果学生群体是青少年,则更多的使用趣味元素,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宗旨,在最终效果上侧重帮助他们提高使用现代媒体进行信息处理和与人交流的能力。此外,一些知名高校也会就媒介素养展开创新型教育。
而香港从事媒介素养培育的主要机构则是市民团体、政府部门以及公共媒介。市民团体多是自发成立的,成员多是在港相关高校的教研人员,多以团体,协会的形式,通过举办各类论坛、交流会、发放刊物等方式开展活动。其资金一般依托于某些基金会。他们不仅帮助受众认识媒介运营,更好地使用媒介而且强调受众的监督权力以更好地改善媒介环境。政府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宏观审查和有限的监督。对市民的媒介素养培育主要是发放刊物到户,普及常识,指导市民的媒介使用,倡导亲子教育。公共媒介则是行业内的自律组织,用以规范媒体的运行环境。他们注重公众利益、社会伦理和职业操守,并能有效的干预不良业界行为,重视市民的反馈,经常组织与市民的互动活动,以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媒介素养的培育必然也是某种程度上学习理念和教育理念的转变。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宏观层面建构的多,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少。媒介素养的培育不仅仅是技术操作层面的娴熟和与时俱进,它更是一种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建设。这种培育是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服务的,这种素养的提升能帮助我们平衡不确定性,平衡矛盾,平衡现实生活中的多样性和权威,提升人们对差异的忍耐和尊重,使得人们更有责任和勇气,敢于批评不平和各自内省,微观可[1]以抵制诱惑宏观可以完善框架。
[1]林楠,吴佩婷.新媒体时代下碎片化现象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12):47-52.
[2]刘少杰.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J].今传媒,2011(10):8-11.
[4]芮必峰,陈夏蕊.新媒体技术呼唤新“媒介素养”[J].新闻界,2013(14):62-66.
[5]张毅,张志安.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特色与经验[J].海外新闻界,2007: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