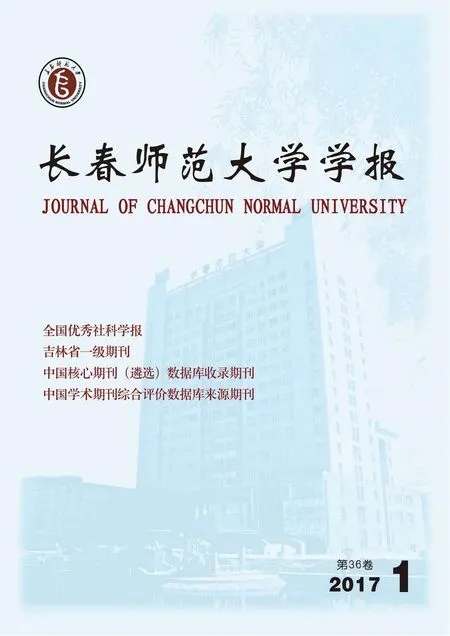雍正朝平青海之役中的“毁寺杀僧”事件再探
王 航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雍正朝平青海之役中的“毁寺杀僧”事件再探
王 航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关于雍正朝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事件,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较多,然而对该事件中清军毁寺庙、杀僧侣这一要案,除却王锺翰先生在《年羹尧西征问题》一文中有所谈及外,鲜有学者进行进一步研究。该事件的真相不仅直接影响到平青海一役的正义性,也关系到清王朝西北民族政策的实施。
年羹尧;塔尔寺;佑宁寺
王锺翰先生在《年羹尧西征问题》一文中驳斥了雍正朝大臣李维钧弹劾“年羹尧于西宁喇嘛寺内喇嘛僧四、五千人,不分奸良,诛无孑遗”的说法,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甚为可信。但王先生该文重点论述的并非此问题,因而并不深入,加之先生并未采用相关寺志,亦未能兼顾年羹尧奏折,缺憾在所难免。本文拟通过各类文献资料,对“毁寺杀僧”一事作进一步澄清。
一、“毁寺杀僧”事件背景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所收满文奏折第52件《奏闻罗卜藏丹津同党来降折》载:“臣我查得,圣上将丹忠之户赏给察罕丹津时,墨尔根戴青拉查卜因察罕丹津独占丹忠之户,而无归顺之意,将其妻达赖喇嘛之姐给与罗卜藏丹津,并合力共同掠夺察罕丹津,缘由甚属可恶”。由此可知罗卜藏丹津是七世达赖喇嘛的姐夫。固始汗之孙和达赖喇嘛姐夫的双重身份,使得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地区有着较高的影响力。康熙朝末期,清军驱逐准噶尔部后,“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治理,获得更多权力、利益,清廷开始调整青藏地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具体做法则是在青藏地区采用各加封赏、分而治之方略,实施中央集权化治理。然而,罗卜藏丹津想获得更多青藏地方的治理权(社会管理权与代表权),或至少保有管理权与代表权,即青海和硕特蒙古应该恢复汗权,这就与朝廷的需求背道而驰。罗卜藏丹津事件之后,青海和硕特的活动被大幅度限制,被传统地承认为西藏之王的固始汗的子孙在这次“叛乱”中丧失了在西藏的所有权力。
罗卜藏丹津发动战争的时间,是康熙帝逝世的第二年(1723),镇守西宁的皇十四子允禵回京奔丧之际。七月,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浑台吉”,强令青海诸台吉恢复旧日名号,正式宣布反清。在青海的达赖喇嘛的属下,甚至某些高级人士也参与了事变。如达赖喇嘛属下的嘉木参堪布统辖有数百户、千余人,虽大部归降,但嘉木参堪布本人带属下二十户投奔了罗卜藏丹津。与此同时,罗卜藏丹津进击拒绝参加叛乱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和亲王察罕丹津(察罕丹津认为罗卜藏丹津最有实力成为藏王,但在罗卜藏丹津起兵后却未追随)等人,而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的子侄投归了清朝。雍正帝闻变后,采取先礼后兵的政策,一面令川陕总督年羹尧预先筹划平叛事宜,一面命兵部侍郎常寿前往沙拉图令罗卜藏丹津罢兵和睦。罗卜藏丹津拘禁常寿,于雍正元年(1723)十月进攻西宁周围,燃起战火。与此同时,塔尔寺、郭隆寺(佑宁寺)、郭莽寺寺院的喇嘛响应叛乱,抗拒官兵,掠夺财物。为平息叛乱,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任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先行征剿西宁周围叛军,继而于1724年初平定塔尔寺、郭隆寺等处的喇嘛叛乱。解决西宁周边的叛军后,年羹尧趁“春草未生”之时,令清军分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自雍正二年(1724)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清军仅用十五日便彻底击溃叛军。在扫尾阶段,清军四面合围、十路并进,不到一月便彻底肃清叛乱。
二、奏折中所见“毁寺杀僧”之事
在平定西北战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年羹尧在失势后遭到多方弹劾,其罪状之一便是在平青海之役中滥杀大量无辜僧人。直至今日,与此相关的绘声绘色的传说还在青海地区很有影响。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年羹尧是如何为自己辩护和同僚如何“力挺”年羹尧的。
早在雍正二年(1724)五月,年羹尧便向雍正帝上《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首次详细阐明“毁寺杀僧”的情况和原因:
西宁各寺喇嘛,多者两三千,少者五六百名,内有西番,亦有蒙古,并有汉人,其人既众,奸良莫辨。更有各处奸徒,干犯法纪,遂逃入喇嘛寺中,地方不能追,官吏不能诘,而喇嘛寺院渐成藏奸匿宄之藪。且西番纳租同于输赋,西海施予,岁不乏入。又莫不潜藏盔甲,制备军器……喇嘛欲阐黄教,而奸徒之冒充喇嘛者实坏黄教也……众目昭彰,势不得不火其居而戮其人。非除喇嘛也,所以除叛逆也;非轻佛法也,正以扶黄教也……
失势遭弹劾后,年羹尧又向雍正帝说明了当时的前方战事情况,指出对喇嘛动武完全是出于自卫之需:
如西宁各寺喇嘛,有为贼人向导者,有助贼人口粮者,所以罗卜藏丹尽(津)敢于三面犯我边城;且临阵之倾,喇嘛竟敢骑马持械,显与官兵对敌,官兵又岂肯留此奸僧,即将对敌之喇嘛杀戮,其余逃窜,随焚郭莽寺与二格隆寺。
此番西海作乱,蒙古、西番显行悖逆,犹是意想不到,惟西宁周围数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虏焚烧,无所不至(朱批:真大奇。再,西海普概背[叛](判),亦属奇事,为何至今尚未来归顺者。此等之人如今皆定否)。察其根由,盖每寺皆有喇嘛二三千以至四五千名不等,藏奸纳污,已非一日。即臣折内所称祁家寺、郭莽寺两处,皆有抢掠民妇在内,而喇嘛之箱柜内妇人衣鞋不可胜计,殊堪痛恨。惟张家呼图克图所住之所郭隆寺少胜他处,臣是以加意护持焉。
吹卜仲呼图克图即郭莽寺坐床之喇嘛也。阿尔卜坦、班朱尔拉布坦、罗卜藏插罕、芨芨克扎布四人侵犯新城、高古城等处,口粮皆取给于郭莽寺,而阿尔布坦翁布围我北川时,吹卜仲遣其寺内之车臣蓝占巴统帅僧番助逆围城。迨至臣遣总兵黄喜林剿灭郭莽贼僧之日,吹卜仲率其僧徒数十人溃围而出,抛石乱打,几中黄喜林面上。黄喜林怒极,连射四矢,毙四喇嘛……至于小阿尔卜坦犯我新城,残杀民人,其妻工格太、其岳阿尔萨朗台吉犯我赤斤、靖逆、卜隆吉一带地方……
其次,在诉诸武力的过程中,年羹尧指出军队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并无赶尽杀绝之意:
西宁附近之僧番人等近已安定十之八九,率众来归者亦多,皆令其造册认纳粮草,各安住牧(朱批:若是假相暂安,终不济事,只图永定之谋为上)。惟塔儿寺再三化诲,不肯输诚,仍然聚守,少迟示以兵威,便可完结(朱批:强化之,貌恭,不如借此更张之,待以图久安长治之策好)。
然而,事情却总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郭隆寺贼僧,臣因其坐床喇嘛现在西宁,而数月以来,未敢显有恶迹,是以加意看待,俟西海平定,再为清查,分别给与度牒,便可竣事。而无故自作其孽,聚集番土一万余人抗拒官兵,自辰至申,据苏丹、岳钟琪密告臣云:自三番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彼众我寡,彼逸我劳,彼在山上面仰攻,将士奋呼,以一当十,直至一千有余之恶狠喇嘛悉死于当阵,而后败退。次日又复搜山剿捕。计两日所杀贼尸六千二百有零,川陕官兵所带腰刀皆臣所造者,砍缺三四百口,可以知此一战矣。
不难发现,清军与寺庙喇嘛及其同伙的战争规模很大。喇嘛伤亡惨重,这是战场上不可避免之事。必须要指出的是,喇嘛纠合同伙作乱在先,清军平乱在后,这场战争的性质不是倚强凌弱的民族压迫,而是维护安定和保护宗教的正义之举。雍正三年(1725)六月十六日,陕西按察司事粮盐道仍带监察御史许容上奏:
奏为据实沥陈仰祈……臣因思年羹尧在西宁时,自臣到之后,奉令领兵,无一非臣。虽臣到西宁甚迟,就臣经历者,亦有塔儿寺、尔格隆寺(郭隆寺)二处。……臣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带领四川汉土官兵到南川营,有兴安镇总兵武正安传大将军密令云:“塔儿寺喇嘛连罗卜藏丹尽(津),帮助口粮,侵犯内地,着臣…前往塔儿寺,将寺内所有喇嘛尽行拿了,于内挑选老诚者三百名,仍做喇嘛,令其寺内居住;其馀强壮者尽行杀了;幼小者令其各归本家还俗”等语。……黎明时到寺,随将寺院围了,差人唤出喇嘛共有一千一百馀名,内有青海蒙古喇嘛六人,其馀皆系附近西宁番子及土司属上人。……据供:“……我等父兄俱畏罪投诚,……与内地百姓一样当差”。臣切(窃)思父兄既已投诚,则子弟虽做喇嘛,亦在投诚之列。若将番子喇嘛中强壮者尽杀,何以示信与番子?随与丹等相商,止将蒙古喇嘛六人正法,其馀除仍做喇嘛三百馀名外,俱令回家还俗。臣等即撤兵回营。……
……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九日,年羹尧面令臣等说:“尔格隆寺的喇嘛反了;要来抢夺西宁,令臣同苏丹、伊礼布带领满、汉官兵由威远堡一路前进;又令总兵黄喜林、武正安由胜番沟一路前进征剿。约定十二日会兵,俟剿杀明白,将寺院烧毁”等语。臣同苏丹等……于十二日辰时到地名华里地方,见对面山上约有八、九千人排列呐喊,恃险拒敌。山下沟内俱系租寺院田地之番子、土民堡寨……随分兵一半攻寨,一半攻山,自辰至申,铳砲之声不绝,连夺三山,攻破五寨……至次日十五清晨,传令各兵放火烧寺,十六日回兵,十七日到宁。臣进见年羹尧,回覆将令。随将拿获喇嘛,据供起衅缘由之事,当众人一一告诉。年羹尧惟面红无语,且并不吩咐追究。臣方觉非厅卫妄行,乃有所主使耳……
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许容的表述似较他人更有说服力。许容向皇帝奏明,塔尔寺喇嘛有明显悔罪表现,故未遭殃,但对郭隆寺之役,年羹尧为何“面红无语,且并不吩咐追究”?王锺翰先生认为这是年羹尧听信了地方官员捏造的“喇嘛反了”的谣言。然而,如果这真是谣言,那便与年羹尧多次奏陈的内容大相径庭,也与许容所奏“见对面山上约有八、九千人排列呐喊,恃险拒敌”自相矛盾。更何况,如果喇嘛没有造反,郭隆寺之战的规模何至像岳钟琪所言“自三番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笔者认为,郭隆寺喇嘛造反是事实,清军平乱也是事实。许容所说“年羹尧惟面红无语,且并不吩咐追究。臣方觉非厅卫妄行,乃有所主使耳”,是在年羹尧失宠、遭遇多方弹劾情况下对昔日年大将军的刻意保护,“有所主使”四字意思甚为模糊。雍正帝朱批:“卿全属心为人,朕所悉知,此等事何用辩明再干,碍不著你,朕保得定,放心放心”。倘若皇帝认为“有所主使”确有道理,为何不去追问?很显然,皇帝一眼就看穿了许容的心思,认为许容所言既有澄清事实的一面,也有袒护同僚的用意,并告诉许容年羹尧失势“碍不著你”。此外,笔者尚未在年羹尧给雍正帝的奏折中发现年羹尧自陈是受地方官员误导而毁寺杀僧的记载。
三、寺志中所见“毁寺杀僧”之事
《塔尔寺志》记载:
青海登真洪太极(按清史记为“青海罗卜藏丹津”),喻如火与胡须不相容他(笔者注:“他”应为“地”)对皇上生起叛逆之心而造乱,于大清第三代皇帝雍正元年岁次癸卯(公元1723),蒙族军兵来到西宁等汉族城市中大肆烧杀、劫掠、捣毁。清廷派遣年公爷(即年羹尧)和岳公爷(即岳钟琪)等将军和多万大军前来平乱,由于地方寺庙色柯等许多寺民与青海有勾结,所有奸人作有坏事而遭讨伐毁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军)来到此间塔尔寺时,寺内仅有年老喇嘛僧三百人,其余僧众都逃回各自乡土。寺主堪布胆识浅薄之故,大军刚一出动,他立即逃走,以此所得报果,使寿命遭到灾厄。从二十七日起寺内每一僧人月俸仅给五根柴火而已。
该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被杀之人多为造反之人,但具体数量不详;二是清军抵达塔尔寺后,寺内喇嘛僧数量较少,这与许容奏折中“止将蒙古喇嘛六人正法,其馀除仍做喇嘛三百馀名外,俱令回家还俗”的说法基本吻合。
郭隆寺又称佑宁寺,是平青海之役中最激烈战斗的发生地。当时被称为安多地区“众多佛教讲修寺院中唯一最先创建,殊胜八方的大佛刹”的佑宁寺如今只有300余人,且较为破败,罗卜藏丹津之乱恰恰就是佑宁寺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佑宁寺志》记载:
雍正帝(公元1723——1735年在位)年间,皇帝厚待青海丹津亲王,但他福泽浅薄,为了反叛朝廷,竟私自征集蒙古兵丁,捣毁附近被称为“山城”的汉族小城……如果此地各寺僧众都能严守寺规,按佛门戒律行事,也就相安无事。但战乱发生前,各寺皆以蒙古人为靠山,无视汉人。有些寺院的主事者邪魔缠身,在寺院间不断制造事端,并逮捕村俗盗贼,罚以断臂,滴以火漆,与出家人的举止格格不入……由于少数人的恶行,致使很多无辜的寺院也遭受株连。兔年(公元1723年),汉兵焚毁赛科寺,却藏活佛何罪之有?只因他是赛科寺上师,汉兵将他和十七名老僧骗至衙门庄活活烧死,并杀害郭隆寺一百多僧人,焚毁郭隆寺的大经堂、藏经殿等。汉兵还毁坏夏吾科一带的三所佛寺,大通河流域的仙米寺、加多寺、霍戎一带的扎德寺。塔尔寺被占时间较早,除杀了该寺的主犯和三十余名家不在附近的老僧外,整个寺院未遭损伤。
通过该寺志的记载,我们也能获取如下信息:寺院主事害民在先,清军毁寺杀僧在后;清军做过滥毁寺庙的举动;塔尔寺未逃走的300余名僧人中被杀的约40人,绝非“不分奸良,诛无孑遗”。
四、结语
综合来看,清军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中“毁寺杀僧”是历史事实,但毁寺并非完全摧毁,杀僧也并非带有明显民族压迫性质的屠杀。在郭莽寺,清军出于自卫之需“连射四矢,毙四喇嘛”。在塔尔寺,“止将蒙古喇嘛六人正法”,“除杀了该寺的主犯和三十余名家不在附近的老僧外,整个寺院未遭损伤”。在战乱规模最大的佑宁寺,“彼在山上面仰攻,将士奋呼,以一当十,直至一千有余之恶狠喇嘛悉死于当阵,而后败退。次日又复搜山剿捕。计两日所杀贼尸六千二百有零”。需要注意的是,郭隆寺战役作乱之人中有“番土一万余人”,清军所杀6200余人中应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寺僧。年羹尧所奏“非除喇嘛也,所以除叛逆也;非轻佛法也,正以扶黄教也”当是对“毁寺杀僧”事件的客观注解。
[1]色多·罗桑崔臣嘉措著,郭和卿译.塔尔寺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51-76.
[2]张书才.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五册)[M].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320-330.
[3]尕藏,蒲文成等译注.佑宁寺志(三种)[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1-65.
[4]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1-370.
[5]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4:1237-1255.
2016-08-23
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重点学科重大项目“雍正朝满汉文朱批奏折中所见藏事辑录”(16ZGSMZD001)。
王航(1990- ),男,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
K24
A
2095-7602(2017)01-007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