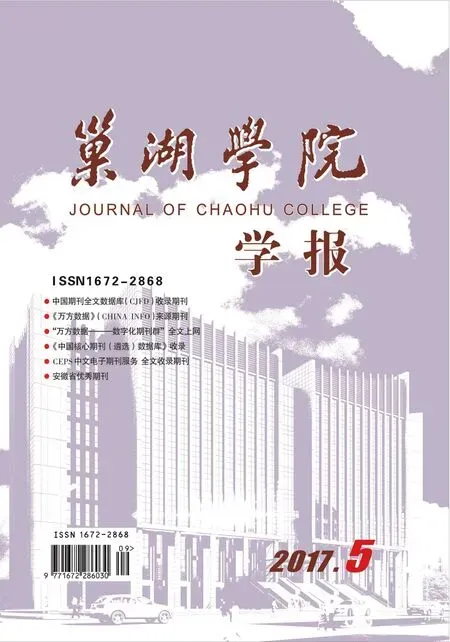生命的沉思之“轻与重”
——爱伦·坡的艺术救赎之路
邵文静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
生命的沉思之“轻与重”
——爱伦·坡的艺术救赎之路
邵文静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
通过对爱伦·坡跌宕起伏的悲剧人生的全面剖析,以及对其作品中展现出的艺术和哲学意义的深入探究,从而冷静地观察他是如何以超脱的眼光去看待人的生存困遇,在生命之“轻与重”中,找到一条艺术救赎之路。
爱伦·坡;“轻与重”;艺术;死亡;
1 引言
爱伦·坡,世界著名的犯罪和恐怖文学大师,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鼻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萧伯纳曾称美国只有两个伟大的作家:爱伦·坡和马克·吐温。其所创作的阴森扭曲的故事印证了他同样扭曲的人生,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第一批职业作家,尽管他的文学成就登峰造极,但却是叛逆、疯子、酒鬼和瘾君子的代名词,一生穷困潦倒,饱受人间白眼。一百五十年来,爱伦·坡作品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国外学者对其作品的评论众说纷纭,许多同时代作家如爱默生、朗费罗、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等人对其评价不高,甚至贬低坡为“打油诗人”[1]。然而在大洋彼岸,法国象征主义三大领军人物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莱里却对他推崇备至,并将其作品翻译介绍给法国读者,在欧洲掀起一股“坡热”。受到这股热潮影响,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学界,肯定了坡的文学地位,一些现代派作家也深受影响,如伊迪丝·沃顿、威廉·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等,甚至连现实主义作家如德莱塞也认为坡是“首屈一指的最伟大的文学天才”。这说明爱伦·坡的文学创作在接受美学的层面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内的爱伦·坡研究则起步较晚,成果甚少,也不够深入,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主要侧重文本分析、主题研究及其作品中丰富的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探究。然而对爱伦·坡短暂人生的深入探讨及其背后反映的人生及存在主义哲思研究则一片空白。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爱伦·坡的人生浮沉进行寻本溯源的考察,再去找寻其作品中反映的人生哲理,以期能够以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目光来看待生命存在的全部真实的境况。
2 生命之“轻与重”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开篇,米兰·昆德拉就向我们质问道:生命,到底是轻还是重?米兰·昆德拉由尼采的“永劫回归说”导入,给出他自己的答案:一切事物转瞬即逝,人的生命也仅有一次,永劫回归,生命之“重”;不可回归,生命之“轻”。这个带有哲学沉思意味的问题俨然已成为自古以来哲学思辨中争论不休的主题: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滚石上山,石头再从山顶滚落,如此循环不已,似乎也暗示了这个生命的难题;德谟克里特斯的“原子理论”也间接支持了米兰·昆德拉的观点,认为人死后没有生命,死后“灵魂原子”就四处飞散;于是,伊比鸠鲁便运用德谟克里特斯的理论来告诫人们要及时享乐,生命之“重”不是人存在的意义,人终究会死,生命之“轻”才是生命的哲学;然而,斯多葛派哲人所追求的生活是却是一种摆脱了激情和欲望冷静而达观的生活,他们认为人只是宇宙秩序安排好的一份子,每个人都是大同社会的一员,因此我们都应当完成自己在社会中相应的责任。那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轻还是重?
纵观爱伦·坡一生所面临人生境遇,可以发现他一直徘徊在“轻”与“重”的交替循环中,保持着两难心态。坡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的父母都是演员,虽然母亲演技超群,但在当时,演员的地位并不很高。坡出生不到两年,父亲便抛下了他们,据说不久就客死他乡。随之,母亲也于一年后因病故去,留下兄妹三人成了孤儿。后来,坡被商人约翰和弗兰西斯·艾伦夫妇所收养,童年时期一直居住在英国,精通法语和拉丁语,饱读欧洲的古典文学。然而青年时期的他和养父约翰·艾伦的关系却变得剑拔弩张,出于对养父的忤逆,他打架斗殴,酗酒赌博,却仍敬爱养母弗兰西斯,直到养母死后,约翰·艾伦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那时他已经在西点军校读书,但是其诗歌才华俨然盖过了军事才能,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负债累累地离开了学校。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他最后来到了巴尔的摩和姑妈住在一起,并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他的表妹及妻子——弗吉尼亚,让爱伦·坡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归属感,这个曾经机敏活泼,无忧无虑地漫步于山间的少女,让每个见过她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沉迷于她的花容月貌和优雅风度中,当然她的堂兄爱伦·坡也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那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然而生命之“轻”并不能真正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反而会增添人的非真实感和一种无可回归的恐惧感,也许生命中的苦难和负担,才会让我们的生命贴近大地,才会真切实在。米兰·昆德拉借托马斯之口感叹道:“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2]
爱伦·坡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很快就过去了,他迎来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星期一”,弗吉尼亚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肺结核,生命之“重”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永劫回归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受到那些探索人类精神的科学家们的启发,对圣经里关于来生的概念产生了怀疑,对于天堂的幻想也逐渐褪色,开始对死亡感到恐惧;加上折磨人的霍乱和肺结核的大肆蔓延,当时的医学水平还不足以治疗这样的疾病,病人有时被误认为已死,其实那只是在结核的肺里浅浅地呼吸斑疹伤寒的昏迷状态,或者在中风和麻痹症时的艰难行走,都使那无法预测的时间里承载着的恐惧一展无遗。年轻的弗吉尼亚与病魔战斗了五年,期间她的病情时常恶化让人觉得她即将死去,爱伦·坡甚至都已经为她准备好了葬礼,但她又奇迹般地好转了,然后他就会变得乐观起来,并热切期盼着新生活的到来,然后她的病情又恶化,就这样不停地死而复生。
爱伦·坡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正忍受这种痛苦的同时,还要承担养家糊口和照顾妻子的重担,他过着双重生活,白天是纽约时报的主编,晚上则是妻子的护士,默默地忍受着妻子长达三年的咳嗽和沉默,然而在精神上的焦虑、内疚和恐惧则让他更加难以忍受,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这种如洪水般的悲伤一次又一次地冲刷着他,此时酒精和写作成了他唯一的发泄途径,他运用自己高超的艺术技巧描绘出这种恐惧,使人读后有种强烈的共鸣感。《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的厄舍就是那个时候的爱伦·坡:“我一定会在这可悲的疯狂感觉中送命。就那样,就那样死去,不会有别的出路。我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一想到任何意外,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令我这敏感焦虑的心灵受到震撼,我就感到不寒而栗……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下,在这种凄惨可悲的处境中,我感到那个时刻迟早会到来,我定会在与恐惧这个狰狞幻影的一次抗争中,彻底放弃我的生命和理智。”[3]终于,那个可怕的时刻到来了,弗吉尼亚于1847年逝世,年仅24岁。
弗吉尼亚给予了爱伦·坡穷尽一生所渴望的稳定、亲密无间和归属感,因此失去爱妻,失去了不可忍受的生命之“重”,得到了自由的生命之“轻”却让人更加不能忍受,失去了弗吉尼亚的爱伦·坡就像是失去了特丽莎的托马斯,在失去永劫回归的世界后,生命只剩下了“轻”,有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使人感到恐惧。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曾阐述了这种渴求自由的生命之“轻”,却又恐惧自由,希望找到生命之“重”的矛盾心理。这也是人类面临的基本困境。叔本华在“生存意志论”中指出,人受到生存意志的支配,所以生命需要苦难,每一个灵魂都是一部痛苦史,幸福与快乐包含在痛苦之中,世界唯有人的痛苦最深。生命的救赎只能转向艺术,尼采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似乎继承了叔本华的衣钵,他认为酒神精神所代表的非理性状态,也可称为“醉”的状态需要日神精神所代表的沉静和理性,也可用“梦”的状态来表达,他认为艺术的真理在于观众可以感受到艺术家创作时那种狂喜的状态(即醉感),并在欣赏美的同时达到心灵的某种升华,从而不断地努力将自己也塑造成一件给予人美感的艺术品,一种“风格”,一种“稀少而崇高”的艺术,只有这样人才能对自己的“人的面目”,对那些生命之“重”完全忍受。所以尼采对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论不以为然,他认为生命的意义不是由存在决定,而是由某种先天的本质,人的生命意志决定,所以他提倡以审美的角度去看待人生的境遇,并赋予生命以一种新的意义,靠艺术来拯救人生,在《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中,他直接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人们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3 爱伦·坡的美学救赎
经历了永劫回归的生命之“重”,爱伦·坡似乎也悟出了同样的人生哲理。对于爱伦·坡而言,生命只有一次,相比于幻想来生,他更着眼于生命之终曲,随着知觉的丧失,一切都走向终止。所以在面对这些生命的重压时,他没有怀疑、妥协,甚至放弃自我,反而用大量优秀的作品予以回击,其作品中描写的那些凄美的爱情、美丽的女性以及恐怖和神秘的死亡,他认为作家通过艺术创造出来的“效果”,能使读者的灵魂感受到一种“强烈而纯净的激动”而得到升华。亚里士多德在定义“悲剧”时,曾引用“净化说”,认为悲剧的效果在于净化人的心灵,引起人们内心的怜悯或恐惧从而使这种情感得净化,爱伦·坡对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进行了批判继承,他认为艺术之美才是从生命之“重”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他强调死亡能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死亡也是摆脱生命之“重”的唯一手段,是生命最纯洁最完美的状态,它赋予生命以本真的意义,因此,爱伦·坡认为人人都“向往死亡”,借此表达超越人生之渴望,正如杜弗海纳所言,死亡是一种“脱胎换骨”,也赋予生命新的意义。但爱伦·坡对人性中黑暗面和死亡进行的细致描述是为了追寻艺术永恒的真理——死亡,作为将其从永劫回归的生命苦海中解救出来的途径。
爱伦·坡的艺术救赎之路始于19世纪早期,那时美国还禁锢在清教徒的伦理道德之下,奴隶制,肆虐的疾病以及贫穷,这些乱世为南北战争埋下了伏笔,与之相伴的还有另外一场革命,即文学革命。作为美国浪漫主义的先驱,他反对美国的清教主义,重新演绎了哥特式文学的恐怖与浪漫,通过对死亡与疯狂的一系列心理探索,极大地满足了读者渴望血腥恐怖故事的心理,他的小说总是与黑暗、恐怖与死亡紧密相连,恐怖俨然成为他的故事的基调。他认为人世间充满了苦难、黑暗和压抑,这些生命之“重”人们无法逃避,对此他怀着既害怕又欣赏的心情。通过艺术创作,探索了许多人类行为中那些边缘化的侧面,试图找寻纯粹的艺术,他的艺术主题常常别具一格,那些人性阴暗残酷的一面在他的作品中暴露无遗,那些神秘难解的艺术符号是他对人类病态能力的观察,即使常常被中产阶级认为是一种恐怖,一种焦虑。评论家约翰·阿登却力挺爱伦·坡,评价那些人是:“他们那种光明磊落和仁爱厚道的天赋品质从未经受过严格的考验。一旦他们经受考验,就土崩瓦解了。”[4]
爱伦·坡艺术中通过营造恐怖的死亡氛围,来达到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而这种效果通过描写女性尤其是美丽女性的死亡更具永恒的审美价值。他曾说过世界上最令人惋惜、最唯美的艺术主题莫过于美女的香逝,只有在思考此类美好的事物时才会产生最激烈、最纯净的感情。美并不是与丑相对的一种性质,而应被视为一种效果。坡的艺术创造灵感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通过研究他与身边的女人的信件、周记、诗歌和散文,我们可以找到反复出现在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的原型:母亲的形象、难以接近的女性和天真无邪的少女,分别对应他生命中的四位女性:亡妻弗吉尼亚,已故母亲艾丽莎,红颜知己萨拉·海伦和倾慕已久的作家弗兰西斯。终其一生,他不是失去她们就是被她们拒之千里,所以在作品中,他安排这些女性不是已经死亡,就是即将死去,又或是她们知道自己的宿命,并最终殒命。对于坡来说,死亡似乎是女性的唯一归宿,他对女性似乎有着某种恐惧,这种恐惧也许来源于一次又一次被抛弃的经历。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坡具有一定的恋母情节。因为他的母亲过世太早,以至于他从来没有真切地认识到她已经死去,不能走出这个心理阴影的他觉得母亲还会回到他身边,因此他在小说中虚构了许多关于复活的情节和设想,其深层原因可能是孩童时候的他,经常看到母亲扮演朱丽叶特和奥莉菲娅在舞台上死去又复活,对于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来说,形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她能够死而复生,然后再度死去。这种心理现象可以从弗洛伊德的“非家幻觉/暗恐”去解读:“暗恐是一种惊恐情绪,但又可以追溯到很久前就已相识并熟悉的事情。”[5]早已熟悉的事情反复出现在脑海里会引起一系列的心理反应。也可以从Talmy的“情感图式”的角度去解读:人们对愤怒、恐惧、嫉妒、孤独等情感的认识来自个人的生活经历并储存在长期记忆中,而且会和其他图式相联系相伴随。虽这是一种认知结构,随个人经历而产生,在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外部世界又以图式化的方式构成个人头脑中的世界。
可能坡永远也理解不了她永远都不会回来的事实。对他来说,母亲就是最强的灵感源泉,这场变故随之而带来的是,他所畏惧的死亡,是一切精彩故事的开端,对他来说,没有永恒的消失,他渴望母亲能常伴左右,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找女性来填补母亲留下的空白,在作品中,他让从未了解的母亲复活,一遍又一遍将她带回到人世。在《丽姬娅》中,爱伦·坡先是以悲伤的基调描写亡妻丽姬娅的美貌与性格,又以客观超然的态度叙述丽姬娅与续弦的罗维娜·特瑞梵农小姐的死亡,最终,他让“借尸还魂”的故事上演,丽姬娅借罗维娜之身复活:早已死去的她又开始动弹了,虽然双眼紧闭,包裹上裹尸布的身躯被送进坟墓,却好像又挣脱了死神的羁绊。爱伦·坡描写死亡与复活一方面出于他的恋母情节或者因妻子的病故所带来的创伤(trauma),却并不局限于女性死亡本身,他更是细腻地描绘了她们死亡那一刻的复杂感受,追求永恒的美时那种“强烈的纯净的激昂”,约瑟夫·毛登豪尔评价道,爱伦·坡在其艺术救赎自我的路上,宁愿让自己“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变成一个“美女杀手”。他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的香消玉殒,固然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悲痛,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尸复活所带来的恐怖氛围,更令人感到恐惧,但同时读者的心灵却达到了某种净化的效果,内心产生一种更纯洁、更美的东西——灵魂,而灵魂不死才能获得艺术上的救赎,才能超脱于永劫回归生命之“轻”与“重”的无限循环。
4 结语
柯勒律治在诗歌《墓志铭》中写道:“曾在生命中发现死亡,此时,或许能在死亡中发现生命!”[6]在爱伦·坡短暂的一生中,他虽然摆脱不了那些生命之“重”,苦难、烦闷和悲哀一直伴随着他,但他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对艺术的追求已成为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在坡的艺术创作中,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死亡”的艺术主题均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升华。其艺术灵感源于他对生命之“轻”与“重”的哲学沉思,生命中那些痛苦成为他艺术创造永不枯竭的源泉,坠入生命的深渊和黑暗的地底使他的艺术创造更有活力和价值,其人生的智慧及力量也更强大,正如尼采说的“那些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他对生命有了更加冷静超然的认识。在给洛威尔的信中,他曾坦率地表示:“我继续沉溺于未来的幻想之中。我失去了对人类完美的信念。我认为人类的努力对人性不会有什么影响。现在的人比六千年以前的人只不过机灵些——但并不快乐,也不聪慧。”[7]
[1]董衡巽,朱虹,施咸荣,等,编著.美国文学简史(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54.
[2]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韩少功,韩刚,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27.
[3]爱伦·坡精品集(上)[M].曹明伦,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44.
[4]希区柯克.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M].史育哲,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
[5]童明.暗恐/非家幻觉[J].外国文学,2011,(4):106-116.
[6]李枫.诗人的神学——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0.
[7]西蒙斯.文坛怪杰——爱伦·坡传[M].文刚,吴樾,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12.
THE CONTEMPLATION ON LIFE——"LIGHTNESS AND HEAVINESS"——ALLAN POE′S WAY OF ART REDEMPTION
SHAO Wen-jing
(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9)
This paper probes into Allan Poe′s tragic life and his works,trying to observe how he looked at the life dilemma in a detached way and found a way of art redemption.
Allan Poe; "lightness and heaviness"; art; death
I106.4
A
1672-2868(2017)05-0091-05
2017-06-06
邵文静(1990-),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