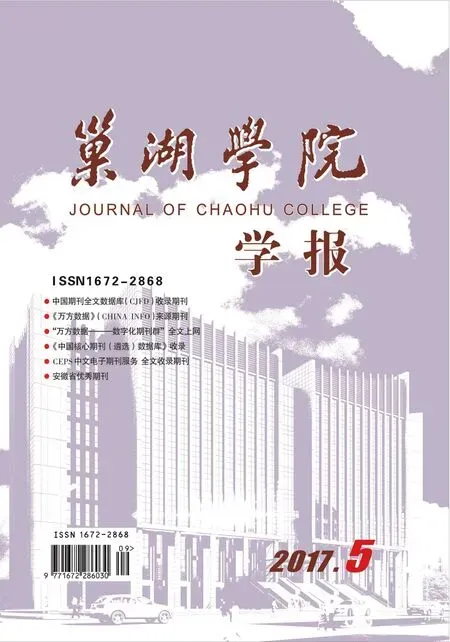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工离婚的司法治理研究
——以G镇法庭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为例
汪开明 董颖鑫 陈效智
(1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2 巢湖市人民法院,安徽 巢湖 238000)
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工离婚的司法治理研究
——以G镇法庭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为例
汪开明1董颖鑫1陈效智2
(1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2 巢湖市人民法院,安徽 巢湖 238000)
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及其婚姻家庭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解体。作为乡村社会司法治理的重要机构之一,乡镇法庭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婚案件进行审理时,要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背景以及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适用国家法,正确处理国家法与乡村社会风俗习惯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社会变迁;新生代农民工;离婚;司法治理
1 导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城市打工,这些人被社会及学界称为“农民工”,也叫“第一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而他们的子女,即所谓“第二代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也先后登上社会舞台。基于不同的成长经历,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在文化程度、思想观念、心理情感、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更是与他们的父辈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地理通婚圈”更大,择偶更加自由,择偶方式更具多样化,婚后的家庭生活模式更多,等等。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方面的上述变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存在激烈碰撞,导致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走向解体。因此,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基层法院,特别是乡镇法庭受理的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也越来越多。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人数十分庞大的社会群体,其婚姻家庭的稳定无论对于他们出生所在地的乡村社会,还是打工所在地的城市社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W县G镇法庭为调查点,通过对该镇法庭近几年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情况的调研,分别采取与案件主审法官及部分案件当事人进行访谈、参与旁听对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的庭审等方法,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乡镇法庭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中的调解和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的对策和建议。
2 乡村社会司法治理及其研究概述
乡村社会的司法治理一般是指国家通过正式制定的成文法律实施对广大乡村的社会治理。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由于“皇权不下县”,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基层的广大乡村地区一般依靠乡绅或者家族,并采取以自治为主要方式的社会治理形式。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法族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家正式承认的法律效力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加强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权力渗透,但由于法律发展的相对滞后,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特别在“文革”期间,国家在农村的社会治理主要以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为依据。及至改革开放后,随着法制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乡村社会的司法治理才逐步正式走到社会的前台,成为“依法治国”背景下国家对农村实施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就乡村社会司法治理的研究来看,尽管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是,正如杨力所言:“乡村司法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司法学界从未成为显学,稍有涉及,也是作为‘水桶上的最短木板’出现的。”[1]可即便如此,众多学者还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术探索。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姚建宗认为,“在乡村社会的司法治理研究中,基本上有两种认识立场。一为法治论立场,即国家制定的法律体系在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均应得到一体化遵行,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应适用同样的纠纷解决态度、诉讼规则和结案方式,以保证法治的普遍性与统一性得到实现。另一种是治理论立场,即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司法需求,在司法实践中应适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态度、诉讼规则和结案方式,以保证法治能够获得农村社会内在性力量的支持。”[2]从研究的进路来看,杨力认为,“现存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条进路:一是从纯粹理论法学角度展开的‘法社会学’研究,……;二是在诉讼法或其他部门法的基础上所作的‘实体或程序规范研究’,……;另外,法史学界对此也有一定的研究。”[1]
上述研究者秉持各自的认识论立场,循着不同的研究进路对乡村社会的司法治理及纠纷解决提出了种种观点,这些观点尽管表述各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的乡村社会司法治理与纠纷解决的不同面相,而在笔者看来,其间贯穿的一根主线乃是乡村社会司法治理与纠纷解决中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二者之间的多元互动,而这种多元互动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具有更为复杂的呈现。
3 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及其婚姻家庭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剧烈的社会变迁不但对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还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及其婚姻家庭产生较大影响,引发了诸多婚姻家庭问题,严重的甚至导致其婚姻家庭的解体。
3.1 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身处当代中国的变迁社会,和他们的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上。第一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在结婚以后去城市打工或经商的,由于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较长,其大部分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及邻里关系等都在农村,农村的各种风俗习惯及风土人情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则不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大都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后就跟随父母亲或其他亲属及同乡、同学等,或者独自一人去城市打工。由于离开家时年龄较小,加之离家之前基本都在学校读书,因此,他们的生活轨迹主要表现为从学校到城市,其很多社会关系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所以,农村的社会环境及其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对这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影响不大。此外,由于刚进入社会就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加之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此,城市的文化及生活对他们的影响较之于他们出生的农村更大。而这种成长环境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心理情感以及行为方式等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3.2 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影响
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在城市打工或经商,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文化及精神层面的等,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产生较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时更加注重自由恋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二是由于在外地打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地理通婚圈”扩大,异地婚姻明显增多。三是由于受城市文化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观念日益开放,婚前性行为及同居、婚外性行为较多。四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模式已经由原来第一代农民工的夫妻两地分居模式转变为夫妻二人和孩子分居的模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大多数夫妻二人在一起打工,但是由于城市生活以及孩子学习等条件的限制,很多人将孩子留在农村家中由老人照料;其中,也有一些是妻子生下孩子后和丈夫分居,留在老家照料孩子等。
总之,上述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及其婚姻家庭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身处当代社会转型期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夫妻如果不能更快地适应变迁社会中的各种情势,不能更好地调适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那么,他们的婚姻家庭就会面临各种危机,严重的会导致婚姻解体,并最终离婚。
4 乡镇法庭对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的审理
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及其婚姻家庭的诸多影响因素,以及乡村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乡镇法庭在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时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基于婚姻家庭的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乡镇法庭在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时,必须要根据社会变迁的现实状况,并针对当事人自身的特殊情况,灵活适用法律,在个案中做到情、理、法的统一,妥善处理案件。实际上,乡镇法庭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涉及的问题很多,限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将主要根据自己的调研情况集中分析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中的法庭调解问题;二是乡镇法庭在处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时的法律适用问题。
4.1 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中的法庭调解
我国《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夫妻离婚案件,应当对二人进行调解;如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经过调解无效,应当准予夫妻离婚。因此,乡镇法庭在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时,首先必须要进行调解。此外,《婚姻法》还规定,夫妻离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协议离婚方式,即男女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离婚,且对家庭财产的分割、债权债务的处理和孩子的抚养等问题都达成协议,双方就可以直接去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离婚。二是诉讼离婚方式,即夫妻中的一方不同意离婚,或者虽然夫妻双方对离婚无异议,但是对家庭财产的分割、债权债务的处理以及孩子的抚养等问题达不成协议,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诉至法院,请求法官审理并做出裁判。
计划经济时期,即使男女双方当事人之间采取协议离婚,当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一般也不会直接批准离婚。在当事人申请离婚时,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都会进行一些调解。而在一方当事人不愿意离婚的情况下,在要求离婚的一方起诉至法院之前,双方的亲朋好友以及当地的村委会或居委会、镇或村的妇联等,一般也都会对双方进行调解。但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乡村社会也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在今日的乡村社会中,“人们的交往和行为,不再局限于乡土熟人社区和基层市场区域,而是镶嵌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中。与此相伴的是,乡村社会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和异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与外部世界频繁密切的互动还使得人们的价值和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3]此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村民们的生存结构正在经历着根本的变化:宗族治理的衰弱、伦理纲常的淡漠,血缘亲缘的疏远。当下的乡村更趋向于以个体及小家庭为中心,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新型生存结构体系。”[4]因此,在上述变迁社会背景下,原先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以及计划经济时代能够对包括婚姻纠纷在内的各种民间纠纷进行有效处理的个人或基层组织的调解也日渐式微;由此,有关婚姻纠纷的法庭调解就显得更加必要和重要。
虽然法律规定的离婚方式很明确,但是,笔者在G镇的调研中却发现,对大多数意欲离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即使双方都同意离婚,或者其中的一方想要离婚,他们或他(她)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去法院起诉。我们固然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做法看作是他们法律意识提高的一种表现,但笔者在对一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访谈时却发现,他们之所以选择去法院解决离婚问题往往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认为,去法院解决纠纷是城里人的惯常做法。作为在城市打工的他们,除了在很多行为方式方面学习或模仿城里人以外,即使是解决包括婚姻纠纷在内的各种纠纷,他们也认为应该像城里人一样去法院解决。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甚至不惜为此花钱请一个律师来代理他们的离婚案件。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选择去法院起诉离婚的这种做法及看法,实际上印证了美国学者萨利·安格尔·梅丽(以下简称梅丽)的一个观点。梅丽在对美国乡村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进行研究时发现,在很多社会底层的美国人看来,“借助法院解决问题是享有尊贵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5]。
笔者在调研中同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直接去法院解决离婚问题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与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影响具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人们大都认为离婚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情;除非万不得已,人们一般很少会去法院解决他们的婚姻纠纷。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受到城市生活的熏陶,他们的思想观念较为“前卫”,他们并不认为离婚是一件有失脸面的事情;因此,他们往往十分主动地选择去法院解决离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直接去乡镇法庭起诉离婚,将他们的婚姻纠纷直接带入到法庭这一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普通村民如果离婚的话,无论是去法院起诉离婚,还是双方协议离婚,在此之前,他们至少要面对以下几个常见的干预网络:“首先是由当事人父母、亲戚、邻居、朋友等人组成的亲情干预网络。……。其次,是由村组干部、家族族长及其他有名望的人组成的道德干预网络。……。再次,是乡司法所等民事调解组织组成的行政干预网络。”[6]尽管在当代社会变迁背景下,乡村传统治理方式逐渐衰退,例如,“宗族力量的牵制力削弱。……。行政管理方式弱化”[7],等等。但是,上述对村民离婚的几个干预网络的“功能衰退”并不等于其“功能丧失”,对于那些从外地回到故乡直接去法院起诉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上述常见的几个干预网络虽然在他们去法庭起诉前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却恰恰为乡镇法庭调解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提供了潜在的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
因此,乡镇法庭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进行调解时,要充分关照当代乡村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今日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各种变迁,人们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是某些久居乡村的老人也很少对人们的离婚抱持绝对的反感。此外,如前所述,原来在乡村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家族力量和集体力量在很多乡村地区尽管日渐式微,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乡镇法庭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婚案件进行调解时,一方面可以考虑如何进一步挖掘乡村社会的传统资源,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离婚案件当事人的亲属关系在法庭调解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切实处理好与当地乡镇政府及村(居)委会的关系,将法庭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乡镇法庭要尽量淡化法庭的“剧场化”效应,不拘泥于法庭调解的形式,可以采取“现场调解”“巡回法庭”等多种法庭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婚纠纷。
4.2 乡镇法庭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时的法律适用
作为处理乡村社会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正式组织机构,乡镇法庭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必须适用国家制定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等正式的成文法。而乡村社会却存在着诸多以当地的风俗习惯及风土人情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 “民间法”。众所周知,国家制定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其法律规范高度的概括性,因此,很多法律规范在适用中需要法官根据实际生活中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适用。以《婚姻法》中关于判定离婚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为例,虽然《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对有关的判定标准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显然不可能完全涵盖现实生活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众多其他情形。而且,如果从一个较长时段的个人生活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在当下“确已破裂的感情”未必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又重新弥合。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那些“破镜重圆”即重新复婚的夫妻。如果单纯从那些先被法庭判决离婚,而后又重新复婚的案例来看,先前的离婚判决多少显得有些讽刺意味。实际上,在乡村社会的法律适用中,法庭总会或多或少面临诸多民间法的掣肘,正如赵旭东所言:“纠纷一旦到了法庭这一场域中以后,国家的法律以及民间的习俗都会被当成一种自我保护的资源被当事人双方调动起来。”[8]所以,在乡村社会的法律适用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是乡镇法庭的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必须要予以慎重对待的事情。而事实上,乡镇法庭在处理当事人的离婚案件时,法官往往会在个案中灵活处理,并采取各种策略,尽力使得有关当事人对案件的审理结果感到满意。
在对G镇法庭的调研中,笔者在阅读该法庭近几年的离婚案卷宗时发现,法官对绝大多数离婚案的一审判决都是不准离婚。但其中的一例却是一审就判决准予离婚。法庭在一审时不会轻易判决当事人离婚,一是受传统民间文化与道德的影响,如“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二是希望当事人不要一时冲动,让他们有一个相对冷静的时间去充分考虑是否离婚。但G镇法庭为什么又对上述的那个离婚案件一审就判决离婚呢?主审这起离婚案的C法官告诉我:
“这件离婚案件的被告是一位外省女孩,而原告是本镇的一个男孩。两人是在上海打工认识的,结婚时间将近一年,没有孩子。结婚半年后因为一次争吵,女孩就离开上海,跑到北京打工,此后就和原告不再联系。在多次联系无果的情况下,原告最终决定和女孩离婚。考虑到被告和原告没有孩子,又是外地人,在本地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加之始终不和原告联系,所以我们就缺席判决他们离婚了。你想想,一来这样的婚姻已经毫无意义,二来我们尽快判决原被告离婚,男方还可以再娶啊”。
在一般的离婚案件中,无论是对离婚本身有争议或是虽对离婚无争议但对孩子抚养、家庭财产分割或债权债务承担等问题有异议的离婚案件,对于那些原被告都是本地人的离婚案件来说,法官处理起来往往会面临来自原被告双方家庭、家族乃至乡镇法庭法官们身处其中的整个乡村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但对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自小便随在外打工的父母离开家乡,他们几乎一直在城市长大,除了户口是农村的以外,他们和城里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夸张一点的说,远在农村的家乡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想象的存在”。此外,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自小在农村长大,但后来由于在打工的过程中发展得很好,已经在外地买房定居并打算不再回老家居住了。对这两类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乡土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与其有关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舆论等对他们离婚的影响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婚案件中,我们确实看到这样的情况存在。笔者在对一起离婚案件中的原告进行访谈时,这位已经在芜湖买房并已经搬迁的男性当事人就说过这样的话:
“要是在老家的话,我离婚可能还会有所顾忌,我和老婆原来是一个行政村的,离婚后和她及娘家人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我现在搬到芜湖了,也就觉得无所谓了,离就离吧”。
因此,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原有对离婚构成某种压力的乡村社会舆论以及某些社会关系,对他们来说影响甚微。因此,法庭在处理此类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婚案件时除了要考虑制定法的规定以外,还要考虑当事人自身及其身处其中的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
5 结语
作为乡村社会司法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乡镇法庭审理新生代农民工离婚案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稳定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乡村社会也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社会的“宗族势力、乡村力量已经大为退色,村落共同体也因生产合作的弱化而萎缩。随着城乡间的频繁流动、现代传媒的长驱直入、交通通讯的便捷普及,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被击破,熟人社会的伦理道义被置换,村民逐渐形成以个体或家庭的生存结构为核心的价值考量,以利益关联为梯度的关系网络,由此而产生彼此交往的内生秩序,并维持村落社会的惯常运作。”[9]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无论从其成长、工作及生活环境来看,还是从其文化程度、心理情感及行为方式来看,他们和传统乡村社会的村民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在当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当新生代农民工出于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官的信任,主动将自己婚姻家庭中出现的问题提交到法庭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离婚案件当事人,乡镇法庭乃至每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都应当知道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使命,即在个案的处理中,既要关注日益变迁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更要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力争在每一个个案中以公平公正的判决让他们坚定对法律的信仰。
[1]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J].中国法学,2007,(6):157.
[2]姚建宗.乡村社会的司法治理[N].人民法院报,2012-01-12(5).
[3]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J].法学研究,2010,(5):36.
[4]张学文.乡村司法策略的日常运作和现实考量[J].政法论坛,2012,(6):139.
[5]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M].郭星华,王晓蓓,王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4.
[6]刘中一.法律下乡与离婚自由[J].东方论坛,2013,(1):25-26.
[7]栗峥.国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转型乡村为背景[J].中国法学,2012,(1):78.
[8]赵旭东.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J].社会学研究,2001,(2):78.
[9]栗峥.乡土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与正义表达[J].中外法学,2011,(2):317.
C913.1;D669.1
A
1672-2868(2017)05-0034-06
2017-04-25
巢湖学院校级科研机构“乡村治理研究所”研究项目(项目编号:XWZ-201609)
汪开明(1968-),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
责任编辑:杨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