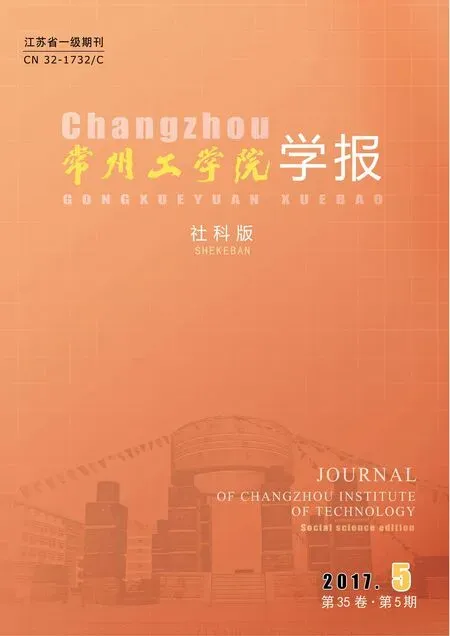台湾文学史书写中浪漫派文学的缺失及其原因初探
李伟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台湾文学史书写中浪漫派文学的缺失及其原因初探
李伟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综观台湾文学史,不论是主题史、文体史、断代史,还是全史,也不论是大陆学者所著之史,还是台湾学者所著之史,都极少有“浪漫派文学”的一席之地。这一现象,不能不令读者质疑:是台湾文学场中真的就没有生产过“浪漫派文学”,还是生产过而研究者对之有难以言说的避讳,抑或认为其不值得笔论?还是被其他某种形态文学遮蔽着?文章对这一缺失现象及其原因作了必要的探求。
台湾文学;浪漫派;文化政策;现代主义;三民主义
I206
一
翻阅众多的台湾文学史,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对“现实主义文学”“反共文学”“战斗文学”“乡土文学”“现代派文学”“都市文学”,以及“军中文学”等都作了研究,不可谓视域不宽,但唯有“浪漫派文学”在台湾文学史中没有一席之地。那么,台湾文学实践中本就真的没有浪漫派作家、没有浪漫派文学作品吗?我们只要审视一下文学史研究之本体——台湾文学,以及辨析什么是“浪漫派”就可发现:台湾文学实践过程中并不缺少“浪漫派文学”。
要讨论台湾“浪漫派文学”,“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是避不开的话题。不过笔者无力也无心在此给“浪漫派”下定义,也不想在此大篇幅地阐释“浪漫主义”,因为自“浪漫主义”产生以来论及者不计其数。正如英国的以赛亚·伯林所说:“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不仅如此,以赛亚·伯林还说,“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脚印指向一个方向;又如波吕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进入,便不可重见天日”①。伯林的这番表述告诉我们,“浪漫主义(或曰浪漫派)”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外延又极为宽广的难以概括的概念,也是一个令人相当难以表述的概念,更是一个难以取得较为一致见解的概念。伯林不想“身陷其中”,不想以概括的方式给“浪漫主义(或浪漫派)”下定义,但他还是向他的演讲听众介绍了几个哲人对“浪漫主义”的看法,他说,“司汤达说,浪漫主义是现代的和有趣的”,“歌德却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疾病,是狂野诗人和天主教反动派虚弱的、不健康的战斗口号”,“尼采说,浪漫主义不是疾病,而是药方,用来治愈疾病”,西斯蒙迪认为,“浪漫主义是爱、宗教和骑士精神的联合”,弗里德里希·冯·根茨认为,“浪漫主义是三头蛇怪的一颗头颅,另外两颗分别是改革和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激进派的威胁,对宗教、对传统、对必将灭亡的旧时代的威胁”,年轻的法国浪漫主义流派“青年法兰西”说,“浪漫主义,那是革命。革命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显然是一切”②。如果我们对以上伯林的介绍加以归纳性分析,便可得出如下三点:(1)浪漫主义是一种具有感伤情状的消极表现;(2)浪漫主义是对现存的、不合理的一种反叛,具有激进的或革命的精神表现;(3)浪漫主义是现代的,具有现代派特征,与现代主义相融合(它与现代主义又相异)。事实上,伯林所列举的“浪漫主义”定义,虽说具有代表性,但只是概念之众的冰山一角而已,更不是浪漫主义发展中的全部理论。浪漫主义思潮是时代的产物,但浪漫主义一直发展演变至今而未消逝。我们所概括的“三点”远不能显现为浪漫主义特征的全部,不过就探讨台湾“浪漫派文学”而言,作为理论资源不可谓缺乏。这“三点”的前两点易于理解,不会令人产生疑问,而第三点就不免使人要问: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具有同质性吗?关于此问题,朱立立在《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一著的“现代与浪漫”一节中,作出了肯定的阐述。朱立立说:“从西方文学史自身发展脉络看,现代派与浪漫派之间原本具有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既有相承续的关联,也有明显的差异”。因为“浪漫主义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意识形态”,而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意识形态”,此二者“是不同时期的产物”,在文学艺术领域,“浪漫主义在反抗古典主义陈规的过程中凸现其历史与美学价值,现代主义则是19世纪现实主义催生出来的逆子”,在表现程度上,现代主义的“焦虑与绝望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激情、想象、传奇,天才理论,在现代主义看来就显得浅薄、夸饰、煽情和造作”③。依据浪漫主义理论去探索台湾文学,我们便会发现台湾文学并不缺少浪漫主义的特质。以张我军为例。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起者之一,出生在1902年日据时期的台湾,1921年(民国十年)19岁,协助林木土到福建省厦门市创设新高银行支店,在厦门同文书院习汉文,并在一文社当文书。此时始接受大陆“五四”新文化。因之改原名张清荣为张我军。1924年1月进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夜间部补习班学习。1924年10月下旬自北京返台北。在台湾居住了近两年后又返京,在这两年中,他竭力促进台湾新文学工作,曾与杨云萍、赖和创办《台湾新文学》,办刊的目的是“想把台湾的社会也使其经过一番的改造”。他认为,“所处的社会是老早就应该改造的”,“我们今日仍处在不合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与其要坐而待毙,不若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倒还干净的很”④。此番豪情壮语透现出强烈的浪漫情怀,他将改造文学台湾为己任,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呐喊着,希望有更多的“亲爱的史兄北姐妹”与他“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旧文学的殿堂”。他“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愿“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为“新文学”的到来“呐喊助攻罢”⑤。张我军不仅是台湾新文学的“呐喊者”,而且还是台湾新文学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的强烈的浪漫情怀浸透在作品之中。在1925年3月26日孙中山先生的台湾悼念会上,他宣读自写的诗般的《孙中山先生吊词》,真可谓有屈原《离骚》中“问天”之悲情,“悲”中有“激昂”,“悼”中存“思”。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深入我人类之伍”的“满身的爱国家爱人类的精神,革命思想和实行的毅力”,“唤醒了四万万沈睡著的人们了”,“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义,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先生的事业,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灿烂!”⑥如果说这篇悼词与他的台湾文学革命的精神一脉相承的话,那么他的爱情诗《乱都之恋》与郭沫若的爱情诗集《瓶》有异篇同曲之风味。《瓶》是疯狂中蕴含着缠绵,《乱都之恋》是炽热中存有幽思。我们不能说张我军的《乱都之恋》是受郭沫若的《瓶》的影响,但他读过郭沫若的诗并受他的影响是无疑的。1925年6月21日,他为郭沫若的新诗《仰望》等三首写过一篇《识语》。他认为:“郭君是一个热血的青年诗人。他对于现社会的缺点、不满,既能痛切地指点出来,亦能切实地指示我们以他的理想。”同时他还提醒文学爱好者,郭沫若“有诗集二部:1、《女神》;2、《星空》。欲研究新文学的人不可不读”⑦。
张我军的文学浪漫情怀不仅受郭沫若的影响,还受歌德的影响。他写于1924年11月11日的爱情诗《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中,就曾引用歌德的诗句:“我欲紧紧地抱住伊,好把恋爱的苦恼来脱除;然若不能脱除这苦恼,则情愿死在伊的胸上!”⑧在德国的文坛上,青年歌德和席勒等人把感伤主义与反封建的热情相结合,形成文学上的“狂飙突进”运动。“浪漫的”在歌德他们那里是一个被肯定的概念。
张我军的浪漫主义情怀既表现在他的台湾新文学主张中,也显现在他的文学实践中。如果有人说,张我军的浪漫主义情怀是受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直接影响而不足以证明台湾文学的“浪漫派文学”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前的“乡土文学”就是浪漫情怀的文学,是对日据统治的抗争,是对“皇民化”的对立,是守根保族,追求“我”的生存书写。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文学”是对50年代“战斗文学”和“反共文学”的厌倦,是对政治神话——“反攻大陆”的遗弃,是一种自我生命和自我生存的追求,是对官方政治价值宰制的解构。此后的“现代主义”“多元化”的文学无不具有浪漫的特质。
二
台湾浪漫派文学如同台湾整体文学一样是复杂的,它的脉动是波状的,而且是多支的、忽明忽暗的。不管怎样表述,台湾浪漫派文学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在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的文学史书写中没有被建构出来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官方文艺主张的遏制。
台湾浪漫主义文学没有得到彰显,其重要原因应归结于国民党执政者对文学艺术及文化的遏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大方面进行改造,对文艺的统治更是铁腕式控制。其手段包括:(1)严管高压。1950年3月,蒋介石恢复总裁之职后,就成立了“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5月又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同时,严格统管传媒机构。(2)强化宣传。动用一切可宣传的资源和力量,进行反共复国宣传,提倡建立“三民主义新文化”。(3)怀柔利诱。“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在得到21.8万新台币的政府经费后,资助出书。例如:葛贤宁的《常驻峰的青春》、潘垒的《红河三部曲》等。当然,这些花费只是国民党政治利益的价值交换。同时,从1950年4月到12月,“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还“经常应征文艺创作部分,包括诗、歌词、曲谱、文艺论文、小说、鼓词、小调民谣、宣传画、漫画、木刻、平剧及地方剧、话剧、广播剧、电影剧本及本事,共计收到2 400多件,有700多万字,采用了400多件,有130多万字,皆得到稿酬的补助。举办征奖部分,包括歌词、歌曲、文艺论文、文艺讲演、小说、剧本各类,先后举办3次,共计收到应征稿1 400件,除曲谱、漫画等不计字数外,有280多万字,前后得奖者17人”⑨。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台湾一方之地,有如此之多的文艺种类,这么多数量,不能不说是掘其源力了。(4)高压威逼。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台湾人民和文艺界人士实行了最为恐怖的管制和约束,制定了各种条例,诸如“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戒严时期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戒严法”等等,这无疑使台湾人民原有的行动自由被禁锢,文艺人士和文化的自由被规矩,人权被摧残,尊严被践踏,“台湾的舆论严格地限在了国民党认可的范围内。在这样的情势之下,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地区只有完全随着国民党的意志打转了,而文化人尤其失去了应有的个性,得按张道藩定下的调子行动”⑩。在如此政治的、情感的、利益的、民族的、“以正义自居的”、“悲情的”怂恿和蛊惑之下,从者之多可想而之。政治文艺的主流话语的强势必然使得他者话语——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话语空间狭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权者总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施行其“反共文学”“战斗文学”的政治文学策略,愚弄民众,遏制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而这又可以视为大陆国民党时期对文艺和文化干预政策的延续,或者说是进一步强化。早在1942年,为对付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张道藩,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期间,于11月14日至17日以个人名义在《中央日报》连载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该文打着建设“三民主义”文学的旗帜,为加强国民党的文学和文化建设,提出了“六不要”与“五要”,其中有一条就明确指出,“不表现浪漫的情调”。张道藩认为“浪漫主义的形式不宜于我们的新文艺”。张道藩的言说表面看是他个人行为,其实不然,他是蒋介石的重臣,“十中全会”之后,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作为“政策”,不是个人行为的权限,只能是集团权力的代表者。该文在文化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梁实秋就强烈反驳。当然,同曲者也不乏其人,王集丛就是一例,是这一集团的不同角色的声音。王集丛在这一时期曾出版过《三民主义文学论》《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在《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一著中,他从五个方面探讨建设三民主义,即:从研究学习中建设三民主义文学;从实际行动中建设三民主义文学;从接受遗产中建设三民主义文学;从批判工作中建设三民主义文学;从政治领导中建设三民主义文学。王集丛与张道藩不同,王是学者应和当时的政治,是御用而已;张是文人从政,深谙政治,是政客级人物。“三民主义文学”旗号不是这时的张道藩才举起的,早在1929年6月,在国民党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就提出以“三民主义文艺”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何为“三民主义文艺”,从字面解即:民族、民权、民生的文艺。但如何有益于民族,建立民权,保证民生,和在何等程度上有益于民族,建立民权,保证民生,蒋介石的国民党无人阐释过,更没有人阐释清楚过。孙中山先生虽没有直接使用“三民主义文学”这一概念,或没有直接使用过“三民主义文艺”这一概念,但他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存在和发展,曾提出过如何发展文化事业。他说:
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
以故吾人深感现在之痛苦,预测将来之需要、从速设立一大印刷机关,诚不可谓非急务矣。果能成事,其利如左:
(一)凡关于宣传吾党之宗旨、主义者,如书籍、杂志等类,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制肘。
(二)本党常有价值券、褒奖状,以及各秘密文件、图籍等,均不必远托外国。
(三)本党自行编译各种新式教科书,以贡献于吾国教育界。
(四)国内各种有益于思想革新之著作,可以代印,并可改良告白,以益商业。
(五)仿有限公司办法,可为本党之一营利机关。
由上可见,蒋介石的“文艺政策”不同于孙中山先生的文化和文艺政策:一是为民而建设文化事业,一是为集团而建设文化事业;一是开放的,海纳百川的,一是防川的,堵流的。蒋介石的文艺政策和文化政策如同他的政治一样都偏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为集团服务,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
在长期的以集团利益为宗旨,只彰显一种声音的文艺政策之下,不论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还是在台湾执政期,特别是在台湾执政期,浪漫主义文学都不会有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有浪漫情怀的作家也只能以转义方式表达出来。当然台湾浪漫派文学得不到彰显和发展,官方文艺主张的遏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如现代派文学者的摒弃,学院派的批判,浪漫派自身的不给力等,这些都是原因。
注释:
①②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9页,第21页。
③朱立立:《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70-172页。
④张我军:《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⑤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第15-16页。
⑥张我军:《孙中山先生吊词》,《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⑦张我军:《仰望》《江湾即景》《赠友》,《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⑧张我军:《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⑨⑩王由青:《张道藩的文宦生涯》,团结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第370-371页。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5.005
2017-06-01
李伟(1974— ),女,副教授。
A
1673-0887(2017)05-0021-04
责任编辑: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