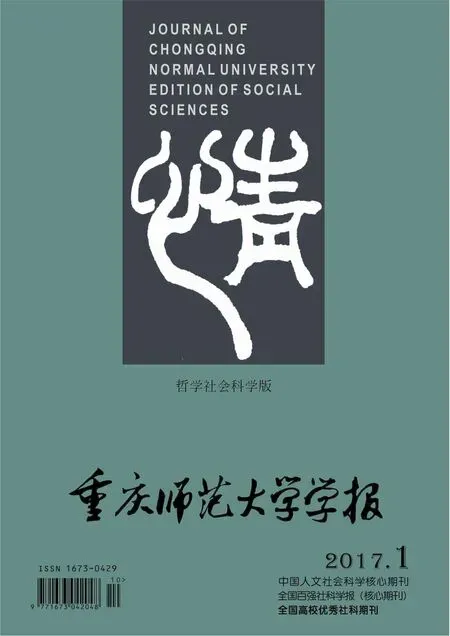从弗雷格的“涵义”到康德的“先验形式”
——试论语言现象统一的必然性基础
肖 福 平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从弗雷格的“涵义”到康德的“先验形式”
——试论语言现象统一的必然性基础
肖 福 平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在语言现象的经验中,我们常常将这种现象的存在统一视为其自身固有品质的表现而具有客观性的存在地位;弗雷格的语言分析注意到了语言现象经验中的相关常识论,提出了一种去心理主义的“涵义”观,并希望以此确立语言现象存在与统一的客观思想模式;弗雷格的“涵义”论揭示了语言现象经验的共同性基础,但这样的“揭示”并没有为“共同性基础”确立真正的源泉,我们只有从“涵义”思想的改造与回归先验哲学的进程中方可探知语言现象存在与统一的必然性基础,即语言现象世界的呈现与统一性特征决定于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决定于纯粹理性世界的语言存在原因。
语言;理性;涵义;先验形式
如果遵循康德哲学的先验论思想建构,我们就可以说:纯粹直观形式源自理性世界并决定表象世界的存在,表象存在的纯粹理性原因应该拥有一种先验形式的存在地位,所有关于表象呈现得以进行的直观形式和所有知识概念得以形成的知性形式都应该具有先验形式及其统一的源泉。换言之,自然世界的统一性源于理性存在的统一性,外在世界的差异性源于直观表象的差异性,外在对象的知识性区分源于知性概念的区别特征。至此,自然过程的统一与表象不可离开理性世界的先验认知形式,一旦这样的形式被贯彻到语言现象与自然物的经验中,它就不仅仅属于先验的存在,而且要造成关于这种纯粹形式存在的经验现实,或许我们对于这种先验形式的说明无法获取有效的经验证明,但我们却无法去怀疑经验现实与先验形式的合乎一致,否则,经验的现实就不会如此存在了。语言存在的现象世界就在这样的经验现实之中,语言现象的区分与统一、语言现象的经验发生与意义获取都要建立在先验语言形式存在的必然性基础之上。
一、语言现象经验中的“指称”与“涵义”
在语言现象经验的现实过程中,我们会面临语音的意义系统、文字的意义系统、句子的意义系统、篇章结构的意义系统,以及与此相关的宏观或微观层面的语言现象的意义系统,那么,作为个体或系统的语言现象为何具有了意义体系的存在呢?或许,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会选取一种常识性的答案:语言现象表达了“什么”,而且是表达了客观自然对象的“什么”,尽管这样的“什么”还没有直接地排除观念或思想内容的“什么”,但观念与思想只是作为一个中间的环节,其最终的决定还是指向了自然对象的“什么”,于是,语言现象作为意义系统的存在决定于客观的自然世界,即自然对象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一切语言现象之意义的来源之所,源于这样的常识性答案,我们所经验的语言现象,如“古树”,就成为了一种意义的载体,成为了语言现象中的一种意义单位,于是,与之关联的各个方面,如发音的经验过程、书写的经验过程、记忆和思考的经验过程,等等,都无一例外地朝向作为自然物的“古树”,并接受其意义确立的地位。然而,在这样的常识性答案中,我们却无法找到语言现象的意义单位与自然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不论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赋予,还是自然物的意义决定,两者的联系和统一缺乏一种必然性基础,即使在同一种自然语言现象里,一种符号或表述形式与一种自然客体或状态间的对应联系也非必然,更不用说那些存在于不同自然语言现象里的情况了。在我们的语言里,“古树”作为语言现象的意义载体(表意符号)对于自然对象的“古树”而言不是唯一的,具有相同意义载体的语言现象总是变化地存在着,并且只是惯例性地指向自然对象的“古树”,任何必然性关系的确立对于自然物而言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断言:是客观自然对象建立了由其自身到语言现象的必然联系和意义的赋予。如果这样的断言不容置疑,语言现象及其意义体系的存在就会完全地归属于自然世界的创造,成为自然决定的语言现象,显然,这样的结果有违于我们的语言现象经验实际。倘如我们将这样的情况扩大到多种自然语言之间,语言现象与自然对象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难以确定。所以,在面临某种自然对象与某种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存在时,它应该是一种被规定的、外在的、惯例性的和偶然性的关系。同语言现象的存在情况一样,自然对象的存在也是变化不定的。在两种流变的现象里,如果双方在认知层面的关系确立没有问题,那任何一方的意义赋予就仅仅是一种相互配置的规定结果,一种外在经验过程的偶然性对应关系的产生,既然是如此对应关系的产生,那它所涉及的就只能是一种经验意义上的相对关系。于是,这种关系下的意义源泉或有效性根本不涉及双方本身是什么的问题,也不涉及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以拥有关于语言现象和自然现象的经验,也可以拥有关于两者对应关系的经验,但我们并未在经验的对象那里获取任何关于“语言现象的意义决定于自然物”的必然性根据,为此,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整体的世界或全部的世界里只有语言现象和自然物,那么,语言现象该是什么呢?自然物又该是什么呢?两者的关系与意义决定又如何呢?对于这样问题也许只有上帝才会知道。长期以来,一些语言哲学或语言学的研究者不断地探寻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在语言现象的符号与自然物对象之间构建一种整齐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发现某种标准的语言现象工具来实现关于自然世界的无歧义描述,如果这样的标准工具存在,那关于自然世界的图式应该就是某种使用语言现象的编码图式,那关于自然世界的逻辑形式应该就是某种关于语言现象的逻辑形式,反之亦然。在弗雷格看来,要获取这种语言编码图式或逻辑形式的表达,数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借鉴,即它们的表达形式相当于数学的函数式f(x),一种具有所有真值可能性但又不具备真值现实的函数形式。在这里,f(x)的真值现实体现在语言现象的层面(自然语言),体现在有关专名、概念词、句子等的使用过程中,尤其以句子的形式最为典型,如果以“那棵古树长在深山里”为例,那我们可以说,关于语言现象的函数式f(x)成为了具有真值表达的句子,任选项x(自变量)以专名或概念词的形式同谓词f结合在了一起,那么,在我们取得具有真值判定结果的语言现象的句子时,我们是否可以在语言现象之内来完成这样的真值判定呢?当然,语言现象不能提供这样的标准,具体而言,我们不能从句子的“古树”、“长在深山里”来判定句子的真值,句子的真值存在应该不同于语言现象的层次。弗雷格认为,作为语言现象的句子之真值是建立在意义(Meaning)层面之上的,而意义层面则相当于语言现象所指称的对象世界,所以,句子的真值最终决定于语言现象所指称的对象(objects),其结果又回到了上文所讨论的常识性答案之上。显然,弗雷格没有满足于如此的分析结果,因为他知道,从语言现象的层面到其意义的层面不能仅仅是一种外在对应配置的关系,更涉及一种决定这种对应关系的本原体存在。因此,在提出“意义”概念的同时,他又提出了“涵义”(Sense)的概念。许多学者将它直接解释为“思想”,或者,句子的涵义就是句子思想,其过程可以表示为:句子→思想→真值,至于说“涵义”究竟是什么,弗雷格在《论涵义和意义》一文中并未提供明确的定义或说明,只是到了《思想》(1918)一文,“涵义”的讨论才被加以了关注。如果说“涵义”就是思想,那思想就是我们“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1]112。或者说,“涵义”的存在带来了关于语言现象的意义呈现和真值判断,只有依靠这样的“涵义”,语言现象的不同表达单位才会成为意义的载体,自然世界的对象才会进入语言现象的意义层面,建立语言现象与自然世界的对应联系才会具备作为第三方存在的决定根据。当然,“涵义”在弗雷格的分析里只是作为了某种衡量“真”的标准或工具,只是作为了某种客观思想的存在而区别于语言现象和自然物,于是,它远非“真”的本身,远非思想的承载者本身(弗雷格并不承认任何关于思想的承载者),或者说,一旦发生了关于“真”之判定的思想借用情况,思想的标准就不应该扮演一种终极的角色,而只可被视为某种结果的应用,那么,产生这种思想结果的原因根据又该是什么呢?
二、语言现象统一的必然性与“涵义”启示
在论及“涵义”或思想时,弗雷格已经触及到了语言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问题。由于两种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远非现象自身可以提供或加以决定的,于是,他在语言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提出了“涵义”的存在,其实质就是要指出:不论是语言对象层面的现象,还是自然对象层面的现象,它们都是关于“涵义”或思想的呈现,都是关于“涵义”或思想作用的成果,至此,“涵义”或许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涵义”在现象间的联系过程中或许提供着某种必然性的基础。倘如“涵义”的作者要将它确立为没有任何承载者的客观思想存在,或将它确立为某种“既不是外界的事物,也不是表象”[1]127的存在,那“涵义”就应该归属于它自身所是的存在,并且在本质上区别于语言现象或自然对象的系列。同时,“涵义”的存在也应该成为语言现象与自然世界之规定和联系的真正源泉,所有关于语言现象和自然世界知识及意义的断言都应该源于“涵义”之“真”的标准,当然,这样的“涵义”已经超越了它的弗雷格之意。如果我们能够对“涵义”的问题进行拓展,而不仅仅是弗雷格的“思想”之路,那“涵义”的自身所是就会突破“思想”作为判断标准的地位而凸现自身作为世界统一的根据地位。也可以说,只有当“涵义”突破弗雷格的“客观思想”之域而拥有世界统一的根据时,它方可称得上“考虑真的东西”的标准,而且,这样的标准也不可能属于外在世界的东西或类似于某种被动的镜面之物。在“涵义”被弗雷格赋予“考虑真的东西”之时,它就应该具有“真”的标准或“真”的模式。由此下去,“涵义”简直就成为了“真”的源泉,一切关于语言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存在和联系判定就成为了“涵义”存在及其统一的经验必然,于是,关于“涵义”的定义应该是一个可以加以说明的问题。然而,令人有点困惑的是:在弗雷格提出了“涵义”问题,并指出了“涵义”就是无需任何承载者的“思想”、就是“借以考虑真的东西”之后,他并没有将“涵义”的讨论联系到一个更为基础、更为纯粹的地位上进行,也没有将“涵义”与“意义”作为同样重要的语言现象分析层面来加以讨论。不论是在“句子→句子的思想→句子的真值”的过程,还是在“专名→思想的一部分→对象”的过程,或者在“概念词→思想的一部份→概念”的过程,弗雷格分析的起点是“句子”“专名”或“概念词”,即起始于语言现象的存在。而分析的完成则要建立在后两个步骤或层面上,第一个步骤归属于他的“涵义”,第二个步骤归属于他的“意义”,两个步骤的分析将会使我们产生关于语言现象的“涵义”和“意义”理论建构的期待,并以此揭示语言现象与自然世界联系的必然基础。但是,在相关的两篇重要论文《论涵义和意义》与《思想》里,我们未能发现“涵义”理论的建立,即使在《思想》中提及“涵义”之时,作者也是出于讨论“意义”的需要来进行的。可以说,文章中只有一个中心,即“意义”中心。实际上,语言现象分析的两个步骤或层面就是围绕“意义”来进行的,“意义”层面的“真”“对象”“概念词”成为了作者反复提及和论证的问题。其中,“对象”(object)更是起到了“真值”决定的最后环节,“逻辑的基本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划归为这种关系”[2]122。于是,语言现象(句子、专名等)意义的决定又回到了自然世界(对象)上,回到了两者联系的现实经验层面,而关于两者联系统一的某种必然性基础并未通过“涵义”问题的提出而获得解决,或者说,在“涵义”面对语言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对应中,“涵义”作为意义可能的“思想”未能确立自身的必然性地位。显然,要将“涵义”建立为某种公共的、客观的、无需任何承载者的“思想”模式或标准就是要确立某种先验的形而上的智性存在,并使之能够提供一切关于语言现象与自然对象联系的必然性基础,即某种理性世界的“高级而纯粹”的基础。然而,对于弗雷格这样的语言分析哲学家而言,确立这样的基础存在就等于添加无必要的“实体”,就等于做出了无必要的“本体论”承诺,这样的“添加”或“承诺”不仅无助于语言分析的过程,更是有悖于解构本体存在的语言分析宗旨。所以,“‘涵义’是什么”尽管成为了弗雷格所关注的问题,并且被明确地加以提出,但关于该问题的答案却并未被提供,更不要说关于“涵义”理论的建立了。
既然如此,“涵义”在语言现象(句子)的分析中出现又能为我们揭示什么呢?不可否认,在从语言现象到其意义层面的联系里,即:句子→思想→真值,作为思想层面的“涵义”仅仅是一个“中介”,而不是一个“中心”,这样的“中介”只能揭示作者在进行语言现象的“涵义与意义”的分析中意识到了某种“第三方”存在的问题,即某种关于语言现象与自然世界如此存在和统一的原因根据问题,所以,“涵义”更多地表明“意识”发生和呈现的“给定方式”[3]66,而非“意识”的内容建构。其次,“涵义”的出现与康德的影响不无关系。弗雷格在创建自己的语言哲学王国时潜心研究过莱布尼茨和康德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后者的先验哲学与逻辑思想,应该说,弗雷格深受莱布尼茨的“普遍语言”论和康德的先验逻辑(纯粹形式逻辑)论的启示,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孜孜不倦地追寻某种理想的语言形式存在,这样的理想语言形式不仅要成为全部语言现象的普遍逻辑形式,而且要等同于全部自然现象存在的普遍逻辑形式。那么,这样的理想语言形式不可能由自然语言(语言现象)提供,更不可能由自然现象提供,它必须建立在某种具备客观性和必然性基础的存在之上,而这样的基础应该联系于康德的先验逻辑及其先验形式的存在,尽管弗雷格的语言哲学理论使用了“涵义”或“客观思想”而没有认可康德的先验形式存在。再者,不论是“涵义”也好,还是“客观思想”也好,它们仅仅是作为了一种语言现象分析中所涉及的意义判定“依据”而提出,至于说该“依据”的出处、形成和有效性地位,弗雷格对此并未提供实质性的添加,以至于语言现象的任何真值决定完全可以绕开“涵义”的环节而回到“经验对象”的最终存在上来,所以,当语言哲学发展到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涵义”就成为了一种多余而被断然地加以了拒绝。至此,在语言现象世界及其与自然世界的统一问题上,弗雷格的“涵义”并未带来关于这种统一的任何必然性基础。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分析所指向的是关于语言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事实,以及两者联系的经验事实,而非追问这种“事实”存在的必然性基础。结果,人们经历“涵义”后所获得的仍然是语言现象意义决定于自然现象的答案,并且,语言现象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仍然缺少同一性的基础和源泉,那么,两者可以体现同一性关系的基础和联系的源泉又会在哪里呢?
在我们面对语言哲学的分析过程时,我们不可离开语言现象的存在事实,只有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才开始了关于语言现象的句法分析、意义索源、真值决定,等等。从此,语言现象作为知识的对象体系才逐渐地被建立和完善起来,其构成的所有部分才成为了意义显现和规范的载体,并最终取得具备真值结果的语言现象的表现形式。当然,语言现象的“事实”不论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存在,还是作为意义载体的存在,它都决不会是一个可以“自在”或“自显”的对象,或者说,语言现象的经验“事实”不是关于其自身作为经验对象存在的表现结果,而应该是被“理性主体”所构建的“第二自然”结果,所以,任何从语言现象的“事实”中去寻找这种“事实”的根据都将是没有结果的。在语言现象的世界中,人们尽管可以把经验纷繁的语言个体对象,以及将自然因果关系体现到纷繁语言现象的联系之中,但语言现象的对象地位始终未能离开“理性主体”的决定与构建过程,不论这样的“构建”是否已经完成,也不论这样的“构建”多么地远离我们而具有自然对象的属性,一旦语言现象的“事实”存在无可争议,作为“理性主体”的存在地位就应该明白无误地加以确立,否则,关于语言现象的一切经验与知识性构建就会变得什么也不是,更不用说去获得语言现象、自然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联系与统一。可以说,在弗雷格的“涵义”或“思想”之外,作为“第三方”的存在就应该明确为创造了语言现象的理性主体,理性主体的存在为现象世界,包括语言现象,提供着最后的源泉或根据,哲学家康德将这样的源泉或根据称之为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那么,不论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存在与统一,还是关于语言现象的存在与统一,它们所依照的并非某种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是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基础。
在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里,理性的先验形式就是一种“自明”的存在,只要我们面对了现象世界的呈现,我们就必然地面对了作为现象基础的“自明”存在,尽管这样的“面对自明”还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发生。在我们经验语言现象、认识语言现象和联系语言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面对语言现象的事实,面对语言现象作为认知对象的事实,而不是面对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存在不仅仅涉及语言现象经验过程的事实,更涉及如此语言现象产生的理性主体原因根据。于是,语言存在关系到语言现象的事实,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这样的事实,或者说,所有依据语言现象经验和语言现象内容的知识,如语音知识、语法知识、语义知识、语用知识,等等,它们可以作为语言经验的认知成果,也可以作为语言现象存在的事实说明,但它们却无法作为对语言存在的完全经验的证实。在常识性的理解中,语言的存在惯例性地被归属为了语言现象的事实,以至于语言现象被视为了语言存在的全部,被视为了语言存在的最后家园,然而,这样的“家园”并未因为语言学家们的辛勤劳作而可靠起来,人们对于这种家园的最后的希冀总会缺少允诺。因此,语言存在问题的揭示既是一个语言现象经验的过程,又是一个回归其自身所在的过程,前者为人们展现语言现象的知识,后者为人们确立语言现象形成的纯粹基础,即作为理性之先验语言形式的基础。
三、语言存在的现象世界与理性的先验“家园”
在语言存在问题探究的先验哲学视野下,我们唯有确立语言现象的先验理性形式根据,关于语言现象的知识才会是可能的、才会是真正属于我们而成为认知的对象世界。或者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认知语言现象、拥有语言存在的经验现实,只是因为我们作为了理性的存在、拥有了关于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原因。不管理性存在的先验语言形式如何地具备其自身的纯粹性特征,也不管它是否可以被加以描述或指称、以及是否可以等同于语言现象的经验特征,它的存在应该是产生语言现象和认知语言现象的前提。只有基于这样的前提,所有关于语言现象的经验现实方可真正地成为理性存在的现实,并呈现为合乎理性之先验形式规定的现象特征,否则,语言现象就会什么也不是,更不用说那些关于语言现象的常识性答案了。所以,语言的存在源自于自然世界或自然语言现象的结论只能是作为一种语言“物化”的假象,其真正的“家园”还是理性存在的先验语言形式。依据语言存在的理性“家园”,先验语言形式在理性存在过程中的地位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关于语言现象的创造,其二,关于语言现象的认知可能。
第一个方面强调理性之先验语言形式并非就是语言现象的事实,先验语言形式因为自身的纯粹性而区别于任何经验过程的语言现象,即:它带来了语言现象存在的系列,但它又不在这样的现象系列之中,一切关于现象世界的自然因果律或时空特征的描述对于它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理性有与现象相关的原因性,那么,理性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力,结果的经验性序列的感性条件才首先开始了”[4]465。它应该是一个纯粹理性世界的智性源泉、一种可能提供所有语言现象之根据的理性能力,这样的纯粹源泉和能力因为理性存在的“自明”而被加以确立,并因为理性的“实践性”而创造语言现象的经验世界。所以,语言现象中的成分表现、要素关联、意义决定、整体统一,等等,它们无一不是在贯彻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的规定。倘如我们依据先验哲学的基本思想将这样的先验语言形式标识为纯粹的理念形式、纯粹的知性概念形式和纯粹的感性形式,那么,对于作为有限理性存在的人类而言,先验语言形式就成为了语言存在中的绝对之在和自由之在,就成为了某种纯粹的可能性原因。这样纯粹的“语言”之因不应该内在于自身而不外显,它必然地跟随着理性实践的召唤而规定着语言经验过程中的创造,其结果就是带来语言现象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当然,这样的结果决不是关于语言存在的纯粹理念形式、纯粹知性形式和纯粹感性形式的经验对象化,或者说,语言现象的经验过程无法延伸到语言存在的纯粹世界,对于先验语言形式存在的“认知”永远是一个人类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否则,语言的存在又会被等同于语言现象而脱离于理性的家园,从而违背语言现象的可认知限制,并引起语言现象何以被认知的无穷困境。因此,在说明语言现象的产生原因时,我们其实是在面对自身存在过程的创造,即面对理性存在的语言现象的创造,不论该创造的结果(语言现象)是否完备,也不论它处于何种阶段,它的产生出现总是要合乎其先验形式的规定,任何逃逸这种规定的语言现象都将是不可能的。那么,语言现象的表现特征,如关联性、规律性、统一性、真假性等,都只能是作为理性存在之先验语言形式的现实体现和反映。显然,在我们经验语言现象之时,我们常常说某个语言现象的个体或单位表达了某个概念或某种意义,即使这样的概念或意义仅仅属于心理经验的层面,语言现象的表达可能性和现实性只有在语言现象作为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的实践成果(先验语言形式条件下的创造成果)时才能存在,否则,语言现象对于概念或意义的表达就会缺失必然性的统一基础,只有源于先验语言形式之规定的理性统一与创造能力,语言现象的经验过程才能通达概念与意义的层面,才能回到语言存在的纯粹根据、回到语言现象何以可能的原因所在。所以,不论语言现象在“自然语言”的定义中如何变得远离理性主体,以及如何变得“客观”而对立于认知主体,语言现象终归还要秉承理性的先验形式规定而作为理性存在的创造性成果。
第二个方面强调先验语言形式基础作为语言现象认知可能与现实的根本前提,即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类所拥有的语言现象知识,如语音的知识、符号的知识、语法的知识,以及关于语言知识系统的划分知识等等,都只能是作为合乎其先验形式规定的经验发生与判定结果。就语音的知识而言,它可以被展开为如何发音的知识、如何标记语音的知识、如何形成语音组合规律的知识等等,不论是作为具备自然物理性质的声音,还是作为描写这种“声音”所使用的符号系统,它们都在语言行为者的经验中奠基于理性主体的先验语言形式,并使之本质地区别于一切外在的过程和内容。在这样的语音知识里,不管我们是在模仿什么,还是在书写什么,以及在发现什么,我们总会说“知道”,总会在经验的意义上明白语音的定义、语音的符号和语音的规律等等,语音的知识就是关于这种“知道”与“明白”的内容。至于说语音的方方面面何以被认知,这与语音的方方面面是否成为了经验的直观对象相关,即一定要表现为某种关于空间中的占据和时间里的持存,只有如此,理性的纯粹时空形式才会具备经验对象的映照,作为语音的方方面面才能被呈现或表象,才能进入关于语音的先验综合过程而取得关于语音的概念与知识。所以,在语音的认知过程中,与其说我们在认知语音的知识,不如说我们在展示自己认知语音的固有先验语音模式。当然,这里的先验语音模式归属于上文的先验语言形式,它既涉及先验的感性模式,又涉及先验的知性模式和理性模式,而且,它就是本文所关注的那个语言现象得以被经验和被创造的先验模式。于是,形成任何语言现象的知识并非是我们认识了某种异己或外在的对象,而是我们认识了语言现象的存在基础与先验语言形式的相通性和一致性。而且,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关于语言现象的知识在我们人类这里才具备了形成和统一的前提,作为“第二自然”的语言现象才会在“是什么”的意义上取得真正普遍性地位的判定。在语言现象作为理性存在过程或人的存在过程的必然现实之时,从语言现象回归其先验形式之路应该是相通的,语言现象“也是通过纯粹理性产生”[5]184,任何的否定则会导致语言现象存在的消失(没有“相通”就无法承认语言现象“直观”的发生),这样的结果有悖于语言现象经验过程的现实。 显然,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语言(现象)是什么”的无穷经验过程,享受语言现象世界的宏大、奇妙、有序、变换与意义, 但我们却一点也不能享受那些无法被直观、无法作为我们的经验对象的语言存在(倘如我们还可以称之为语言存在的话)。所以,语言现象与其先验形式的相通无疑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情形:语言现象一定是作为我们经验直观对象的存在,其如此呈现的根据必然联系于理性之先验语言形式的存在。尽管语言现象的“是什么”判断总是被限制在经验直观的世界之中发生,但这样的限制却丝毫不会影响相通性的存在,从经验直观到其纯粹直观形式、从纯粹直观形式到其纯粹知性形式,以及纯粹理性形式的进程都应该是相通的。不仅如此,语言现象与其先验形式既是相通的,又是一致的,语言现象与其先验理性形式的一致性区别于它作为知识存在的一致性。我们拥有关于语言现象的知识,可我们并不拥有关于先验语言形式的知识,所以,这里的“一致”体现为语言现象对于其先验形式规定和要求的完全贯彻、合乎与响应,体现为语言现象无一例外地归属于理性之先验语言形式的存在结果,体现为现象世界的语言知识统一缘起于纯粹理性的形式统一的关系存在。总之,只有我们立于了两者之间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关系,关于语言现象的知识才具备了真正的意义存在,即语言的现象关系和呈现事实在于拥有其决定根据或理性的先验形式存在。在理性存在的世界里,语言现象的知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一切关于语言现象的分析与综合,一切关于语言现象的思想与探寻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从现象到本质的“返回”,一种关于语言存在的寻根之旅,其主体只能是理性的存在或人类自身。所以,任何关于语言存在问题的澄清必然联系到关于理性存在或人的问题的澄清,那种将语言存在问题仅仅归属于语言现象问题的研究只能导致语言实践的结果凸显而忽略关于这种结果的理性根据或原因追问,并且,这种研究所能取得的成果除了作为一种有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认识成果之外,它无法带来关于语言存在探寻的真正统一性和全面性基础,只要我们置身于语言现象的世界里,只要我们将语言现象视为语言存在的全部,那语言存在模式或决定根据就会变得纷繁复杂,处于流变之中而难以确定,更不用说去寻觅语言存在的统一性原因。所以,纵使有无数的语言研究者能够提出无数的语言学理论和规律发现,操控语言存在之路对于他们而言依然是那么遥远和困难,除非他们能够回归语言存在的理性世界。
总之,在语言现象及其统一的必然性基础问题上,如果我们可以从弗雷格的“涵义”思想中获得其拓展和通向康德的先验分析之路,我们就可以说:“涵义”作为一种在语言哲学中被讨论的“客观思想”已经具备了将语言现象及其意义源泉联系于语言行为者的可能趋势,只是弗雷格因为自己的“心理主义”考虑而要将这样的“涵义”客观化。在“涵义”被弗雷格阐释为“客观思想”时,他是无法回避“涵义”作为语言现象存在的产生性模式的,这样的产生性模式不可能因为它的客观与普遍性地位赋予就能同语言行为者的主体性世界区分开来。只要我们将“涵义”及其产生性模式回归到它应该所是的位置,这样的“位置”只能属于语言行为者的世界。如果我们将语言现象及其统一的必然性基础同“涵义”及其“客观思想”联系起来,那“涵义”的“客观”与“普遍”之意就应该是语言行为者作为理性主体存在所共同拥有的语言存在模式,即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不论是涉及语言现象经验的感性阶段,还是涉及其知性阶段,作为先验形式存在的语言基础总是在提供着一种产生语言表象世界中的统一性和区分性特征的纯粹理性原因,所有关于语言现象世界的区分、综合与统一在于理性主体的先验语言形式。简而言之,同自然世界的情形一样,语言现象世界的统一性源于理性存在的统一性,其具体语言现象内容的差异性源于直观表象的差异性,其定义的区别性特征源于知性概念的区别特征。至此,先验认识论提供着这样的前提:自然过程的表象与统一不可离开我们所具有的先验认知模式,一旦这样的模式被贯彻到语言现象与自然物的经验中,它就不仅仅属于理性的先验存在形式,而且带来了关于这种纯粹形式存在的经验现实。当然,语言存在的现象世界就在这样的经验现实之中,语言现象世界的区分与统一、经验直观与概念综合同样要源于理性的先验语言认知模式或先验语言形式的存在。
[1] 弗雷格.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集[G]. 王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王路. 逻辑与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肖福平,肖绍明.走进语言哲学[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4]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t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33.
[5] Heidegger.TheEssenceofHumanFreedom[M]. trans. Ted Sadler. London, 2002.
[责任编辑:刘力]
On Necessary Foundation of Language Phenomenon and Its Unity
Xiao F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ing language phenomenon, we often take the phenomenon and its unity as its inherent quality, and has the status of objectivity; Frege’s language analysis notes the relevant knowledge in his language philosophy theor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sense” for getting rid of psychologism, and hope to establish the objective model of language phenomenon’s existence and unity; Frege’s concept of “sense” reveals the common basis for experiencing language phenomenon, but such “reveal” has not establish the real source for “common basis”, only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nse” and the returning to the thought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can we ascertain the necessary basis of the being and the unity, i.e. the whole world of phenomenon and its unity has been decided by the rational being and its form a priori, including pure language form a priori.
language; reason; sense; transcendental form
2016-09-20
肖福平(1962-),男,重庆璧山人,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语言哲学研究。
IH0-0
A
1673—0429(2017)01—007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