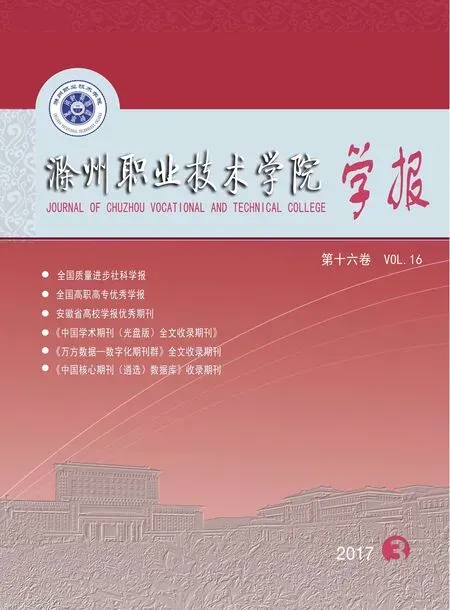“读者因素”对译者的影响
——以《呼啸山庄》伍译本为例
刘嵘
(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 合肥,230601)
“读者因素”对译者的影响
——以《呼啸山庄》伍译本为例
刘嵘
(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 合肥,230601)
聚焦《呼啸山庄》的伍译本,从翻译的历史性出发,以描写性的手法从三个维度来考察该译本,从而加深译界对伍光建翻译策略及翻译伦理的理解和认识。研究的结果表明:伍光建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始终心系读者,极为重视民国时期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读者因素”对其策略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伍光建;《呼啸山庄》;翻译;“读者因素”
1930年伍光建译的《狭路冤家》,作为《呼啸山庄》的首译,只在为数不多的文章中稍有提及,却没有深入细致的系统性分析,这与伍光建“翻译界之圣手”的地位以及这部作品在文学界的影响力是极不相称的,其价值亟待学界发现。笔者将弥补以往此类研究中的不足,聚焦《呼啸山庄》的伍译本,从翻译的历史性出发,以描写性的手法从多个维度考察该译本,分析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民国时期,译本如何作为第三空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从而加深对伍光建翻译策略及翻译伦理的理解和认识,以期为勃朗特姐妹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节译或是全译?
节译一直被公认为是伍光建译著的最大特色,从《侠隐记》到《孤女飘零记》,在自然景物和人物心理描写上都有所节缩。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笔者对《呼啸山庄》的伍译本与原著进行了仔细的对比阅读后发现:伍光建在译《呼啸山庄》这部作品时采用的是全译法,并未对原文有任何的删节或改写。同一译者针对不同的文本,为何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呢?
《呼啸山庄》自出版后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奇特的小说”。它的“奥秘莫测”不仅与它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主义有关,更体现于它别具一格的叙事技巧:由若干叙事层面构成的嵌套式叙事结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主要是通过洛克伍德和奈莉两人之口,尤其是奈莉之口,在读者面前完整地呈现了男女主人公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以及两个家族的兴衰变迁。故事的两位主要叙述人都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洛克伍德是位局外人,而关键的叙事人奈莉也只是故事的目击者、见证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边缘人物。他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回顾往事时,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故事的,叙述人站在故事的边缘讲故事,只能忠实地记录自己观察到的东西,或偶尔在叙述中掺杂一点自己的议论或看法,却不能直接去揭示故事中主人公的内心隐秘或波澜,否则故事的客观性及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因此,《呼啸山庄》中不仅缺失人物的内心独白,甚至连用来烘托人物心境的景物描写也难得一见。正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无法站出来直接向读者披露他们的真实想法,叙述人则倚赖大量的人物对白,尤其是主人公的直接话语来展示他们的情感世界,从而使读者接近故事的中心并身临其境地感受小说激烈的情感以及暴风骤雨式的情节变化。可见,该小说所呈现出的心理及景物描写几近空白、而人物对话极其丰富的特点是由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决定的。
与《呼啸山庄》不同,在《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让小说的主人公简·爱担当唯一的叙述人,自始至终她一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典型的以小说主人公的眼光而发起的第一人称叙事。这种叙事方式无疑拉近了读者与故事的距离,因为叙事人在叙事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向读者敞开心扉。因此,内心独白和自我剖析在这部作品中随处可见。此外,作者在景物描写上也不吝笔墨,例如,为了烘托简·爱被求婚前曼妙喜悦的心情,她在第二十三章的开头即用了四大段,共计427个单词描绘了盛夏时节桑菲尔德花园黄昏时分的怡人景色。在《简·爱》的伍译本中,研究者发现,原著中多处的心理及景物描写被省略、压缩或提炼。这与伍光建在许多其它译作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并无二致。而他在翻译《呼啸山庄》时却忠于原文,并未进行多少节译。这种差异由何而生?作为民国时期享有盛誉的翻译家,其翻译策略的确定决非偶然或随意选择的结果。茅盾在论述伍译的特点时曾说道:“他的删节很有分寸,务求不损伤原书的精彩。”[1]翻译西洋名著时,虽然他对长篇累牍的景物及心理描写常做删削,但对展现人物个性和情节发展的文句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予以保留的。《呼啸山庄》这部小说情节紧凑,动作性强,人物对话比比皆是,而心理及景物描写屈指可数。如果对这样一部小说进行大刀阔斧的删节,恐怕会伤及原作的精髓并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妨碍读者的理解。那么,伍光建为何对《简·爱》采取节译呢?清末民初,80%以上的国民不识字,教育水平极其落后。由于文化水平和欣赏能力的限制,民国时期的“一般读者”阅读小说时最关心的就是“意思”和故事,并无多少耐心或兴趣去品味原文本中那细腻入微的心理或景物刻画,更谈不上理解其中所包含的隐喻意义了。所以,他有原则的节译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从而达到迅速有效地推广西方文化、唤醒民众的目的。节译也好,全译也罢,伍光建并非盲目而为,其翻译策略的抉择充分体现了他“靠近读者”的翻译伦理,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有其积极的意义。
二、白话或是文言?
伍光建译出的西洋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点:译本全都使用白话文,而且读来通俗易懂、流畅自然。笔者从《呼啸山庄》的伍译本中摘抄了以下五例:例1:“我很晓得你不喜欢她!”[2]100;例 2:“......,你胆敢想我是坏人,我真想让希斯克利夫打你,打到你害病!”[2]103;例 3:“这是一个闷热天,并无太阳,天色昏暗,快要落雨。”[2]234;例4:“我昨天晚上在山庄的花园有六点钟之久,…….。”[2]136;例5:“希斯克利夫捉牢她的膀子,放在自己膀子之下,……。”[2]264尽管伍译的部分词汇(如以上例子中的“晓得”、“害病”、“落雨”、“六点钟”和“膀子”)在现代书面语中已不大通行,有拗口过时之嫌,但他用的白话还是贴近当时普通大众的日常口语的,其时代进步意义不言而喻。清末民初,国家已至生死存亡之关头,白话由于具有言文一致、浅近俚俗等优点,比“曲高和寡”的文言更能担当起普及教育进而焕发全体民力的历史重任。
尽管白话取代文言顺应了社会现代转型的大趋势,但二三十年代,“文白之争”绵延不绝,文言与白话并举成了普遍现象。伍光建始终坚持用白话翻译西洋小说。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擅长写白话,恰恰相反,这位学贯中西的翻译家不仅因留洋而精通外语,其国学素养也相当深厚。学界关注的焦点多半集中于伍译的白话小说,殊不知,他以文言译出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比如:1910年编译的《西史纪要》第一卷、1918年《西史纪要》第二卷、1925年译的《霸术》、1929年的《伦理学》、1930年的《人之悟性论》及1931年《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等。这些译著读来典雅凝练,文采斐然,充分展示了译者精深的古文造诣。耐人寻味的是,面对不同体裁的文本,这位翻译大家为何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很明显,伍光建灵活应变的译法并非为了炫人眼目,究其根源还是出于对受众的考虑。与历史哲学类专著不同,小说是一种颇为“亲民”的文学样式。与其它文体相比,小说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所以早在清末年间,小说就被当作改良"群治"的政治工具而备受重视。那么,为了保证小说的社会功效,通俗的白话便成了不二之选。这也正是伍光建用白话译小说的初衷所在。而史哲类书籍严肃深奥、艰深晦涩、可读性不强,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不可否认,它的受众面非常有限,潜在的读者群也仅囿于高雅层次——文人达士或专业人才。与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的老百姓不同,这些社会精英们身居高位,足以左右政局,他们渴望研读此类西书以了解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西为中用、变革中国的目的。除了本身就具有较强的阅读动机之外,伍光建笔下那优美独特的古文消解了他们的隔阂与拒绝,愈发刺激了他们的阅读欲望,对于那批“嗜好渊雅古文”的传统士大夫们来说尤为如此。可见,伍光建对不同文体的潜在读者群有着精确的定位。文言也好,白话也罢,都是他反复斟酌之后做出的策略抉择。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他始终心系读者,极为重视读者的接受能力,因为他深知:译文只有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经验,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进而更有效地为社会服务。
三、欧化或是归还?
清末民初,从文言向白话的转换过程中,西方语言对汉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来语的引入对汉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翻译小说出现过因语言“畸形欧化”而令人难以卒读的情况。
纵观二三十年代的翻译和创作实践,非驴非马的白话文随处可见,多半都是由句法层面的欧化引起的。以梁实秋为代表的多位译家就曾多次撰文批评鲁迅的“硬译”,认为他置汉语的自身规律于不顾,一味地引入、效仿西洋的句式和文法,结果译出来的文字让人难以下咽,“生涩难懂,佶屈聱牙的紧”[3]。林语堂也认为句法是一个语法体系中最核心、最稳定、最不容易变化的部分,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主张“欧化之大部分工作在词汇,若语法乃极不易欧化,而且不能句句皆欧化也。”[4]
欧化语与汉语的语感有着相当的距离,最终因‘不顺'被淘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可它对当时的知识界影响深远,甚至一度成了书面语的主流,巴金、鲁迅、冰心、陈西滢等的作品中都有不少欧化的用法。难能可贵的是,伍光建并没有随波逐流。胡适于1928年给友人的信中曾指出:“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认为伍昭扆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十二册,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谨严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他。”[5]近现代的评论家在谈及伍译时,都一致公认其翻译风格清新脱俗,语言地道自然,毫无翻译腔。遗憾的是,这一观点普遍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笔者将采用描述研究的方法,分别从《呼啸山庄》的伍光建译本和杨苡译本中收集具有代表性的实例,通过逐一对比来凸显伍译的语言特色。
(一)“被”字句
They had invited them to spend the morrowat Wuthering Heights,and the invitation had been accepted,……[6]48
他们已经邀请小林惇兄妹第二天来呼啸山庄,这邀请已被接受了,……(杨译)[7]36
他们曾请林顿一家明天来玩一天,他们答应来…(伍译)[2]48
汉语中,用来表示被动的词并不少见,除了“被”字以外,口语中更常用的有“叫”、“让”、“给”、“为”、“挨”等,正式的书面语中还有“将”、“于”和“为……所”等。有趣的是,不少译者但凡看见“系动词+动词的过去分词”的结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它一下。“被”字逐渐成为了被动语态的标志词,被视作英语被动式的最佳对等表达,不能不说是语言欧化的结果。其实,按照汉语的传统表达习惯,“被”字通常含有消极的色彩,一般表示遭遇灾难或不幸,比如“被踩了脚”、“被车撞了”等,后来在西语影响下才突破了这种局限,开始被赋予了中性甚至正面的涵义。和杨译相比,伍译的高明之处在于译笔灵活。伍光建在忠于原文内容的前提下,不为西洋文法所束缚,这一点从他对被动式的变通处理中可见一斑。他并不似杨苡那般对原文文法亦步亦趋,而是在译文中补出了“行为者”,改被动为主动,这样一来译文的可读性就大大提升了,也更贴近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二)长定语
He was,and is yet,most likely,the wearisomest,self-righteous pharisee that ever ransacked a Bible to rake the promises to himself and fling the curses on his neighbours.[6]36
他过去是,现在八成还是,翻遍圣经都难找出来的,一个把恩赐都归于自己、把诅咒都丢给邻人的最讨厌的、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杨译)[7]28
他从前是,大约现在还是一个最令人憎厌的,自以为是正人的伪君子,搜遍《圣经》也找不出这样的人,把福气都留给自己,把晦气推给别人。(伍译)[2]36-37
原文中pharisee一词有繁复的修饰成分,不仅前面有两个形容词做定语,后面还跟了一个很长的定语从句。这样复杂的包孕句在英语中俯拾皆是,究其原因,还在于英语重形合,它能借助时态、语态、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和连词等显性的形态标志把句子各成分衔接在一起。由于自身意合的特点,汉语的形态远不如英语发达,但其文法高度简约,形散而神合,主要凭语义上的关系和联想来实现连贯,因此语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语序,句子结构通常短小精悍,灵活多变,少有层层叠套的长句。就定语而言,汉语中是没有后置的短语定语和从句定语的,名词的修饰成分只能放在前面,而且一般不宜过长,两个以上的修饰词就会给人繁冗啰嗦的感觉。杨译之所以翻译腔十足,问题就出在长定语上。在中心词“法利赛人”之前,她共用了五个修饰语,字数长达38个字,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读不顺口的。如此冗长的定语终究逃脱不了汉语自身规律的裁决,必将受到“排异”而惨遭淘汰。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有经验的翻译家往往会调整位置,把冗长的修饰语放在中心词的后面做补语,这是汉语固有的表达方式。伍光建就做到了这一点。
从以上两例中不难看出,为了照应民国时期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伍光建对译文采取了归化式的处理。他的译文在主要意义上是忠实于原文的,而在语言形式上则顺从译文,他会根据需要变更原文的词序,而且还巧为连接、善于断句。他的译作自面世之日起就广受欢迎并经久不衰,说明他的翻译策略为大众所认可,是成功的翻译手法。笔者以《呼啸山庄》的伍译本为例,从“节译或是全译”、“文言或是白话”和“欧化或是归化”三个维度展现了伍光建“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伦理。事实上,直至20世纪60年代,“读者因素”才开始正式地进入译学研究者的视野,并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毕竟一部译作,只有为读者所接受,才能实现其价值。就这一点而言,伍光建不能不说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译界圣手”。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4.
[2]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M].伍光建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12.
[3]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J].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M].璧华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9:67-70.
[4]林语堂.论翻译.翻译论集[M].罗新璋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17-432.
[5]胡适.胡适译短篇小说[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195-196.
[6]Bronte,Emily.Wuthering Heights[M].Bantam Books,1981.
[7]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杨苡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0.
I106
A
1671-5993(2017)03-0084-04
2017-07-10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民国时期勃朗特姐妹译介研究”(SK2013B013);安徽省教育厅2017年度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伦理学视角下的伍光建翻译研究”(SK2017A0005)。
刘嵘(1975-),女,安徽黄山人,硕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