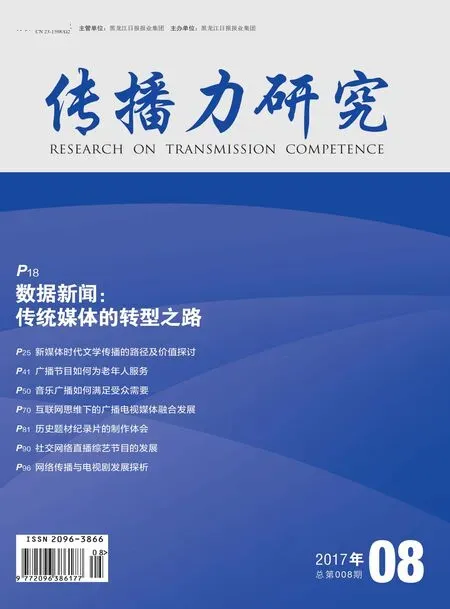网络信息传播“再中心化”现象研究
文/孙频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截至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9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10.1 个百分点。[1]同时,随着移动时代的到来,传统纸媒和门户网站转型加快、自媒体不断涌现,网络已经成为了社会公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公众获取和分享信息、传播兴趣内容、学习专业知识、建构舆论导向的重要平台。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的兴起也为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发展契机。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考察腾讯公司时就曾表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而在2016年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就曾经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这一切都推动我国互联网发展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但是,在积极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存在于互联网信息传播领域的许多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个体扩散信息的能力极大地增强了,而传统媒体功能与信息引导能力却被大大削弱了,这便对国家对社会舆情的控制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一、互联网时代的 “去中心化”现象
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受传播学奠基人库尔特•卢因 “把关人”理论的影响很大。该理论认为,什么样的信息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是由传媒组织传播者来决定的;大众传播被视为一种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传媒与受众的关系模式主要是“传送者——接受者”。这种模式下,传统的媒体机构成为了舆论传播的中心。同时,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受众只能被动地在大众传媒为他们“设置”的有效“议程”中进行有限挑选,从而在源头上影响社会舆论状态[2],进一步强化了大众传媒机构的中心地位。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需要将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需要调用的资源是十分巨大的。无论是大规模出版还是建立广播电视运作机构,普通个体或者小型机构绝对是负担不起的。因此,只有少部分媒体机构能够做到大规模的信息传播覆盖,而使其成为社会主要信息源,成为左右社会舆情的信息中心。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资金与技术手段已经不是阻碍信息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了,互联网及社交媒体软件提供给所有社会行为体一个低成本的大众传播平台,因此依靠巨大基础设施投入而获得统治地位的传统媒体却因为缺乏立即适应互联网时代公众信息需求的能力,使得其信息传播中心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在现实社会中就变现为媒体“去中心化”,这种现象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互联网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源呈现出极高的分散化特征,信息处理的方式也将是分布式的。依靠传统行政体制或者媒体市场建立起来的信息传播“中心”机构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而在网络时代早期崛起的被设计为网络传播“中心”的大型门户网站也将在社交媒体的冲击下“去中心化”。社交媒体的繁荣和移动化将使得信息源极其丰富,数据资源也变得更加容易获取,任何机构或者个人难以再扮演“把关人”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公共舆论的发起、传播和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回归到大众传媒兴起前自然集体选择的状态。
其次,公共舆论的传播方向发生转变。信息传播不再是单行道式的“传送与接收”模式,更多的表现为信息交换模式,不同的信息传播者互相影响对方的态度与观念。网络数据本身,由于具有体量的巨大性、来源的广泛性、产生的自发性等特点,难以再被“把关”,因此将显得更加的贴近公众的现实生活,更加容易获得公众的认可,而成为公共舆论的新基础。公共舆论将不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机构,或者一个政府能够依靠议题设置或者“把关人 ”这样的机制轻易主导。
最后,信息成为“自在之物”。互联网时代公共舆论将经历真正的去“中心化”,或者说网络数据本身将替代舆论中心,那些基于舆论源控制的传播理论将会逐步失去存在的基础,公共舆论的发端将变得更加客观化、多样化。无论是媒体、政府或者新兴的自媒体,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网络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已经成为自在之物,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已经无法实现对社会信息传播内容进行有效的控制。
二、“去中心化”对中国舆情信息安全的挑战
信息安全包括:网络安全、信息保密、内容安全。网络安全是指网络的抗侵入、抗摧毁等能力;信息保密是信息的不可解读能力。而舆情信息安全是信息安全在政治、法律、道德层次上的要求。具体是指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是健康的,信息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信息内容符合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规范。当然广义的内容安全还包括信息内容保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隐藏和隐私保护等诸多方面的要求。[3]维护信息安全的一方面在技术上要对互联网信息进行审计监管,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合理的网络信息引导机制,保障信息源与舆论环境的健康。因此在互联网世界中,如何有效监督、管理、引导网络舆情信息成为了我国信息安全领域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发展依然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信息传播工作一直以来都受到高度重视,建国以来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信息传播体系,以及非常高效的传媒机构。虽然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后,许多传统媒体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是其主体功能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其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信息传播与社会议题的“把关人”。
不过正如新华社前总编南振中指出的那样,现实生活中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民间舆论场”。主流媒体舆论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间舆论场更多的是在披露新闻、针砭社会、议论时事、参与问政[4]。由于传统中民间舆论场的传播能力有限,主流舆论场能够非常好的引导国内的信息传播内容,从而实现对社会舆情的有效疏导,维护社会的稳定与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能力却被削弱了,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决定信息传播的不再是传播渠道而是信息内容。这便使得过去依靠渠道建立起来的传统信息传播“中心”被抛弃了。这种变化在西方国家使得大量的传统媒体,如生活杂志,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也造成了民粹主义与极端思想的泛滥,分裂了社会认同,影响了社会稳定。一些国际恐怖组织,一直以来都是依靠社交网络来传播其极端思想,招募成员,煽动仇恨与指导恐怖袭击。而在中国,传统媒体在舆情信息监管与引导能力也被严重削弱了,公众舆论在网络时代变得更容易失去理性。随着社会转型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这一问题给社会带来的许多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传播的失控与失真。在无中心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内容成为了吸引关注的唯一手段,在网络世界中,公众的关注代替了信息成为互联网平台中的稀缺资源。因此为了通过吸引关注而获得利益,使得许多机构或者个人跨越了道德的底线,不惜以搞怪、色情、猎奇甚至是提供虚假信息等各种方式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由于当下面对互联网的海量多媒体内容我们还缺乏有效监管手段,这种恶性竞争只会愈演愈烈,并将社会道德的底线逐渐拉低。而部分受众的知识基础有限,使得他们难以在众多信息中有效区分真伪。类似与网络上传播的许多所谓“科学与技术成果”或者“养生秘方”多数明显缺乏依据,甚至仅仅依靠常识就能识别其逻辑漏洞,但却依然广为流传。
第二、成为意识形态渗透,制造社会认同分裂的主要渠道。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与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及社会认同的完整性。在前网络时代,中国各种传统媒体都能严格的遵守职业操守,将传递健康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作为基本职责,引导公众理性的分析判断社会现象。但是在“去中心化”的网络场域中,社会信息传播处于失控的状态。如前所述,网络世界中关注度成为了信息传播者的生命,很多网络行为主体希望通过资本运作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其必然会成为资本的附属品,甚至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渠道。很多时候,炒作特立独行的立场代替了理性分析。
第三、成为极端思想的传播平台。国际上,社交网络早就成为了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策划袭击的主要组织平台。通过社交网站,极端分子经常散发恐怖袭击视频,传递恐怖气氛,同时也招募吸纳新的成员,并传播恐怖袭击技巧,使得互联网成为了极端思想蔓延的主要渠道。
综上所述,相对于互联网时代前的地位,传统主流媒体是被“去中心化”,这一现象,造成了社会舆情信息管理的失控。使得各种信息在网络世界中肆意传播,严重威胁了我国的信息安全,同时也冲击这传统社会稳定的社会认同基础。
三、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
在早期的网络时代,传统的媒体“中心”,被网络“中心”所取代,而随着市场对网络各种信息传播平台的洗牌,那些幸存下来的网络信息平台基本都获得稳定的受众群体,舆论传播在经过了一轮去中心化之后,出现了“再中心化”现象[5]。有研究表明,在一些突发事件中,网民习惯从“意见领袖”那里寻找中肯的解读、深刻的剖析、犀利的批判[6]。这似乎表明,舆论传播必然存在一个中心,早期的网络时代看似去中心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中心转移的过程。为什么信息传播在经历了“去中心化”后还会出现“再中心化”现象呢?
首先,公众信息需求转变。在信息传播领域公众的注意力最为关键的资源,但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那些碎片化的杂乱无章的信息难以长久的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诺贝尔奖获得者 Herbert Alexander Simon指出:“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而现实中,信源的多元化和丰富化反而会弱化注意力的强度。而专业媒体对热点事件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和眼力独到的言论,才具不可替代性和集聚注意力的作用。
其次,网络空间社会分层结构化。网络提供的新技术与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衔接出现空隙,使得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有能力依靠网络的信息传播能力获取社会权力,在短期内产生“去中心化”现象。但是,随着网络空间的不断发展,经过多次的博弈与淘汰之后,新的网络精英群体会逐渐浮现出来。加之原先社会精英群体的不断介入到互联网这一新的领域之中,最终将使得互联网空间再次结构化,并产生分层。这一过程中会产生新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中心”。在微博上出现的各种所谓的“大V”,其实质就是这一过程现实反映,线上与线下社会结构依然存在一定的映射关系。
再次,网络信息传播专业化程度提高。公众“注意力”成为了获得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重大要素,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一种新鲜事物,其技术与理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各种资源、资本、技术及理论方法都已经普及,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信息送达的有效性成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关键。草根阶层依靠精英阶层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出于对互联网空间的轻视或者谨慎而获得的短暂话语空间,已经被严重挤压了,互联网上流动的巨额资本决定了话语权最终依然回归到了传统社会精英手中。
最后,网络信息传播技术门槛提高。大型机构在互联网技术上的优势,导致了传统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网络“草根”信息源难以维系其暂时的信息传播优势,最终网络话语权将再次落入那些传统的专业机构手中。比如当前发展迅速的大数据技术,其能够接受并处理大量的非结构数据,包括图片、音频和视频资料,极大地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手段与空间,也扩大了受众面。同时,其自动化处理方式,能高效地分析诸如社交软件中的非结构数据,使得信息传播者能够准确地处理信息受众的偏好,做到个性化的信息传播,增强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但是,大数据技术的门槛非常高,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巨大的,不是一般独立个体能够承担的。可见,随着网络发展的深入,专业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而专业化必然导致“中心化”,将那些纯粹的草根排除在外。
综上所述,通过互联网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互联网发展初期信息传播碎片化并不是互联网的本质,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与资本的渗透,互联网空间中社会权力结构化趋势变得十分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活跃在网络上的各种行为主体具有非常明显的草根性质,但当前流行的“网红”——即网络红人却成为网络资本投资的主要目标,“网红”发展到今天,已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如时下“网红”Papi酱在微博上有1100万粉丝,其视频在网上积累了5000万点击量,就在她成为热点时,风险资本立即向她投资1200万元人民币。很难相信,接受了巨额投资的“网红”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其背后的出资者不成为其真正的主人。
四、网络空间“再中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互联网空间的发展与其他社会现象是具有共同特征的。经历了发展初期的迷茫与混乱之后,各种社会资源逐渐认识到了网络空间的重要性,并且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掌握了互联网运作的规律,大浪淘沙最终将会在互联网空间中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互联网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其实是互联网信息传播中心与话语权中心的一个重新聚集并移动的过程,不过当前这一过程仍然处于初始阶段。
中央领导在谈到网络安全问题时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7]。在网络发展初期的“去中心化”过程中,我们传统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与监管体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社会舆情在很多时候处于失控的情况。特别是面对自媒体与社交网络时,主流媒体逐渐失去对话语权的掌控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主流媒体为了经济利益而主动迎合了这一趋势,在舆论引导工作上失去了立场。但是,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再中心化”这一过程给了在“去中心化”时代看似被边缘化传统媒体再一次进入信息传播中心,重新掌握话语权的机会。从当前中国的情况看,网络信息传播“再中心化”过程重为传统国内主流媒体重新掌握话语权,重新成为信息内容“把关人”,保障国内舆情信息安全提供了诸多的机遇。
从内容生产能力上看,主流媒体可以利用“再中心化”过程,重新树立对各种渠道信息内容解读、挖掘的主导地位,从而再次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随着网络自媒体发端初期的过度膨胀,信息受众对信息消费的偏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众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舆情事件的理性思考与分析之上,而非简单的猎奇与发泄情绪。随着网络用户学历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信息传播的专业性要求也水涨船高,普通的自媒体已经很难重复简单的爆料模式来获取“注意力”。而深度报道,专业分析是传统媒体的强项,同时传统媒体在经过了信息化改革之后,在信息的获取能力,多网络的舆情的敏感程度上完全有能力超越普通的自媒体。通过社会化媒体发声,快速化、碎片化、直接化是新媒体结构传统媒体权威的三大主要特征。但是在网络技术充分发展下,信息传播方法已经理论化并透明化,这些特征已经不再是自媒体的专利了。2012年 12 月 15 日,世界首份纯网络收费杂志《The Daily》停刊,其提供内容同质性过高,极易被其他媒体替代,而传统媒体《纽约时报》则成功转型,在信息收费后,实现发行收入与广告收入平衡,同时数字报纸订户已经超纸质版。可见,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质量上是存在巨大优势的,只要善于利用,在网络时代再次成为信息中心并非难事。
而从信息传播渠道上看,主流媒体具有技术与资金的双重优势。互联网社交平台与电商平台经过了激烈竞争,最后只有那些具有技术与理念优势的应用被保留了下来。这些能够最终在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平台无不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与巨大的资金保障。相对于那些寄居于各色互联网信息平台上的新媒体,传统媒体无论在资本体量和技术能力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随着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全媒体手段采访、报道已是媒体发展的根本方向,这一点是普通人或者说是草根自媒体绝对做不到的。因此,只要传统媒体掌握好时机,在传播渠道上无论是覆盖能力还是传播有效性上都具有重新成为“中心”的优势。
不过,虽然互联网信息传播“再中心化”对我国主流媒体重新掌握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再中心化”是一个网络生态发展的自然现象,最终也是网络信息受众集体选择的结果,不能因为传统媒体具有的先天优势就必然能使得信息传播的“中心”再次回到他们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主流媒体也必须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挑战。
首先、网络信息传播“再中心化”面临国际资本的挑战。我国主流媒体在传统上是官办媒体,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但其本身具有的“机关性”却一直难以抹去。在面对具有庞大资本背景的国际知名媒体集团时,在市场化运作与网络化存在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在传统情况下,我国媒体运营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网络空间实践中却缺乏有效约束手段。互联网作为一个逻辑上全球一体的虚拟场域,国内监管手段在管辖范围上就已经无法有效运行了,更不用说对新媒体及新渠道的规范了。因此,我国的主流媒体面对的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信息传播机构的挑战,应对不好的话新的信息传播中心可能就为他人所有,从而彻底丧失公众对其的认同,再次陷入边缘化。这种情况将比一个无中心的互联网对中国的舆情信息安全产生更为严重的威胁。
其次、传统媒体面对网络时代新社会关系的挑战。互联网的“再中心化”过程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即在网络上创造出一批意见领袖。网络舆情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亿万网民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些言论的核心却是意见领袖赋予的。那些公众关注的事件、热衷话题,其实最初都是由一些意见领袖进行分解,重新编码,甚至是符号化后创造出来的,其本质是将价值判断传递给公众,或者在价值上产生共鸣。这种价值的共鸣就是公众人物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也是公众人物与普通公众联接的纽带。因此,要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中心”必须依靠这种新型的关系。在“推特”网上,2 万名精英用户占注册用户总量 0.05%,却吸引了 Twitter50%用户的注意力,一半的“推文”是普通用户对精英用户言论的转发和评论。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说,“《人民日报》的确曾一言九鼎,但在新环境下,政治晴雨表的作用正在淡化”[8]。传统媒体对新一代人没有影响力,传统媒体精英无法与新网络受众建立稳定坚实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建立并维护好传统媒体与普通受众的信息关系,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特别是网络传播进入移动终端后,关系渠道与信息有效传递的渠道高度重合。网络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更多成为了人们编织自己社会关系的手段,人与内容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使得信息内容嵌入到了社会结构中,信息安全也嵌入到了社会安全中,信息内容安全的影响力被急剧放大了。如果“再中心化”过程中,这种新型关系资源被其他社会精英群体占有,那么公众的注意力资源也将被他们占有,信息内容的设定权也将最终旁落。
最后、“再中心化”过程的不可控因素众多,也有再次陷入无中心的可能性。“再中心化”现象的产生,其实质是受众需求变化所导致的,而非制度设置的结果。网络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是检验信息传播“中心”资格的主要指标,如果在互联网文化圈中无法出现一个在能力与实践中都能发挥信息传播“中心”的行为体,那么“再中心化”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传统主流媒体不能坐等“再中心化”过程将自己送回中心,还必须提高自身信息传播能力,在能力的竞争中实现“再中心化”。同时,“再中心化”也极有可能发展为网络信息多极化,形成数个信息传播中心,如果这些中心互相对立,那么对中国社会认同与社会整合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而舆情信息安全也将无从谈起。
“再中心化”过程,是一个客观社会现象,其发展的趋势是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在网络“去中心化”后,这一过程是中国的信息内容安全面临的是一次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因此有责任与担当的传统媒体必须在“再中心化”过程中尽快实现信息化变革,增强自身能力,承担起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中心维护舆情信息安全的责任。
五、互联网信息传播“再中心化”的应对策略
信息内容安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安全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行为体依靠互联网技术,借助精心设计的多媒体内容,实现舆论引导、议题设置,解构社会认同,煽动社会矛盾,以实现自身政治与经济利益。因此,如何维护互联网信息安全,特别是舆情信息安全是一个重要议题。除了网络技术手段控制与监督之外,在媒体宣传方面,必须能够保障真实、理性、积极的信息占据网络信息传播的主流,保证能够肩负社会责任的媒体成为信息内容的“守门人”。而网络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过程,为传统媒体回归“中心”打开了一个时间窗口。
首先、在信息管理机制上,有关部门要加强网络空间规范化建设,“再中心化”创造良好环境。第一、要规范网络信息传播平台,设立准入机制。有关部门应该从平台入手,将网络传播纳入到一个规范化的管理框架中,为公共网络平台从建立准入机制或者设立从业证书,提高门槛,将那些没有底线的人拒之门外。第二、从监管金融资本与网络推手出发,约束各种传媒推手的行为。很多时候,这些推动力量除了自身经济利益之外,也有部分人抱有政治目的。网络“去中心化”或者“再中心化”过程中,隐藏在线下的推手将成为构建健康网络舆情信息环境的主要挑战。只有监管了这些操纵者,才能釜底抽薪,为“再中心化”创造一个健康公平的环境。第三、传统媒体要严守职业道德与专业操守,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市场化的需要使得很多主流媒体加入网络追捧和炒作之中,这大大损害了这些媒体一直以来得以立足的专业精神及公众声望。因此,主流媒体应该把社会价值的重心摆正,在群众中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
其次、传统主流媒体自身需要加强网络信息传播能力建设,善于利用自身及公共网络平台传播信息,使自己具有成为网络信息“中心”的能力。第一、传统媒体需要实现自身的网络化,具备网络媒体的所有优点。美国 2012 年 12月底数据显示,87%的报纸杂志开发了 iPad 网络应用,85%有 iPhone 网络应用,75% 推出 Android 网络应用。BBC甚至要求,一线的记者优先为自己的网络平台供稿,而且必须增加图片等多媒体信息的比例。第二、加强自身的专业性建设,实现自身信息的不可替代性。“注意力”是网络空间中的稀缺资源,自媒体依靠迅速高效的传播速度赢得了注意力,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这种优势已经不再重要,全媒体时代仅仅依靠简单的第一手资料很难保证自己不被替代。而专业的分析与解读,传递独到的观点这样的思想产品将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同时,原始数据被反复转载后,第一时间发表者变得无关紧要,而以传递思想与价值为目标的信息传播,无论如何分享都可以看作是对信息源的一种关注。因此只有能够生产出思想的媒体才是不可替代的。最后、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信息传播的关系网络,实现信息的个性化传播,增加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改变了大众传播粗放型方式。大数据技术可对复杂的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高效快速的处理。对于类似公共舆情实时状态,过去无法实现精确的测量与监管,但是大数据技术可以实时生成报表,了解舆情的实时传播状况;大数据技术可以对舆情的整个过程以及各种舆情之间的关系进行关联,不仅仅是简单的因果分析,而是更多的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为突破主流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壁垒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也为主流媒体合理引导互联网信息传播,维护内容安全提供了基础。
最后、通过吸纳与整合把新兴网络精英与意见领袖纳入到网络安全制度体系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将网络精英或者意见领袖纳入到一个有序的网络行为管理框架内,使其中具有社会责任感,坚守社会道德准则的成员成为的网络信息传播“中心”的一部分,鼓励他们参与网络“再中心化”过程与主流媒体之间产生良性竞争,促使网络信息传播健康发展。有学者曾经以“行政吸纳社会”的观点阐释中国当下社会领域的结构变迁。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不是纯粹的自治扩大或政府控制重建,而是在社会自治增加的过程中重建行政控制。政府需要探寻新的行政主导模式,实现对社会组织的限制与发展,既利用其服务能力,又限制其挑战潜力。[9]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科层吸纳”的方法,将网络社交平台等信息传播平台纳入到国家信息安全体制结构中,使得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平台在运行时更具有公共性更能承担社会责任,最终使得这些网络平台具有办公共机构的特性。所谓“科层吸纳”原本指国家明确利用一系列科层的或半合法的制度来消解社会冲突[10]。部分学者认为,这些科层制度把社会民众吸纳到政府结构之中,敏感的政治诉求被科层游戏、人际关系、物质让步等方式所化解。而对于网络信息服务运营平台而言,无论是国内的微博、微信还是境外的脸书、推特,利用国内的科层制度下形成的规则来消解其与舆情信息内容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有效的,私营机构的行为一旦纳入了公共服务结构中,其本身的社会责任属性就会增加,化解个人隐私、运行管理、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与政府监管的矛盾。
六、结语
在经历了互联网发展初期的“去中心化”过程造成的信息内容监管失控,舆论管理失控后,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主流媒体信息传播主导权的重要性。随着互联网社会的不断发展,经历了“去中心化”后的网络社会逐步出现了“再中心化”现象。对于中国的传统媒体及网络安全监管部门,这是一个重新掌握网络信息传播主导权的契机。虽然这一过程中,要恢复传统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恢复其“把关人”的角色与功能,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传统媒体已经在市场化过程中逐渐成熟,对互联网中信息传播特征也有了比较深刻理解,相信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在“再中心化”过程中重新回到全媒体时代的制高点,成为社会价值的道德的担当。同时,在“再中心化”这一重要的社会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将新兴媒体中的积极因素吸纳到主流媒体之中,通过良性的内部竞争实现内容监管与舆论引导体系的自我更新。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月),第 3 页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601/P020160122469130059846.pdf
[2]大众传媒的这种“议事日程”功能,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 M.E麦库姆斯和 D.L肖在 1972 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3]张焕国,韩文报,来学嘉,林东岱,马建峰,李建华,“网络空间安全综述”,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6年02期,第127页
[4]卞学全、张晓频,传统主流媒体的再“中心化 ”,视听纵横,2014年01期,第44页
[5]中心化(Centraliza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其年的著作《信息方式》中首度提出“去中心化”。“在信启、方式的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参见[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页。
[6]Cho Youngsang,Hwang Junseok,Lee Daeho.Identification of ef-fective opinion leaders in the d iffus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EB / OL].[2013 - 11 -01].http:/ /wenku.baidu.com / link?url= 7K - ED4r Eos1 _ oy _ LM -ge3s Qr NXAfsj MUp3v LNSNoa G _ Aj Q _ r Fki2b Kd2f9 -R o Ol Ot St KXh LIA6t N0t M -f Nt H0Xc6t Cffh8jv Ggz Z9Ee BBUa.
[7]新华网,习近平: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2014年02月 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7/c_119538788.htm
[8]卞学全、张晓频,传统主流媒体的再“中心化 ”,视听纵横,2014年01期,第45页
[9]康晓光、韩恒、卢宪英:《行政吸纳社会》,世界科技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0年版,第 286-288 页。
[10]LeeCK,ZhangY,The Power of Instability: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3,118(6):1475-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