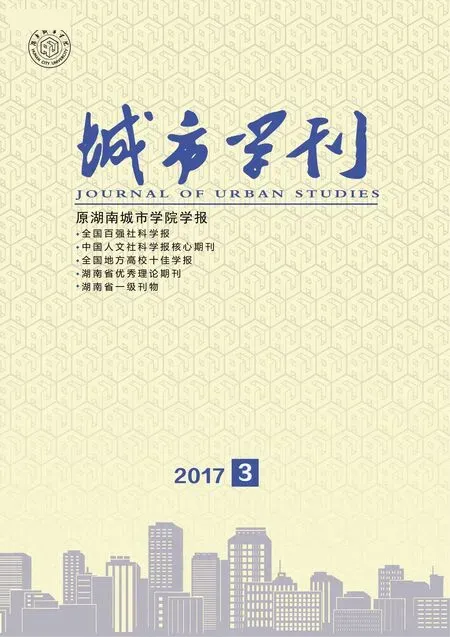北宋汴京都市元宵节狂欢与帝国合法性的建构
刘 方
北宋汴京都市元宵节狂欢与帝国合法性的建构
刘方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从元宵节狂欢夜入手展示的节日空间,揭示不同社会阶层的元宵节文学书写,体现出新的都市文化特征与都市文学风貌。有关北宋东京都市元宵节的御制、奉诏文学作品,构成了北宋城市文学写作中一项特殊的题材与内容,也构成了凝视帝国都城文化的一种特殊视角与特殊目光,建构了一幅皇权象征下的与民同乐的画卷,成为建构皇权合法性、体现国泰民安的一项重要方式。
北宋;元宵节;帝国合法性;建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岁时节日,是自然季节变迁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而形成,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中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节点与生活节奏。
而在传统中国的众多节日中,元宵节是其中十分典型和突出的一个岁时节日。
元宵节自六朝、唐代就有,但是到了北宋才在城市革命背景、城市经济、商业繁荣和市民崛起历史语境中真正繁盛。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和战乱不断的社会状态,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的措施。而伴随宋代城市革命而日趋繁荣的都市社会,促使市民阶层的形成并且日益壮大。这一新兴的都市文化中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形成具有都市市民阶层自身色彩的文化与娱乐的心理需求,而元宵节之夜的狂欢,恰好满足了宋代都市文化中各个文化阶层的这种文化娱乐需求。宋初延续了三元张灯的习俗,到了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六月,下令罢去中元、下元张灯,“六月丙午罢中元下元张灯”,只保留上元灯展习俗。[1]
丰富的都市元宵节日文化,为城市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而具有不同社会身份,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都市中各个阶层的人们,对于元宵节盛大的节日庆典与难忘的狂欢场景,有着各种不同的认知、理解和看法,也会使他们投向都市节日文化的目光有所不同,从而使他们凝视帝都节日文化的所见产生差异。
有关北宋东京都市元宵节的御制、奉诏文学作品,构成了北宋城市文学写作中的一项特殊题材与内容,也构成了凝视帝国都城文化的一种特殊视角与特殊目光。建构了一幅皇权象征下的与民同乐的画卷,成为建构皇权合法性、体现国泰民安的一项重要方式。
在北宋统治的170年中,中原息兵,人口增长,汴京成为全国以至全世界最繁华的都会城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中的文字记载,生动详细,正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相互印证: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2]
如果说《东京梦华录》是从描绘帝京总貌的角度,展现其壮观繁盛画面,那么柳永的都市词,则呈现了北宋时期伴随着都市文化逐渐走向繁华,元宵节的都市盛况。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载,“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3]曾传入禁中的词,即是柳永的《倾杯乐》: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薫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䓤蒨。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雉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棃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抃。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4]
上阙“禁漏”三句描绘皇宫景象,宫漏声声,花木深深,惠风习习。“变韶景”数句则是写都城元宵节夜景,整个皇城都笼罩在月光灯火之中。“连云复道凌飞观”数句,极力夸饰皇宫的楼台殿阁雄伟壮丽,复道凌空飞架耸入云端,笼罩在一片葱郁的祥瑞之气中,仿佛神仙的居所。
下阙“龙凤烛”数句,描绘元宵节夜晚灯火辉煌,与天上闪烁的银河交相辉映。“对咫尺鳌山”数句,是夸饰众臣随皇帝观赏彩灯和皇家舞队乐队的精彩表演。巨鳌形的彩色灯山,宛若孔雀开屏般绚丽,舞队乐队的精彩表演仿佛天上仙班。据《宋史》巻一百四十二《乐志》记载:
每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栅上用散乐,女弟子舞。[5]
显然《宋史》所记录的北宋皇家上元观灯的用乐史实,正是柳永词中数句所本。而对于元宵节皇家仪式与舞乐,宋孟元老撰《东亰梦华录》卷六《元宵》有更为详尽的描绘: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朩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踘、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铁剑李、外宁药法傀儡、小徤儿吐五色水、旋烧泥丸子、大特落灰药榾柮儿杂剧、温大头、小曹嵇琴、党千箫管、孙四烧炼药方、王十二作剧术、邹遇、田地广杂扮、苏十、孟宣筑球、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䖝蚁、杨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呇,上皆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揺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朩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縳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幷左右军百戏在其中,驾坐一时呈拽。宣德楼上皆垂黄縁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帘内亦作乐。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彩结栏槛,两边皆禁卫排立,锦袍幞头簮赐花,执骨朵子。面此乐棚、教坊、钧容直、露台弟子,更互杂剧。近门亦有内等子班直排立。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6]
对照孟元老的描绘,柳永的词句,原本都是从眼前即景书写,包括神仙、仙境一类文学想象,也都有了着落。“向晓色”数句,描绘都城的元宵节狂欢之夜,通宵达旦,最后词人愿每年的元宵之夜,都能在天子的仪仗队伍中看到圣上的车驾,能让他再有机会一睹天颜。
宋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七《同民乐》条记载:
仁宗正月十四日御楼,遣中使传宣从官曰:“朕非好游观,与民同乐耳。”翌日,蔡君谟献诗云:‘髙列千峰宝炬森,端门方喜翠华临。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恵爱深。(东斋录)[7]
而柳永的词可谓正中下怀,完全符合仁宗的想法与要求。既称赞了皇宫的富丽恢宏,都城的节日盛况,又歌颂了皇帝的与民同乐,万众欢呼,最后还表达了对于帝国与皇帝的美好祝愿。因此能够“传禁中,多称之”,得到了皇帝的首肯。
都市文化经济的繁华,社会的升平安乐,为宋代城市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而宋代自皇帝为首的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积极参与,则进一步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裕的精神与物质条件。宋朝自立国以来,采取重文抑武的治国策略,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几乎各代皇帝都雅好艺文,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盛赞:“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8]
宋代最高统治者常常亲身参与各种文学活动,君臣之间宴饮唱和,蔚然成风。
宋徽宗赵佶在元宵节庆典之时,有词作《满庭芳》并序:
上元赐公师宰执观灯御筵,遵故事也。卿初获御座,以满庭芳词来上,因俯同其韵以赐。
寰宇清夷,元宵游豫,为开临御端门。暖风摇曳,香气霭轻氛。十万钩陈灿锦,钧台外、罗绮缤纷。欢声里,烛龙衔耀,黼藻太平春。
灵鳌,擎彩岫,冰轮远驾,初上祥云。照万宇嬉游,一视同仁。更起维垣大第,通宵宴、调燮良臣。从兹庆,都愈赓载,千岁乐昌辰。[9]
范致虚,《宋史》卷三六二有传:
范致虚,字谦叔,建州建阳人。举进士,为太学博士。邹浩以言事斥,致虚坐祖送获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见,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宁初,以右司谏召,道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蔡京建请置讲议司,引致虚为详定官,议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处华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张商英,贬通州。政和七年,复官,入为侍读、修国史,寻除刑部尚书、提举南京鸿庆宫。[10]
初,致虚在讲议司,延康殿学士刘昺尝乘蔡京怒挤之。后王寀坐妖言系狱,事连昺论死,致虚争之,昺得减窜,士论贤之。迁尚书右丞,进左丞。范致虚进左丞在宣和初。而宋徽宗此词的作年,也应当在宣和年间。范致虚今存词一首《满庭芳慢》:
紫禁寒轻,瑶津冰泮,丽月光射千门。万年枝上,甘露惹祥氛。北阙华灯预赏,嬉游盛、丝管纷纷。东风峭,雪残梅瘦,烟锁凤城春。
风光何处好,彩山万仞,宝炬凌云。尽欢陪舜乐,喜赞尧仁。天子千秋万岁,征招宴、宰府师臣。君恩重,年年此夜,长祝本嘉辰。[11]
从此词与宋徽宗唱和词作的词牌、韵脚和题材内容看,应该就是当日范致虚上宋徽宗的词作,也是宋徽宗唱和词作的原作。从范致虚词作可以看出是写君臣于北阙预赏华灯时候的场景。词作先从元宵节时候的天气写起,皇宫中天气微微有些寒冷,皇家园林中的池水已经结冰。而元宵节的月色十分明艳,遍撒银光。君臣预赏华灯,都市中士民是嬉游盛、丝管纷纷。一派歌舞升平的节日景象。而在料峭的东风中,都市中红梅白雪,一派早春风光。下阙则从元宵节的彩灯写起,以尧舜来比喻宋徽宗,整个下阙基本是歌功颂德的庾词。虽然从艺术的角度,上阙尚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下阙则几乎是毫无艺术色彩的庾词。但是从政治的意义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是必要的,是正好满足了皇帝大肆举办元宵节与民同乐的政治需要。也正是如此,宋徽宗才特意要唱和其词以赐,以示嘉奖。
宋徽宗词序谈到“上元赐公师宰执观灯御筵,遵故事也。”上元佳节,皇家会举行盛大的元宵节活动,而且皇帝常常要召大臣们伴宴观灯,这一惯例是在宋初奠定的:“太祖建隆
宋代杨湜《古今词话》中《徽宗皇帝》条记载:“《满庭芳》和左丞范致虚。(词略)” 《岁时广记》十引上阕,前有序云:“上元赐公师宰执观灯御筵,遵故事也。卿初获御坐,以满庭芳词来上,因俯同其韵以赐。”
二年上元节,御明德门楼观灯,召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使、端名、翰林、枢密直学士、两省五品以上官现任前任节度观察使饮宴,江南、吴越朝贡使预焉。四夷蕃客列坐楼下,赐酒食劳之,夜分而罢。”[12]可见,在宋太祖时便已有招召臣僚伴宴赏灯的节日习俗。宋初的观灯御筵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形成惯例,便成为宋徽宗序中所言的“遵故事”了。宋代陈元靓引《岁时杂记》中记载:“祖宗以来,每灯夕,命辐臣诣太一焚香,赐会寺中,或大臣私第。自仁宗以来,专在景德,嘉祐中,曹相公恳请诸公迁就开化一次。元丰末,王丞相就宝梵行香厅作御筵,后又迁在开宝。元祐中,又于启圣,皆出临时主席之意。”[13]此记载可以了解虽然观灯御筵形成惯例,但是宴席的地点往往并不固定,经常是根据情况而定。
与范致虚作品中寒、东风峭等描绘天气的用词不同,宋徽宗特别强调是暖风摇曳,而且是空气中充满了香气,所谓“香气霭轻氛”。在传统中国,焚香、熏香等等,往往是权贵人家的习俗。而到了宋代,由于社会经济、商业的繁荣,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香的习俗更为普及。[14]
宋徽宗词中以“十万钩陈灿锦”来描绘皇家壮观华丽的仪仗。钩陈,一种用于防卫的仪仗。《北史·艺术传下·何稠》:“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隋书·礼仪志七》:“八年征辽,又造钩陈,以木板连如帐子。”《续资治通鉴·宋太宗淳化二年》:“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钩陈羽卫之严。”
灿锦,是描绘仪仗的威仪与绚丽的色彩。美国著名汉学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女士,曾经撰写有《Taking Out the Grand Carriage: Imperial Spectacle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Northern Song Kaifeng》一文,专门研究北宋皇家仪式及其政治和文化意义,[15]而北宋时期皇家仪仗的威仪与绚丽的色彩,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驾卤簿图卷》一幅画作中可以得到直观的震撼性感受。[16]
宋徽宗在词的上阙中,通过暖风的触觉感受,香气的嗅觉感受。十万钩陈灿锦,罗绮缤纷,烛龙衔耀的视觉盛宴和“欢声里”的听觉感受,调动了读者的各种感官活动,描摹刻画出了一幅太平春图卷。下阙写万民同庆,君臣唱和,千岁乐昌辰,依然是歌咏太平盛世的基调与主旨。
关于宋徽宗时期元宵节的君臣唱和,宋陈鹄撰《耆旧续闻》卷三记载:
大观初上元赐诗曰:“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隍中。”群臣应制皆莫能及,独有府尹宋乔年诗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乃赵䶵之子雍代所作也,雍少学于陈无已,有句法。[17]
说明宋徽宗君臣之间,元宵节唱和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唱和文体有诗有词,唱和方式,或者宋徽宗赐诗群臣应制,也有时候宋徽宗对于臣下的作品进行唱和。
宋代张知甫《张氏可书》中记载:
王初寮安中,自翰林学士承旨迁右丞。值元宵,从宴宣德门。徽宗命以五门端阙为题,令赋诗。安中即席应制曰:“斗城云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缯巘千峰连璧月,珠帘十里晃灯莲。五门端阙初元夕,万历宣和第二年。盛世亲逢叨四近,颁觞连日缀群贤。”上嘉之,移宴景龙门,上自调黄芽羮以赐。[18]
这一记载反映了元宵节从宴群臣应制赋诗情况,而从诗歌内容中谈到“宣和第二年”,则应该是在宋徽宗的《满庭芳》和左丞范致虚的次年元宵节。
王安中(1075-1134)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徽宗时历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以谄事宦官梁师成、交结蔡攸获进,又附和宦官童贯、大臣王黼,赞成复燕山之议,出镇燕山府。靖康初,被贬送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又内徙道州,复任左中大夫,不久去世。
王安中品行颇遭物议,而文章却可观。他擅长诗和四六文,在当时很受推重。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徽宗燕赏元宵,命王安中、冯熙载进诗》条记载: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谟殿张灯预赏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书侍郎冯熙载为诗以进。[19]
由于王安中、冯熙载两人诗歌均属于长篇之作,仅就王安中作品分析于下,以见元宵节应制长篇诗歌之一斑。
王安中的这首应制诗歌,可谓长篇巨制,文字达1 209字,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内容丰满,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宋代元宵节皇家宴饮赏灯的许多具体内容。诗歌开头数句先从神霄上帝写起,以迎合宋徽宗的道教信仰,以粉饰其皇权的神圣合法性。然后又用《易经》大壮、乾的卦象,进一步称颂宋徽宗自身皇帝权力的正当性。都是极为符合应制文学主题的写法,但是在具体书写上,不是象范致虚一类作品抽象、直白地表达,而是更为具有文学的想象,神话的神奇色彩和经典的理论依据。
诗歌接下来具体描绘元宵节的自然气象和皇宫宫室的恢宏壮丽,装饰繁复。然后交代自己撰写诗歌的缘由,描绘应诏进入睿谟殿所见所闻,“兽铺金半阖,鸾障绣微褰。霁景留庭砌,雷文绘桷梃。宫帘波锦漾,殿榜字金填。花拥巍巍座,香浮秩秩筵。”
“高呼称万亿,韶奏侍三千。华岁推尧历,元玑候舜璇。”则不过是再一次以庾词称颂宋徽宗。以尧舜比拟宋徽宗,似乎已成为当日君臣的共识。
冰霜数句,描绘了皇宫中多种植物芳菲斗妍,“错落飞杯斝,锵洋杂管弦”等数句,则是描绘了宴饮中的觥筹交错,管弦奏乐的场景。“乃圣情深渥,诸臣意更虔”则是称美君臣情深,体现君臣关系之美好。
“要赏嬉游盛,俄追步武遄”以下,则是开始具体描绘在宴饮之后的观灯游观活动的所见所闻了。“腾身复道”反映了北宋皇宫建筑复道的实际情况,“旁临艮岳”反映了观灯所在宫殿的具体位置,艮岳为宋徽宗所修筑的著名皇家园林。
“讴歌纷广陌,箫鼓乐丰年。赫奕攒轻幰,珍奇集市鄽。博卢多袒跣,饮肆竞蹁跹。”则是从宫殿中所见北宋汴京繁华的都市节庆景观。街道上是歌舞升平,来往的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装饰华美,炫耀夺目,集市中珍奇荟萃。而关节的市民,袒跣赌博,众多酒楼连绵不绝的宾客,描绘出一幅万民祥和的图卷。
“浩荡三山岛,棱层十丈连。”数句则是描绘元宵节所扎各种景致的彩灯,不仅有高达宏观的彩灯建筑,而且也有“光透垂枝井,晶衔带壁钱”的精巧的制作。
“冰轮挂银汉”之后,再次转入元宵节的描绘,点题。“比闾增板籍,疆场罢戈铤”称美天下太平,四方来朝,皇帝多男,百姓丰收,“庙鹤垂昭格,坛光监吉蠲。灵芝滋菌蠢,甘醴涌潺谖”数句,则是通过天下各种吉祥的祥瑞,称颂宋徽宗的统治。最后再次回到君臣际遇千载难逢的话题,自谦诗歌写的才悭难称。
王安中的这首应制长篇,构思精巧,辞藻华丽,即要不离庾词的歌功颂德、歌咏太平的主题,又不失文学的韵味,写的典雅富丽,颇有汉代大赋风韵。
在元宵庆典中,通过作为最高权力的绝对拥有者的皇帝,对于群臣的锡宴,排立仪卫的像征,检阅诸军表演,并且赐予市民观赏的权力等等,呈现和确认了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仪式、表演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
合法性是政治上施行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它是统治的政府和被统治的人民共同认可的一种法则或理念。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同运用统治权力的政治权威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论述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一是传统型的。这种权威的政治特征是政治权力的世袭制和君权神授。统治权力之所以被人民认可,是因为它被认为当然如此和从来如此。二是神授型的。这种权威的特点,是对某种超凡的政治领袖的崇拜。这种权威往往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与某种意识形态相纠合。三是法理型的。法理型统治立基于一种信念之上,即认为某些规范性的律则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只有根据这些律则而建立的政治权威才具有合法性。而韦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切权威一方面均可归类为“神授型”,这种政治权威建基于人民对某个个人所具有的超凡神性、英雄气质或模范性格所产生的归顺之心,以及对这位英雄所启示和创造的某些规范模式所产生的信仰之上。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威亦兼带有某些传统型的气质,即认为远古而来的传统具有神圣性,据此而建立的权威自然地具有合法性的身份。[20]正如研究者介绍现代相关学说与理论所指出:“在神圣政治中,重要的不是言说的话语(尽管君主从未放弃用话语来证明自身的存在及权威),重要的是展现君主身体形象的仪式。”[21]
皇帝与民同乐的仪式与表演,臣民奉旨而创作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学作品,其独特价值与不可替代性质,就在于它不是直接、强迫地为现成政治制度维持与辩护,使现实问题、矛盾合法化。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节日娱乐与文学想象的方式,隐含着肯定既定的大一统帝国合法性的前提,正是在这种娱乐表演与文学表述中,不断肯定和重新肯定现存制度、权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为了体现与民同乐,皇帝在元宵节的狂欢之夜,在繁琐、奢华的典礼与仪式中参与并且君臣唱和,也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1]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一太宗淳化元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701.
[2]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
[3] 叶梦得. 避暑录话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9: 49.
[4] 柳永. 乐章集校注[M]. 薛瑞生,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5.
[5] 脱脱. 宋史: 巻一百四十二乐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348.
[6]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540-542.
[7] 祝穆. 古今事文类聚: 前集卷七[M]. 四库全书本.
[8] 陈寅恪. 金明丛馆二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9] 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898.
[10] 脱脱. 宋史: 卷三六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1327.
[11] 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694.
[12] 脱脱.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三嘉礼[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698.
[13] 陈元靓. 岁时广记: 卷十丛书集成本[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9: 102.
[14] 扬之水. 古诗文名物新证[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26-125.
[15] Patricia Buckley Ebrey.“Taking Out the Grand Carriage: Imperial Spectacle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Northern Song Kaifeng”[J]. Asia Major, 1999,12 (1): 33-65.
[16]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4-25.
[17] 陈鹄. 耆旧续闻: 卷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307.
[18] 张知甫. 张氏可书[M]. 守山阁丛书本.
[19] 王明清. 挥麈后录: 卷四[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3669-3670.
[20]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洪天富,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21] 李猛. 论抽象社会[J]. 社会学研究, 1999(l): 13-15.
(责任编校:彭 萍)
Construction of Lantern Festival Carnival City Bianjing and Imperial Legitimac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 nasty
LIU Fang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Zhejiang 313000, China)
The festival space starts with the Lantern Festival carnival night reveal the new urb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rban literature style that ref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writing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in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kyo City Lantern Festival the imperial Feng literary works, a cit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terary writing in a special theme and content also constitute a special angle of view and the special gaze imperial capital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mbol of imperial power under the picture becomes the construction that is fun with the citizens, imperial legitimacy that reflected an important way of the peopl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antern Festival; imperial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G 127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3.017
2096-059X(2017)03–0088–06
2017-03-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1FZW010)
刘方(1964-),男,北京人,二级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中国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