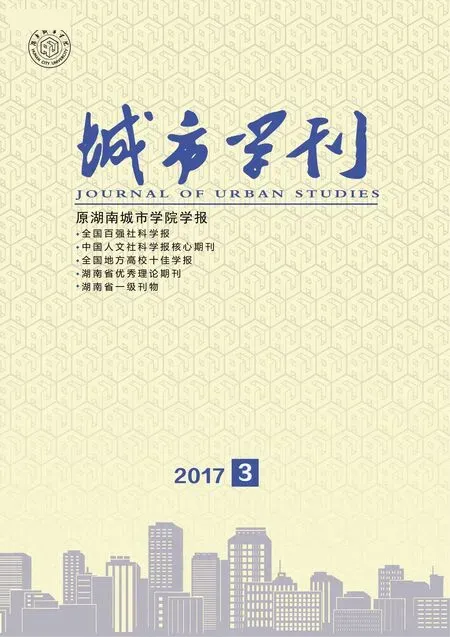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团聚研究
任谢元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团聚研究
任谢元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科研处,济南 250307)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开启了实践多元的破冰之举,使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开始进入到公众视野。但因国家政策布局尚未完善、家庭团聚条件受限、深层次矛盾存在、合法性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的基本权利尚无切实保障。为此,要通过打破制度壁垒,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方式,为农民工家庭自由流动创造条件,使“进得去城,回得去乡”成为一种常态。
城市化;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
经济全球化刺激、推动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开始出现、发展和壮大,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人户分离”的农民工群体规模愈加庞大,对作为社会最基本组织细胞的“家庭”造成冲击,由此引起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的不断往复迁徙,出现从“个体流动”到“家庭式迁移”的明显趋向。目前,国内关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是以直接切题式、旁证侧引式、介质楔入式等模块形式来展开论述。其中,有关农民工家庭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心理问题、犯罪问题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多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引起了社会、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共鸣。
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现状
农村的传统经济在城市化浪潮的激荡下其发展进程出现中断,甚至是遭到严重的破坏,由此导致了传统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农式经济困境,数以万计的农民开始被迫走出家门,横跨千里从农村涌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或沿海城市谋求生计或寻求更好地发展,他们成为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被冠以“农民工”称号。农民工问题是农村经济遭到破坏后产生的次生问题,是农村问题在人身上的进一步延续,也是城镇化建设的一大瓶颈。直观上看,因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差异,限制了农民工把家庭带到“工作地”生活的权利,使得这一群体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样因谋生地差异而不断地漂泊,从而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家庭被迫分离,天各一方,使“家庭团聚”这个人类生活最朴素的愿望,成为农民工在所谓后现代时期最奢侈的梦想。据国务院农民工办公室的调查数据,2008-2011年流动人口举家流动的比例还很低。外出农民中举家流动的比重基本稳定于二成左右,近八成的外出农民工单独或仅与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即近80%的家庭是不完整的流动家庭。[1]进入“十二五”时期后,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增速从2010年的3.54%上升至2013年的4.4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结果,201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1.66亿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3 525万人,占21.22%,比2010年增长了1.19个百分点,趋势逐渐加强。[2]并且,很多农民工选择在离家更近的乡镇务工,跨省流动比重继续下降。流动人口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在2013年达到了62.5%,比2011年上升了5.2个百分点。[3]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缓解由家庭分离带来留守子女家庭教育的异化和感情的淡漠,弥补了社会和家庭教育的缺失。
同样,这一变化还从不同方面反映出来。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网站2014年1月10日以《他们也是父母:中国留守儿童家长研究报告》为题报道了其对珠三角和重庆地区1 500名工人的调查。调查显示,虽然92%的农民工认为抚养子女是父母的责任,但实际上能做到的仅五分之一,孩子通常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亲戚照顾。作为通向未来之路的“家庭”问题,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联合国不仅设立国际家庭日,并且把2000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定为“家庭:发展的发动者和受益者”;把2015年国际家庭日口号定为“事业再忙也要抽时间,家和才能万事兴”。通过主题的变换方式,来凸显家庭问题的重要性,以提高国际社会和公众对于“促进家庭和睦幸福”社会发展进步的认识。这说明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都充分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对家庭造成的冲击问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主题。就中国而言,政府、民间团体和爱心人士也采取多样形式来助推农民工子女到城市实现团聚的梦想。各地慈善总会、工会和团组织充当了先锋军角色,通过深入调研、访谈,了解到农民工的迫切需求和心声,在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如广州市总工会在2011年发布的《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一文中指出,夫妻子女团聚等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传统的经济因素开始居于第2位。宁波市文明办2011年出台《宁波市开展关爱“小候鸟”文明行动的实施意见》,号召宁波市各级各部门建立关爱“小候鸟”的长效机制,为农民工暑假接子女团聚创造条件。这些行动是历史性的破冰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冲击,使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成为继每逢岁末年初的民工荒、追讨欠薪、民工返乡潮等现象之后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进入到公众视线中。同时,它也是对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组成单位的家庭权利的回应,使得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对未来充满期待、对生活品质有所追求、甚至渴望身份变化。但是这些局部举措尚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及其家庭问题,仅仅是对农民工家庭问题诉求的社会呼吁和局部调节。
因为政府的倡导、发动,社会力量特别是基金会组织也积极参与到这一事业中来,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弥补了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引起了政府关注。在民间团体中尤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农民工关爱计划之农民工救助专项基金”——“幸福列车”项目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农民工子女一起过大年”两个项目因特色鲜明、平台高端,最为引人注目。
农民工家庭处于对未来团聚的期待,也通过一系列适应、维系、修复等自救性行为,顽强地维系着家庭基本功能,使其在离散中呈现弥合效应。有学者用“补偿性行为”来称呼那些因家庭离散出现关系疏离、矛盾和危机时,家庭成员的自觉行动。[5]近年来有关留守儿童的系列报道,特别是2015年出现贵州毕节4名未成年兄妹,因其父母长期离家,在哥哥带领下集体服毒死亡事件,经媒体持续报道后,对外出务工父母触动很大,他们开始直面孩子的学习、生活、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外出务工型家庭的父母为弥补对孩子的亏欠,通过给孩子较多的零花钱、寒暑假接孩子到城里团聚、尽量满足孩子各种要求等明显的补偿性行为,来减轻补偿心理造成的负重。很多个案也显示,他们对长期和孩子分离带来的孩子情绪消极、性格孤僻、内心失衡、认知偏差和情感疏远等表示出担忧和困惑。对由于长期缺乏亲情的呵护,很多留守儿童出现的性格异化、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浅薄,社会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引发的青少年犯罪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反思。正是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有些外出务工的父母为了孩子的成长,不计城市生活成本,把孩子留在身边。更有甚至,因为孩子寒暑假不肯进城和父母团聚(孩子不愿一家人挤在一间出租屋里),每两个月就回家探望孩子一次。[5]
二、影响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的因素
虽然农民工家庭团聚出现了令人振奋的一面,但种种现实困境依然阻碍着长效机制的建立,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仍旧难以掀起波澜,他们还是如“候鸟”般来回迁徙。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家政策布局尚待完备
全面解决农民工系列问题的全国性政策尚待出台,由于20世纪末经济政策和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致使农村局部传统经济出现衰退,失地农民大量出现并率先被迫规模化涌入城市。加之我国的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也出现了对廉价劳动力的规模化需求,使农民工家庭、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诸多问题爆炸式出现是始料不及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新时期城市管理的研究、城镇化建设也处于初探和尝试阶段,新问题的出现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对问题的预计,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策准备都显得力不从心,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将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完善、城镇化发展、新型城市管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去统筹谋划和分步骤解决。但是,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彻底实现社会福利和待遇的完善,最终实现农民工家庭团聚问题的根本解决仍是一个长期过程。
(二)空间区域零散,且分布不平衡,仅局限于个别大中城市、发达城市
综观为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搭建桥梁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尤以北京、杭州、宁波、广州、深圳等地为主,广大内陆地区、边疆地区较少,出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信息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涵盖了从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产学研转化水平到第三产业发展等方面,是中外经济交流、融合之地,具备了现代大都市的突出特征,充分发挥着吸附功能,成为产业集群区域和消费人群的载体,其人口聚集能力和空间辐射扩散效应强大,强烈吸纳着内陆和边缘地区的农村人口,造成了农民工汇聚地的群体形象,成为政府和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正因为农民工聚集效应,这些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成为了许多科研机构、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调研的对象,其形成的调研报告通过不同形式递交于政府部门或通过媒体加以传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效应。
(三)梦想拥有“体面工作”,获得家庭团聚的“时间和经济条件”受限
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稳定性较差、工资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缺失,由此导致农民工在个人自由时间缺乏支配自主权,每天“出不见日出,回不见日落”,没有稳定的“假期”,有的甚至晚上还要继续加班工作,一个月难得休息,更不用说回乡探亲。新华网调查显示,68%的受调查农民工把没时间照顾孩子列为亲子分离的主要原因。即使是留守儿童进城与父母团聚了,由于父母超长的工作时间,“飞”来团聚的“小候鸟”也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和监管,面临着比农村更多的危险,如溺水、触电、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意外伤害等。2011年夏天,仅浙江地方媒体报道的外来务工者子女因为意外溺水死亡的事例就不下20起。[5]此外,较低的劳作收入水平,务工地居高不下的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也成为制约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一位受访的农民工如是说“留在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关键是没法教育孩子,不如在老家。”[5]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无奈,经济条件成为阻碍众多农民工家庭团聚难以跨越的障碍,渴望增加工资,增加保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同时能够经常回家看看成为众多农民工的心声。
(四)“蜻蜓点水式”的尝试,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尚待突破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现行户籍制度把人们的户口划分为常住户口与暂住户口、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且不同户口待遇相异,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把家庭带到“工作地”生活的权利。从现行的家庭团聚模式和实施主体来看,它们采取的各种措施,只是缓解“相思之苦”的短暂、临时的方法,不论是官方还是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支持都是在现行国家户籍制度控制范围内进行的行动。
(五)合法性制度认同的缺失
法律法规是以条文的形式告知人们行动的规范,是社会秩序稳定、有序的保证,是实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根本基石。农民工群体作为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特殊产物,实现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需求的家庭团聚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从上述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是三种力量的自发行动,其模式、标准及组织形式不一,尚未出现全国统一的机构来规范、指导这些行动,各地区、各部门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究其原因就是合法性的制度认同的缺失,加之相关的社会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保障福利政策涵盖范围和城乡文化、习俗不同等多重因素作用,使农民工群体承受着的沉重压力,只能在社会大潮中以无声而“亮丽”的迁徙引起媒体、社会组织的注意,期待有一天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每个家庭成员不再忍受煎熬、相思之苦。
三、实现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的对策
为保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加快农民工家庭市民化进程,必须消除二元体制的影响,形成公共服务公平覆盖农民工的制度,为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清除障碍,实现人类社会最基本组织单位的最原始形态。
(一)持续推进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农民工家庭团聚的首要迫切条件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主要是以城乡为界点,防止两方人员互流为目的,当然还有其他诸如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功能,这导致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城镇本地居民的巨大差距,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悖离,不仅削弱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是挫伤了其在城市发展、扎根的勇气和积极性,不利于“以人为本”宗旨的实现。虽然经过30余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可以自由地流动到城市就业,或者可以到一些小城镇落户,但农民工因种种内外因素的限制,在大中城市的稳定就业和安家落户仍难以实现。而且,出现了城市越大,户口越难以取得的现象。在很多大城市,只有极少数农民工精英自身具备了技能、资金实力或满足了如购房达到一定面积等某些“苛刻”的条件之后,才能有机会获得落户的权利。
长远来看,要冲破户籍制度的重重壁垒,使其功能单一化,不再成为人们身份的标识和难以跨越的“鸿沟”,已刻不容缓。国家应该出台统一的法律法规对流动人员的户籍进行管理,通过破除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引导农民工在全国这个大范围内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工作属地管理模式。各地可根据自身特点实行“弹性融合”的办法来弥补国家政策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这有利于突破户籍制度壁垒的限制,对属地外来人员,依据其工作时间年限来界定享受该居地民的待遇的方式,在实现逐步融入的同时,由户籍管理向居住地管理转变,从而取消人员流动的部门界限、省份界限和地域界限。
(二)推行农民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实现家庭团聚的重要条件
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并为此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方针,使其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但从实际施行来看,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地仍然壁垒重重,由于高额的借读费、建园(校)费的征收,使囊中羞涩的农民工望而生畏,教育平等权并未真正实现。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平等问题,就必须打破以户籍为基础的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以居住地为参考基础的管理体制改革,使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问题不再成为媒体、网络报道的“常客”。政府要采取相应举措,接纳儿童在父母务工所在地入学,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同时要逐步制定政策改革城乡教育不一体制,统一教材使用,消除升学制度、学籍管理等方面的地区差异,从根本上改变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儿童教育的二元孤立状态,使流动儿童能够保持学习的连续性,改变儿童教育的“城乡分治”格局。此外,城市义务教育要改变现行的逐级划片或学区管理模式,严格实行义务教育的就近管理模式,避免教育资源向某些学校集中,从而使务工人员子女能够有机会进入资源较好学校,享受到政府统一拨付的教育经费预算和生均经费。同时,在政策全面落实制定之前还应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师资培训、教学设备购置、校园用地等方面予以支持,保证农民工子女能接受质量合格的基础教育。
(三)推进城镇化进程,使农民工能够在属地就业,消除农民工家庭分离的潜在障碍
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逐步实现农民就业城镇化和农村基础实施城市化,从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逐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要求,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基础实施配套、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实施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并举的就业发展战略,一方面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文化水平,促进充分就业。借力引智加快产业引进,形成产业聚集区,通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增加就业岗位,同时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扩大就业容量,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场所,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促进农民就近就业,稳定就业。从根本上看,彻底有效解决农村问题,发展调整农村经济政策,严厉制止圈地运动,因地制宜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将“难民”式流动转化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农民向城市的有序流动,建立健全覆盖全局的超越城乡二元体系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均衡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特别是在定居、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策平衡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及其家庭问题的根本性举措。
(四)制定国内移民家庭团聚的法案,是实现农民工家庭团聚的法律保障
家庭团聚是公民应享有的社会权利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因维系家庭成员生存、发展的需要,许多人尤其是农民未能充分享受到这一权利。要打破这一“瓶颈”,就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打破常规,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内移民家庭团聚法案,成立专门机关推进、指导、规范、监督各个地方实施情况,依靠国家行政力量保证政令行的统一。但是专项法案仍只是过渡性解决方法和指导性举措,根本之策还在于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彻底融入的最终实现,即包括政策的全面制定实现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更包括农民工家庭与城市的长期自然融合。
(五)农民工要进行自我调适,筑牢立足城市根基,为家庭团聚创造条件
农民工要想在城市真正实现家庭定居,成为产业工人和市民,首要的就是要进行自我调适,冲出固封自制的圈子和传统认知,实现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具体来说,一是要拓展社会人际关系,改变对“城里人”的认识,勇敢地同“城里人”交往,突破传统对“如何才是城里人”标准的认识和理解;二是要行为适应和自我认同,适应“城里人”的交往方式,从心底里认同所在城市文化,改变过去对自我身份、自我形象的不恰当认识,实现心理认同。唯有实现了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农民工群体才能有底气、有勇气,充满活力地奋发图强,从而筑牢立足根基,为实现家庭的永久团聚创造条件。
实现家庭团聚是家庭健康和谐发展的基础保障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经济水平,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同时,家庭发展与社会发展琴瑟相和,家庭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助推力和稳定器;社会发展对家庭发展施加着深刻的影响,增强了家庭的发展能力,拓展了家庭需求内容,提高了家庭的发展效率和服务水平。然而,农民工作为一个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特殊人群,一直以来都游离于家庭单元之外,长期漂泊在异乡,为自己的家庭不断地输送着维系生存的“燃料”。农民工只是被城市作为一个经济要素加以吸纳,却忽视他们作为父母和子女、作为市民的需求,农民工子女便只能在留守与流动之间徘徊。[8]家庭团聚这个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却成为农民工最奢侈的事情。我们相信,随着城市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体制性分割和排斥的持续弱化,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开放度不断提高,城市社会融合步伐的加快,突破“我抱起砖头就无法抱你,放下砖头就没法养你”的窘境,实现流动人口家庭从分离走向团聚将不会遥远,建设美好家庭、实现社会更加和谐指日可待。
[1] 杨菊华, 陈传波.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3(3): 2-13.
[2] 蔡昉, 张车伟.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0-51.
[3]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4: 177.
[4] 金一虹. 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2): 98-102.
[5] 车辉, 沈洁. 留守儿童暑期进城探亲,教育和安全问题待关注[J]. 平安校园, 2011(8): 32-33.
[6] 熊易寒. 中国农民工不重视家庭团聚吗?[J]. 时代报告, 2015(7): 15.
(责任编校:彭 萍)
Study on Farmers Children Reunion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REN Xieyuan
(Iinstitute of Crafts and Fine arts of Shandong, Jinan, Shandong 250307, China)
With speed of urbanization advance and the multi-actions of ice-breaking are conducted. The farmers’ children can enter the city home house with their parents. However, the a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certain policies incompletion, limitation of reunion existed, the deep contradictions existed and short of reasonable systems, the right of farmers children reunion can not guaranteed. It is therefore that the population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set up to guarantee farmers and their children floated freely.
urbanization; children of farmers; family reunion
C 913.11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3.012
2096-059X(2017)03–0064–05
2017-03-25
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JNSK17C32);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5AJY009)
任谢元(1979-),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