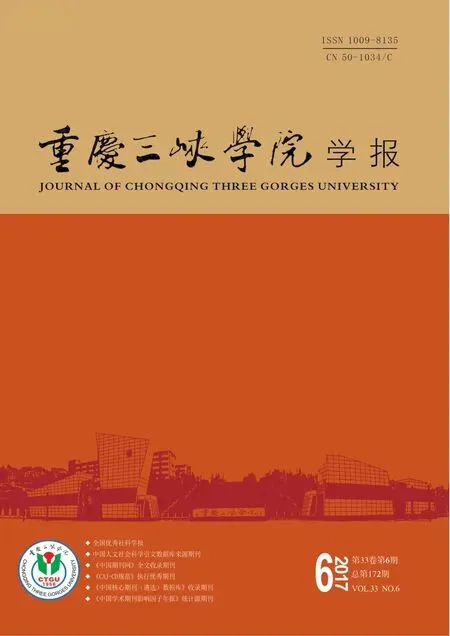地域文化视野与两湖现代文学研究
刘保昌
地域文化视野与两湖现代文学研究
刘保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 430077)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两湖现代文学,需要辩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动态与静态、地域内与地域外、文本与理论、种族环境与地域文化、自我“他者化”与外在“他者化”等关系问题。两湖现代文学可以也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地域传统文化的现代呈现,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开拓;地域书写是两湖现代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地域文化的现代书写加强了两湖现代文学创作中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蕴和精神纵深度,增强了富含地域特色的文学魅力;地域文化促进了两湖现代作家创作理念、表现形态和艺术精神的形成,推动了传统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塑造了两湖现代作家的艺术个性;两湖文化传统在现代文学中有特色彰明的精彩呈现,并对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精神和现代文学审美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地域文化;两湖现代文学;美学准则;乡土文学;文化结构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两湖现代文学,几乎与两湖现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进程同步展开,也与其他地域现代文学研究相伴而行。何西来认为,“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是在国人的世纪反思潮流中被提上日程的”[1]。尤其是1985年以后,这种地域文化反思潮流愈发来势凶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理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的激烈振荡,地域意义层面的外面世界和时间意义层面的现代未来双向同时打开,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感到情感振荡、内心惶惑之余更加重视当下的此在、此地,更加迫切地想要确证、追溯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地域文化因其悠久的传统性、亲切的此岸性和熟悉的日常性,引人流连,容易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被文学创作所重视。
在小说创作领域,地域文化已经成为重要的“小说美学准则”,诚如丁帆教授所云:“从鲁迅、沈从文、茅盾、巴金、老舍到新时期‘湘军’‘陕军’‘晋军’‘豫军’……的异峰突起,几乎是地域特征取决了小说的美学特征。就此而言,越是地域的就越能走向世界,似乎已是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共认的小说美学准则。”[2]
两湖青年作家马笑泉的《小说的三重结构》更是将小说中地域文化所呈现的价值和意义,归纳为小说“文化结构”的主要形式之一。他认为,在小说的语言、细节、人物,乃至小说氛围等“表层结构之下,有文化结构存焉。无论是千姿百态的行业文化如梨园文化、金融文化,难以精确定性但又确实存在的地域性文化如巫楚文化、吴越文化,还是国族性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亦或是更大范围内的宗教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均可以内化为文本的深层结构。小说虽不负有阐释此种文化的责任,但小说的语言、细节、氛围乃至人物的性格、心理,都是从这一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不但洋溢着该种文化的浓郁气息,而且小说的逻辑也符合这一文化的逻辑”[3]。此论的确是创作金针。但要将地域文化因素与小说文本水乳交融,不拼贴,不僵化,不突兀,不造作,在小说叙事的表相之下构建精妙的文化结构,其难度显而易见。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两湖现代文学,其前提当然是两湖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色彩斑谰的地域文化画卷,活跃着一批以地域文化书写为志业的作家,如鲁迅称许的“蓬勃着楚人的敏感与热情”的黎锦明,善于再现湘阴地方色彩的彭家煌,唱响湘西边城牧歌的沈从文,传神表达黄梅田园风味的废名,精确把握江汉平原地方风情的聂绀弩,将楚文化精神发扬光大的闻一多、胡风,文字洗练如雨后青山清新如茶子花开的周立波,展开湘南风俗画卷的古华,带着浓郁的两湖西部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黄永玉、孙健忠、蔡测海、叶梅、李传锋、马笑泉、田耳、于怀岸,书写两湖东部革命历史和乡村生活的刘醒龙、邓一光、何存中、林白,开掘长江中下游平原文化、保存历史记忆的刘继明、彭见明、达度、刘诗伟、王十月,立体表现汨罗乡村风情的韩少功,虚构出一片灿烂温暖的油菜坡村的晓苏,文字中巫风弥漫的残雪,攀爬上文坛神农架高度的陈应松,擅写长沙日常生活的何立伟和市井传奇的何顿,贴近武汉烟火人间的方方、池莉、彭建新、何祚欢,寻找楚人风骨的熊召政、任蒙、王开林、王芸,等等。
上述成名作家的群体性出现,并非偶然。诚如丹纳所说:每一个杰出艺术家的横空出世,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总会“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也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家宗派或艺术家家族”[4]5-6根深才能叶茂,两湖地域文化书写成为一种群体性选择,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当然离不开博大精深的两湖地域文化基础,离不开两湖地域人们的集体性的感觉文化认同。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两湖现代文学的相关学术成果,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宏观理论探讨。国外有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自然气候论、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西欧文学南北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历史的地理基础”论、泰纳《艺术哲学》的种族、环境和时代论等。在我国古代则有《诗经》采辑十五国风,《礼记》“异制异俗”论,《文心雕龙》“楚人多才”论,《隋书》“江左河朔”文学风格之辨。此外,司马迁、班固、李延寿、袁中道、王夫之、顾炎武、沈德潜等也有相关论述。近代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涉及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联。1980年代以来,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以及李继凯、毛迅、邹建军、段从学、陶礼天、郝明工、李敬敏、周晓风、徐明德、张明、曾大兴、靳明全、张伟然等人的相关论著,都从宏观理论视角,探讨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第二类是区域个案与相关专题研究。如杨义、吴福辉的京派海派文学研究,王嘉良、黄健的两浙文化与现代文学研究,李怡、陶德宗的巴蜀文化与文学研究,段崇轩、傅书华的三晋文化与现代文学研究,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王齐洲、王泽龙的《湖北文学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等“省域文学史”撰述,以及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周仁政《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龚敏律《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楚文化》、《光明日报》“作家群现象”笔谈等专题研究中,都涉及到楚文化与两湖现代作家、作品的关系。刘洪涛的专著《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5]虽然以“湖南乡土”命名,却并没有被“湖南省”这一行政区划所囿拘,重点探讨沈从文、周立波及其影响下的作家群体与湘楚文化的意义关联,论著中的西部民族文学、先楚文化、近现代湖湘文化等概念及其内涵,虽然限于论题范围没有充分展开,却无疑具有两湖地域的共性特征。这些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三类是在地域文化视野下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涉及或者重点论述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如田中阳的《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重点论述区域风俗、地域方言、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当代小说的重要影响与规范,兼具宏观理论高度和地域个性色彩,该书认为:“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样孕育着小说家,塑造着小说家的主观世界。尤其是区域文化中的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因素,影响着小说家的包括直觉或感受方向在内的主观世界,诸如精神气质,情感内涵,表情达意的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等。因此他本身就成为某种区域文化的载体和体现者,以至于形成了与这种区域文化同质同构的心理定势。”[6]24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7]将中国当代文学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划分,分别研究北方文化系统中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和南方文化系统中楚风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以及城市文化中的京味小说、海味小说、汉味小说等。贾剑秋在《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8]中以关东作家、中原作家、西南作家、荆楚作家、浙江作家、台湾作家等来划分和命名中国各个地域的作家,对其创作进行文化审视,尤其注重凝聚于小说人物形象身上的风俗民情环境因素,论点令人信服。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9],着眼于乡土小说的发展流变,以历史时间为经线,以小说家与地域乡土为纬线,纵横交织探究地域乡土与小说书写的复杂关系,涉及到的两湖地域乡土作家有废名、沈从文、彭柏山、冀汸、周立波、韩少功、方方、池莉等。黄道友的《地域文化与新时期湖北文学》[10]从地域文化属性的角度,将当代湖北文学分为鄂西、武汉、鄂东三个文化区域,分别论证李传锋、叶梅、陈应松、方方、池莉、林白、刘醒龙、邓一光、何存中等人的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以上成果都没有对“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作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同时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提升不够。无论是宏观理论研究,还是区域个案研究,沿袭传统的“文学南北论”和“文学东西论”的论述思维,都会显得较为空疏;既有研究成果对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风土人情、时令节俗、地貌风物、方言俚语等浅层性特征较为关注,对两湖地域文学特征、人文环境和文化心理结构开掘不深;对作家主体的创造性和地域文化的流变性关注不够,地域文化与文学文本的关联研究较为勉强,有些成果甚至陷入封闭性的“循环互证”,不可自拔,最终形成僵化的文化决定论。二是实证研究不够。没有很好地实现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的有效结合;对两湖地域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不够、研究不足,对文本的审美体贴不够;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历史现场感不强,文化空间还原不够;从线性历史中总结、归纳出的文化经验或规律,在论述中往往被“固化”或者“单面化”,没有充分关注到时间性历史形态的地域文化经验叠加的复杂性。
有鉴于此,我们采用地域文化的中观视角,研究两湖文学创作中的诸多事项和问题,具体来说,一是从文本出发,以文学化的地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注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创性的文学史贡献;三是分辨具体文本中关于地域文化的经验性书写与想象性书写,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意义;四是在文化、文学层面研究地域与世界的相通性;五是注重地域文化的流变性和嬗递性,寻找到“变”与“常”的辩证演进规律;六是从文本出发,寻绎作家的童年经验和成长环境对其创作的重要影响。
开展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可能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形成学术突破:一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突破。此项研究系中观性的新选题,是对既有的省域文学研究、具体作家作品与地域文化对应研究等学术范式的突破,两湖文学有共同的高势位的楚文化源头,楚文化具有极强的横向辐射力和纵向影响力,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具有行政区域和文化传统的诸多地域共性,综合研究两湖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可以有效规避分省域研究的重复与视域的狭窄。二是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的突破。中观选题可以形成学术研究的必要张力,既能在具体作家、作品等微观层面将材料弄扎实,进行地域文化的生命还原,又能在跨省域的宏观层面进行必要的理论提升,再现地域文化的强劲活力,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文学史意义上的理论借鉴。
在研究视域上,我们将两湖地域文化与两湖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整体,突破省域文学研究模式,突破既有文学研究的政治性、现代性框架,通过“双重发现”将地域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纳入考察视野,以中观视角切入,兼顾微观文本解读与宏观理论研讨,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灵活性、张力性和借鉴性。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将通过实证性研究,经由“文化还原”,回归历史现场,揭橥两湖现代文学地域性、反思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相交织的真相;结合现代文学文本、两湖地域文化典籍和民族风俗等材料,相互参证,注重两湖现代作家的主体创造性和个体差异性,在传统文化的动态新变中考察其与区域现代文学的关系,是对以往研究多以地域文化特征论证作家创作、以作家创作印证地域文化特征的“封闭循环式”论证模式的突破,更具开放性。
而以现行行政区划作为论证依据的省域文学研究,虽然存在着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可行性,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国别文学史就是扩大的省域文学史,但省域文学史却又事实上在学理性方面为不少学者所诟病。如李仲凡、费团结就认为:“首先,以当代政区作为划分文学地理的单位,忽视了山脉、河流、湖泊、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在文学地理单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这种做法忽视了民族、宗教、语言、生产方式等人文地理要素对文学的影响。再次,这种做法忽视了历史上政区变迁对于文学分布的内在影响。”[11]5因此,我们将两湖现代文学视为一个感觉文化整体进行研究,同时在这个感觉文化整体之中,又以文本为依据划分若干亚文化地域,如武汉、长沙、武陵、神农架、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东部山地等等,这种圈块结构的文学地域划分,与两湖现代文学发展实际庶几近之。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两湖现代文学,需要辩证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
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两湖地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现代时段位于传统长河的下游,在作为地域文化源头的楚文化之外,从秦汉迄于民国,两湖地域文化不断吸纳其他文化支流,加上时代主流文化的重要影响,现代两湖地域文化色彩斑斓,需要我们辩证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不胶柱鼓瑟、抱残守缺,亦不与世俯仰、任意发挥,而要善于寻找和发现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动态结构,在充分观照文化传统的同时,也需要格外注重两湖地域的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化生态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地域传统与现代精神之间形成的文化张力可能会令我们耳目一新。
二是动态与静态的关系。两湖地域文化本来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我们在总结地域文化特征和提炼地域文化精神时,往往是一种抽象的归纳。与静态的文化特征论和文化精神论相对照的,则是地域文化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和变动不居的动态现实,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处理好文化的动态与静态的关系。同时,作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也要予以辩证的关注,作家的出生地、童年和少年所生活的故乡,属于“静态分布地域”;作家成年后的外地求学、迁徙谋生、四海漂泊等,属于“动态分布地域”。静态分布地域的文化对作家往往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说过:现代小说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失去的家园的乡愁”。俄国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对于诗人或者作家来说,童年生活是“最可贵的礼物”:“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要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长的冷静的岁月中,没有丢失这件礼物,那么他就是个诗人或者是个作家。说到底,诗人与作家之间的差别是不大的。”[12]26-27而动态分布地域的文化影响,一般来说,是在静态分布地域的文化“前结构”过滤下选择的结果,一旦经由作家主体的积极认同和创造性发挥,动态分布地域的文化呈现,也可能达到精彩绝伦的程度。如宋人马存在《赠盖邦式序》中分析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行文“有奇伟气”的原因时说:“南浮江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观之,岂不信哉!”以当代作家周立波为例,他本是湖南益阳人,“40年代他在东北参加土改,一部《暴风骤雨》就写得粗犷、豪放,一如那片林海雪原的风格;50年代他回湖南参加合作化运动,又以清新秀丽的《山乡巨变》传尽湖南山水的灵秀!两种风格,统于一身,不正好揭示了文学与地域的缘分么?”[7]279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此之谓乎!于此可见作家主体性创造的积极能动性和审美选择性功能的强大。地域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就是如此意义重大!为了不至于产生凌空蹈虚的论述,我们将以作家的文本呈现作为论证的唯一基础和理论前提。
三是地域内与地域外的关系。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两湖现代文学,作家文本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无疑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研究对象。这就意味着,两湖作家书写两湖地域文化的作品当然是我们的重点考察对象,两湖地域之外的作家书写两湖地域文化的作品也是我们的重要考察对象,而那些没有书写或者很少书写两湖地域文化的作家及其创作则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地域文化特征不强烈的文本我们将会舍弃,即使该作家是两湖地域的终生土著或者著名作家也不例外。陈思和在评价张鸿声的著作《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时,就特别指出:“不管作家是否在上海居住,只要他的创作是有关上海的描写,就能列入‘想象’的谱系,呈现出‘文学上海’的面貌。”[13]4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可以称为“文学的两湖”,即以文本中的两湖地域呈现及其审美意义和价值表达作为研究重心,并不认为作家的籍贯、出生地、生长地等地域性因素与其创作之间具备必然的意义关联。
四是文本与理论的关系。新时期以来湖南高校所编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经历了从“外部研究”到“内外结合”的转变过程[14]。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已经形成僵化的理论模式,其学术操作步骤如下:界定某地域文化的特质——形成双向互证研究格局,以地域文化特质证明地域作家作品,以地域作家作品证明地域文化特质——片面注重历时性的地域文化构成——对地域文化作出积极的、正面的价值评估。形成这种僵化的理论模式,原因在于对“地域文化性质的界定在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内部预设了作为前提的宏大叙事,构筑了关于自身独特本质的神话,再以历时的几个特点进入到对作家和文学现象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将研究对象提纯,将丰富的作家精神世界和文学现象以简单的几条性质来割裂和泛化,形成一种决定论的思维方式”[15]。地域文化特质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循环论证,无疑是一种封闭性的理论操作,缺乏文学研究所必需的开放精神;同时,从历时性角度将地域文化静止化、凝固化,无疑也是一种机械主义的僵化运作,缺乏对于文化流动性、交融性、变异性和主体创造性的充分考量。诚如杨义所说:“讨论地域文化,千万不要将之看作封闭的、凝固的系统,而应该如实地看到,它只不过是中华大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子文明、一个分支系统,而且是以其独特的因缘和相互的关系,而经常变异着的子文明或分支系统。正因其变,才在总体上形成中华文明多姿多彩的活力。”[16]90我们认为,回归文本是唯一可行的路径,文本的丰富内涵将是冲破历时性固化传统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五是种族、环境与地域文化的关系。1864年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写道:“欧洲人的智力、精神以及身体的素质都是优等的;曾经使他在几个世纪里从野蛮的游牧部落状态上升……到他现在的文化和进步的状态……的那种同样优越的力量和能力,使他能够在与野蛮人的生存斗争中征服对方,以野蛮人的牺牲作代价来扩展自己的势力。”[17]162针对此种种族论,汤因比分析说:“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以‘种族’原因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做法相当流行。人类在体质上的种族差异,不仅被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而且还被当成人类心理方面的、永恒的种族差异的论据。人们以为,这些差异是我们亲身见到的各人类社会具有不同的命运和成就的原因。然而,目前西方流行的种族主义,与现有的科学假设风马牛不相及。像这样如此强烈的偏见不能用如此理智的原因来解释。现代西方的种族偏见既是对西方科学思想的一种歪曲,又是对西方种族感情的一种虚伪的思想反映。”[18]64事实上,单纯的种族决定论和单纯的环境决定论,都以其学理的偏执及其与现实的冲突而无法成立,因为任何时候、任何事实都有例外,任何静态的论证结论都无法适应永恒运动的现实世界。但是,汤因比也并没有因此否定种族和环境对地域文化所起的作用,其《历史研究》第十五章《艰苦环境的刺激》指出,“艰苦的环境对于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18]95。汤因比坚定地认为,“挑战和应战”是产生人类文明的重要动力。这与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糜非斯托的功能相似,在《天堂里的序幕》中上帝告诉糜非斯托:“人在努力时太容易松懈,/很快会爱上绝对的清闲;/因此我乐意造一个魔鬼,/让他刺激人,与人作伴。——/而你们真正的神的孩子啊,/享受这生动而丰富的美吧!/永恒的造化生生不息,但愿它/呵护你们,用温柔的爱之藩篱。/世间万象飘飘渺渺,动荡游移,/坚持思考,把它们凝定在心里。”[19]17上帝因此将糜非斯托称为“否定的精灵”,派他下到凡间人世,“让他刺激人,与人作伴”,以“否定”的力量,引导人们在“挑战和应战”之间前行。从强调差异性的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两湖现代文学,既要关注到两湖地域环境对于地域内人们性格、精神的塑造,地域内人们对环境的挑战和应战的历史过程,也要警惕种种诸如“湖南人”“湖北人”“南方人”“湘西人”“武汉人”等潜藏着种族、血统含义的冠名所带来的文化前见和偏见。种族、环境决定论都不可取。
六是要警惕地域文学研究的自我“他者化”倾向。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现代文学,是因为认识到地域文化因素对于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0],因此,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者的首要关注点,在研究方法上,一般总会“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20]。毫无疑问,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域,是对现代文学整体性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但是,这种对于地域文化独特性的“审美偏执”,这种对于地域文化风情的“奇观化”展示,在有的学者看来,仍然是“为了建构关于现代文学的大叙事”,即“建构关于现代文学的大叙事这个先在的目的,引出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的需要”[21]。现代性大叙事的迷误在于时间膜拜,以时间统驭空间,将地域文化的功能性差异编排进先后早晚的时间序列,各种偏远地域被想当然地“安排”进时间序列的前现代阶段,供人凭吊和感伤,而无法形成共时性的有效的平等对话关系。一方面,对地域文化、文学独特性的强调,具有质疑和破解中心文化霸权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叙事的现实功能;另一方面,在地域文学研究中,我们也需要警惕自我“他者化”倾向,即不能凭空构建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本质神话,在共时性对话的表相之下重复着自说自话的个体独白。
从地域文化视野切入研究,我们会发现:两湖现代文学可以也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地域传统文化的现代呈现,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开拓;地域书写是两湖现代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地域文化的现代书写加强了两湖现代文学创作中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蕴和精神纵深度,增强了富含地域特色的文学魅力;地域文化促进了两湖现代作家创作理念、表现形态和艺术精神的形成,推动了传统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塑造了两湖现代作家的艺术个性;两湖文化传统中上下求索九死未悔与冷眼观世逍遥自适的精神张力性结构,在两湖现代文学中也有特色彰明的精彩呈现,并对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精神和现代文学审美品格的形成,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两湖现代文学不是西方现代性的横向移植,而是根植于地域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两湖作家以自己的方式继承、改造了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和精神传统,建构了新的文学表现场域、美学形态、艺术精神和意义空间。
[1] 何西来.关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40-56.
[2] 丁帆.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J].学术月刊,1997(9):44-50.
[3] 马笑泉.小说的三重结构[N].文艺报,2016-8-26(02).
[4] 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 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6] 田中阳.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 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 贾剑秋.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M].成都:巴蜀书社,2003.
[9]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黄道友.地域文化与新时期湖北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11] 李仲凡,费团结.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2]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戴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3] 陈思和.序[M]//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 向点思.从“外部研究”走向“内外结合”——新时期以来湖南高校所编文学理论教材简评[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4):153-155.
[15] 邓伟.地域文化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另一思路[J].文艺理论研究,2006(4):116-121.
[16]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7] 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下卷[M].胡万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8]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9] 歌德.浮士德[M].杨武能,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20]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创作,1995(1):9-11.
[21] 段从学.地域文化视角与现代文学研究[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4-17.
(责任编辑:李朝平)
Regional Culture Horizon and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of Hubei and Hunan
LIU Baochang
To study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of Hubei and Hu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research, it need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dialectically, such as tradition and modern, dynamic and static,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 text and theory, race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culture, self-“otherness” and external-“otherness”, etc.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of Hubei and Hunan should also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which is both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a modern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tradition. It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s. Besides, regional writing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modern literary nat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Hubei and Hunan. The modern writing of regional culture strengthened modern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depth of connotation and spirit and enhanced the literary charms that are rich in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promoted modern writers’ creation concept, manifest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artistic spiri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shaped the writer’s individuality.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Hubei and Hunan were magnificently presented in modern literature, thus formed the concept of modern literature, modern literature spirit and modern aesthetic character.
regional culture; modern literature of Hubei and Hunan; aesthetic standards; vernacular literature; cultural structure
I206.6
A
1009-8135(2017)06-0082-08
2017-09-21
刘保昌(1971—),男,湖北仙桃人,文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14BZW1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