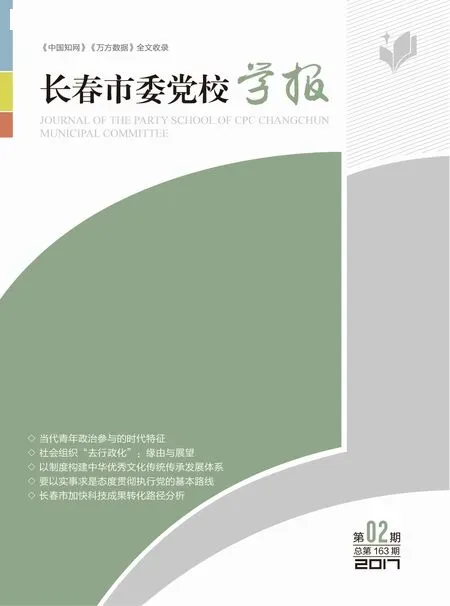领域法学: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文/张学博 李玉云
领域法学: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文/张学博 李玉云
法教义学者和社科法学者们都意识到传统的知识和方法已经无法指导不断涌现的新的法学学科研究了,但双方并没有关注到制约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部门法学所形成的壁垒。研究方法的争论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部门利益才是根本问题所在。在这个法学困局之下,财税法学者首次提出了新的法学研究范式——领域法学。
法教义学;社科法学;领域法学
改革开放三十八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学研究也迎来了春天。当年的冷门学科今天俨然已经成为社会中的显学。法学研究也经历了跑马占地,再到今天学科众多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三十多年的法学研究中,有两大方法论占有显赫的地位。一个是法教义学,另一个是社科法学。法教义学主要是民法和刑法等传统部门法学科,而社科法学则主要是以法理学界为代表。两方学者均声称自己是未来法学研究的主流。苏力声称“大约30年后,法教义学的研究——有别于教学,很可能不再能进入中国顶尖高校法学院顶尖学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会转移到二流或三流法学院中去。”[1]而法教义学学者则认为:“如果法学研究不能确立或者至少是理解法教义学的视角,中国未来的法治很难让人有乐观的期待”。[2]两方学者近年来均发表了不少文章进行论战,对未来法学研究流派和格局之形成有重大影响。所以,作为既非法理学科,又非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有必要对此两者进行认真审视,以便找到符合学科特点的研究道路。
一、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由来
作为研究方法而言,法教义学目前有几种比较权威的定义。正如诺依曼所说,“法教义学要以对一国现行实在法秩序保持确定的信奉为基本前提,这也是所谓的‘教义’的核心要义所在。”[3](P17)王泽鉴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的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与解释工作的规范科学”。[4](P11)但是今天的法教义学已经融合了德国学者的观点,不仅局限于传统的以法条解释为核心,而是升级为法律解释学,将自己的领域不断扩展,甚至到了公共政策等无边界的领域。如果有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介绍什么是法教义学,还是苏力的理解比较明了:“主要关涉制定法的司法解释,但除了制定法、判例外,也包括个别部门法学者长期奉行的学说,如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这是以规范和教义为中心的研究”。[1]
社科法学则在十余年来异军突起,现在俨然已经与法教义学成分庭抗礼之势。用苏力本人的话来说,“社科法学是针对一切与法律有关的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也集中关注专业领域的问题(内在视角),同时注意利用其他可获得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包括常识(外在视角)”。[1]如用孙少石的话来描述则更加形象:“这些青年一代结合他们自身的生活经验,杂糅其他学者的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有他们自己特色,但内在理路却又一气相贯的旁支,如侯猛的司法制度,陈柏峰的乡村问题,王启梁的边疆治理、法人类学研究,尤陈俊的新法律史,桑本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甚至还有触及自然科学的,如李学尧的法律与认知科学。”[5]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社科法学在法学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其影响从传统的法理学者不断向其他部门法学者扩展。
二、两者之异同、优势和缺陷
尽管社科法学已经异军突起,但是法教义学者们并非日薄西山。下面将对两大学派的异同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首先,法教义学者们以传统的民法、刑法学者为主。而社科法学尽管经过了十多年发展,仍然以法理学者为主。十多年前,法理学者就宣称法条主义者没有前景,但是今天法条主义者们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挖掘了新的学术资源,与德国法接轨,仍然牢牢占据着学术的主流地位。尽管今天中国的法律体系构建中,不断引入英美法的内容,但是以德国法为主导的学术思想仍然牢牢占据着法治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国的法律体系仍然以大陆法为主体,短期内看不出有任何变化的迹象。法教义学者们占据着绝大多数学术资源,以成文法来解决现实纠纷的思想仍然占据着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
其次,社科法学严格意义来讲,并非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法学学科中来。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确精妙,但是法教义学者们以实定法的解释者自居,不论何时,仍有其存在之价值。
再次,法教义学虽然掌握了最多的学术人马和学术资源,但是按照部门来进行法律部门划分的确已经无法适应法学学科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法律本身是经济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法学学科在产生,按照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划分来确定学术资源和发展空间,的确已经不合时宜。社科法学虽然没有颠覆法教义学的主导地位,但的确由法理学者们向传统部门法学者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跑马占地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个学科需要自己的学术空间。可以说,之所以社科法学由法理学者们产生,正是市场机制倒逼的结果。法理学者们最有危机感,他们很难与市场经济亲密拥抱,所以必须在学术市场上随时保持一种危机感。最关注司法改革的是法理学者,对社会事件最关注的往往是法理学者,最关注研究方法的也是法理学者。
某种意义上,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论战是法学研究的一场危机。当法学学者们还在各种毕业生致辞上为法治春天而自豪时,法学专业毕业生已经成为史上最难就业的专业。①这实际上是一个隐喻,即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法学是一个实践科学,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文科学。
三、领域法学: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两方论战之际,财税法学者提出了“领域法学”的概念。在新兴的法律学科中,包括金融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互联网法,体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学科中,财税法学者首次提出了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实际上法教义学者和社科法学者们都意识到,传统的知识已经无法去指导不断涌现的新的法学学科研究了。但是法教义学者们和社科法学者们都停留在对研究法学的争论上,而没有关注到制约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部门法学所形成的壁垒。研究方法的争论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部门利益才是根本问题所在。部门法学者之所以要以法教义学方式捍卫自身学科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实质是因为他已经占据了重要的领域,不希望别的研究者们进入到此领域,所以要构建专业槽。而法理学者们之所以打着社科法学的旗号,表面上是研究方法的论战,其实质还是因为法理学本身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学术资源,他们必须到别的学科挖掘学术资源。双方其实心知肚明,却又义正言辞。
正是在这个困局之下,财税法学者提出:“领域法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交叉性、开放性……但又在方法论上突出体现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鲜明特征,是新兴交叉领域‘诸法合一’研究的有机结合,与部门法学同构而又互补。”[6]说到底,每个学科都希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直到如今,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等传统学科的争论仍未有彻底终结,多少新学科为自身的独立性耗费大量资源去论证。可以说,领域法学的提出正当其时。改革是问题倒逼的。如果一定要说“领域法学”理论是一门“找位置”的学问的话,“领域法学”不仅仅是为财税法学找到了最为适合的位置,也不仅仅是为所有法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找到了适当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为整个法学在这个“法律现象领域化”或者说“法律问题综合化”、“社会问题跨领域化”的时代找到了自己最为适合的位置。[7]
四、领域法学的主要特征
首先,领域法学秉持实定法规范和实定法秩序的实用主义研究立场,主张打破部门法桎梏,以问题意识为关怀起点,以经验研究为理论来源,综合借鉴与运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成熟方法进行研究。[6]在这一点,领域法学并不与传统的法教义学发生冲突。领域法学并非对于法教义学的颠覆。社科法学对于法教义学的冲击,主要是一种研究方法的颠覆。在社科法学者看来,法教义学代表了一种法学界的保守势力,是墨守成规的把持者。正因为法教义学的强大势力使得青年学者必须找到新的出路。某种意义上讲,社科法学是在别的学科找到利器来对法教义学进行颠覆。如孙少石所言:“一个语词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层面,将不只有交流沟通的功能,它会类似于标签,还存在着与权力意志如影随形的诸如甄别、分类、促人“站队”的功能……使用者未必自觉、但也势必带入这样的利害关切。”[5]相反,领域法学则是兼容性的。他以实定法的秩序为前提,并不冲击法教义学本身的领地,只是代表着包括财税法学、知识产权法、网络法等新兴法学学科自身学术研究拓展的需求。这是一种立体共赢的思路,并非以挑战者姿态出现。
其次,领域法学呈现开放性和立体性。传统的部门法体系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进行学科划分,具体表现为法学内部二级学科的相对封闭。各个学科之间相对比较封闭,各个学科的学者之间很少交流,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进行研究,缺乏开放的心态。“规范法学研究者把本来属于一个整体的法学研究予以肢解,使得宪法、刑法、民事、行政法和诉讼法的研究相互隔离……‘一亩三分地’……对于超出自己学科领域的法律问题,既没有解释的能力,也没有研究的兴趣。”即便是向法教义学发起挑战的社科法学,并没有走出这条老路,仍然是重复他人昨天的故事,只不过是试图以新的圈子代替旧的圈子。如此的挑战很难让人信服。而领域法学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进行学术门派划分,不以某个学科化分界线,每个学科、每个学者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自由进行交流。在领域法学的理念之下,每个学科,不论是传统的部门法学科,还是法理学科,或者新兴的如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学科,都不仅可在自己的领域安身立命,不用担心别的新的范式的挑战,而且可以与其他领域的学科、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并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互相之间也不用发生冲突。
再次,领域法学以问题为中心。法教义学最大的特点在于追求法学学科自身的圆满性,试图找到一种法学学科自身存在的理由,所以其所有的研究立足于法律文本的解释,最多扩展到司法判决对法律解释的影响,并对公共政策适当的予以考虑。但不论如何,法教义学的根本其实就是规范法学,也就是以规范和应然为价值取向的法律科学。其核心是价值导向的。而社科法学则以研究范式为导向,追求价值无涉,追求法律背后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其实质是以社会和实然为取向的社会科学。但是中国的社科法学与国外那些其他学科出身研究法学的学者还有一个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科法学学者多数是野路子出身,本身对于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工具的运用并不熟悉,所以往往沦为一些常识的论证。“一些社科法学研究经常将一些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既有理论。或许,这种研究足以论证规范法学是存在缺陷的,也是无法解决中国法律问题的。但是,这种零零散散的研究,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成体系的理论呢?”[8]所以,研究方法固然重要,围绕问题为中心,才是法学研究更应该关注的重点。法学研究不论运用哪种方法,目的都是法学法律条文背后真实的规律,提出对中国法律实践富有解释力的法学理论。
[1]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学[J].法商研究,2014,(5).
[2]张翔.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J].法学研究,2012,(6).
[3](德)乌尔弗里德·诺依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意义法哲学与法社会论丛(第5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孙少石.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对社科法学的述评[J].交大法学,2016,(1).
[6]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J].政法论丛,2016,(5).
[7]梁文永.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J].财税法学动态,2016,(61).
[8]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J].中外法学,2015,(1).
张学博,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财税法、经济法学和法律经济学。
李玉云,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民族宗教。
责任编辑李冬梅
D913
10.13784/j.cnki.22-1299/d.2017.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