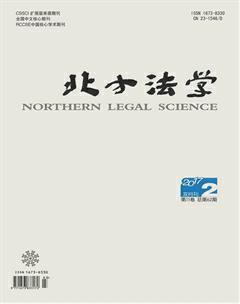论单方面石油活动在海洋划界中的意义
董世杰
摘 要:争端当事国的单方面石油活动要想成为海洋划界的考虑因素,必须通过其单方面石油活动证明存在临时协议、默认、明示或默示协议。由于临时协议仅具有历史意义,而明示协议在实践中又不可能出现,那么只能寄希望于默认和默示协议。主张默认或默示协议的当事国,负有很高的举证责任,而成功的先例更是寥寥无几。其他声索国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非法实施的单方面石油活动,一直为中国政府所反对,自然不能作为日后海洋划界的考虑因素。
关键词:单方面石油活动 海洋划界 临时协议 默认 明示或默示协议
中图分类号:DF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7)02-0140-09
争端当事国在争议海域的单方面石油活动,能否作为划界的考虑因素,是海洋划界过程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研究该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南海其他声索国一直以来都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实施大量的单方面石油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这些单方面石油活动到底会对最终的海洋划界产生何种影响。为了更好地阐释单方面石油活动对海洋划界的影响,笔者将现有的相关国际判例分成两类进行分析:“不作为划界考虑因素”和“作为划界考虑因素”。
一、不作为划界的考虑因素
在1982年“利比亚—突尼斯大陆架划界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与确定划界方法高度相关的情况就是当事国的行为,但在分析当事国的石油活动后,国际法院并没有发现当事国之间存在默示协议(Tacit Agreement)。①通过对国际法院判决的分析不难发现,如果能够通过当事国先前的石油活动证明默示协议的存在,那么当事国的石油活动就是确定划界方法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际法院未能通过当事国的石油活动得出默示协议,但是却认为,当法国和意大利分别负责突尼斯和利比亚对外关系时,法国和意大利就渔业管辖权的分界线所形成的临时协议(Modus Vivendi),应当作为大陆架划界的考虑因素。1913年发生了意大利的鱼雷艇在突尼斯主张的ZV45°线②以内海域逮捕希腊渔船事件后,意大利划了一条与加迪尔角(Ras Ajdir)海岸线垂直的界线,意大利当局在1931年再次重申了这条界线,这一情形持续到突尼斯和利比亚独立。在此期间,负责突尼斯外交的法国当局一直沉默和不抗议,国际法院认为这足以证明临时协议的存在。虽然仅凭临时协议尚不能证明两国之间存在公认的海上边界,但是对于临时协议的尊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正式反对,这可以确保在选择两国间大陆架的划界方法时,它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性理由。参见前引①, paras.93—95.尽管该案中临时协议的出现只与渔业问题相关,但仍为后来“缅因湾划界案”中加拿大主张石油活动应当作为划界考虑因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因此,“利比亚—突尼斯大陆架划界案”开创性地提出了判断当事国的石油活动是否应当作为海洋划界的考虑因素的具体方法,即能否通过当事国的石油活动证明当事国之间存在默示协议或临时协议。
在1984年的“缅因湾划界案”中,为了证明应当适用中间线作为划界方法,加拿大主张其在争议海域中间线的加拿大一侧所实施的石油勘探活动获得美国方面的默认(Acquiescence),两国的实践也表明,它们已经就中间线作为双方石油特许权区域之间的界线达成临时协议,因为加拿大所主张的中间线与美国所主张的线出现重合,这两条线重合的情况,至少从1965年到1972年一直被当事国双方以及许多石油公司所尊重。参见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4, paras.128, 131, 132, 135, 149.可见,加拿大极力主张其石油活动应当作为确定最终划界方法的考虑因素。但是国际法院分庭的判决,并没有支持加拿大的这一主张。理由是:(1)國际法院分庭无法得出美国默认在乔治浅滩(Geogres Bank)划界中使用中间线的结论。分庭认为,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海上边界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之前,美国的态度一直不明确并且有相当的不一致。加拿大所提供的事实不能保证得出以下结论,即美国政府彻底地承认中间线作为两国大陆架管辖权的边界;也不能保证仅仅因为对于加拿大从1964年到1969年11月间所发放的勘探许可证,美国政府没有作出回应,就在法律上阻止美国继续主张沿着东北海峡的边界,或者阻止美国主张调整后的垂线的西南部所有区域。虽然在加拿大颁发第一个勘探乔治浅滩的许可后,美国保持沉默展现出它一定程度的轻率,但是任何试图将禁止反言的法律后果归因于这个短暂的沉默,似乎有点过分。根据上述分析,国际法院分庭认为,仅仅由于美国的迟延,就认定其已经默认同意加拿大的主张,或者放弃其权利,显然逾越了援引默认所必需的条件。参见前引④, paras.137, 138, 140—142. 通过国际法院分庭的分析可知,对于加拿大在争议海域的石油活动,美国政府没有及时提出抗议,并且这种状态持续了数年,但是在国际法院分庭看来,尚不构成默认,只是被认定为迟延。可见,在默认的认定过程中,对于时间要素有着较高的要求。(2)国际法院分庭也没有发现存在临时协议。分庭认为,即便假设在当事国各自颁发许可证的区域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界线,这也不能认为,与“利比亚—突尼斯大陆架划界案”中国际法院得出结论所依据的情形具有可比性。此外,即便根据加拿大的观点,从1965年到1972年,至少是临时协议的形成时期,但在分庭看来,这一段时间太短,即使事实正如加拿大所宣称的那样,当事国双方的石油活动都没有逾越重合的界线,也不足以产生此种法律效果。参见前引④, paras.150—151.由此可见,时间因素对于临时协议的形成同样至关重要。通过对“缅因湾划界案”的分析可以看出,争端当事国虽然可以主张其石油活动获得其他当事国的默认,或者当事国之间已就石油活动的范围达成临时协议,但是在认定默认或临时协议过程中,对时间要素有着较高的要求。
在“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划界案”中,马耳他认为,利比亚为部分石油特许权区域所确立的北部边界,使得许可证获得者不得在中间线以北区域进行石油活动,这表明了利比亚对马耳他所主张的中间线的默认。当事国已经通过其行为表明,中间线与本案最终划界非常相关。但是国际法院却很简洁地否定了马耳他的主张,国际法院认为双方争端的历史,以及当事国有关大陆架的立法和勘探活动,无需详细列明,国际法院认为其无法从其争端历史中找出任何值得考虑的事情,在本案中无法对任何一方的行为模式进行识别,以便充分明确地构成默认。参见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a/ Malt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5, paras.24—25.
在“法国—加拿大仲裁案”中,对于双方当事国同时颁发的一些勘探许可,是否应当作为划界考虑因素的问题,仲裁庭认为由于双方相互抗议,当事国均没有实施钻探作业,这种情况下,仲裁庭没有理由去考虑潜在的矿产资源对划界的影响。参见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Areas between Canada and France: Decision in 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Areas,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31, No.5, 1992, para.89.仲裁庭之所以不将当事国的石油活动作为划界考虑因素,原因在于当事国的石油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其他当事国的反对,任何一方当事国都无法主张默认、临时协议的存在。
“喀麦隆—尼日利亚划界案”也就单方面石油活动会对争议海域的划界产生何种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在该案中,对于G点以南海域的划界问题,尼日利亚认为当事国所实施的有关颁发石油特许权以及开采石油的行为,会产生事实上的分界线,在确立海洋边界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待划界的海域内,国际法院不应该重新分配已由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和喀麦隆的实践所确立的石油特许权,国际法院在决定海洋边界走向时,应当尊重现有特许权的布局。国际法绝不会为了重新分配石油特许权而无视这些国家实践,因为由于重新分配而导致长期存在的石油特许权的变化,将会制造很大困难,也与划界中的公平考虑不相符。尼日利亚声称,喀麦隆所主张的界线,完全忽视了在争议海域大陆架上长期存在的、被尼日利亚和喀麦隆遵守的、有关石油勘探开发的大量实践,这将导致将原本属于尼日利亚或赤道几内亚的大量石油特许权分配给喀麦隆。尼日利亚认为,其在喀麦隆所主张的海域内的石油活动是长期公开的,在启动诉讼程序之前,喀麦隆从未提出质疑和反对,足以构成默认以及确立权利的基础。参见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Nigeria: 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 ICJ Reports 2002, para.282.作为回应,喀麦隆认为,在国际判例法中,石油实践在划界中只能赋予有限的意义。因为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是固有的,不取决于沿海国行使该权利。在G点以南不远区域,存在一个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三国特许权的重叠区域,因此该区域不存在一条事实上的分界线可以作为划界的基础。此外,喀麦隆还否认其对于尼日利亚特许权的沉默构成默认,因为尼日利亚当局并没将新的特许权通知喀麦隆。前引⑨, para.283.国际法院认为,“尽管在理论上,当事国之间就它们各自的石油特许权的位置达成明示或默示协议,可能意味着它们就各自拥有的海域达成合意。但是石油特许权和油井本身,不能被视为证明调整或改变临时界线具有正当性的相关情形。如果当事国的石油实践是基于当事国之间明示或默示的协议,那么应当予以考虑。但是在本案中,当事国双方并未就石油特许权达成协议,因此当事国的石油实践不是海洋划界应当考虑的因素”。前引⑨, para.304.通过对该案判决的分析可以看出,尼日利亚主张在海上划界中考虑石油活动的理由,仍是其石油活动获得喀麦隆的默认,或者当事国之间就石油活动的范围达成明示或默示协议。但是相较于先前的案件,该案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尼日利亚非常看重石油活动在划界中的作用,甚至将其上升到“决定性因素”前引⑨, para.303.的地位。
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领土海洋争端案”中,洪都拉斯认为,基于当事国双方之间的默示协议,两国之间存在一条以北纬15°线为界的事实上的界线。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洪都拉斯提出了一系列证据,其中就包括当事国双方的石油活动。洪都拉斯主张,自从1906年西班牙国王作出裁决后,双方有关北纬15°线的石油特许权实践是一致的,甚至沿着该线进行了协调,这足以表明存在默示协议。洪都拉斯指出,其在南至北纬15°线的区域颁发了一系列的石油特许权,并未引起尼加拉瓜的抗议;同样,尼加拉瓜在北至北纬15°线的区域颁发了一系列的石油特许权。洪都拉斯认为,尽管尼加拉瓜的一些石油特许权区域没有明确其北部边界,但由于尼加拉瓜石油特许权区域的布局和面积刚好契合将北纬15°线作为其北部边界,等于承认了该条界线的存在。洪都拉斯还特别提及科科马里纳油井(Coco Marina),这可以为尼加拉瓜明确承认有关海上边界的协议提供决定性的证据。这个由两国联合经营的横跨北纬15°线的油井,是由洪都拉斯联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 of Honduras)和位于尼加拉瓜的中美洲联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 of Central America)共同经营,并事先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参见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Honduras),Judgment, ICJ Reports 2007, paras.237—239, 257.國际法院认为:“有关存在默示协议的证据必须令人信服。确立一个永久海上边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能轻易推定存在默示协议。一条事实上的分界线,在某些情况下相当于存在一条经协议的法定边界,更多的时候仅具有临时分界线,或者基于特定具体目的分界线(例如分配稀缺资源)的性质。即使有一条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了便利的临时分界线,也与国际边界存在区别。”参见前引B13, para.253.对于洪都拉斯提出的将尼加拉瓜颁发的石油特许权作为默示协议的证据,国际法院认为,尼加拉瓜在其颁发的石油特许权中,通过使其特许权区域的北部边界处于尚未确定的状态,或者回避提及其与洪都拉斯的边界的方式,对自己与洪都拉斯之间海上边界问题保留了立场。虽然国际法院也注意到,在1961年到1977年的这段时间内,北纬15°线似乎与当事国双方的行为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国际法院认为其时间跨度短,不足以认定当事国之间存在一个法律上确定的国际海上边界。参见前引B13, paras.254, 256.
二、作为划界的考虑因素
在笔者所收集的判例中,“也门—厄立特里亚仲裁案”是唯一明确将当事国的单方面石油活动作为海上划界考虑因素的案件。厄立特里亚认为,众多石油合同的存在足以表明,应当沿着中间线确定海上边界,并坚称,仲裁庭在第一阶段所作出的判决支持了“历史性中间线”,应当将其作为两国海上边界线,并强调,在也门与外国石油公司所缔结的一些石油合同中,在不考虑争议岛屿作为基点的情况下,合同区域从也门海岸一直向西延伸到红海的中间线。厄立特里亚发现,其所缔结的一项石油合同的区域与也门所缔结的一项石油合同的区域,正好沿着中间线穿越大哈尼什岛(Greater Hanish)。厄立特里亚还指出,也门的一项石油合同中含有一条中间线,将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的被继承国)标在中间线以西,也门被标在中间线以东。在也门提交仲裁庭的一份地图中,两国石油合同区域的边界线正是沿着双方海岸之间的中间线延伸的。厄立特里亚认为,虽然当事国的石油合同本身不等同于相互接受中间线作为边界,或者接受一条临时分界线,但是在不考虑争议岛屿对海上界线走向的影响的情况下,当事国的石油合同为采用“历史性中间线 (Historical Median Line) ”划分红海海域,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基础。参见 The Eritrea-Yemen Arbitration (Phase 2: Maritime Delimitation), 3 October 1996, para.79.仲裁庭在其最终判决中将石油合同视为划界应当考虑的因素,“两国的海上界线应当是一条多用途的单一中间线,尽可能的是两国相向的大陆海岸线之间的中间线。这种方法不仅符合类似情况下的实践和先例,同时也为当事国双方所熟知……在不考虑岛屿争端的情况下,也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所缔结的海上石油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在厄立特里亚和也门之间的相向海岸以中间线划分各自管辖权”。参见前引B16, para.132.虽然仲裁庭直截了当地认定石油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间线的划界方法,但并没有给出这一结论的具体理由。笔者认为,通过双方当事国过去的石油实践,可以看出双方原先石油合同的地理范围一直沿着中间线划分,这就表明长期以来,双方当事国已经通过各自的实际行动,就石油活动的范围达成合意,这也足以支持本案中的石油合同应当作为划界的考虑因素。
三、判定单方面石油活动能否作为海洋划界考虑因素的标准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不难发现每一起案件中都有当事国主张应当将其先前的石油活动作为划界的考虑因素,但仅有一例判决是将先前的石油活动作为划界的考虑因素。这也印证了“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仲裁案”判决中的论断,“与资源相关的标准,在国际法院和仲裁庭的判决中会被谨慎对待,国际法院和仲裁庭并没有普遍地将这一因素作为影响划界的相关因素”。Arbitration between Barbados and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relating to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tween Them, Decision of 11 April 2006,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XXVII, 2008, para.241.即便如此,所有判决在分析是否应当将原先的石油活动作为海上划界的考虑因素时,其所适用的标准是一致的,即是否存在临时协议、默认、明示或默示协议。遗憾的是,上述所有判决并没有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详细阐述,只是零星地提及这一问题。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详细分析,以了解单方面石油活动在何种情况下,方才构成临时协议、默认、明示或默示协议的效果。
(一)临时协议
“临时协议(Modus Vivendi)”并不是国际法上的专门术语,其主要是指争端当事国在争端最终解决之前,达成的初步、临时或过渡协议。参见Wojciech Burek, Modus Vivendi,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www.mpepil.com, visited on 22 October, 2015.“临时协议是一个典型的有缺陷的国际法行为,通常都会被后来更为详尽和正式的国际协议所取代;临时协议通常不具备法律拘束力,其主要功能在于暂停有关临时协议规定的事项的冲突,以便当事国之间在争端解决之前,进行和平且富有成效的互动”。参见 W.Michael Reisman, Unratified Treaties and Other Unperfected A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nstitutional Functions,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35, No.3, 2002, p.738.临时协议通常用于指代非正式和临时的政治安排,必须和条约进行区分,条约是国际层面上当事国之间更为稳定的协议,如停战协议或者投降协议,随后会被实质性的和平条约所取代。参见 Don E.Scheid, Modus Vivendi, in Deen K.Chatterjee (ed.), Encyclopedia of Global Justice, Springer, 2011, p.705.早在1974年“英国—冰岛渔业管辖权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就对临时协议的内涵进行了阐述,“1973年的临时协议没有将自己描述为争端的解决,除了具有明确的期限外,无疑还具有临时安排的性质,既不损害当事国的权利,也不规定任何一方放弃有关争端事项的主张”。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v.Iceland),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4, para.38.这也就意味着,该案中的任何一方当事国,不得依据该项临时协议,妨碍国际法院依据争端事实本身作出判决,也不得迫使国际法院作出驳回一方法律主张的判决。对于石油活动同样如此,即使当事国之间因为石油活动达成某项临时协议,任何一方都不得将其作为支持自己划界主张的依据。正因如此,对于“利比亚—突尼斯大陆架划界案”认定临时协议作为划界考虑因素的做法,文森法官(Judge Evensen)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一项临时协议含有两个基本要素:首先,争端解决之前的临时协议具有临时性;其次,这一安排不得对当事国双方造成损害”。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 ICJ Reports 1982,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Evensen, p.292.“臨时协议”这一术语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及20世纪上半叶时,曾得到广泛使用,主要涉及渔业、海上划界以及商业关系,但是现在使用其表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做法已经消失,截止到2011年,联合国集中使用这一表述的条约共33个,最后一个的注明日期为1977年。参见 Wojciech Burek, Modus Vivendi,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www.mpepil.com, visited on 22 October, 2015.在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涉及石油活动的海洋划界案中,只有“利比亚—突尼斯大陆架划界案”和“缅因湾划界案”提及临时协议这一术语,从1984年之后的所有相关案件中再未出现,只剩下默认、明示或默示协议的表述,足见在海洋划界案中,临时协议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临时协议的淡出也在情理之中,临时协议涉及的是有关海上划界的问题,属于事关国家领土主权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后,方才具有法律效力。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鉴于临时协议仅具有历史意义,笔者就不再分析如何通过单方面石油活动,判定是否存在临时协议。
(二)默认
“默认”是上述诸多案例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术语。“字典对于默认解释就是默示同意,本质上是一个消极的概念,是指一国在面对构成威胁或侵害其权利的情形时,所表现的不作为,该国不打算以一种积极的形式作出回应,默认通常是在需要以一种积极回应以表示反对的情形下,采取沉默或不抗议”。I.C.MacGibbon, The Scope of Acquiesc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1, 1954, p.143.布朗利(Ian Brownlie)也认为,“没有提出抗议的行为模式,通常被描述为默认”。Ian Brownlie, Recogni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3, No.1, 1982, p.201.通过这些表述,不难发现抗议对于能否认定默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常说来,“抗议就是构成抗议国的正式反对,从而使得被抗议国知晓,抗议国不会承认抗议直接针对的行为的合法性,不会默认该行为所创造的或者将要创造的情形,也无意在此情形下放弃自己的权利”。参见 I.C.MacGibbo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Part of Protest in International Law,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0, 1953, p.298.既然当事国的消极不作为会催生默认,那么默认又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呢?“在国际社会中,一国原本有违现行国际法的行为或措施,会因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利益相关国家没有提出有效的抗议,就可以产生有效的法律权利”。Phil C.W.Chan, Acquiescence/Estoppel in International Boundary: Temple of Preab Vibear Revisited,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 No.2, 2004, p.422.在“缅因湾划界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也明确指出,默认源自于善意和公平这两个基本原则,默认等同于,通过会被另一方当事国理解为同意的单方面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默示承认。参见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4, para.130.迈克尔·拜尔(Michael Byers)声称,默认本质上源自于“合法例外原则”。参见 Michael Byers,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06—107.“默认的功能等同于同意,被史密斯教授( Professor Smith)描述为‘国际法的立法过程,使得先前仍在发展的规则以及尚未形成的权利盖上了合法性的印章……默认的价值在于,作为认可某一行为合法性并排除其非法性的一种形式,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客观而实际的标准”。前引B26, p.145.一旦通过默认,使得一国的不法行为符合现行國际法,表示默认的国家就不得再否认该行为的合法性。参见前引B29, p.424.
虽然默认是用以排除不法行为的违法性,但是鉴于其在划界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实践中不能轻易地推定存在默认。参见 Kaiyan Homi Kaikobad,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octrine of Continuity and Finality of Boundaries,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4, No.1, 1983, p.126.
构成默认至少应满足以下两种条件:
首先,在认定当事国的行为是否构成默认时,应当对默认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解释,确保默认规则得到实际而可接受的适用。不是当事国的沉默都可以被解读为默认,关键取决于沉默做出的环境。“如果一国在被告知某一情形,或者某一情形广为人知时,并且该国当时可以或应当提出抗议,但是该国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就可以理解为默认,或者放弃提出相反的主张”。前引B26, p.170.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1)如果认定一国的沉默是默认,就必须以其知晓某一情形作为前提条件。由于默认通常是隐含的,而非真实存在的,需要通过对当事国的行为进行分析而推定得出,如果一国不知晓某一情形,默认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参见 D.H.N.Johnson, Acquisitive Prescrip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7, 1950, p.347.那么如何认定一国是否知晓某一情形?最直接的方法就看该国是否得到通知,也就是说,当一方当事国在提出主张或做出行为后,是否将此情况及时通知其他当事国。早期的观点并不认为正式通知是默认成立的必要条件,前引B26, pp.176—178.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时宜,在上文提及的一些案件中,一方当事国是否发出正式通知,往往成为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例如,在“缅因湾划界案”中,加拿大主张从1964年起,在乔治浅滩的东北部实施了由其授权的地震勘探研究,而美国当局也知晓这一行为;但是美国政府却认为,加拿大从未发表过官方的公告或者其他的出版物,以期自己的海洋主张为世界所知晓,美国无法通过间接的方式推断这种主张的存在。参见前引④, paras.131, 134.同样在“喀麦隆—尼日利亚划界案”中,尼日利亚认为,其长期的石油实践构成了默认的基础;同时,尼日利亚否认自己没有履行通知的义务,它认为有关其石油实践的信息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公开获得的。但是喀麦隆并不认同尼日利亚的观点,主张不应该从其对于尼日利亚颁发的石油特许权的沉默中作出任何猜测,因为尼日利亚当局并没有像其曾经承诺的那样,将新的石油特许权通知喀麦隆。参见前引⑨, paras.282—283.为了消除这种原本可以避免的争论,笔者认为,任何一方当事国在争议海域单方面实施石油活动后,应当及时正式通知其他当事国,更何况如今的通讯技术十分发达,可以很便捷地给其他当事国发出正式通知。(2)当事国可以或应当提出抗议,却保持沉默 。进行抗议似乎是一国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因此一国在适当情形下未提出抗议,那么国际法庭在审查该国给出的未进行抗议的理由时,就会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参见前引B26, p.171.(3)当事国的这种沉默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因为根据沉默而推定的默认,会随着沉默持续的时间长度而成比例地得到加强。虽然关于持续时间的长度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但是可以从已有案件找到一些参照。例如,在“英国—挪威渔业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挪威国内法所规定的划界方法为国际社会所默认,整个沉默的时间从1869年一直到1933年,持续了64年。参见 Fisheries Case (United Kingdom v.Norway), Judgment, ICJ Reports 1951, p.138.而在前文多次提及的“缅因湾划界案”中,对于1964年到1969年11月加拿大发放勘探许可证,美国政府在这5年时间内没有作出回应,国际法院分庭仅认定为迟延,尚不构成默认。参见前引④, para.138.
其次,在判定是否构成默认时,还应注意另一个限制性规定,即在当事国之间的争端已经公开化之后,也就是在关键日期确定之后,不应再主张任何一方的沉默构成默认。因为此时有关争端的重大事实均已发生,参见 L.F.E.Goldie, the Critical Date,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12, No.2, 1963, p.1251.当事国之间的海洋主张已经出现基本的对立,意味着在争端解决之前,双方各自的立场是不会发生改变的,这也就为自此之后当事国的行为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即使针对其他当事国的某些行为未提出抗议,也不能认定为默认。
前文已经提到,一方当事国要想主张其单方面石油活动,获得其他当事国的默认,必须要证明该活动发生在关键日期之前,而且已经将相关情况及时地正式通知其他当事国,其他当事国在收到通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提出抗议。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一系列的标准很难全部满足,尤其是在将实施单方面石油活动的信息正式通知其他当事国后,其他当事国肯定会提出抗议。因此试图以默认为由,将单方面石油活动作为海上划界的考虑因素的想法,实施起来困难重重,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在前述案例的判决中,均未出现认定存在默认的情形。
(三)明示或默示协议
在上述案件中,“明示或默示协议”也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术语。其中明示协议不难理解,就是指当事国之间就各自石油活动的范围,达成明确的协议,可以直接通过协议的字面意思,知晓当事国之间已就各自拥有的海域达成合意。虽然明示协议简单明了,但是在实践中却难觅其踪迹,原因在于当事国之间很难就争议海域内的石油活动范围达成明示协议,否则争议海域也就不复存在了。至于“默示协议”这个术语,本身也不难理解,就是说当事国之间未就石油活动达成明示协议,只能从当事国各自的石油活动,发现当事国之间就石油活动的地域范围达成合意。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默示协议和默认表述相近,而想当然地认为二者关系密切。实际上,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首先,默认是一个单方面行为,能否构成默认,就取决于默认国一方的态度;而默示协议本是一个双方行为,需要当事国之间达成合意。其次,默认需要默认国消极的不作为,从而推定其同意;而默示协议则需要当事国的积极作为,只有通过对全体当事国的行为进行分析,方能发现当事国之间已经就某些事项达成合意。参见 Coalter G.Lathrop,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 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Malaysia/Singapor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2, 2008, p.834.鉴于默示协议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当事国之间是否存在合意,因此,只要能够通过全体当事国的石油活动,发现当事国之间已就争议海域内各自活动的范围达成一致,那么就可以作为海上划界的考虑因素。
那么究竟如何通过当事国的石油活动,认定默示协议呢?实践中对于默认协议的认定,也有着很高的标准,正如“尼加拉瓜—洪都拉斯领土海洋爭端案”中国际法院所指出的,“有关存在默示协议的证据必须令人信服,确立一个永久海上边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能轻易推定存在默示协议”。参见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Honduras),Judgment, ICJ Reports 2007, para.253.对于洪都拉斯所提交的证据,笔者认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两国石油公司联合经营、横跨北纬15°线的科科马里纳油井。虽然尼加拉瓜主张,“两国联合经营的行为,刚好表明在没有就海上边界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石油公司都无法进行单方面开采。如果真如洪都拉斯所主张的存在默示协议,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跨国合作,完全可以由对该油井享有所有权的国家的石油公司单方面开发”。参见前引B45, para.248.笔者认为,尼加拉瓜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即便双方就北纬15°线为海上边界达成默示协议,如果发现单一油气田跨界分布,基于维护矿藏的完整性,同样也有必要进行共同开发,所以尼加拉瓜将联合经营作为反驳存在默示协议的理由,略显牵强。虽然洪都拉斯的主张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国际法院最终还是没有认定当事国之间存在默示协议。这就意味着主张存在默示协议的一方当事国负有很高的举证责任,必须提出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证据,参见Abhimanyu George Jain, Maritime Disputes (Peru v.Chil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9, 2015, p.385.而不是简单地罗列当事国在争议海域所实施的石油活动。即便是 “也门—厄立特里亚仲裁案”,仲裁庭将先前石油合同作为划界考虑因素的结论,也不是轻易得出的。仲裁庭花了很大篇幅分析当事国双方的原先石油合同,特别是分析这些石油合同的区域分布,在发现双方的石油合同是沿着中间线分布后,方才认定当事国之间已就中间线作为管辖权分界线达成默示协议。有趣的是,仲裁庭没有指明当事国之间存在默示协议,而是直接认定石油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间线的划界方法。参见 The Eritrea-Yemen Arbitration (Phase 1: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Scope of Dispute), 3 October 1996, paras.389—439.此外,时间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时间跨度短,当事国在争议海域能够实施的石油活动数量有限,将直接影响用于认定默示协议的证据数量,因此时间跨度宜长不宜短。目前,对于时间的跨度并无确定标准,仅有个别案件判决可作参考。例如,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领土海洋划界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认为1961年到1977年的这段时间内(跨度为16年),即使当事国的石油活动与北纬15°线存在关联,但是时间跨度短,不足以认定默示协议。而在“也门—厄立特里亚仲裁案”中,仲裁庭分析的既有石油合同集中分布在1972年到1993年的这段期间(跨度为21年),在仲裁庭看来,就足以认定默示协议。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争端当事国的单方面石油活动若要成为海上划界的考虑因素,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即通过其石油活动证明存在默认或者默示协议。无论是主张默认或默示协议,提出该主张的当事国都负有很高的举证责任,而成功的先例更是寥寥无几。众所周知,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他声索国的单方面石油活动严重侵犯中国的海洋权益,完全是非法无效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这些活动的合法性,并多次提出抗议,因此其他声索国是无法通过其单方面石油活动证明存在默认或默示协议,这些单方面石油活动自然不可能成为日后海洋划界的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