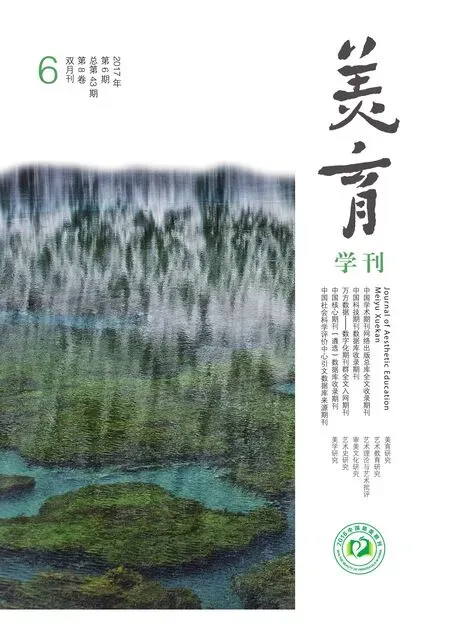张君劢美育思想的视野和路径
侯 敏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张君劢美育思想的视野和路径
侯 敏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现代中国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张君劢在20世纪上半叶对美育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他对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和德国近代美育理论均作了精辟的阐释,对人生情操化问题和中西美育结合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迄今为止,张君劢的美育话语尚未被学界所认知。发掘历史深处曾经起过“启蒙”作用的张君劢美育理论的脉络和内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美育的探索历程与真实轨迹。
张君劢;美育思想;现代中国
在20世纪中国人文旅程之中,一批知识精英握紧人文精神之魂,在民族“启蒙”与“救亡”的阶段,凭借自己的著作形态和思想活动,在时代的学术风气中自树一帜。 张君劢(1887—1969)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这样一位知识精英,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从容吸纳中西文化,学以致用,腾挪流转,探索中国文化建设之路。在“五四”后期,张君劢发起“科玄论战”,首倡“新宋学之复活”,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现代再造与复兴,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张君劢繁杂多样的文化哲学体系中,美学与美育思考占有重要的位置,其美育的视野与路径,仍值得今人记取。
一、德国美育思想的介绍
在20世纪中国哲学美学知识背景中,西方哲学美学被中国学者借用来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其借用方式是译介与输入。张君劢在20世纪初期曾经两次赴德国考察学习。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给予他以深刻的影响。他说:“康德哲学,合大陆理性派与英伦之经验派于一炉而冶之。其所以安排科学与宗教问题者,亦能独出心裁。”[1]他服膺康德哲学的“自由”理论和“审美无利害性”的观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审美鉴赏规定为一种“无利害观念的快感”,使人获得愉快和享受。康德的先验自由、道德实践自由的学说,以及审美活动中纯粹美和依附美的论述,给张君劢以思想上的启发。
张君劢倾心于德国席勒的美育理论,是现代中国学界最早介绍席勒美育理论的学者之一。他之所以对席勒美育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是因为席勒的美育论与康德的美学观相通,且具有现代意义。席勒虽然没有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但因为他继承和发挥了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并将康德美学理论中的“自由”观念从形而上学的云端带到现实生活之中,试图通过美育的途径实行人性的改造,从而建构完备而系统的美育理论体系,给欧洲思想界和教育界以巨大的影响。席勒的美育理论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具有启蒙的作用。1922年,张君劢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德国美学家席勒之美育论》一文。这是他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所作的一个演讲,后整理成文发表,系统地介绍了席勒及其《美育书简》,着重介绍了席勒《美育书简》的主要内容和观念。
其一,人性完善。席勒目睹近代欧洲存在人格破碎、人性割裂,因此需要完善。古希腊时代人的理智和美感是协调的,但近代欧洲由于工业革命,出现分工的局限,致使人的本性分裂,国家与教会分立,法律与风俗背离,享乐与劳动分离,手段与目的脱节,人性遂不完整,更无法得到协调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审美途径克服人性的异化,走向人性的整全与和谐。
其二,两种冲动。席勒认为人有两种“冲动”:一种是出自人的物质生存或天性的“感性冲动”;一种是出自人的理性的“形式冲动”。而单纯感性的人或者单纯理性的人都是片面、偏狭的,唯有通过审美教育,才能使人的发展与成长得以完整、自由,最终使人迈进高雅、崇高的境界。
其三,游玩活动。席勒强调“游戏冲动”。人要获得自由自在,应当寻求介于“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游戏冲动就是美或艺术。只有靠美和艺术才能创造美好的乐趣,弥合人性的分裂。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是缺失的,艺术则保留了人性的自由圆满的天性。唯有美和艺术才能造福于全人类。
张君劢根据自己的理解,抉发出席勒美育理论的精华与闪光点,确实捕捉到席勒美育理论的核心意涵。在介绍席勒美育的过程中,张君劢还作了别出心裁的理论阐发:“美育者,并非教人发明真理,又非教人履行义务,乃导人于天机活泼、自由自在之一境。”[2]张君劢聚焦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自由自在,向国人输入席勒的人本主义的美育观。席勒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美育理论,对于致力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张君劢来说,具有一种时代精神的诱惑力和感召力。
更重要的是,张君劢在这篇文章的附录部分,结合席勒的美育论,阐发了他本人对中国现代美育建构的意见:“国中教育家言智育、德育、体育之重要者,众矣,独于美育则未之及,我以为此乃偏而不全之教育也。……若夫人格之养成,必求其可以贯彻一人之全身者,是为美,是为美育。以我观之,全国之众,束缚于流俗,牵制于习惯,事之是非,本极明白,以一身利害所关,竟不敢说出,此皆情感抑塞,自己本性不敢坦坦白白于天下以共见也。”[2]为此,张君劢呼唤和落实美育,认为这既是教育家之责任,也是美术家之责任。通过审美教育,国人可以培养理想人格,使社会风气返于浑厚敦朴,使人性臻达完善自由。
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就注意到席勒的美育思想。王国维最早介绍席勒的美育理论,写有《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1904)和《教育家希尔列尔》(1906)两篇专门评述席勒的文章。文章中的“格代”,即歌德;“希尔列尔”,即席勒。王国维对席勒美学思想的内涵有十分准确的把握,在1904年《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他论及席勒的美学主张时写道:“德意志之大诗人希尔列尔,而大成其说,谓人曰与美相接,则其感情日益高,而暴慢鄙倍之心自益远。故美术者科学与道德之生产地也。又谓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故气质之欲灭,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审美之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于道德之境界则统御之(见希氏《论人类美育之书简》)。”[3]王国维青睐席勒的“审美无利害”的文艺价值观。
张君劢是继王国维之后又一个系统介绍席勒美育思想的人文学者。由于他亲历过德国文化与哲学的熏洗,故能利用第一手学术材料,理通神会,予以理论阐释,他比王国维更能吃透席勒的美育理论精华——“游戏冲动”理论。但由于张君劢不习惯用白话文表达自己的思想,坚持用文言文书写,《德国美学家席勒之美育论》一文,文辞表达显得佶屈聱牙,较为晦涩。新潮的思想介绍与古奥的文字表达之间构成一种不易消化的形式局限。故这篇早期重要的文章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久不为众人所知晓,但其现代性启蒙的思想蕴涵闪耀着掩抑不住的美育理论光辉。
二、宋明理学美育的阐释
现代中国人文学术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产生的。西方话语作为新潮的理论形态,被现代学人用以激活中国传统思想,实现学术思维的现代转换。虽然西方理论是张君劢美育思想的外在资源,但更重要的是,张君劢毕竟是本土的知识分子,他有意识地承续了传统美学的内在资源,以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为基础,构建其美育思想的内核。
张君劢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一个世家望族,6岁进入私塾接受国学启蒙教育。少年时代研读过原始儒家的《论语》《孟子》,宋明儒家朱熹的《近思录》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清代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曾国藩的《曾文公全集》,从小深受儒学文化的熏陶,国学根底雄厚,这为他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打下了基础。在长期的人文探索中,他试图从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儒家思想中挖掘出值得现代继承的审美精神。
儒学传统文化是张君劢探索的基础,尤其是宋明儒家学说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张君劢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文化的至宝和民族精神的结晶,宋明儒家关于内心修养的思想是国人安身立命之本,能够指导人们认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吾国思想中的孔圣之垂训,宋明之理学,自为吾国文化之至宝,以其指导吾人以修己立身与待人接物之方。申言之,指使吾人以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也。以吾国固有之名词言之,亦称为义理之学。”[4]223基于这一认知,他首先肯定儒家道德主义的观念,因为儒家主张的“德性”确是出自人的内心,历经万世而具恒久不变的价值。古代优秀的道德传统当是文化重建中不可或缺的一维,现代中国人要树立民族自信心,就应以儒家精神充盈自我。孔子关注人生,孟子倡言民本,开出德性维度与心性路向;宋明儒家更是拓展了儒家的德性与心性思想。因此在张氏看来,复兴儒学即复兴心性之学和道德理想主义,我们从中可以开掘出儒家的现代化因素来。张氏身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时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他致力于为中国文化寻找一条新出路,此出路乃是儒学的复兴,正如同宋明新儒家从原始儒家那里寻绎精神资源一样,藉此方法今人可以找出传统儒学的精神价值。
《白沙先生诗文中之美学哲理》一文,是张君劢研究宋明新儒家美学思想的一篇重要论文,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文章论述的白沙先生,即明代心学大儒陈白沙。张君劢服膺陈白沙哲学思想,是因为白沙先生有一颗真诚至美、虚明静一之心:其学问以“自得”为求,以“自然”为宗,以“虚静”为径。白沙先生追求的是一种自得之乐、一种与“道”翱翔的精神境界。
在新儒学思想发展史上,陈白沙是从陆九渊到王阳明心学发展的中间环节。“自然之乐”是陈白沙心学美学的核心。张君劢从三个方面研究了白沙先生的美学和美育思想。
其一,“心与道合”。即人与宇宙融为一体。白沙心学提出了“心与道合”的命题,赋予“心”和“道”同等的地位。人之“心”,因为“受朴于天”,遂“禀和而生”。君子之心,神完气足,自得自乐,“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这是一种人“心”回复“道之初与”的天机状态,“心”自然地与“道”相合,从而“身心”与“道理”化合相交,使人在主观的心理体验上与自然融合在一体,不着一物亦不舍一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浑融的生机勃勃的整体。
张君劢运用陈白沙的哲理诗歌阐发诗人的人生态度。例如,白沙《太极涵虚》诗曰:“混沌固有初,浑沦本无物。万化自流形,何处寻吾一”。张君劢认为白沙在诗中表达了“浑沦一体之意”。从诗中可见出审美心境、审美情调。正是“心与道合”的认知,使陈白沙“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在“天人合一”的本真状态中,人之“心”与 “道”,比翼双飞,悠然翱翔。“心与道合”的哲学命题最终带给陈白沙与“道”翱翔的自得意趣,给予他心灵的关怀与安顿,最终成就了白沙作为一个高世之儒不出世的洒脱。
其二,逍遥自得。即悠游自足。在自然生化的万物感应中,陈白沙随处体认“虚静明”之境界,一种平易淡朴、洞达自然的风格和鸢飞鱼跃、任真自得的境界。白沙把理学的“心性”、道家的“虚静”、禅宗的“悟入”融合为一,建立起一种尚自然、贵自得、主性情的美学思想。张君劢欣赏陈白沙诗歌中的不为物所役、自由洒脱的心境。
例如,白沙《寄太虚上人照用旧韵》诗曰:“众生尊我我须劳,公在吾儒公亦豪。数点晓星沧海远,一床秋月空山高。性空彼我无差别,力大乾坤可跌交。十二万年如指掌,且并闲弄在甄陶”。张君劢指出:“若晓星沧海,一床秋月,此为诗人之语,尽人而能之。至于隐几无穷,春生酩酊,筋斗虚空,乾坤跌交之语,非真逍遥自得之精神,发挥至于极至者,谁能作此语乎?”[5]118。这种“化境”创造出“天命流行,真机活泼”的自然之境。人之“心”可以“通塞往来”,没有凝滞,同“道”一样灵动运衍。
其三,沉醉之境。即以酒醉代下意识。张君劢发现白沙先生写过不少饮酒诗篇,表现了一种逍遥自得的妙境。例如,“万杯春覆酒遗老,一枕日高天与闲”,“江山偶得三人醉,风月还添一榻清”。格调轻松高逸,非寻常诗中所能见,诗歌表现了类似于西方文艺家的幻想和下意识的沉醉与朦胧的意识。但是,张君劢又觉得“白沙子要为学道之人,其诗中虽充满宇宙之美,然究与太白酒仙不同。”[5]120也就是说,陈白沙与李太白的诗歌虽都带有酣畅淋漓的沉醉意识,但两者仍有不同,白沙饮酒诗歌清峻闲雅之态活跃于眼前,这与李太白之乘风凌云的飘逸姿态有所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张君劢所青睐的“沉醉之境”,不同于尼采的“酒神精神”。“酒神精神”其本身即是欢乐神,播撒欢乐与慈爱,而另一面则冷酷、野蛮、残忍,代表着世界意志本身的冲动,在个体身上表现为摆脱个体化原理而回归世界意志的冲动。 在酒神精神的作用下,尼采心目中的个体处于一种癫狂的“醉”态,如同服用了“妖女的淫药”,使得“天性中最凶猛的野兽径直脱开缰绳”,冲击一切秩序。而张君劢所谓“沉醉之境”,则处于主客体浑然一体的朦胧状态,主体融合在这一不能分解也无须分解的整体当中,形成“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精神体验。
在张君劢看来,宋明儒家对“道境”的痴迷,即是对艺术的天地境界的追求。它既蕴涵着对人格自由向往所拥有的愉悦感,又意味着对艺术欣赏所带来的共鸣感。因为“道”的艺术自由精神就寓于大化流行、唯变所适之中。因此,“道”的艺术自由精神说到底是主体人的自由精神显现。张君劢强调审美的两种基本特性,即普遍性与超脱性,他始终围绕陶冶情感、完善人格这一美育目标来展开论述,阐发陈白沙的美学思想。
三、“人生情操化”的推崇
在中国现代美育学术史上,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刘伯明、李石岑、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等均是时代场域中的学术翘楚,对现代中国美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那么,张君劢的理论贡献何在呢?笔者以为,张君劢同样向我们提供了凝练的学术思考。探讨张君劢的理论成果,我们既可以看到其在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领域中的意义,又可以窥见现代学者在美育方面的拟构形式和理论重心。
“人生情操化”是张君劢的一个重要的美育思考向度。张君劢认为人生情操化体现在儒家哲学与中国文艺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伦,肯定道德自觉,关注人性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能够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道德情操。中国自孔孟儒家至宋明理学家,重视内心生活修养,形成了古代一种特有的精神文明。中国艺术“以天地纳于山水之中,则山水自有一种穆然意远、天地为俦侣之意。如深山流水旁高僧修道之像,立意既超绝人寰,则意境自深远矣。王维、米南宫之画,淡墨数行,而富有宇宙无穷之意味,此乃天地与艺术合而为一之所致也。”[4] 176艺术的美,则在于妙手偶得于无意之中,此是中国知识分子悠游自得之情趣,中国艺术中饱含着人生情操化的思想,而这正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特色与特长。
“人生情操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是追求精神自由与艺术趣味。这是张君劢研究中国哲学与艺术的心得体会。这个观点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曾经通过“趣味”与“情感”及其相互关系,论述了“无所为而为”的人生实践精神及其情感本质,从而张扬了一种以生命和创造为核心的审美观念。此种人生美学理念,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和人文主义情怀。梁启超之于张君劢,两人是亦师亦友之关系,两人曾经同去欧洲考察。张君劢尊敬梁启超,1918年9月,张君劢加盟梁启超等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主张解放国人精神、物质层面的一切不自然和不合理之状态,同时吸纳现代世界文明之新潮,以为改造中国之用,即从思想观念上改造国民,启发民智。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张君劢畅谈未来政治、学术、艺术之新方向。他认为中国文艺自有特色,光耀东亚,而欧洲艺术之特长亦有为吾国所无者,也不能排斥。“以欧人游心于无限之境,其所超境界,往往为吾人所不及。如诗歌中长篇作品,但丁之《神曲》,歌德之《浮士德》,吾国诗文中无此体裁与意境也。至于雕刻、建筑、音乐、戏剧,常有人焉就其民族心灵之深处而体味之,而表现出之,故亦当在日新月异中。其他为西方所有,吾国所无者,尚不可胜数。吾国人苟在此方面继续加以努力,则除旧日成绩外,应有新领域之扩张与新创作之表现。此精神自由之应表现于艺术者。”[6]380这里,张君劢把人生情操与艺术境界绾结起来,揭示了中西艺术境界的互识、互补与融会,试图沟通中西艺术思想之精华。
张氏天资聪颖,学贯中西。少年时即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青年时期又得以留学日本、德国,精通英、法、德、日等多国语言。尤其是师从德国奥肯教授研修人生哲学后,张君劢发现奥肯学说与孔子学说具有暗合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肯的人生哲学思想关乎健康的人生观的形成问题,张君劢叩问:“人生之解决,非求真善美乎?真善美者,总言之,实在是己,实在为物。有谓属于可知,有谓属于不可知。”前者是柏格森,强调个人的直觉,“义取美术家之于其作物,默识而心通之,合主客观而成一体”。后者是奥肯,强调精神的直觉,“义取宗教家精神之感召,超于相对待之境,而另为直接溥遍自由实在之境界也”[6]60。二者方法虽异,但其以强调情感畅达、心灵美化之目的则是相同的。
“人生情操化”是张君劢研讨人生价值的论题。他说:“科学以分疆划界为主,而道德以善恶是非为褒贬之准则。此二者自有其绳墨规矩为学问家、为立身行己者所不可不守者也。以云所谓美,虽出于人之感觉之主观,然其人人胸襟须以宇宙与一身一心合而为一体,且超出乎世俗所谓生存常变、富贵贫贱之外,而后心旷神怡,乃能领略宇宙间种种之美,如山峙、如水流、如日出、如日落、如鸢飞、如鱼跃,为天地自然之美,惟有有道者胸襟开阔,不为物欲所蔽者乃能得之。此则美学之所以与科学哲学与道德二者迥乎各别者也。”[5]114张君劢是在“智”“情”“意”三者合一、“真”“善”“美”三者合一的系统中,论述审美的价值特性问题,而审美的核心是在“天人合一”“身心合一”“性情合一”之中。如此,人们能够心旷神怡,自由自在地领略宇宙间诸种之美,走向“人生情操化”的理想境界。
四、中外美育思想的比照
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中国化”进程,常常是与学界对“中国——西方”这个二元模式的价值取向联系起来的。在学术知识构造上,中外美学资源均被纳入张君劢的学术视野。张氏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如何把西方学说与中国古典传统进行有效的融合。张君劢的美育思想是在承继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吸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精华的过程中构筑起来的。
中国传统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美育思想,十分看重审美在涵养人格中的积极作用。张君劢据此指出,孔子的美学思想中有着和席勒美学相通的精神质素。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的“游于艺”,就是一种审美活动。而孔子的“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人生感慨以及赞许曾点“浴沂舞雩”的人生情趣,与席勒“以美为人生最高之一境”相比,两者基本精神颇相契合,皆能“知造化之妙”,其宗旨是“精神的自由自在,绝不停滞于物质”[2]。在张君劢看来,中国古代的协和宇宙,参赞化育之话语,与席勒所说的“超乎自身之外,而与至美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
张君劢是洞悉东西方世界大势的知识分子,目光高远,但思想复杂,一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纠结于理想与现实之境。在思想导向上,张君劢最初推崇“精英主义”,提倡培养“先觉之士”。但是,1918年他从欧洲考察回来后,思想发生了若干变化。192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之良政治,未有不以国民为基础者也。盖判断得失,决多少数,其最终之一步,不能舍国民而他求。欲求由此种能力值国民,方法甚多,而根本上不外教育普及,人人自觉,人人有知识,服而后可以语夫政治。”[7]张君劢通过欧洲考察,开始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实现,不仅要依赖上层精英的主导,而且还要依靠国民的坚强后盾。因此,大众教育及其美育对国民的思想改造是不可或缺的。1923年10月,张君劢在黄炎培、史量才等的支持下,创设国立自治学院,学制包括预科、本科和研究科,本科分为省政科、市政科、乡政科、社会科。开设课程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哲学、伦理学、近代本国史、西洋近百年史、教育原理、教育制度、教育史、进化论、英文、国文等。学院试图实行“自由主义”的教学计划,聘请张东荪、吴经熊、瞿菊农、潘光旦、闻一多等教员,但因资金和政治的原因,三年后被迫关闭。抗战期间,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办中国民族文化学院(1938年)。他对现代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建设,倾注了满腔热忱,不畏困难曲折,致力于思想启蒙,贯彻“立人”“新民”主张,以此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现代学者胡秋原称赞道:“张君劢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国的思想,他是这一百四十年思考中国出路问题贡献最大之一人。”[8]这就彰显了张君劢学术在中国现代思想转型过程中的价值特性:人文理想追求和社会精神改造。这两个特性贯穿于张君劢一生的人文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之中。
在中外文化学说借鉴问题上,张君劢指出:“今海外新智输入之机大动,凡欧美任何派别之学说,皆可供我取用吐纳之资。”[6]82晚年的张君劢寓居美国期间,著有《新儒家思想史》,他借助西方哲学方法梳理儒学发展脉络,将中西哲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找到中西哲学的共通点。尤其是以康德与新儒家作比较,发现康德强调道德意志比理论悟性更具有优先性,在这点上也就更接近于中国思想。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哲学有用于否,并不单是表现在理论架构上,而重在如何使德性更完善地落实于人生层面。张氏通过分析比较,认为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重视道德价值。对中国人而言,道德价值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粹抽象知识具有更重要的功用。二是强调道器合一。凡是形而下的都可以归溯于形而上的;凡是形而上的都应该用这世界的现象来加以解释。三是倾注心灵生活。中国人关注“内心生活”和“心性修养”,不为物欲驱使,不为褊狭所遮蔽。四是注重知行合一。人若有志于道,就应“身体力行”,为家庭生活和国家兴旺尽心竭力。这四种优点和长处是中国文化重塑的根本。张君劢在继承儒学传统、涉猎西学的基础上,以中国心性论为本,兼采西方知识论之长,阐发了自己的新儒家哲学美学思想。
现代中国美学与美育的建构,除了时代因素之外,还与具体的个人的知识背景及其个人运用过程联系在一起。张君劢是博通中西学问的大家,自身积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进而形成一种国际化且有民族特点的学术视野。在张君劢的心目中,正统的儒家以德性美育作为造就人格的手段,与德国古典美学有着遥契之处。张君劢在为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一书作序的序言之中说道:“东方所谓道德,应置之于西方理智光镜之下而检验之;西方所谓理智,应置之于东方道德甘露之中而和润之。然则和东西之长,熔于一炉,乃今后新文化必由之途辙,而此新文化之哲学原理,当不外吾所谓德智主义,或曰德性的理智主义。”[6]447从学术史的层面看,“德性的理智主义”既是中国现代审美教育的锁钥,也是张君劢美育思想的纲领。正如学者张汝伦所言:“张君劢的哲学结合了中西哲学的多种资源,他的‘德性的理智主义’构成其一生言行进退的背景,使得他成为一个少有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家。”[9]在张君劢身上显示了知识融合的内在迹象,彰显了一种将中国传统的人文情趣与近代西方的人文理想进行相互协调的可能性。
中国现代美育是在中国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的土地上,借助于西方美育理论而中国化的行程中孕育出来的一种审美理论和实践活动。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默契本真,贮兴而发,其美育话语既有开阔的世界视野,又有中国智慧的儒家元素。尽管张君劢的学术话语存在着学术与政治的纠葛,带有隐晦艰涩的言语表达局限,但掩抑不住其间的新儒学光色。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张君劢以其所倚重的新儒家的心性价值特性,吸纳西方美育理论,同其他学术大家一起共同开拓了现代中国美育的理论场域。
[1] 翁贺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22.
[2] 张君劢.德国美学家席勒之美育论[N].时事新报·学灯,1922-10-2.
[3]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M]//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55.
[4] 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M]//当代新儒学八大家·张君劢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223.
[5] 张君劢.义理学十讲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 翁贺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7] 张君劢.政治活动果足以救中国耶[J].改造,1921(3):6.
[8] 翁贺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9] 张汝伦. 张君劢与哲学[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18.
(责任编辑:紫 嫣)
VisionandPathofZhangJunmai′sIdeasofAestheticEducation
HOU Min
(School of Art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Zhang Junmai,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social activist, explored the issu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fter making a penetrat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dea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German ideas in this field, he put forward his own opinions on the problem of lif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 education. At present, Zhang Junmai′s aesthetic education discourse has not ye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Therefore, it helps us to trace the course and track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context and connotation of Zhang Junmai′s idea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which once played a role of enlightenment in history.
Zhang Junmai; idea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modern China
2017-09-27
侯敏(1961—),男,江苏句容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
B83
A
2095-0012(2017)06-00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