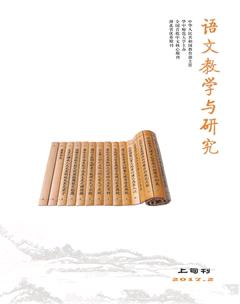储光羲的庙堂之忧和江湖之愿
袁海锋 何智敏
储光羲的《田家杂兴八首》(其二)收录在粤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元散曲》一册。无论课文的注释,还是教案给出的解读,都把这首诗定位为“写自己归隐田园之乐”[1]。基于这样的理解,在梳理诗意的过程中,整首诗的意脉却显得颇不流畅,中间存在若干意义龃龊之处。
整首诗共十四句七十个字,在这样局促的空间中,“所乐在畋渔”“所愿在优游”二句无论从句式,还是文字的表面意义,都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如果仅是要通过句式和语意的重复来达到强调的目的,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几乎没有效果。另外,从人之常情和山水田园诗对山林景致的常规描写看,山泽往往是诗人理想的归隐之地,而且常常以沉静秀丽之态呈现,至少在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人的笔下是这样的。但诗人在“山泽”之后用了“晦暝”一词,把这写成了一处昏暗阴沉的所在,明显有违常理。再者,“归家暂闲居”句中,“归家”“闲居”都是山水田园诗中十分常见的词句,相对而言“暂”字的使用则少了很多。即使《题李凝幽居》的“暂去还来此”,“暂”指向的也不是山林闲居,而是俗世生活。归隐闲居的“暂”总是透漏出些诗人内心不甘不愿,这在山水田园诗里亦是极为少见的。
这么多有违常理,这么些语意龃龊,与其说是诗人不经意间留下的创作笔误,不如说是诗中个别词句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整首诗的情感定位出现了问题。这首诗除了表达诗人仕途的决绝之态、山林归隐的无尽痴迷外,还有一种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庙堂之忧,以及归隐山林的江湖之愿在求庙堂之忧而不得后的萌发、强化和纠结的复杂情绪。储光羲置身江湖庙堂间的犹豫与迟疑不是教参中一句“平和恬淡的心态”就能说的清楚的!
整首诗中,最容易出现理解偏差是第四句中的“畋渔”一词。课本将其注释为渔猎,并顺势将其理解为田园劳作的闲适生活,这是导致前述语意龃龊的根源。除了依照“畋渔”的字面意思将其延伸理解为田园劳作,它的意义还可以从另一向度进行理解。《史记·越世家》中有云“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其中“良弓”“走狗”是打猎用具,意义上则是对奔走效劳之人的隐喻。“畋渔”本意是打猎围捕的行为,如果从奔走效劳这一层意思理解,这首诗意义则有峰回路转的新意。
从奔走效劳之意理解“畋渔”,可以使前四句的对比手法有了更为切实的落点。众人耻贫好富,贪慕功名利禄,而“我”是情怀坦荡的,要为国家君王奔走效劳。这里的对比不是把众人的追逐荣华富贵与“我”的看淡浮名、安贫乐道比较,而是将众人的自私自利与诗人家国天下的庙堂情怀形成对比。储光羲要在此给读者展现的不是一个避世的隐者形象,而是一个决绝的入世者形象。由“我”的坦荡与众人的耻尚宕开,让人看到的不只有储光羲士人理想的坚定,众人的卑劣恶俗,更有整个盛唐社会所折射出来的从上至下的深刻危机。进一步关注“乐”字的含义,表面上看,“所乐在畋渔”与“所愿在优游”的“乐”“愿”语义相近,但是“乐”的语义并不能通过“所愿在优游”这一相近句式对比实现,而应将其置于前四句构成的对比小语境中。众人对于贫贱的态度是“耻”,而“我”的态度是“浩荡”从容,众人追逐物质利益,“我”看重的则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乐”与“尚”形成意义的对应。“乐”字指向的是宏大的庙堂大情怀,而非个人小情趣,是未来自我愿景的“崇尚”而非置身现实的“喜欢”。这其中可以看到储光羲对家国情怀的看重,却也无意间隐隐地露出一丝未来命运的不确定。相对而言,“优游”的意义指向比较明确,可以理解为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与“乐”的宏大、抽象、难以确定相比,“愿”字是对置身田园生活真实感受的写照,是可以切实掌控的种植、饮乐的小生活,是真切的“喜欢”,而不是宏大的“崇尚”。
基于“畋渔”一词的意义转向,“山泽”也不再是储光羲向往的隐居之地,而是他奔走驱驰,施展抱负的“畋渔”之所。它可以指的是官场,亦可泛指整个堂皇大气却已摇摇欲坠的王朝。展现在储光羲面前的山泽没有王维笔下“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清新秀丽之象,而是晦暗不明,不可卜测的寥落。由山泽的表层之意往深里看,这片山泽的晦暗不明不止来自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史思明等众人的耻尚之间,更有当朝天子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意欲驰骋的“山泽”已是如此,那“畋渔”忧国忧民之心自然显得有那么点一厢情愿。在孔子时代的儒家价值观设计中,已经注意到了仕与隐的问题,形成了相应了的应对策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道是处置仕与隐的核心标准,当然也为储光羲指明了道路——归隐并非他的初心所愿,而是迫于家邦无道的无奈;绝仕是情非得已,有道驭宇便可复仕、复谷、复见。一个“暂”将他在入仕与归隐之间的犹豫与观望写得淋漓尽致,写到妙不可言。而这些与储光羲二十岁(开元十四年)中举入仕,却又仕宦失意,归隐山林再又出山,以至后仕伪朝的人生轨迹一致,又与传统士人出离在庙堂之仕与江湖之隐间的那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的那种内心纠结一脉相承。对此诗而言,这些可视为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支撑。
紧接四句是诗人真正的归隐生活中田园景致的描写,内蕴的情感依然由前置的情感基调承袭而来。园中种植的是葵、藿这样喜阳的菜蔬,房前屋后种满了高大的桑树榆树,禽雀翔集于茅檐之上。诗人以白描手法手法写出了自己置身田园之中的简单轻松愉悦,似乎又不止这些,至少诗人选取的意象具有太过丰富的意义可能。葵霍本性喜阳,向阳而生,古人遂喜借葵霍以明心志,如王维《责躬荐弟表》中“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马之意,何足动天”句;《旧唐书·倪若水传》中“草芥贱命,常欲杀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愿隳肝以报主”句。这里的葵藿已经不是简单的菜蔬,而蕴含着臣下对君主忠诚无二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理解此诗,理解储光羲,意脉更加通畅。与之相比,桑榆的文化意味更加丰富,有日暮、晚年、归隐等不同的意义取向,从储光羲归隐后再次出山、以至入职伪朝的人生轨迹看,此处笔墨凭空多了一种“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入世意味。禽雀知道诗人闲来无事,却也只是知道诗人空闲而已。说到底储光羲不是个陶渊明、王维一样的真隐士,他并非真正地倾心于田园,诗人的闲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赋闲,是身闲而心烦。储光羲时时置身于这些简单愉悦的田居生活,闲下来的是奔波的身体,闲不下来是时刻没有放下的庙堂之忧。这样的禽雀知闲也只是“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其中味道复杂。
也正因为此,他要强调他所愿的优游,这优游不是展示他的自得其乐,也不是向朝堂宣示了他的决绝,而是向州县小吏们宣告他“邦无道则隐”这样形而上的理据和自有优游之樂这样形而下的感受。无论从现实的仕途官位,还是理想的人格道德,储光羲尚未实现传统士大夫的生命完满,他自然没有,也不可能有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性格决绝洒脱和文化自信霸道。这是他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纠结的最为根本的节点,以至于他在诗歌的结句依然难以超脱出来。面对轻松简单的山林田园生活,储光羲找不到王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那种放空自己的自得其中、轻松自在。他感受到的是有限人生中时光快速的流逝,是脆弱肉身与南山磐石同老的时间压力。面对此情此景,诗人自然不可能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无我的真闲适。他迅捷地举起酒杯,划然而尽。他饮下的何止于酒,还有他的人生期待,他的仕隐纠结,他的庙堂江湖冲突,他的愤愤不平与无可奈何。
短短几十字中,全然是储光羲庙堂之忧与江湖之愿的纠结,全然是他内心纠结的斗争史。他本可以写的堂皇超脱一些,他本可以用骗自己来骗世人,可他还是选择了真实地面对自己,真实地剖析自己。这样的储光羲,或许更为难得。
参考文献:
[1]参见粤教版《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教师教学用书第31页对此诗的基本解读部分。
[2]参见《论语》中《卫灵公》《宪问》《泰伯》等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