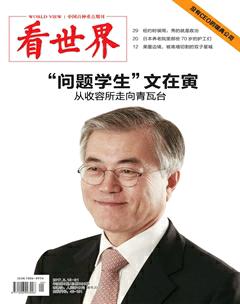被神话的伊朗电影
李明波
据说,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获得了至少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一个国家的电影更能帮助局外人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与历史。比如伊朗,在外人看来这个充满了神秘且遥不可及的国度,因为电影而缩短了与世界的距离。
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又一部伊朗电影闯入了全世界影迷的眼睛。2017年的奥斯卡,除了让世人记住最佳影片乌龙事件外,最大的冷门莫过于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影片《推销员》击败了呼声颇高的《托尼·厄德曼》,这已经是法哈蒂的第二座最佳外语片小金人了。2012年,法哈蒂就曾经凭借《一次别离》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阿斯哈·法哈蒂还不是最早一代的伊朗世界级导演。1997年,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曾凭借《樱桃的滋味》荣获第5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与今村昌平导演的《鳗鱼》并列,而当年的戛纳主席是“法国女神”伊莎贝尔·阿佳妮,堪称电影节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伊朗为何能生产出世界级的电影产品?这确实是一个谜一样的话题。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以严苛闻名于世。伊朗的电影审查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有些镜头绝对不能出现,比如男女亲吻。电影制作完成后,会有审查员逐条审查,看成片是否按审查后的剧本拍摄。伊朗导演必须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将剧本、详细的演员表以及样片呈交文化部伊斯兰宗教审查委员会,接受审查。
但很快,一些具有创新思想与政治意识的电影人发现儿童电影可以变为一个承载更丰富意涵的载体。他们可以在一个众人皆懂的故事背后加进他们对伊朗社会严苛现状的思考,而后者就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明白。由此,一种伊朗电影独有的运作模式应运而生。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称为双层运作模式,也即在表层的故事下潜藏着一个隐喻层,观众可以通过观看一个故事自行揭开背后的寓意。
伊朗电影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影坛异军突起,最先为其积累声誉的就是一种被称为“伊朗儿童电影”的电影类型。这种独特的电影类型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为契机,最先引起了国际影坛的关注。
虽然说“儿童电影”是伊朗电影人应对国内严苛的审查制度想出的“妙计”,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的“无心之柳”。当一男一女同框的画面也会被剪去,那么将摄影机镜头对准儿童看起来是最少可能触碰到审查底线的权宜之计;同时,讲述儿童故事的电影不仅会受到伊朗国内占到很大比重的儿童欢迎,也值得成年观众欣赏。
不过,在被神话的伊朗电影背后,还有一个更令人唏嘘不已的现实。在伊朗国内,由于严格的审查,能够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只有三种类型:政治宣传片,商业片,还有就是所谓的“阉割片”。
伊朗电影绝大多数没法输出,而国内票房只能说是一般。外界所知晓的在国际上获奖的伊朗电影,多半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叫好不叫座,有些甚至没法通过伊朗国内的审查。而很多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导演或许并不如商业片导演受欢迎,不少伊朗影迷认为获奖的导演和作品都是迎合西方的产物(比如反映穷苦百姓生活,容易让人产生对该国生活的误解),现实中的伊朗要比电影中表现的落后、闭塞的伊朗强很多,伊朗人也可以是很现代很时尚的。當然伊朗国内也充满了表现都市中产阶级的商业电影,不过在艺术水平和文化价值上几乎无法与那些获奖的影片相提并论。
2011年,《一次别离》在柏林大获全胜,获得金熊奖等三项大奖后,导演法哈蒂却表示:“虽然拿了金熊奖,可我不是英雄,无论我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伊朗电影的现状。我能做的就是用电影阐述更多现实和情感,希望能对它有所促进。”
伊朗电影怎么样,导演心里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