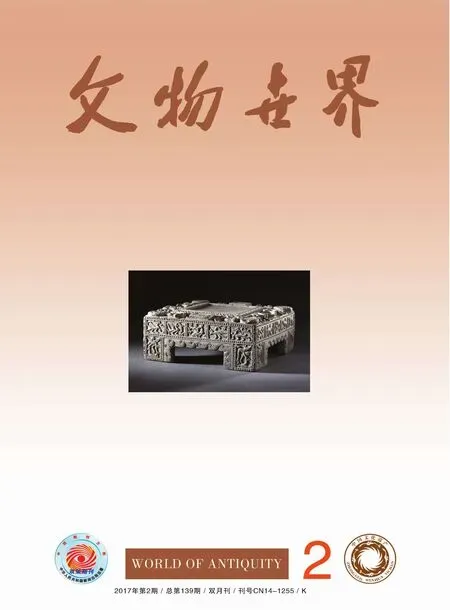《大慈灵和尚觉灵神道碑》碑文考释
□燕飞
《大慈灵和尚觉灵神道碑》碑文考释
□燕飞
本文通过对《大慈灵和尚觉灵神道碑》碑文的考释和核定,对撰写者衔名中提及的行政层级及佛教管理职衔进行了梳理,为研究泽州地区佛寺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信息。
神道碑衔名行政层级
《大慈灵和尚觉灵神道碑》(下文简称《觉灵神道碑》),是笔者在晋城市晋庙铺镇大池头村发现的。该碑保存完整,字迹和图案清晰,长196厘米,宽61厘米,青石质,正面朝外横嵌于旧大队的外墙上。碑面刻有文字和图像,主体为文字,分别是碑右上小楷书写撰文人的姓名,以及花押,正中为正楷书写的墓主尊(谥)号及法号,左下角为立碑人及时间;作为装饰的图案,分布在碑左右边沿,分别格出十个栏,栏内是浅雕。根据落款时间,可知碑刊刻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观其内容,大略可知是佛教弟子们请他寺僧人为其师——法号觉灵的僧人——撰写的神道碑。尽管文字数量很少,内容也简单明了,但仍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专名考释,以及图像的说明。本文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考释,略述如下。
碑额题有三个字,为“山丙向”。这种碑额,笔者首次遇见。翻检近几年所出墓志铭诸书册,亦未见同类碑额,可谓孤例。“山丙向”,是传统堪舆风水学中辨位定穴的专有名词。由于神道碑被搬离了原位,加之当地乡民说墓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平整土地中已被铲平,对当时墓穴的方位也没有确切的记载,故而无法根据墓穴的方位及方向,确定是“壬山丙向”,还是“艮山丙向”等。碑额选择堪舆专名的缘由,笔者认为并非简单地标识方位,而应该包含更丰富的内涵。至于具体的内涵,尚需要进行细致的田野访谈,方能有合理的解释。
神道碑右起文为“特授山西太原省承宣布政司使泽州府选充灵岩寺僧纲司僧纲源习”,是神道碑撰者源习的职司、地望、衔名、法号等。短短二十八字中,有很多值得推敲的信息需要挖掘。从衔名中职官名“承宣布政使司”[1]前的直省名称来看,“山西太原省”的表述非常罕见,且有悖于现有政书、志书提供的行政等级结构。简单将此种表述,归为僧人对常识理解不清带来的讹误,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无法揭示历史的真实。
稽考《东华续录(咸丰朝)》、《清文宗实录》等材料,以及《大清会典舆图》、《(光绪)山西通志·舆地志》等典志体志书、政书,清文宗咸丰年间,山西并没有太原省独立设置为直省的记载。从习见的行政等级结构来看,自明洪武时,山西由行中书省改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之后,太原府便是其附郭及布政使司治所,且隶属于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在神道碑树立的咸丰年间,泽州已经升为府,与太原府同级,属于府一级的行政区划。这种知识体系下的行政层级及隶属关系,如图所示:

大慈灵和尚觉灵神道碑(局部)

而碑刻中的“山西太原省”的表达和成文,与上述政书、志书中的行政层级及隶属关系迥然不同,初步示意如下图:

“省下有省”的情形,《觉灵神道碑》并非个案,但区域已超越山西。侯杨方教授根据乾隆七年(1742年)《奉天等省民数、榖属汇总黄册》档案中列举的“西安省”、“安庆省”,指出省会城市西安、安庆后加“省”,是作为陕西省、安徽省的代称出现的,其行政空间和辖区与陕西、安徽省完全一致[2]。从前述诸个案可以得知,清人概念中的“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地方一级政区,涵义较为广泛,用法也很灵活,“清代官方对此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志书、政书也仅代表官方意识的一种,并无成文法甚至习惯法的约束力”[3]的论述,可谓的确。但侯氏所居例子中,“西安省”、“安庆省”皆为单独列举,其省城代指直省的结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觉灵神道碑》中的“太原省”,上从属山西省,下辖泽州府,从这样的行政层级来看,作者强调的是递次统属关系,故而侯教授的结论不适于这一种“省下有省”的个案。山西“省”中“省”的确切含义,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太原省承宣布政使司”的职官名已经十分清晰,其行政空间亦不局限于省城附近,而囊括山西全境。前面加“山西”,并非作者的冗余与同义反复,背后有着乾隆时期督抚制取代清初的布政使司制的历史大背景。作为清代官制系统里外官的一种,布政使亦非一成不变。清初沿袭明制,地方一级长官称承宣布政使;乾隆时改为督抚,沿至清末不改。随着巡抚辖区固定,巡抚逐渐由临时差遣变成了地方长官,而布政使则成为巡抚的下属。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朝官方正式确定督抚升于布政使之上,“今外官之制,督抚专制一方,而《会典》载天下府县及外官品级,犹以布政使司布政使领之,称名殊觉不顺。清改《会典》所载外官品级,以督抚居首,次及布、按两司”[4],这标志着巡抚正式取代布政使成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神道碑刊立的咸丰年间,山西巡抚亦已固定,故可以对前述图作如下修订:

作如上解读,《觉灵神道碑》中“山西(巡抚)太原省承宣布政使司泽州府”的衔名及职官名的复原,方符合咸丰时期的历史事实,亦不致囿于“省”的舆地沿革考察,而忽略“省”相关的职官变化。
衔名后半部为“选充灵岩寺僧纲司僧纲源习”,提供了清代泽州僧政管理的很多信息。神道碑中的“灵岩寺”,亦见于《(雍正)泽州府志》:“松林寺,在城西南松岭山。一名灵岩寺,隋建;明僧法亮于南都造藏经六千四百卷,六百四函,建塔藏之,刘龙有记。金刺史杨庭秀碑,李俊民篆额,金太和(泰和)丙寅端午。一名法轮禅院。”[5]田野调查中,松林寺原址只有20世纪80年代建筑,旧貌已不可知。惟山顶有一祠,亦非旧物,稽考《松林法轮禅院碑》,“岭之阳,有佛宇耶,即古之灵岩院也……是寺僧感念卫公之惠,乃于山顶建祠,迄今存焉。”[6]根据碑志记载,咸丰年间泽州府僧纲司驻锡在灵岩寺(即松林寺)。而在明清诸方志中,泽州地区僧纲司驻锡地记载阙如,倘或如是,此点可补史志之阙。《(雍正)泽州府志》虽然没有明言灵岩寺为僧纲司驻锡地,但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灵岩寺藏有大量的经卷,“明僧法亮于南都造藏经六千四百卷,六百四函,建塔藏之,刘龙有记”。与之相比类,大同府僧纲司所在华严寺亦有大量佛藏经,“大同华严寺,国朝洪武三年改正殿为大有仓二十四年即教藏置僧纲司寺复立焉”[7]。清代的僧纲司,设于府一级的佛教管理职衔,为末流散职。《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僧录司左右善世各一人,左右阐教各一人,左右讲经各一人;左右觉义各一人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属曰僧纲司,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州属曰僧正司,僧正一人;县属曰僧会司,僧会一人,各掌其属释教之事”[8]。由《皇朝文献通考》可知,府一级设立“僧纲司”,职衔为“都纲”,而《觉灵神道碑》中为“僧纲源习”。两下比照,“僧”或许为“都”之讹误。
《觉灵神道碑》的刊刻者选取堪舆术语为碑额,带有晋东南浓郁的地方气息;撰文僧人衔名中“山西太原省承宣布政使司”,是清代“省”行政层级概念和运用的重要个案,可以与他省信息相互参证;“僧录司”的信息,又可补泽州地方佛寺管理的史志之阙。以上是对碑文内容简单的考释,求正于方家。
[1][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4,《吏部三·官制三·外官·各承宣布政使司》,明万历内府刻本,第1页。
[2]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5卷第3辑,第21~22页。
[3]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第27页。
[4][清]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28《乾隆二十八·十一月丙辰》,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第61页~62页。
[5][清]朱樟修《(雍正)泽州府志》卷21,《寺观·凤台县》,清雍正十三年刻本,第2页。
[6][金]杨庭秀《法轮禅院记》,[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3,《金》,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第26页。
[7][明]胡谧修《(成化)山西通志》,卷5,《寺观·大同·华严寺》,民国22年景钞明成化十一年刻本,第52页。
[8][清]稽璜等《皇朝文献通考》卷88,《职官考十二·附僧录道录等司》,清浙江书局本,第21页。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晋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