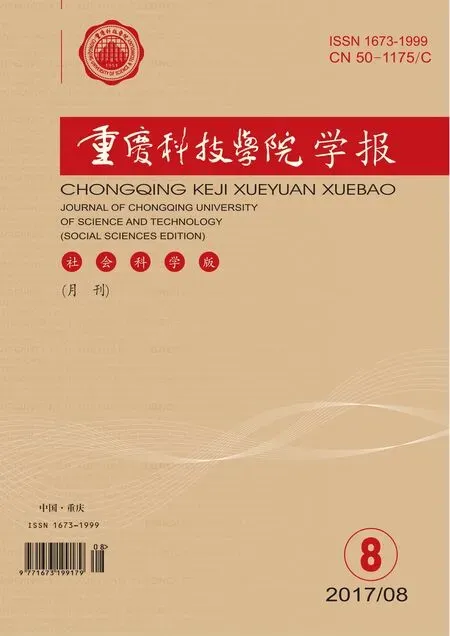寻找与逃离:《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重复叙事解读
曾薇,刘俊玲
寻找与逃离:《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重复叙事解读
曾薇,刘俊玲
通过对卡波特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进行文本细读,从重复叙事这种结构范式切入,发现文本采用了结构重复,意象重复和场景重复的手法,体现出作者对小说主人公乔尔的“寻找”和“逃离”之路的独到理解和处理。从这3种重复叙事语言的分析入手,探讨其重复叙事中所隐含的潜藏文本和深层主题意义——逃离孤独、寻找关爱和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小说叙事;重复叙事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Other Voices, Other Rooms,以下简称《别》),是美国南方文学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具有美国南方哥特风格的自传性质的成长小说。小说围绕13岁男孩乔尔·哈里森·诺克斯的寻父(亦是寻觅自我)的历程而开展,对孤独、恐惧、成长、爱情等主题进行了探索。小说通过比喻和象征,叙述了主人公乔尔从孤独恐惧的童年走向认同自己身份的历程,展现了生命中潜在的希望和失落的天真。小说通过重复叙述手法,以半隐秘的语言营造出诗意、奇特而神秘的氛围,展现出作者惊人的语言文字驾驭能力。约翰·贝伦特为该书撰写导读,评论到:“这是有声有色的文字游戏:华丽、璀璨、大胆,没羞没躁地炫耀”。尽管当年书中的某些内容,如伦道夫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对爱情的独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该书总体评价很好,读者众多,成为了美国南方哥特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1948年,该书出版后,批评界的反映非常不错,《纽约时报》的每日评论员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称赞“(卡波特)魔力无边的文笔”,并且声称该书“是明确的证据,证明一个才华横溢的新作家已经到来”。
《别》所呈现的是卡波特众多小说所共同体现的主题——逃离孤独,寻找关爱。伦道夫说:“任何存在于人的天性中的爱都是自然、美丽的,只有伪君子才会追究一个人所爱为何。 ”[1]165《别》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然而,透过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卡波特运用重复叙事的策略,让读者体验到一种言尽意未尽的阅读感受。小说强化了乔尔在寻找和逃离之路上变化纷呈的内心感受,呈现出独特的讲述效果,突出了文本的形式审美和主题的深邃。
重复,最早是修辞学术语,指依靠重复某一词或短语来表达特定的修辞手法。正如热拉尔·热奈特所说,“一件事不仅可以发生,而且可以再发生或重复”“‘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构筑,它去除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出现的共同点”“一系列相似的、仅考虑其相似点的事件在这里将被称作‘相同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复现’”[2]。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式成链条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在先锋文学的叙事策略中,重复叙事起到了强调“存在”的真实性的作用。“存在与不存在的界限被拆除了,每一次的重复都成为对历史确定性的根本怀疑,重复成为历史在自我意识之中的自我解构”[3]。重复叙事是指叙述过程中语言和事件的反复重复,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叙事手段,它注重事件和情节的反复性,并以此增强叙事效果。J·希利斯·米勒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复”理论,将小说“重复”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细小处的重复,如词语、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第二类,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比第一类大;第三类,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另外,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指出,“不管是什么样的读者,对小说这样的长篇作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重复及其所产生意义的认同来实现的”[4]。我们将从文本的结构重复,意象重复和场景重复3个方面探究小说的主题。
一、文本的结构重复
《别》的重复叙事集中体现为叙事结构是不平衡的、重复的,叙事呈现出循环发展的趋势。文本整体结构分为3个部分:第1部有5章,125页;第2部有5章,97页;第3部只有1章,33页。文本的不平衡使整部作品似乎头重脚轻,但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在卡波特独具匠心的运用下,巧妙地刻画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揭示并强化了乔尔想要逃离被抛弃的恐惧、孤独的悲伤、渴望寻找被爱和被理解的主题,达到了增进叙事效果的目的。文本的结构重复首先表现在主人公乔尔流浪的生活状态的不断重复——不断反复地逃离和寻找。乔尔自小就被父亲遗弃,和母亲在新奥尔良过着阴郁的生活。母亲病逝后,他随埃伦姨妈一家一起生活,斯卡利庄园来信后,他独自踏上了寻父之路,一路辗转颠簸,到达庄园后却发现父亲无处可寻,当最终被允许见到父亲的时候,他采纳了伊达贝尔离家出走的建议,再次踏上流浪之路。米勒提出的重复并非简单的故事内容的重复,而是通过重复表现一种深层意义。小说的故事内容事事相连(这有利于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反映小说意图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但小说包含一种共同的情景:当它出现后,又以某一种形式出现于另一个场合。这一系列情景可以被认为是重复[5]。结构重复在于通过一系列结构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词语和句子,将所要表达的东西以明显的语言形式呈现出来,以重复使用来表达某种需求愿望或心理诉求等。《别》中比较明显的结构重复包括乔尔的主要生活经历的重复以及他的心理状态的不断重复等,这些都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驱动读者细读品味。首先是“I hate……,he resented……,I don’t like……”类似的结构多次出现,表达乔尔在流浪、成长的过程中产生的孤独感和恐慌感。无论在埃伦姨妈家还是在斯卡利庄园,乔尔都不快活,每一次都幻想着离开。乔尔寄宿在埃伦姨妈家时,他的内心世界是“恨他们”[1]12,具体表现就是不愿意与他们说笑,从不参加饭后姨夫发起的游戏,嘲弄有点耳背的表姐,总喜欢指出别人的语言错误。乔尔的第一次幻想是在离开姨妈家前,他幻想自己是《冰雪女王》里的小加伊,“中了魔法被带到冰雪女王的冰封宫殿,那又有谁会勇斗强盗骑士,前来营救他?”[1]12到达斯卡利庄园后,乔尔再现了生活在姨妈家的情形,他讨厌这个宅地,讨厌假小子伊达贝尔,“心里恨透了她,希望她最好从树上掉下来,摔断脖子。”[1]122他的第二次幻想是给埃伦写信的时候,他希望埃伦此时此刻就陪伴在他身边,“她会安排他离开去上学”[1]123。见到父亲桑瑟姆先生后,乔尔对瘫痪在床的父亲感到失望至极,从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想要离开。他“害怕回去换衣服碰上埃米,她可能会说不许他去,或者还会叫他去念书给父亲听”[1]139。不管是离开姨妈家还是从斯卡利庄园出走,逃离的实质其实是逃离孤独——乔尔觉得往鱼钩上穿虫子很恶心,但他愿意和伊达贝尔一起,“只要不孤独,做什么都无所谓,管它是穿虫子,还是亲吻她的脚,都无所谓。 ”[1]138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文本重复使用“he was glad to go,he’d like to go……”的类似结构来表达乔尔离开的喜悦。作者反复运用对比性叙事的重复结构来展现乔尔在“逃离”前后的矛盾心情,增强叙事效果。乔尔从妈妈家辗转到庞恰特雷恩湖畔的埃伦姨妈家,再跋涉到斯卡利庄园即他的父亲——桑瑟姆先生家,然后出走到中天城,每一次在路上他都热情洋溢,既充满希望又夹杂些许恐惧。斯卡利庄园来信后,12年前抛妻弃子,离家出走现在又不可思议地突然冒了出来的父亲来信后,乔尔很高兴能离开,他不觉得意外,“因为他一直都期待着会有类似的福祉降临”[1]14。在抵达庄园前,乔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很害怕,因为自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失望”[1]14。与父亲见面后,当伊达贝尔建议离家出走时,乔尔马上响应,逃离斯卡利庄园令乔尔振奋不已,如同当初离开埃伦姨妈家,逃离之路“就像任人漂流的河流,仿佛有一只罗马烟火筒,突然被一口自由的气息点燃”[1]209。 离家出走的乔尔在听了巡回表演的侏儒紫藤小姐的故事后,意识到“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1]209。 故事的结尾是乔尔逃离到中天城后被伦道夫找到并送回斯卡利庄园。但是这个结局真的就是作者呈现的既定的,唯一的结尾吗?乔尔在花园里幻想“自己坐在圣代沃尔大街的街边,或者在露天剧院的外面”[1]260。 读者禁不住思考:乔尔是继续留在这个日渐下沉的死寂的庄园里,还是终有一天会无法忍受那样的死寂,再一次逃离那里,继续流浪?卡波特在整部文本结构上运用的这种重复叙事方式所营造的叙事循环——一种周而复始的封闭式结构给叙事带来了不确定性,产生了叙述空白,从而产生了一种跳跃性思维。这体现出对乔尔的寻找和逃离的处理别具匠心。
二、文本的意象重复
“意象表现的是一刹那时间中理智和情感的复合……是任何一种内心冲动所获得的最充分的表现或解释”[6]。这是意象派诗歌的创始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所解读的叙事意象。《别》中充满了各种象征物:庄园,蛇,剑,眼睛,镜子,花园,雪,钟等。 卡波特反复运用诸多的叙事意象,不仅给读者呈现出乔尔矛盾复杂的内心感受和性格特征,而且强化了文本表达的深层主题意义,使读者产生切身体验的叙事效果。
眼睛作为最重要的叙事意象重复出现了多次,给读者呈现出一种哥特式的怪诞和离奇。来到斯卡利庄园后,乔尔猜想这所老房子里的画像上的眼睛“根本不是眼睛,而是一些窥孔”[1]56。 乔尔甚至怀疑父亲已经通过这些窥孔在暗中见过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冒牌货”,因为父亲期待的儿子应该更高,更壮,更英俊,更聪明。他设想如果父亲要把他打发走,他该何去何从呢——“去异国他乡……做个手摇风琴艺人,做一个在街头卖唱的盲孩子,还是做个叫卖铅笔的乞丐?”[1]57如此叙事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热情,令读者产生先入为主的观点——在这个神秘的庄园里会发生怎样离奇的故事:乔尔是会鼓足勇气,耐心等待父亲的召见还是不堪忍受这种不知期限的等待。卡波特为乔尔之后的离家出走埋下的伏笔。孤独可怜的乔尔一方面渴望与父亲相认,一方面又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不被接纳、不被爱。
意象是一种诗化的语言表现手段。卡波特描述黑人女孩密苏里打量乔尔时的双眼像酸葡萄又像黑瓷;伦道夫的眼睛像天蓝色的大理石。乔尔在伦道夫“无邪的圆眼睛”中,看见自己的脸“像是映在单反相机镜头里。”[1]96乔尔与埃米聊天编故事时提到他曾见到一个“有一双恶魔般的眼睛”的女人,“女巫一样狂野的眼睛,冰冷翠绿,犹如北极的海底”[1]91。 所有这些有形的,无形的眼睛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作者反复书写的这些眼睛象征着一种审视和监督,乔尔内心不仅担忧父亲是否认可、接受他,同时也努力想讨好这个安静、死寂的宅地里的其他成员。卡波特通过对桑瑟姆先生眼睛的描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乔尔第一次和父亲见面,看到镜子里映出卧病在床的一双眼睛,从“注意到它们的那一瞬间起他的眼里便不再有别的东西”[1]135。乔尔给瘫痪在床的父亲朗读故事的时候,父亲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只是瞪着眼听。乔尔甚至认为父亲的眼睛可以“看见他心里的活动”[1]192,自己无法躲避这双眼睛,“它们的确像是渗透到了房间的每个角落”[1]191。 “桑瑟姆先生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双荒唐的眼睛”[1]192。 眼睛代表着父亲,而父亲则代表了社会秩序和道德的维护者与实施者。乔尔为自己没有更加同情并关爱桑瑟姆先生感到愧疚,自然不愿意受到这双几乎从来都不闭上的眼睛的审判,乔尔认为自己不可能躲避这双眼睛,无法躲避这种监督和审判。
乔尔的容貌在叙述进程中出现不多,但却是重要的叙事意象。卡波特借司机拉德克利夫之眼表达了对乔尔长相的不喜欢,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孩儿,“他太漂亮、太精致、太白皙……眼里有女孩儿家般的柔情”[1]5。 借罗伯塔小姐之口,乔尔给人的印象是“漂亮的小家伙”。在假小子伊达贝尔嘴里,他被称作“娘娘腔”“小鸡崽子”。唱歌的时候,他的声音“高亢甜美,像个小姑娘似的”[1]180。 作者反复描写乔尔阴柔的气质,与乔尔内心想象自己是正真的男子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庄园的第一个早上,乔尔认定敲门的是他的父亲,他做好准备,要给对方留下“一个最好的、最有男子汉气概的印象”[1]48。
乔尔容貌这一叙事意象的复现,表达了乔尔内心的微妙变化,清楚地呈现了乔尔在精致的外表下有一颗遵循主流社会对性别判定要求的心——用主流男性社会的规范来要求自己做一个男子汉。令乔尔痛苦难堪的是他力图表现的男子汉气概常常受到现实世界的挑战和打击。乔尔和伊达贝尔洗澡后,乔尔撒谎说自己从来不哭以示顽强,并想通过拥抱亲吻伊达贝尔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扭打搏斗。乔尔在强烈而困惑的愤怒下,反击未遂,仍不愿意承认投降,只说自己流血了来结束这场打架。渡河时,乔尔冲到了前面,他认为“不管伊达贝尔怎么说,他到底还是男孩,而她是女孩,如果再一次让她占了上风他就可真叫见鬼了”[1]201。近距离面对一条水腹蛇时,乔尔僵硬地愣神,感觉桑瑟姆先生的眼睛在水蛇头上,“眼里心里都只看得见桑瑟姆先生在盯着他”[1]202;伊达贝尔夺剑杀蛇,毫不含糊,保护乔尔,大获全胜。这一幕出现了人物内心透视和外在描述的相互转换,是乔尔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文本中的亲吻,蛇和剑种种意象,都充满了象征意义,暗示了乔尔无法如自己想象的那样表现自我,对如何正视自我,改变自我的无能为力。
卡波特通过对意象的重复叙事,表达了特殊的主题意义——乔尔前往斯卡利庄园寻找父亲的旅途是走进自己,也是走进作者卡波特潜意识的一个过程,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整个寻父之旅的目的除了希冀寻找爱和温情,还包含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命题,即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寻找自身价值。作者巧妙运用重复叙事技巧,让读者和乔尔一起慢慢地拨开重重迷雾,寻找并走进真正的自我——当乔尔最终摆脱寻父的烦恼后,剩下的就是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乔尔·诺克斯是谁?乔尔在文本的结局,意识到了“我就是我……我是乔尔,我们是一样的人”[1]255。 文本的另一个叙事意象——站住窗口的神秘白发女人——其实也是文本的另一个主要代言人——伦道夫,在文本的结尾处召唤着乔尔,乔尔知道自己必须到她那儿去。他转过头去看了一眼“那个他已抛在身后的男孩”[1]261。很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这个结局意味着乔尔会如卡波特那样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生活下去。然后,卡波特说自己从未想过乔尔在30或40岁时会是什么样子。戴安娜·特里林在《国家》周刊上的书评中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她认为卡波特试图在说“一个男孩成为同性恋者,是因为他的生活条件拒绝给予他的感情需求以另一种、更为正常的满足”[7]。我们认为这样的评论毫无根据,因为整个文本没有一处有这样明确的意图。通过走向窗口边的女人,笔者更倾向于解读成——乔尔走出了童年的恐惧和阴影,不管自己是否足够勇敢,是否能够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他知道自己已经足够强壮,终于能接受自己,正视自己了。
三、文本的场景重复
米勒指出,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的活动方式,是通向作品内核的秘密通道,如果有这一内核的话。循着重复的踪迹,文本中场景的重复成为阐释意义的有机线条,将读者带到不同的意义场域。具有一定寓意的场景,片段在关键时刻反复出现可以达到刻画人物,深化主题的目的。文本中神秘恐怖的场景,充满哥特风格的现实与梦境的反复交织,突出了主人公渴望被爱、恐惧孤独的主题。
《别》的开篇就呈现了一系列怪诞诡异的场景,很多场景是乔尔的想象或者幻觉。文本中反复描写乔尔的各种幻想,其中有一部分想象是卡波特为乔尔的寻找和逃离铺设合理路径的描述,特别是乔尔对父亲的各种幻想。乔尔的寻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文本的核心事件是乔尔寻找父亲,读者大多和乔尔一样,认为从埃伦姨妈家到达斯卡利庄园就是寻父的全部旅程,顶多在这个宅地里睡一晚后就可以见到父亲。整个文本共261页,读者和乔尔在刚得到关于桑瑟姆先生的一点线索就被带到另外的事件的焦虑的等待中,在文本的135页时才等来了与父亲的相见。在和父亲见面之前,卡波特多次描写乔尔头脑里想象的父亲形象和见面的场景。幻想场景的复现凸显了父亲角色的长期缺失,母亲的离世,对乔尔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和困扰。乔尔一方面期待一个温暖的怀抱,一个温馨的家,另一方面又恐惧这种未知的生活,在找到去庄园的马车后,这两方面的冲突达到了高潮——“乔尔忽地有一种想要叫他回来的冲动,因为他突然不想独自去斯卡利庄园了”[1]33。
乔尔的父亲最初是以一种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乔尔的生活中,那时的乔尔还住在姨妈家,终日幻想有谁来营救他,比如有人给他寄来塞满了钞票的信封,使他可以离开埃伦一家;结果来拯救他的就是他的父亲,“这在他看来简直就是莫大的幸运”[1]11。 父亲此刻的形象是慈祥的。在独自寻父的途中,由于没有获悉任何来自庄园的信息,乔尔再次幻想父亲的生活境况很可能和之前写信时“截然不同”[1]14。这时对父亲喜悦的幻想被乔尔忐忑、焦虑的幻想取代,想得越多他就越害怕,甚至使他无法控制地战栗、流泪。他希冀路上遭遇的每一个人都能进一步细说些庄园的情况,以此补足或者修正自己对父亲形象的想象。在庄园的第一个早上,乔尔一遍又一遍激动又紧张地幻想着、演练着与父亲第一次谋面的情形。他一直在心里默默地准备着,预演与父亲相遇时的情形,比如他应该如何称呼并问候桑瑟姆先生——“是拥抱,握手,还是亲吻?”[1]48这是卡波特就乔尔对父亲幻想场景的第3次描述。与父亲见面未遂,乔尔从第一时间的些许失望,到怀疑“是不是父亲其实已经见到过自己了?”[1]56他站在父亲的角度想象着父亲并不认可自己的场景:父亲要的是一个更高、更壮、更英俊、更聪明的儿子,而自己只是个“冒牌货”,一个“小骗子”,随便就可以被打发走。这次幻想场景的描写充满了悲情色彩,尽显乔尔挥之不去的孤独痛楚、伤痕累累的内心世界。与之形成对比的第5次幻想场景的描写发生在给好友的信中乔尔满纸胡言,其实他勾勒的就是自己想象的,期许的父亲形象——“如此这般的英俊”,声音是“洪亮又慈爱”“对于一切有关飞机的事儿都了如指掌”“不戴眼镜”“不抽雪茄”,“抽斗烟”“很高”[1]102,他还天马行空地编织出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情景:父亲送给他一把步枪做礼物,冬天俩人一起去打猎,回家还要炖负鼠汤。作为一个13岁的小男孩,正是想象力丰富的时候。在与父亲见面前,乔尔既期待又恐惧,自然对父亲这一角色充满了各种幻想。他期许的父亲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强者形象,能够指引他,成为他成长的榜样。
在卡波特笔下,种种想象场景的复现,使一个生动鲜活的小男孩形象跃然于读者面前。这些幻想的场景时而令乔尔感觉终于有人来真正地关爱他,可以给朋友炫耀这个与众不同的父亲;同时他也深受这些幻想的折磨,担心父亲不喜欢他,害怕父亲认为他缺乏男子汉气概。正是在这一次次难耐的等待和惶恐的想象中,乔尔的再次逃离成为必然——不想再为无处可寻的父亲这个事烦恼。这种逃离,实际就是一种逃避,在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者无法解释的情形时所产生的一种本能心理。每一次逃离都是为了去到别的地方,离开此地,前方总会有适合的生存之路。乔尔的足迹表明了即使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过去的影响也是挥之不去的。他在斯卡利庄园会想起曾经幻想逃离的埃伦姨妈家,离家出走后又念念不忘伦道夫。正如文本中的隐士小阳光在叙述云中酒店的故事时,解释自己为什么留在这个可怕、怪异的酒店时说道:“如果他走了,就像曾经离开过的那次,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些逝去的模糊声音将总会萦绕他的梦乡。”[1]112读者从中会得到一种暗示,体会到文本标题的内在涵义进而领悟到作者的用意。结合卡波特自身的童年生活经历,乔尔身上毋庸置疑叠加了卡波特本人的经历。和小说中的乔尔一样,卡波特的童年不幸福,4岁时父母离异,被送去母亲的远房亲戚那里生活,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一个温暖、安全的成长庇护,孤独恐惧成为卡波特童年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些对父亲的幻想不仅属于乔尔,也属于卡波特自己。
四、结语
解读卡波特小说的深层意蕴,必须透过叙述的表层,层层剖析,才能挖掘出文本的真实内涵。叙事的巧妙运用,使读者通过自居作用,不仅沉浸在故事中,还参与了文本的意义构建,“让接受主体随着人物意识的流动,直接进入作品人物的灵魂深处”[8],大大加深了读者对乔尔情感世界的洞察力和对主题核心的理解力。透过《别》这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卡波特运用重复叙事的策略,让读者体验到一种言尽意未尽的阅读感受,感受到乔尔被遗弃的深深恐惧,孤单带来的痛苦,对于被爱的渴望,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找爱,逃离孤独,寻找希冀和温情,逃离不知所措的惊惶。乔尔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之路是由古怪却明智的伦道夫给出的,在卡波特笔下,最终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并非部分评论家把乔尔的身份解读为一个同性恋者;而是乔尔最终走出童年的恐惧,摆脱自我怀疑,正视不够勇敢、不够完美的自己。仅以寻父为叙事框架,通过对结构、意象和场景等方面的重复叙事,卡波特成功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强化了乔尔在寻找和逃离的成长之路上的内心变化纷呈的感受,使整部小说呈现出独特的讲述效果,突出了文本的形式审美和主题的深邃。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读,证明要挖掘《别》的潜藏文本和主题意义,对重复现象的合理阐释是一有效途径。
[1]杜鲁门·卡波特.别的声音,别的房间[M].李践,陈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3.
[3]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6.
[4]MILLER J H.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M].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
[5]罗杰鹦.对米勒《小说与重复》中的重复观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15(4).
[6]林骧华.西方现代派文学综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3.
[7]PURINGTON G.Truman capote[M].New York: Anchor books,1998:79.
[8]李常磊.意识流小说的叙事美学[J].山东社会科学,2006(10).
(编辑:王苑岭)
I106
A
1673-1999(2017)08-0071-04
曾薇(1981—),女,硕士,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研究;刘俊玲(1980—),女,硕士,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研究。
2017-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