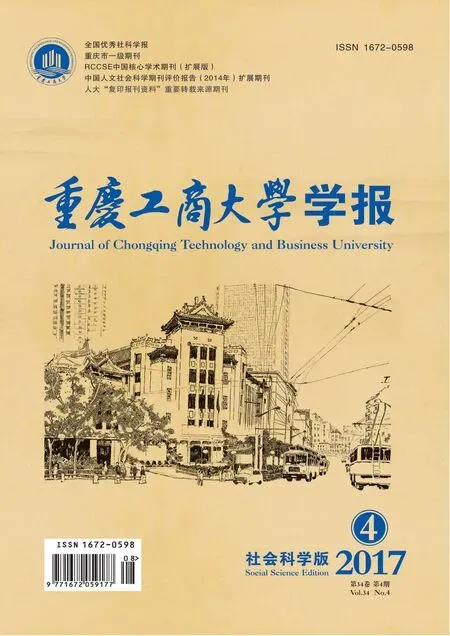论《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身份焦虑*
杜明业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论《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身份焦虑*
杜明业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讲述了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克隆人,凯茜等人具有强烈的身份焦虑,一直在试图发现“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渴望寻找自己“可能的原型”,以图建构起自己的真正身份。石黑一雄试图揭示出克隆人的身份的暧昧与焦虑以及由此带来的认同危机问题。从凯茜等克隆人内在的身份焦虑之缘由和身份建构过程入手,研究克隆人的心路历程、成长困惑及其命运归宿,试图揭示这部小说本身所蕴藏的哲理上的普遍意义和重要的当代价值。
《别让我走》;克隆人;身份焦虑
1897年2月,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完成了一幅充满哲理性的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整个画面刻画出了人由生到死的生命轨迹。在斑驳绚丽的画面中寄寓着画家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给人提供了哲理思考的素材。这是人类群体对自身的拷问,涉及人类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归属定位。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更是引发人类对自身的深思,甚至是怀疑。这与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 )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2005)所刻画的克隆人的命运发生耦合。
《别让我走》讲述了凯茜·H(以下简称凯茜)等克隆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作为人体器官供应者的故事。克隆人在短暂的一生中,凝结着浓重的身份意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将到哪里去”三个问题困扰着这些人类的新品种。这批克隆人群体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最初对自我身份的模糊认识,到对身份的寻访与确认,最终构建起自己的身份。这一过程折射出的是克隆人深层次的身份焦虑问题。本文拟对这一论题予以探讨,以揭示出克隆人的心路历程、成长困惑和命运归宿。
一、身份的谜团
从词源上看,英语中的identity(汉译为“身份”“认同”或“身份认同”)一词来自于拉丁词 identitas。它有两种基本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表示人或者物的绝对同一性,即两者是相同的;第二个含义表示人和物在时间中的持续性和自身统一性,表示自身的独特性。换而言之,身份是指从本质上能够确认或识别人或物的特征总和。身份涉及多个方面,如伦理的、法律的、社会的、职业的等等。对身份的观察也可以从哲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多个角度展开。而身份问题的核心是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即对于“我(们)是谁”的追问,以及对他人身份的认定,即对于“他(们)是谁”的追问。陶家俊将身份认同分成四类,分别是: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1]。小说中的克隆人的身份认同兼有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后一种。
在克隆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克隆人的身份问题一直是科学界、社会学界、医学界和法律界争论的焦点。生物学认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个体的人是自然生育而来到世间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都是社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身父母和特定的人伦身份。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还具有感知觉、情感、意识、思维等属性。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从笛卡尔到福柯始终在寻求人作为主体的“自我”认证,现代哲学则试图探讨“我是谁”的本体问题。如何在生物学等不同层面的规定性下审视克隆人,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都是难题。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克隆人可以批量地被“制造”出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克隆人的“我是谁”的本体问题?如何界定单个人与克隆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克隆人的伦理身份?
“我们是谁”的问题始终让凯茜等所有克隆人群体感到困惑,他们对问题答案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追问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身份焦虑的体现,其实质在于如何定位他们的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
在现实世界,孩子的法定监护人通常是父母或直系亲属,而小说中的克隆人没有也不可能有法定监护人父母,他们在黑尔舍姆的“监护人”是由埃米莉小姐、杰拉尔丁小姐等“正常人”充当的。这些特殊的“监护人”还身兼教师的角色,教学生学习各种课程,阅读诗歌,做游戏等。克隆人的最好绘画作品常常被神秘的埃米莉小姐挑走送进“画廊”。 汤米·D(以下简称汤米)曾一度因为绘画作品没有“入选”而懊恼不已。为什么克隆人要学习绘画,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迹。小说后半部分写道,当凯茜和汤米前去拜访埃米莉小姐时,他们心中的疑惑才解开。埃米莉小姐解释道:“我们拿走你们的美术作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能够展示你们的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你们也是有灵魂的。”[2]239这才是黑尔舍姆学校开办的目的,即试图把克隆人被培养成为“和任何正常的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2]240。
命名是借助于某种名称符号对事物予以确定性的表达。在基督教传统中,命名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和仪式。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把他所创造的万物给予各种名称。而身份认同作为一个过程,命名(naming)是实现这种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好莱坞电影《逃离克隆岛》(The Island 2005)讲述了这样的故事:21世纪中期,一对克隆人夫妇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中,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被选中成为没有任何污染的一个“天堂岛”的访客。不久,他们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他们的“原型”(originals)提供各种更换用的身体“部件”。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最终安全逃离了“神秘岛”到达南美洲。电影中的两位男女主角林肯·6E和乔丹·2D的命名相当特别。林肯和乔丹是他们的名字,其中的E、D是非法生化机构的E、D代产品,6和2分别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顺序。在这群身处偏僻乡间的儿童与世隔绝,除了露丝以外,每个人的姓氏中都包含一个英文字母,如凯茜·H、汤米·D和亚历山大·J。每个人名字中的字母可能是他们被克隆的人类“原型”的姓氏缩写,凯茜·H、阿瑟·H、玛莎·H可能来自同一个父本或者母本。克里斯托弗·C、珍妮·C、帕特里夏·C、戈登·C与希尔维·C等也是如此。这些字母包含着他们的身份来源信息。与此相反,黑尔舍姆学校的“正常人”或监护人都有正常的名字或称呼,如玛丽—克劳德夫人、埃米莉小姐。而向学生透露真情的“监护人”露西小姐还有她的全名——露西·温赖特(Lucy Wainright)。令读者费解的是,凯茜、汤米等克隆人从未问过“我有没有家庭?谁是我的父母?”之类的问题。至于克隆人和“可能的原型”(possibles)之间的关系,有人说:“我们和我们原型之间为什么必须是‘自然的’上下辈份呢?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婴儿、老人,那会有什么不同呢?另外的人则回敬说,他们会使用正处于健康巅峰的人做原型,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可能是那种‘正常父母’的年纪。”[2]127这就为后文中这些克隆人寻找“我们的原型是谁”埋下了伏笔。
“我们是谁”的问题始终让所有克隆人感到困惑。如果说克隆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对其自我身份的追问,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又是谁”又相伴而起。在克隆人眼中,两者是不同的。克隆人力图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种认同感,“他们”是凯茜等克隆人的“他者”,他者即为自我之镜,通过他者可以反观自我。显然,小说中的“他们”既指黑尔舍姆学校围墙之内埃米莉小姐们等,也指黑尔舍姆学校围墙之外的人——偶尔来学校送货物的人,在“村舍”居住时供给他们生活用品的人,取走他们主要器官的“白大褂”们。但在黑尔舍姆,有人不断地告知克隆人“你们是学生,你们是……特别的”[2]63。不过,对克隆人到底“特别在何处”的敏感问题,埃米莉小姐等人一直在刻意地回避。当露西小姐向学生透露出他们的“特殊之处”后就被迫离开黑尔舍姆。凯茜等克隆人生活在“被告知而又没有真正被告知”的现实中。换而言之,这些克隆人生活在被“他们” (即正常人)蒙蔽的状态中,对凯茜等克隆人而言,其自身的身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有待于解开。
相对于克隆人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在“他们”眼中,这些克隆人的身份是异常明确的:黑尔舍姆学校所有学生都是“人体器官提供者”(donor)。只不过那时他们的各种器官发育尚未成熟而已。凯茜等克隆人非但没有像鸡鸭牛之类的动物那样被饲养,反而能够在黑尔舍姆接受教育,是因为埃米莉小姐力图向世人表明克隆人“根本上也是有灵魂的人”;并且,假如把他们“养育在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长为和任何正常的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2]240。这就是黑尔舍姆学校存在的价值。可以说,这所学校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阴谋。
二、对身份的追问:寻找“可能的原型”
在目前身份研究的各种理论中,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是影响较大的一种,是由泰弗尔(Henri Tajfel)和特纳(John C.Turner)等人所共同创立。在泰弗尔看来,社会认同是指“个人对他/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3]社会认同包括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基本阶段。类化是指人们把自己编入某一个社群,认同是人们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所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劣、地位和声誉。该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文学研究中。科幻作品中的另类生命,如玛丽·雪莱笔下的“怪物”、泰国作家维尼暖的《克隆人》中的启万和傲拉春、伊拉·莱文的《巴西男孩》中“巴西男孩”以及好莱坞电影《逃离克隆岛》中的林肯·6E和乔丹·2D等都会遇到类似的身份认同问题,而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过程中也会经历上述历程。在玛丽·雪莱笔下,弗兰肯斯坦曾经创造了“人造怪物”, 这个“怪物”没有名字,也没有身份。“怪物”曾经质问弗兰肯斯坦:“我究竟算什么呢?我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这个缔造者又是谁?对此我全然不知……”[4]“怪物”在和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误解、伤害,才要报复人类。如果说“怪物”想要确认自己的身份,想要了解自己的出身与来历,那么《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也想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复制”的,各自的“可能的原型”又是谁。在克隆人看来,只有找到自己的原型,才能解开身份之谜。不过,凯茜等人从来没有像“怪物”那样追问谁是自己的“创造者”,只是想找到自己的“原型”。
离开黑尔舍姆以后,凯茜等八个人被送到一个破旧的农场,即“村舍”(Cottages),其他人去了白楼或白杨农场。在“村舍”期间,这八个克隆人与来自其他地方的克隆人“老兵”如克丽西、马丁、罗德尼等一起生活,将进入一个过渡期。在这里,他们不必为生计而发愁,不用去参加任何工作,只需要接受“培训”,生理上也会逐渐成熟。在对自己的特殊身份有所了解后,他们对自己的来历怀有更加强烈的神秘感和好奇心。尽管来自黑尔舍姆的学生在第一次听说“可能的原型”时感到不安,认为“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事……这不是一个你可以随意谈论的话题”[2]127。然而,“我们都想知道我们的原型”[2]166还是成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他们之间也有过激烈的讨论,意见分歧很大。但是却又坚信世界上有自己的原型。他们渴望知道自己“可能的原型”是谁?又在哪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自己的原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内心深处的自我,也许还能预知自己未来生活的某些事情”[2]128。如此一来,他们每次外出时都会刻意在各种场所找寻各自“可能的原型”。
露丝是坚定寻找自己原型的其中一位。她曾经在一本彩色杂志中看到一幅带有现代敞开式布局写字间的广告画面,便想象自己的原型应该是一位在安装了漂亮玻璃门的写字间里工作的体面职业妇女。而罗德尼和克丽西也在一个海滨小镇搜寻这样的地方。终于罗德尼在海街闲逛时意外了露丝“可能的原型”。为了证实他的发现,罗德尼与露丝等人驱车去诺福克镇寻访自己的身份。最终他们在一个大写字间里看到一位女士。这位女士50岁左右,身着蓝色套装,身材良好。露丝对这位女士仔细观察之后,感到绝望。她的绝望恰恰说明了露丝等克隆人对自己的原型极度关注。小说没有也不可能给出答案,这种谜团留给了读者去加以猜测。
在“村舍”时期,克隆人在试图找到自己的“可能的原型”,可以说在试图找到高更之问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然而,寻访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不管是露丝、凯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原型”。 事实上,露丝等人不遗余力地找寻自己的原型的行为,显现出克隆人的强烈的身份焦虑感。可以说这是高更之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谁”的延伸。
三、对身份的认同:“安静的牺牲品”
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身份的建构需要一个过程,然而一旦这种过程结束,个体或群体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就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或认可并接受,或拒绝与抗争。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克隆人对自己的群体和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是与“正常人”不同的“人”,两者分属于不同的世界。虽然凯茜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原型”是谁,但他们知道自己是被“复制”过来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凯茜等克隆人在寻访“可能的原型”的努力失败后不久就被转移到了一个叫金斯菲尔德的地方。在这里,看护员(carer)、捐献者(donor)是他们的身份。如果说看护员、捐献者尚且属于一种职业身份的话,则这种职业则是他们命运的最后一程。“捐献”是他们的生存价值,他们被“正常人”“复制”过来的目的是为了捐献主要的器官。此时,他们已经完成了身份的建构,坦然接受并认可了自己的角色。
看护员是克隆人在接受培训后的另一种身份,是未来的器官捐献者。“捐献者”在参加捐献前都要做一段时间的看护员。这似乎要他们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看护员的工作很辛苦,要不停地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从一个康复中心到另一个康复中心奔波,还要忍受孤独、寂寞,睡眠也不好。有人乐观对待,有人应付时日,有人自暴自弃,被动地等待被叫去捐献。看护员的工作就是照料那些参加过捐献的人,等捐献者身体康复再参加下一次捐献,直至死亡。看护员的时日结束后,他们就要被叫去作捐献,他们在捐献后再由别的看护员照看他们,直到他们也经过不同次数的捐献后“终结”。
如上文所述,在金斯菲尔德,克隆人已经彻底地认识到自己是“捐献者”的身份。他们对自己的职责——如果“捐献”也能称之为职责的话——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恺蒂认为:“命运与责任是石黑一雄作品中惯有的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永远是安静的牺牲品,对于‘责任’认命且默默承受,不知道‘抗争’是什么。”[5]露丝、汤米等克隆人视责任重于一切,他们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意识和观念。因此,露丝告诉汤米说:“当我成为一个捐献者时,我是相当有思想准备的。感觉该那样了。毕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是吗?”[2]207可以看出,这种淡定是悲哀的,是克隆人的“无奈的哀鸣”[6]。对他们而言,既然捐献器官不能逃避,那么只能去坦然面对和履行自己的责任。布彻(James Butcher)指出,凯茜等克隆人已经“被洗脑:相信捐献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他们谁也不想逃走以摆脱自己的命运”[7]。而单伟爵(Wai-chew Sim)则认为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念,“这种宿命论吸引了读者的注意,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8]。或许就是小说中的宿命论思想浓厚,使得小说蒙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
虽然克隆人视“捐献”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又表现出对生命的渴望,对真爱的留恋。于是,有人企图通过“真正相爱”以延缓捐献,渴望在三四年内能够共同生活与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如露丝最终意识到凯茜和汤米深深相爱,并建议他们去争取这种机会,只是凯茜认为为时已晚。不过,凯茜还是与汤米做爱、聊天、朗读,试图证明他们曾经真的相爱,并找到埃米莉小姐申请推迟“捐献”。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真爱挽救不了厄运,汤米还是要走上手术台去做最后一次“捐献”。这说明在那种环境下克隆人的任何努力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通过阅读小说,不难发现,克隆人结束生命的时间异常早,虽然算不上少年早夭,也可谓青年早逝。如小说的叙事者凯茜开始讲述故事时不过三十有余,而她却即将走上“捐献”“终结”之路。与这批克隆人不同的是,面对死亡的命运,《逃离克隆岛》中的克隆人选择了反抗——逃离克隆岛,揭破所谓的“天堂岛”的谎言。而在泰国作家维尼暖的《克隆人》中,启万和傲拉春等许多克隆人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恋爱、信教,但却被当作实验用动物一般对待,器官被一个个移植走然后死亡。《别让我走》的露丝第二次捐献后“终结”了,汤米第四次捐献后“终结”,凯茜也汤米死后不久接到了第一次捐献的通知。这就是他们的归宿。在李厥云看来,“这些克隆人的特殊身份总是被反复强化,目的是向他们灌输一种主导的观念,即不管是有目的的还是无意识地要把这些克隆人变成人类温顺的动物。”[9]没有逃离,没有抗争,默默地迎接自己的命运。这也是对高更之问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将往哪里去?”的回答。凯茜等克隆人的“捐献”“终结”多了几分悲剧的色彩。
四、结语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别让我走》向读者展现出一个虚构的社会场景。克隆人并非现代生物学意义的自然人,而是现代科技的结晶。凯茜等克隆人短暂的生命历程和难以逃避的命运归宿令人唏嘘不已。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身份:“捐献者”。这种身份始于模糊,终于清晰。模糊之际充满了对自我身份的焦虑,清晰之时则是对身份的认同:我为捐献而“生”,也将为捐献而“死”。因为克隆人的“出生”和“死亡”,乃至其整个生命历程和生活方式都不同于自然人,因此克隆人问题也就引发了人们的深度思考:如何认识克隆技术,如何看待克隆人。卡尔·谢道格斯(Karl Shaddox)认为,“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可以视为一部关于科技在人类和人权方面被滥用的警世小说。”[10]小说也进而迫使我们去思考人类自身:在人类已经取代上帝可以创造生命的时代,如何看待现代人身份的困惑,如何破解我们内在的身份焦虑,如何定义我们人类自身。
[1] 陶家俊.身份认同.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G].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465.
[2]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 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Abrams, Dominic & Hogg,Michael A. ed. Social Identity Theory:Constructive and Critical Advances[G]. 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0:2.
[4]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M].刘新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17.
[5] 恺蒂(郑海瑶). 平常人心非常人(代译序).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
[6] 朱叶,赵艳丽. 无奈的哀鸣——评石黑一雄新作《千万别弃我而去》[J].当代外国文学,2006(2):156-160.
[7] Butcher, James. A Wonderful Donation[J].Lancet,2005(365):1299.
[8] Sim, Wai-Chew. Kazuo Ishiguro[M]. Abingdon:Routledge,2010:81.
[9] 李厥云.多元文化下的漫步者:石黑一雄国际化写作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155.
[10] Shaddox, Karl. Generic Considerations in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013(35):448.
(责任编校:朱德东)
An Inquiry of the Clones’ Status Anxiety in Never Let Me Go
DU Ming-ye
(SchoolofForeignStudies,HuaibeiNormalUniversity,AnhuiHuaibei235000,China)
Never Let Me Go, a science fiction by Japanese-born British author Kazuo Ishiguro,tells a story about a group of clones’ life experience. As clones,their identity is very special, therefore a strong identical awareness is formed. They desire to find out their real identity, and long to find out their “possibles”, and finally they know they were brought out as “donors”.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clones’ identity, revealing clones’ mental course, their confusion of growth, and their destiny.
Never Let Me Go; clones; status anxiety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4.015
2017-01-21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AZD090)“‘世界文学史新构建’的中国阐释”;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2017A0368)“石黑一雄小说的伦理主题研究”
杜明业(1969—),男,安徽萧县人;文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I106.4
A
1672- 0598(2017)04- 0109-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