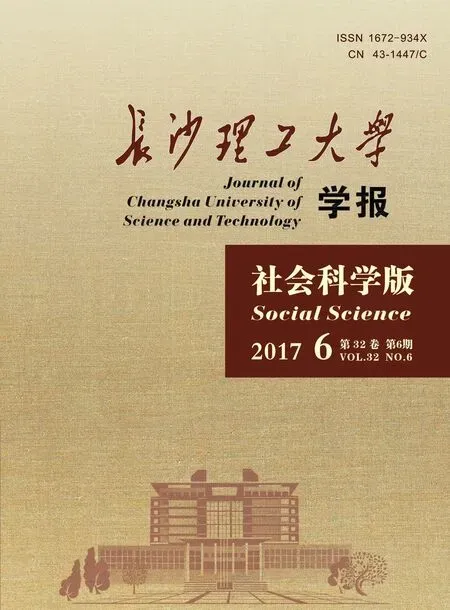论敖德嘉的三段论式技术哲学思想
孙广华,林 影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论敖德嘉的三段论式技术哲学思想
孙广华,林 影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敖德嘉在他的《关于技术的思考》中,提出了“人的存在”之谜的主题。他以一个三段论式的人与技术关系来阐述人的生存问题。他认为,在创始期,人在技术中展开自己属“人”的东西,将人创造成为了他自己的主体。第二阶段,人从潜在地“无所不是”,变得实际上“一无所是”,堕入自己构造的虚假主体性。第三阶段的拯救之途,敖德嘉提出展开西方技术与东方文明的对话,找出“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的生存方向。敖德嘉最后的思想虽然并未明确,但他的思路引发我们思考和了解东方文明中的生存智慧,以及人作为主体的根本所在。
属“人”性;虚假的主体性;“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
“人的存在”问题,是亘古不变之谜;殚精竭虑,对人乃至一切万物的存在方式和意义进行不倦的思考,是哲人固有的传统。技术哲学研究也在直面这个问题。20世纪西班牙哲学家敖德嘉·加塞特在《关于技术的思考》中直接说:“在对技术的讨论中,我们碰到了‘人的存在’之谜。”敖德嘉在其文中,以一个三段论式的人与技术关系来阐述人的生存问题。重读经典可以发现,其思想发轫于20世纪上半叶,但非常有趣,引人深思,对我们回应当代复杂的技术与人生存的关系问题仍具有重要启迪。
一、技术:“一切属‘人’的东西由此展开”
在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中,认识自我实际上始终是一个阿基米德点。敖德嘉经过一番分析后提出,技术,“一切属‘人’的东西由此展开”[1](P271)。敖德嘉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技术中属“人”的东西是什么?当人展开他的技术旅程,他是何种存在物?
敖德嘉说,人是从技术开始的地方开始的。人,本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是一种“在自然中受迫而生”的存在。首先,和其他存在者一样,他必须得活,繁衍延续,尽管可能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必须得活,但他并没有想死,他接受环境以及环境强加的条件,接受生存的必需,进食、取暖、行走。但人绝不止于此,他继而善用其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能力,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展开了属人的行动,“发明、开展第二类活动:生火、盖房、耕种田地、设计汽车。……创造一种程序,它在一定限度内,确保随心所欲地、方便地获取我们需要而自然中找不到的东西”[1](P266)。终于,他超越了受迫而生。敖德嘉认为,生存是指在自然中所必需的活动,而人超越这种动物性“必需”,将原本动物性的生存追求降到最低,他“是这样一种动物:他单单把‘客观上多余的东西’视作必需”,那“多余的东西”才是必需,人就是由此发现他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不同,他具有自己的超自然的必需。
那么,这“多余之需”是指什么呢?敖德嘉说,人不同于动物,人具有“活得好”“幸福”的渴求,希望得到“精神的愉悦”。怎样才是活得好、幸福呢?“‘去向’就是人的生存计划。我们管它的充分实现叫什么?显然是‘活得好’、‘幸福’。”[1](P276)人对自己是有 “欲求”和谋划的,人会对实现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具有清楚的意向,具有生存的去向、渴望和计划,唯如此,人才是自己“真正的存在”,“人不是‘物’,而是一种‘希望’,希望成为这、成为那”。敖德嘉将这叫作人的“人格”“自我”。舍此“多余的东西”,宁愿死去。为了满足这“需中之需”,人“反作用于环境,不听任‘世界之所是’”,此即“人的特性”。而技术,帮助人反作用于环境,就是人的“创造性生存”,人在技术创造中创造着自己。“人、技术、活好,内涵相同。”没有技术,人就不成其为人;有事可做,有广大的生活领域,他才觉得最有人味儿。其他动物没有这种创造意识和能力,因此它们只能维持生存的客观之需。技术使人时时刻刻创造他的人格和自我,在自然赋予他的逆境中成为他自己,“技术为他在自然中开出的闲适,是他的‘超自然存在’栖身的小屋”[1](P275)。技术“发明了人”,技术让人“有空”去“成为他自己”。
这样,敖德嘉强调了一个观点,技术是人成其为人的一个要素,人在技术中开始,继而不断生成和完成自己。这一分析,与芒福德的心理冗余论构成了对技术一体两面的观察。芒福德将技术看成人的心理能量冗余的结果。他提出,相比于动物,人类在早期技术上实际上并没有独特的优势,但“人是卓越的使用头脑、创造符号和自我控制的动物;人类所有活动主要发生在他的有机体内。人只有首先对自己做些什么,才能对周围的世界做点什么”[2]。他认为,借助于高度发达的、持续活动的大脑,人类获取了比单纯动物生存层次更多的心理能量,技术是人的内在心理资源的疏导。芒福德强调的是,人先于技术,技术是人的创造,是人的不断自我发明和自我实现,是人自我的逐步外在化。而敖德嘉着重观察到另一面,即人的待完成性,人由于技术创造而生成的人对人自己的创造和成就。
关于“人”,卡西尔曾说,“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满。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3](P87)。敖德嘉将人与技术二而合一的思想正与此契合。技术是人最早开始的一种劳作,无疑也是人的基本结构的一个部分,也是圆满人性的一个扇面。在人和技术的最初开始时,人与技术相互仰赖,进而人建立起“超世界”的存在,技术则贯穿着人性而展开,在彼此创造的过程中二者逐渐展开它们的价值,彰显意义和希望。人逐渐发展人之“所是”,在技术中展开他属“人”的东西,“人、技术,活好,内涵相同”,实际上,人将人创造成为了他自己的主体。
二、“最技术化”时代:构筑起虚假的主体性
敖德嘉的第二个问题试图阐明,人类和技术堕入自身造就的危险。说到“危险”,海德格尔的理论最为著名。“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救渡!”尽人皆知。海德格尔属于芬伯格所说的实体理论一派,这种理论的观点是,“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体系将整个社会世界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的对象,它最终侵入每一块前技术的飞地,塑造社会生活的整体”[4](P6)。海德格尔的“危险”是指,技术正在将包括人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转化为“持存物”,转化为技术过程中的原材料,也就是说,人和其他存在物被技术置于一种危险之中:贬黜为单纯的对象。
敖德嘉的危险是指什么呢?为了说明危险的来源,敖德嘉以人与技术的初始关系作为区分原则将技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偶然性技术阶段,人不把自己看作各种发明的发明者,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有一种能力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求塑造“超世界”。在手艺人-工匠技术阶段,工具是人的补充,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一种能力,有能力的人虽然是主要起作用者,但人也意识到他的欠缺和限度。而到了技(术)师技术的现代阶段,技术摆脱个人和传统,它可以“创造一种活动计划、一种方法或程序机器”并执行之,具有了高度独立于“自然人”的功能。然而,如果这种创造活动变得在原则上“没有限制”时,技术行为和技术成就“暴涨”,人“被过剩的技术对象、技术程序所包围,它们形成了高密度的人工环境(原生的自然藏于其后面)”,结果是,人陷入一种危机,“于是有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起初,技术的惊人扩展使它从人类自然活动的朴实无华的背景中脱颖而出,使人获得对它的充分意识;而现在,它的极大进步又有遮蔽它的危险”[1](P287)。人类只能寄居技术之中就像原始人只能处于自然环境中一样,人不再是那个自己的主体。
实际上,人堕入了虚假的主体性。当技术的进步遮蔽了它自身,高密度的人工环境遮蔽了真实的自然,人与自然之间插入一个技术创造物“专区”,人与自然分割,甚而彼此对抗和竞争。不仅如此,在手艺人那里,本来技术专家、工人以及技术是统一的,现在分了家,这使得技术成了一种似乎独立于人的东西。在方法上,技术的独立使得技术变成了与人分割开来的目标,针对目标的方法变成了与科学的“分析”方法相一致,就是把一个整体的统一体拆成各个部分,人与技术的统一体分割开来,技术成为一个科学化思维的产物。于是,技术也像最形式化的逻辑,给人以物品的形式而缺乏生活的内容。技术的进步、技术看似潜在的无限能力,也使其高高在上,使人产生了看似对它的绝对信仰。所以,今天的技术专家热情投身发明事业,视其为最标准、最确定的活动形式之一。这就像埃吕尔所说,当自主的力量赋予技术,技术便凌驾于所有传统的或竞争中的价值之上,甚至凌驾于人之上。
结果就是,这一切使得人的“精神”变成了“太渺茫的作用者”,产生了“迷失在它自身的无限可能性的迷宫”的危险,人“要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变得更加困难”。“做一个技师而且只做技师,这意味着潜在地‘无所不是’,而实际上‘一无所是’。”人自己 “变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最技术化的时代,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空虚的时代的原因”[1](P286)。结果就是,技术从使人最有人味儿变得最没人味儿,它的本来目标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在创始时期,人、技术、活好,内涵相同。现在,即便就像伊德所说,现代技术已经“进入到我与环境的身体的、活动的和知觉的关系中”[5](P56)。“具身是我们参与环境或‘世界’的方式”[5](P55)。但如果精神被技术化的身体架空,那又如何不算是貌合神离呢。如此这般,人这个“主体”便总是处于对物质欢愉的欲望、对财富的渴望的包围之中,其他的价值便会干涸。物质愈加侵淫,灵魂愈加软弱。人堕入“一无所是”,堕入虚假的主体性而不自知。
因此,真正的危险在于,西方文明和技术构筑了一种虚假的主体性,它原本试图将人类创造成为自然的主人,一种自由的主体。培根在《伟大的复兴》的前言和概要中主张说,人应当利用自己的技艺和双手,迫使自然“离开其自然状态,对它进行压榨和塑造”。笛卡尔在其《方法谈》中也提出要使人成为“自然的主宰者和拥有者”。包括敖德嘉也是如此,他认为人类生活首先是与自然“奋争”。但结果却变得相反。到今天,这个虚假的主体性的东西仍然主导着我们。人类至今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傲慢,仍然固守自己的“主体性”。从福柯意义上来看,这是一种侏儒哲学,只有侏儒才会要求把自己变成主体。正如海德格尔说,现代人无所归依,有失掉自己的危险。海德格尔的方案是人应诗意地栖居,经由“仰望天空”而“回归大地”,达至存在的“敞开”与“澄明”之境。这个方案招致了不少人的追捧,虽然让人有些晕乎。敖德嘉也具有一种深切的忧患情怀,也试图寻求拯救之途,他的途径是向内,走向人和技术灵魂深处。
三、人类生活:“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
敖德嘉的方案是,人类生活并不只是“与自然的奋争”,还是“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敖德嘉并未将“危险”的责任推给技术,而是把挽回的道路和方向指向人自身。在这一点上,敖德嘉与安德鲁·芬伯格不谋而合,芬伯格说,“许多社会批评家宣称,技术理性和人类的价值在争夺现代人的灵魂”[4](P1)。芬伯格认为这是陈词老调,并指出技术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政治家的价值观和行为,在于人的决策和行动。
敖德嘉三段论式技术思想在此逐渐显示了重要的价值意蕴。他考察了不同地区,例如欧美和亚洲的不同生存方案,展开了与东方文明“对话”。虽然他对亚洲“关于灵魂的技术”有一些误读,但这反而促使我们多加深思。敖德嘉对亚洲生存方案的考察以西藏为典型,并以体现东方文明和生活方式的亚洲佛教为代表。但显然,他的考察是有局限性的,很明显的一点是,他的文化和生活背景导致了他对佛教精神的错误理解,障碍了他的灵魂拯救之途。他说,“‘不再去活’或‘尽可能少地活’是菩萨的首要考虑。……活着却像没活,不断努力消除世界和生存本身……作菩萨意味着没有运动、没有性欲、不觉快乐亦不觉痛苦——一句话,是活着的‘对自然的否定’。……佛教中没有肩负人类之拯救的神。”[1](P277)认为“水土导致了佛教徒式的生存”。他对佛教的理解既有逻辑上的错误,又与事实完全不符,而这种错误导致了他不能理解亚洲文明和东方技术的灵魂。其实,如果他真想从佛教来理解亚洲生活智慧、找寻亚洲技术的灵魂,如果路走对了,那恰巧能够寻到一些极为有益的启示。
事实是,作为一种“生存方案”中的佛教,不仅没有教人“不再去活”,反而主张人们要活得幸福。这与敖德嘉发现的技术的最初价值完全一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菩萨救苦救难人尽皆知,虽然人们常常并不知道她究竟怎么救。佛教的生存方案与 “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正相符合。敖德嘉认为,我们无法选择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我所是的“希望”在“我的环境”中或遇到阻碍,或得到推进;“我”既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心灵”,而是一出“戏”,一种无休止、为了“成为我之要是”的奋争。这样,超越“我的环境”不是一个纯粹外部环境的问题,而是“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佛教的生存方案恰好提供了与自我奋争的方法,主张向内审视,观察“我”的心态和意向,超越“我所是”及其“希望”,这可以在根本上引导人们修正自己的内心价值以及行为而拯救自身、达至外境,这才真能走向海德格尔说的“敞开”“澄明”与真正的自由。
那么,当西方技术追求的物质主义方案“达到的荒唐境地”,“让我们在自然处境中不停地忙活”,“生命规划变得暗谈模糊,技术不知服务于谁、服务于什么目的”时,亚洲文明的生存方案便可以多有借鉴。佛教倡导人的中道生活,不堕极端,舍二边的极端以取中道,不刻意去过贫穷的生活也不穷奢极欲;中国的儒家也主张恪守中道,无过无不及,将中庸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中道是东方文明的最高的生活智慧。遗憾的是,敖德嘉没有能够理解到这一思想。但有益的是,敖德嘉预见到“创造性生存”的意旨已经变成不断挖掘人的过多而虚假的欲望,认识到现代社会中唯一达成共识的价值就是效率。事实是,人用现代技术创造了自己的贪婪而不自知,使得自己的灵魂处于追逐欲望的不安宁之中,而不自知。如果说人曾经成就了自己这个主体,那他现在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
实际上,当人类的生活目标成为“与自然的奋争”时,就已经走向歧途,人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对立面,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主体。现代技术应可以从东方文明获得启示,东方文明,例如中国文化、印度哲学、亚洲佛教的生存方案中历来主张万物和谐,从不把自然看作自己的对立面。万物总是彼此相连,就如同花朵弥散芳香分享喜乐,而腥膻之物污浊空气。所幸西方文明演变到当代,也已经发展出非人类中心主义。后人道主义理论也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后人道主义者认为,不要把技术看成是人和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技术是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共同显现的’。人类、自然和技术只有在理论上能区分开,因为三者首先是通过各种实践区分开的,而在这些实践中,三者都参与了,而不仅仅是只有它们中的人类参与了。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是一种由人类、自然和技术这三个方面互相定义的复合体”[4](P33)。这个观点与东方文明的万物和谐思想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
“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就是要寻回“人”自己。人被隐匿在高密度的技术背后,但隐匿身份就有机会直面自己。“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3](P8)“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就是不应当将贪婪视为自己的责任,要提升掌控欲望的能力。如果世界上的人都能避免浪费,并摆脱囤积财物的欲望,那么这世上大多数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与自己灵魂的奋争”,就是不能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机械,就像一台台设定了既定程序的机器,而是要对与人毗连的世界万物生起同理性和同情性。世界万物,应“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灵魂的本性是智慧和爱。人类本来懂得爱的咒语,但是忘记了去用。“爱他人”在孟德斯鸠那里时就是人类社会的固有法之一。真正的技术进步应当试图限制单一的效率价值,当化曲为直,以便使同情、爱、审美等其他的人类价值也繁荣昌盛。人当寻回自己,人乃因有智慧和至善的灵魂才成为圆满的人,“人的存在”的真义,就在于创造万物的和谐、自由和幸福。这也是“创造性生存”技术的本义。
[1][西班牙]敖德嘉·加塞特.关于技术的思考[A]//吴国盛,主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71.
[2][美]芒福德.技术与人的本性[A]//吴国盛,主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500.
[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4][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5][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6.
[6][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86.
On Ortegay's Philosophical Idea of Three-stage Technology
SUN Guang-hua,LIN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42,China)
In the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JeséOrtegay Gasset put forward the theme of mystery toquot;human existencequot;.He expounded the human existence with a three-st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He believed that in the founding period human unfolds his own things for being human beings in the technology,and makes himself his own main subjectivity.In the second stage,from the potential ofquot;being everythingquot;,human becomesquot;being nothingquot;in reality,thus falling into the false subjectivity constructed by his own.Finally Ortegay tried to develop a dialogue between western technology and oriental civilization,to find the survival direction of struggle between man and his soul.Although the last thought of Ortegay is not fully stated,his thought could still lead us to think and understand the wisdom of survival in the ea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root of man as a subject.
being a human being;false subjectivity;quot;struggle between man and his soulquot;
N03
A
1672-934X(2017)06-0040-05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6.007
2017-10-20
孙广华(1964-),女,辽宁丹东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林 影(1975-),女,广东汕头人,讲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管理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