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四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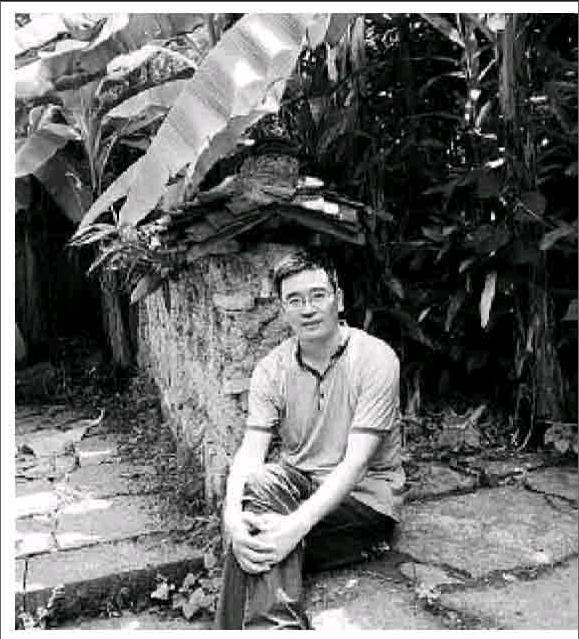
文河,安徽太和县人,主要写作散文随笔,偶尔写诗。出版有随笔集《漠漠小山眉黛浅》。另著有书稿《浮尘》《抚今与追昔》《城西之书》等。
札 记
男女之间——女人了解一个男人之后,往往会爱上他;男人了解一个女人之后,往往就不爱了。有时,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两个句子。似乎有道理,似乎又没道理。这句话也是突然冒出来的。放在《聊斋》里,似乎有道理;放在《红楼梦》里,似乎又没道理。
同是写情,《红楼梦》走向意境。天上(太虚幻境)人间(荣宁二府),最后白雪茫茫。《聊斋》走向幻境。草木虫鱼,花妖鬼狐,泛然无涯际。
《西厢记》写情,“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写的是相思。相思在《红楼梦》里达到了极致。《牡丹亭》写情,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对应于《聊斋》,生死之事大矣,但比起一个“情”字,还是小了。这就是理学后的中国。
日本的《源氏物语》,写情。其实是艳情。日本文学写情,男欢女爱之中,总有一种清冷之意。中国的是,“来日大难,皆当喜欢”,有世俗的热闹和温度。
《金瓶梅》写的是欲。也是世情。
唐传奇,奇情。奇情壮采。唐诗中,李白的诗句里出现了“我”字,“我本楚狂人”,“我欲因之梦吴越”。《游仙窟》里,也有了个“余”。第一人称的叙事,在中国古小说中,灵光一现。很有意思。可惜没有被后人很好地继承发展下去。文以载道,诗赋为上。古小说,不登大雅之堂也。第一人称的叙述,太有嫌疑。
好的东西,好到极致,就变得危险了。女人美到极处,是为不祥的尤物,倾国倾城。好的作品,好到极致,有毒。这也是物极必反的意思。
我看一朵花,一朵花看我。“我”消失的时候,世界是一个明亮的安静。一切早已发生,一切又似乎从未曾发生,就像春风泛泛吹过。但是,天地已经有所不同了。
中国传统小说不讲结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也不是结构。这两句话真好。以前倒没觉得。记得顾城有个奇妙的诗句,“花很多,有两朵”。中国文学受佛教影响很大,《华严经》有一个内在的精巧的结构。或者说《华严经》体现了一个心理上的结构性。但佛教典籍对中国文学叙述性的影响却很微弱。中国建筑讲究布局对称,内部结构并不复杂。鲁大夫臧文仲为他占卜的大乌龟盖了个房子,很豪华,“山节藻棁”,在《论语》中引起了孔子的批评。但“山节藻棁”,只是装饰性的。中国古人追求自然。叙述上自然也就“顺其自然”。
晚上沿河堤散步,空气里有浓郁的植物的气息。上午下了雨,草地和树丛还有很大的潮气。还有两天就立秋了,这种气息里似乎有某种盛极而衰的停顿。也许是我太敏感了,产生了一种过度的心理反应。这种气息仿佛在屠格涅夫的笔下感受过。在布宁的笔下也有。俄罗斯作家最善于描写大自然。除此之外,应数英国作家,尤其是哈代。
群星灿烂,有小飞机一闪一闪,从星群间缓缓穿行。飞机在夜空中看着好,小巧玲珑。夜色中,蝉声一缕,也好听。一种最简洁的微带金属质地的声音。
“顺着一条河流的曲线……”在河堤上行走,脑子里又突然冒出一个句子。但顺着一条河流的曲线,会走到哪儿去呢?有时候,哪儿也不想去了。有时候,又想到处走走。
中国小说中的自然描写,却往往是八股式的,程式化的。《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里有自然风光。中国文人大都跑到诗文里游山玩水去了。
写一写小说。小说,小小的说说、随便说说的意思。本文标题本来想叫“小说”,但怕显得大了,还是叫“札记”吧。
鸳 鸯
有人送一只板鸭,说是鸳鸯。脱毛的凤凰不如鸡,脱毛的鸳鸯和肉鸭没有什么区别。真是一种可悲的现实。我尝了尝,肉质远比板鸭细腻,也更香。但吃了两块,吃不下去,心里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就给我妈送去了。我小时候,我妈老是吃我吃剩的东西来着。
我这种别扭的感觉,是由于从小读过的诗词在肚子里作怪。鸳鸯在古典诗词里,一直是爱和美的化身。让我吃鸳鸯,简直是饕餮爱情,有负罪感。几年前,在一个水塘里,看一群花色艳美的禽鸟在嬉戏,像鸭子,又不是鸭子,问人,才知原来是鸳鸯。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这种久仰大名的禽类。
鸳鸯让我想到温庭筠的词,尤其是那组《菩萨蛮》,富丽泛彩。温庭筠名好,字也好,飞卿,但据说长得却极上不了台盘,被人称为“温钟馗”。少年时代,读他的词读多了,铁定认为此人必然英俊儒雅。后来看了古人笔记中的相关记载,好一段时间转不过弯儿来。废名认为以前的诗是一个镜面,温庭筠的词则是玻璃缸的水,在里面养个金鱼儿,插点花儿什么的都可以。也就是说,词到了温庭筠这儿,变得立体了,有了很大的空间感。其实还有一点废名没有看到,在温庭筠的词里,就是在他的《菩萨蛮》这儿,有了一个精美的内在的结构,用《论语》中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山节藻棁”。一间大肆装潢的屋子,斗拱、短柱什么的结构精美。由此而产生出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用他自己的句子来说,就是“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这种结构有时让我想到博尔赫斯的小说。这种结构不是封闭的,温庭筠写女性的闺阁、居所、庭院,但是他却把这一处所置于一个广大的风景里。鸳鸯锦,鸳鸯枕,鸳鸯突然就从某种静态的私密性的场所飞了出去,飞到了另一个无遮的空間,风景无限。
飞就飞了。现在不写温庭筠了,写一写杜牧。写来写去,反正都是写鸳鸯。
“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乍想到杜牧的这两句诗,我一时错当成了韩偓的。这才是真正的鸳鸯浴。现在的鸳鸯浴,不敢见天,只能孤芳自赏,其实应该叫荤澡。我们知道,杜牧年轻时,也是个爱玩的主儿。这两句诗前面还有两句,“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这首《齐安郡后池绝句》,写于杜牧不得意的时候。在寂寥富丽的夏日,诗里隐隐透出一丝性意识。王维雅人而偶作艳语,艳起来真是不得了。“映竹解罗襦”,可让明人的春宫图黯然失色。智极成圣,情极成佛。艳极可以通禅。
温庭筠的词,也大都蕴含着淡淡的性意识。但它们看起来很艳,其实是秀,秀色可餐的秀。好的东西,有时会给人带来某种饱满的感觉,强烈得接近一种生理意识。没有比吃更现实的了。
枯 桑
如果以树来喻,春天是柳,垂丝欲芽,临水自照,妙曼不可方物。树有姿,有色。唯柳既有姿,又有色,姿色双全。树中最冶艳的尤物。不过芳华刹那,数日姿色便忽忽丧失殆尽。
冬天是桑,老桑,天寒叶落,桑皮开裂,老枝纵横盘空,如将军万里杀敌归来,未解甲胄。
我想到的桑,是枯桑,比老桑更进一步。写到这里,突然有个感觉,是有关风骨和气韵的东西。老桑属于秦汉。柳属于宋明。秦汉,有风,有骨,有气,好像没有韵。南朝似乎才开始有韵,南朝水汽氤氲。到了近代,李叔同还有诗句,“红楼暮雨梦南朝”。
我考虑问题,不会考证和推理,向来只凭感觉。有个说法,感觉有时是靠不住的。既然“有时”靠不住,不过话又说回来,“有时”感觉也是能靠得住的。说不定,感觉甚至比感情还更靠得住些。
我想到枯桑,可能与古乐府有关。“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有空旷的空间感,质朴,大气,凛然无情。诗歌里的“无情”,往往是个掩饰。是情到深处转无情。诗歌的表面现象才真是靠不住的。想到枯桑,又想到马,还是与古乐府有关。“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古乐府中的很多诗,不会拐弯,直来直去,是硬的。不是生硬的硬,是一种质地,像长城上的方砖。很奇怪,长城拐了很多弯,但长城还是硬的,我的意思是说,长城有一种直来直去的历史感。但一条河,即便是直的,还是柔软的,给人一种纵深的感觉,纵深到遥远之处,就开始九曲回肠地转弯。
枯,没有生命的生命。有绝对意味。绝对的东西,更有力量,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比如,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枯桑就像枯墨,枯中有另外的一种新生。
本来是写枯桑,怎么突然又想到了霜天晓角。治大国如烹小鲜,写文章如骑骏马。信马由缰,这种感觉最舒服,就像青春期梦中跑马。不过快速跑起来,还是要拉一拉缰绳的,不然会人仰马翻,不知所云。行行重行行,到哪儿去呢?“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我现在太喜欢这两句诗了,喜欢得立即就想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霜天晓角。天色欲明未明,钢青色,清霜如剑,森森逼人。角声深沉,破空而来。此时的人如此庄严豪壮,不可以有丝毫荒废。
偶尔(比如,这两天)也会怀念一下裘马轻狂的少年时光。醉里挑灯看剑,牛×得不知东西南北。理想呀,事业呀,爱情呀,好像生活无穷无尽似的,有着无数种触手可及的可能性。那种状态,腾云驾雾,脚不连地。——其实,倒也蛮好的。
那么,马呢,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得找一株枯桑拴住它。人生不能太切题,但也不能太离题。
从文札记
抒情性,也是诗性。抒情性的作家,善于描写女性,三三,萧萧,翠翠,夭夭……
曾经,我也幻想过要和一个单纯朴实的女孩子在一起生活,和一种美好自然的人性相守。一座小山坡,一条清澈的溪流,一片青森森的竹林,一些开满花朵的果树。嗯,树荫也可以很多,一大片一大片,静静的,或轻轻晃动。当你刚走远一点,就有一个牵挂的声音喊你。人间小小的一隅,洒满温暖的阳光,让人一生都走不出去。
单纯其实是诗化的、理想化的。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世界已经很乱了,但总是显出很新的样子。
在时代的潮流中,沈从文的痛苦深度,并不亚于鲁迅,只是个性和气质不同,其表现风格也就各异。鲁迅的痛苦是石头,硬,冷峻,嶙峋,鲁迅是“江流石不转”;沈从文的痛苦是月亮,明亮,温和,清寂,沈从文是“孤月浪中翻”。
沈也许是近、当代作家中最具生命意识的人。
我似乎从他的作品中嗅到几丝屈原《九歌》里的幽远气息。“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种说不出的来自生命深处的美好和怅惘。如果追根溯源,沈从文的文化传统可以接续《楚辞》一脉。极具想象力的楚文化有一种自然性和社会性交织的幽深激切。
一个人走路、过桥、看云,这都很好。遇到一个美好的人,像一枝新开的花,珠露莹莹,娟然迎风,这当然好。只是,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很多事情,到后来,就变了。不易觉察地变了。
其实不是事情变了,是人变了。人都会变的。也很可能,从一开始,你所爱上的,只是一个你自己虚构的形象,而非事实存在本身。
我也曾遇到过一个美好的人,一个春天的夜晚,雨水嘀嗒、嘀嗒………后来就很寂寞。人在生活中,得经常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抒情的人,有一个自己的桃花源。
桃花源是静态的。但并不是静止的静,不是一种停止。是花朵和青草的静,是静水流深的静。静静地出现,成长,变化,死亡。血慢慢流出来,很美,比如《菜园》《静》。有失落、痛苦、悲剧,一切人间的喜怒哀乐,但笼罩在一个淳美而静谧的氛围里,像一个含泪的无言的微笑。
他的作品语言有些杂芜,不顺溜,甚至憨拙,像带有疤痕的乔木枝条,但从整体上来看呢,却显得浑朴典雅,富有深刻的生命意蕴,像“幽树晚多花”。
没有情韵,废名的《桥》一无所有;没有情致,沈从文的《边城》一片枯索。
生活很美好,人很美好,但又总有一些无奈,怅惘,完整中又总有一些无法修复的破碎,幸福中又似乎总有一丝难言的酸楚,快乐中又似乎总有一丝捉摸不定的感伤,命运又总是不经意间便被一些无法主宰的外界力量所改变,又总有一种不确实的希望存在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
生活是一头辛劳的驴子,面前总挂着一把似近而实遠的青菜叶儿。
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文章,批评沈从文是一个“桃红色作家”、一个“奴才主义者”、一个“地主阶级的弄臣”。这种火药味十足、带有强烈攻击性的言辞让沈从文大受震惊。
同经安史之乱,王维和李白写意性的诗歌语言体系已无法充分反映和容纳那段动荡的现实。这段历史只能凭借杜甫诗歌语言追魂夺魄的高度写实性来表现。
“文革”结束后,沈有一张在书房的照片,应该是在和别人交谈时被抓拍的。头向后微倾着,双手合十,面容朗阔,开心地笑着,笑容干净,纯真,恬然,慈祥。从表面上看,根本看不出这个人曾经精神崩溃过,自杀过,漫长地沉寂过。雨过地皮儿湿,那么多难以想象的苦难,都封藏在内心深处的哪个角落了呢?
1980年夏天,七十八岁的沈从文游香山,看到林木葱郁,众鸟飞翔,突然兴致大发,就学起鸟叫来。历尽劫难,童心犹在,他仍然是一个赤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