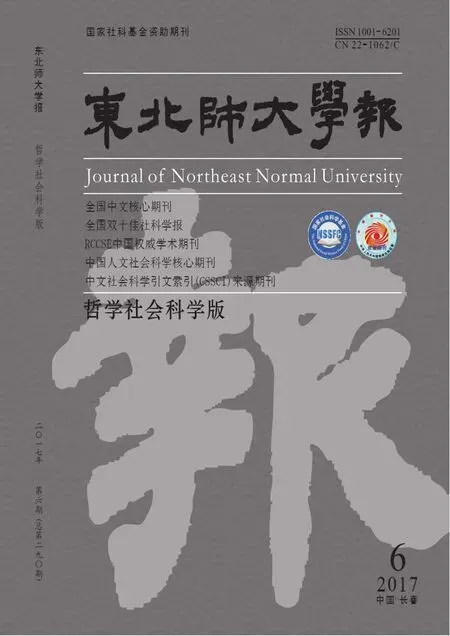法治视域下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改进
——基于英国财税法治早期经验的思考
陈 兵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
法治视域下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改进
——基于英国财税法治早期经验的思考
陈 兵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
新时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解决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财税法治与税收法定成为破解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出发点与着力点。透过对英国财税法治经验的考察,发现其地方财税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在“税收法定原则”与“无代表不征税”的基础上,实现了公共财政的集中征收与合理支出,突显出英国代议制下中央集权主义与地方自治主义的博弈,体现为事权与税权的法定、央地财税关系的厘清、社会监督主体的参与以及央地财税权分享与共治的阶段性演化等特征。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强调财税法治化建设,以税收法定为基准,以财政民主为抓手,改进和完善法治化语境下的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成为了当前深化经济改革的发力点与突破点。基于此,清醒看待域外经验,服务我国现实,从分享与共治的维度来提升中央与地方财税法治化建设的水平。在此过程中还应特别注意政治经验对央地财税法治建设的影响和作用。
央地关系;财税法治;税收法定;分享与共治;政治经验
一、问题提出
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机制一直是我国财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中居核心位置。目前,我国各项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改革面临着从原有的摊大饼式的“帕累托改进”迈向改革分饼机制的“卡尔多改进”。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这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可以用改革的总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1]61。此背景下,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调整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破冰之处。这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再分配,也涉及中央与地方治理事项的再调整,更关乎经济社会治理的民主法治化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各项事业改革,尤其是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牛鼻子”*在此背景下,知名经济学家高连奎提出了“新财税主义”,核心是不同方面的税收要“升降”分明,对税收进行重构。他建议进行全面财税调整,主要是“五增五减”,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最后是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纳税群体,支撑地方财政。参见高连奎:《财税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牛鼻子”》,中国网,2016年8月10日发布,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gnjj/20160810/385291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7日。。
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法治化离不开对财政权配置的法治化。然而,长期以来受全能型政府[2]30-31意识的影响,尤其是中央集权管理模式导致我国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配置和行使上缺乏协调性,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上的使用效率。故此,此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即在于调整征税权和用税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配置[3]60-73。在税收法定原则下中央与地方税权分置的法治化是中央与地方事权配置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事权与税权相匹配是中央与地方治理关系法治化的基本原则。目前,通过征税权回归“人大主导”,刚性的财税预算,用税权的合理转移支付和“议会型”税权审计监督模式的建立,实现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法治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在法律模式的构造和实践上趋向于大陆法系模式,但是,作为后发展国家在进行制度建设和治理模式选择的过程中,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亦有可能借鉴一切有利于本国现实发展需要的人类制度及其实践的有益经验。税收问题是任何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抑或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共通性与相似性。
考察域外财税法治经验,英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现代财税法治发生、发展的先锋,无论是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4]23-25,还是1640至1688年间的资产阶级革命,其背后无不闪烁着“为财税而斗争”的光影,“无代表不征税”的思想深深镌刻在英国各阶层民众的心底,并指导着其国民的认知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讲,其国家法治的发展也可以解释为财税法治的发展。财税法治作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的平衡机制,在英国国家历史上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并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财税法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英国央地财税关系的早期经验考察
自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逐步确立了议会主权下的君主立宪制,在政治上肯定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权力(利)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结构和基本法治框架得以确立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制度力量,极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一大批工业城市随之兴起。为了改造旧有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开征了各类专项税,以满足地方建设发展的需要。在这一进程中地方税权与事权的相适性逐步确立,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法治化得以发展。
譬如,1700年,布里斯托尔市通过法令,允许开征铺路税以铺设和维修大街小巷的路面。1735年,伦敦当局开启汽灯风气的先河,并征收一种特别的照明捐。其他城市纷纷以伦敦为参照予以仿效,布里斯托尔、诺里奇、巴思、坎特伯雷、骚斯伯里先后开征路灯税。到19世纪初,各地方当局又根据自身需要相继制定了大约400个市镇改善法案以适应人口快速聚集、公共设施落后所带来的新情况。该类法案要求:城市要建设公共厕所、公共浴室、洗衣房、公园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市镇当局要对穷人的房屋定期进行清洁消毒并检查审批出租的公寓等等[5]96-97。这一趋势持续至19世纪后期,地方政府在应对工业化给城市建设带来的诸多挑战时,在治理方式的选择上主要依靠税收,像地方税、过桥费、市场税等,由此也逐渐确立了地方事权与税权相匹配的治理方式。
地方当局除因时因地开征专项税外,鼓励社会公众对于地方事务的出资,也使得英国央地事权在早期发展中得以逐步理顺。经考察,发现英国地方政府是地方公共财产主要的管理者与分配者。也正是基于这点,在中央集权主义与地方自治主义博弈的过程中,公共财产经由征税手段收集后在央地事权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权与分权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表现为经由财税调控手段从过度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权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6]19-20。1835年的市议会组织法案(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 1835)是有关英国地方政府结构的第一次立法。该法案的初衷是改善地方政府体制的混乱与发展不均衡,以满足不断加深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需求,并最终确立了代议制基础上的英国现代地方自治原则[7]57。依照市议会组织法案的规定,较大的市镇成立了178个选举产生的多功能市议会统管地方事务。市议会属于综合性地方政府,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并随时接受市镇居民的监督。尤为重要的是,市议会可以决定税率并征收地方税,而其自身的行政开支基本上完全来自于这种地方税,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和监督。可以说在稳固的财政基础上,地方政府从中央政权的不当干涉与控制之中得以解脱出来[7]58-60。并解决了央地问题中两个关键的部分:一是它们的职责划分;二是它们的权力界限。首先,一切纯属地方的事务,即一切仅涉及一个地区的事务应归地方当局负责,如铺路、照明、排水以及街道清洁等。其次,既属于地方又可属国家的事务,它们是公共行政某些部门属于地方的那部分,例如监狱、地方警察、地方司法等应置于中央监督之下。此外,对于第三种类型的地方事务,即中央集权主义与地方自治主义都难以界定的事情,地方政府应当被授予自由决定权,有条件地受中央政府监督或者控制。
然而,过度地方自治所引发的弊端也日益突显,中央政府为此不得不加强集权,而税权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着眼点,因为地方自治的基础便是财政自主。1601年旧济贫法的颁布使得英国地方当局可经由征收地方税的方式来全权负责地方事务。该法令所创设的“地方事务由地方税收负担”的财政原则在历经三个世纪的演变后逐步延伸至更多的公共财政领域,如治安税、道路税、桥梁税、监狱税、教会税等等[8]140。至少在1888年之前,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中央政府仅以特别拨款形式支付分派于地方政府所从事的个别事务[9]57-58。然而,英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中央财政拨款以维系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战后重建工作。中央财政通过不断提高拨款额度使得地方政府的自治权日益削弱,并逐渐转变为中央政府的地方代理人。
审视英国的央地税权配置关系,其对于公共财产的征收和分配不仅有效适应了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公共服务快速扩张,更侧重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平衡,即在代议制原则下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可具体概括为如下一些特点:
(一)事权与税权的法定原则
英国“议会主权至上”的法治思想与制度安排始终贯穿于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无论是新建或修缮公共设施、拓宽公共服务,还是增设被委托授权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无不需要议会事先讨论通过各类专项法案予以确认,比如1902年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Act of l902)、1835年的市议会组织法案等等。而此类法案又大多秉承“出资即受益”的原则,即规定了专项事务的专项税权,例如,在拓宽城市街道、安装路灯、扩建市政建筑等无不征收特别的税收以支付改造费用,当建设费用过大时甚至可依法转向信贷领域。
(二)央地关系的财税面向
基于对地方所收集的公共财产的使用,中央与地方政府就各自职权负责,交叉部分则由法令规定其责任归属,从而基本上实现了事权与财权的科学分立与有效统一。毕竟,在由工业化引发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措施多为地方事务范畴,而在具体问题上最有能力的当局应该负责处理具体问题[10]219。然而,随着工业化逐步完成,地方政府的过度自治现象对于中央集权的消极影响愈发突显。在理顺央地关系的过程中,英国当局清晰地把握住了地方自治的经济根源,即地方税收基础,通过中央财政拨款等财税手段逐渐理顺了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间的不匹配,从而在二战后有效地实现了中央权力集中。
(三)税金分配主体的多元
从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来看,除地方当局外,还有诸多私人性质的各类专门委员会,经由法令或者议会授权,从公众到政府,均可通过一定途径为城镇建设做出贡献[11]209。这无疑使得地方自治的水平不局限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地方政府进一步将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公共管理职权下放,有助于降低地方事权履行过程中的财力隐形损耗,将纳税人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公共财产真正落实到关键用处。
(四)央地财税分享与共治的博弈
从英国央地财税法治实践的历史演进来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与事权的博弈一直存在,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价值排序,并由此形成了央地财税关系的基本样态,即以分享与共治为基调,以地方税权的必要性与中央税权的补充性在地方事权行使上的协调为表征,以税收法定为准绳和进路,推动了英国央地财税法治的建设。
三、中央与地方财税分享与共治的法治进路
当前在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构建央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其重点在于建立起分享与共治理念下的公共财产理论之于财税法治中的基础地位,使公共财产的取得、用益、处分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严格遵循法定主义,使之过程透明公开,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纳税人的整体利益[12]129。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合理配置与行使构成了其核心问题。没有合理的财权与事权配置,公共财产权的确立犹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缺少运行的现实基础,但同时,公共财产权的确立与行使也为财权与事权的正当性提供了法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具体到实践领域,立足我国现实,参照英国央地财税法治化的经验,认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法治化的改进的基调在于分享与共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分税的治理模式下,如果不能保证地方政府对于征税权的相对独立性,基于税收总量的恒定,国家税过重的结果将难以保障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各界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并由此不断扩张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所需的财政收入。作为央地财税关系的另一面向,央地事权的合理配置对于税种的立法规定、征收管理、税收支出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和解释作用。实际上,自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地方主体税源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地方财力缺口如何填补一直是各方讨论的焦点。然而,由于税制改革未完全到位,地方税体系建设尚未完成,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有一个过程,此时对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与财力的依法调整就显得非常必要,也需要格外审慎。
首先,我国应在法律层面明确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通过法律机制保障和促进各级政府履行事权。在明晰政府职能边界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手段、遵循谦抑原则厘定事权范围。事权划分法治化应当制定财政基本法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13]102。在保持中央与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范畴,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
其次,明确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体系,将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合理联结,适当提升中央的事权支出责任。将国防、外交、国内安全、全国统一市场规制等涉及国家主权行使的事项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通过统一管理,提高全国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将区域性公共服务明确为地方事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转移支付问题,现有转移支付体制应当予以优化,重点在于简化转移支付规则,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中央政府应当高度自律,对于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事项应提前编制预算并设置专门管理事项,依据法律规定公开的部分应当对社会公开,接受民众监督。同时尽量以税收优惠政策替代转移支付,力争在既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给付问题,减少可能发生利益寻租的环节,保证央地两级财政体系的统一与透明。
再次,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调整财税法制度设计的同时,针对我国央地事权关系的客观实际,简政放权下的市场机制引入与社会公众参与问题尤为关键。然而,其具体方案还有待进一步摸索,要做好失败所可能带来风险的预案。英国在央地关系的历史调整过程中,其所信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以及私有财产神圣等显著特点,导致了公权力在征税过程中在观念和制度约束上相对审慎,这种生长于西方法文化而长期形成的财税法治思维和方式对英国央地关系的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这一点自中华民族进入帝制时代以来[14]2,在历史上却未曾以正面样态出现过,长期的大一统思维和治国方式,家国一体的权威统治模式,导致在传统法文化上不存在对抗公权力行使的基因,以服从和义务为基调的礼治文化,更注重和谐与一统,对于分治与共享,对立与平衡的认知也只从清末启蒙开始。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简单移植他国经验在我国存在一定政治、法律以及文化风险。法律作为一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与习惯的组成部分,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们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15]6换句话说,也就是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很难被移植,尤其是那种简单地、机械地脱离本土实际的非有机的借鉴,更是不可能奏效。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多维度展开,从经济物质维度扩展至思想文化乃至政治法律领域,各国和地区的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得到了积极的碰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财税法治文化的精髓及其实践方式存在可资借鉴的可能与空间。
当然,客观上必须承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以行政权为主导的财税运行机制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事实上,随着民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必须提升,其所需要的财政基础将日益扩大,此时将财税机制的稳健运行置于首位,其直接关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正确与经济健康。因此,在当前央地财税关系法治化改进的过程中,必须立足现实,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党的领导和法治高度统一的财税法治实践方案,重视公权与私权以及央地关系的平衡与平稳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应鼓励公民在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轨道上做更多的事情,激发公民在参与地方事务上的权利主体意识,与此同时也明确规范公民在参与地方事务上的义务与责任,实现权责统一,确保公民在地方事务上“天然在场者”角色的合法合理运行。
四、余论:政治经验之于央地财税法治的意义
经由对英国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历史经验考察,发现其央地税收实践的法治化尝试,有效应对了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化问题,在“税收法定主义”与“无代表不征税”的财税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公共财政的集中征收与合理支出。而对于财税权力的论战与争夺也构成了该时期英国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间关系的主要特征,突显出英国代议制下中央集权主义与地方自治主义的博弈,可具体概括为事权与税权的法定、央地财税关系的厘清、社会监督主体的引入,以实现税收法定主义下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交织进程中分享与共治模式的制度实践。
固然,英国历史上财税法治实践的经验,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国情民俗,不可能直接用来解读当下我国在央地财税法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更不可能照搬照抄用来消解当下我国央地财税体制法治化改进上的困难。然而,从宏大的历史与社会维度观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间事权与财权配置的矛盾、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就财政权与用税权分置体制需求以及代议制与税收法定相结合的法律架构与设施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英国在央地财税关系探索中的技艺部分可以作为破解我国当下央地财税法治困局的积极借鉴。同时,也应清晰地认识到英国历史上重大财税事件和实践的展开都离不开同时期重要政治事件的发生,譬如,1215年的《大宪章》,1688年的光荣革命,1775年的北美独立战争[16]924-930以及步入二十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如前文所述都对当时的财税制度及其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财政与税收作为财税制度调整的两大主体,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已在前文中有了叙明,再次予以强调无非是想表达在对英国财税法治经验予以学习和借鉴时,不能脱离对当时政治环境和实践的理解,财税法治的建设应构筑于传统的政治经验以及同时期政治环境之上。
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文明大国,政治与法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实践经验,从伦理法、政党法、政策法到法治法的过程,也是国家政治与法的关系、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不断演化与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治经验”的形成一直处于政治经验的涵摄之下,很难想象在中国语境下离开政治经验去讨论西方任何法治经验的借鉴与引入,很难理解在中国语境下离开政治经验去讨论法治经验独立发展的困难与风险,为此,需要在深度描绘中国政治经验的基础上,讨论法治经验的历史与现实,阐释我国法治经验的特征,把握法治发展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实践和积累财税法治实施所需的经验,更好推动财税法治的实施。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步入“深水区”,传统的政治经验和改革模式面临挑战,经济新常态之于政治新常态的影响,使得财税体制改革的法治化改进之于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乃至政治民主的意义越发重要,成为了撬动新时期国家、政府、社会法治化建设有力杠杆。在此背景下,考察域外财税法治建设中的有益经验,立足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失衡失调的现实,强调以税收法定为财税法治的基准、以分享共治为税收分配的维度、以“税收契约”与“理财治国”为理论依据,从“强化预算管理”、“规范税法体系”、“厘清央地事权”三个具体层面出发,探索新时期新常态下中央与地方财税法治化建设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案,这既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践行落实,亦是改进当前央地事权财权失衡失调的必由之路,更是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经验的回应与创新。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政治经验与法治经验的融合下保障和推动央地财税法治的改进。
[1] 杨茂林.从帕累托改进到卡尔多改进谈起[J].前沿,2014(1).
[2] 陈兵.简政放权下政府管制改革的法治进路——以实行负面清单模式为突破口[J].法学,2016(2).
[3] 叶金育.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权的阐释与落实[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4] 程汉大.《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2(2).
[5] 陈日华.19世纪英国城镇卫生改革[J].史学理论研究,2009(4).
[6] 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英国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7] David Wilson and Chris Game.Loc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M]. Palgrave Macmillan,2011.
[8] Bryan Keith-Lucas.The Unreformed Local Government System[M].Routledge,1980.
[9]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M].杨伟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 [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英]S·李德·布勒德.英国宪政史谭[M].陈世第,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2] 刘剑文,王桦宇.公共财产权的概念及其法治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4(8).
[13] 刘剑文,侯卓.事权划分法治化的中国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17(2).
[14]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6] 陈兵.征税设计是宪政建设的核心——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的解说[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责任编辑:秦卫波]
ResearchontheImprovementofFiscalandTaxationRelationsbetween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fromthePerspectiveofRuleofLaw——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the Early Experience of British Rule of Law of Fiscal and Taxation
CHEN Bing
(School of Law,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of the new era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overnance and the financial power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rule of law of fiscal and taxation and the statutory tax have become the start and focus to ease fiscal taxation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British rule of law of fiscal and taxation,this paper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of local financial system,Britain realized the centralized collection and reasonable expenses of public finance based on “statutory tax” and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which highlighte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 and local autonomy in British representative system. Meanwhile,it also embodied the following features: the statutory governance and tax,clarification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subject of social supervision,stage evolution of the share and co-governance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wer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 on. On the occasion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the start and breakthrough of deepening the economic reform at present has become the emph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of fiscal and taxation,statutory tax as the standard,fiscal democracy as the key point,the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financial power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the context of legalization. Therefore,China should soberly look at the foreign experience;serve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he aspect of share and co-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China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xperi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Rule of Law of Fiscal and Taxation;Statutory Tax;Share and Co-governance;Political Experience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6.018
2017-06-22
吉林省法学会2016年度一般研究课题(JFXH2016B2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5—2017年度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20150029);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的资助。
陈兵(1980-),男,湖北荆州人,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国仁荷大学法学院招聘教授。
D922
A
1001-6201(2017)06-00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