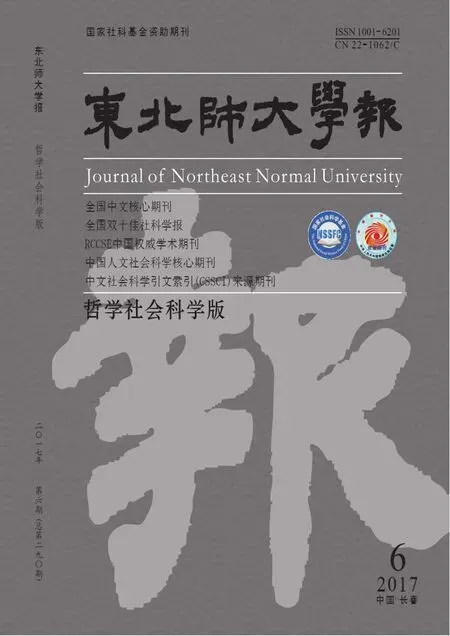自传契约:秋瑾弹词小说叙事研究*
杜 若 松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自传契约:秋瑾弹词小说叙事研究*
杜 若 松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近代女性弹词因其逐渐消亡而被研究界忽略,但作为近代女性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却孕育着女性文学中的女性“身份”确认、叙事、语言风格的现代性转型问题。秋瑾的弹词小说《精卫石》为启蒙女智、倡导女权而创作,自传性的叙事内容成为研究秋瑾复杂创作动机、探寻近代女性心路历程的重要途径;而《精卫石》叙事遮蔽、叙事典型化手段的使用则体现了文本的自传性叙事特征,具有向现代女性文学过渡特征。
秋瑾;《精卫石》;弹词小说;自叙传
弹词是流行于吴语区的讲唱曲艺,弹词小说指的则是借用弹词七字体的案头读物。17世纪以来,尤其是18、19世纪,韵文体的弹词小说在中国南方广受欢迎,阿英在《弹词小说评考》中就认为“弹词小说是南方的平民文学的一种”[1]9,女性弹词更是作为女性案头文学的代表进入女性文学史。民初的女性弹词小说*根据谭正璧的统计,目前所知的清代弹词小说有三百余种。参见谭正璧:《弹词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与《评弹通考》(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发展也是比较惹人注目的,诞生了如秋瑾、姜映清这样的著名女性弹词者,虽然随着五四新文学狂飙突起的文学飓风而被历史迅速吹散了它的踪迹,但在至今保存良好的女性期刊中仍可窥见它的萍踪侠影。这给了我们一个既可以探究女性叙事类文学的窗口,同时又提供了一个对近、现代女性文学接壤地带观察的绝好机会。
一
为何女性独在弹词领域取得一席之地,甚至从明清以来成为被正统文学默许的一种女性创作样式?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说:“女性作家独喜创作弹词,而且篇幅不厌冗长,内容不限复杂,如《笔生花》,长至一百数十万字,如《玉钏缘》、《再生缘》、《再造天》,不厌一续再续,在中国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她们都占到第一个位置。这是因为弹词是韵文的,女性大都偏富于艺术性,她们不独因富于情感而嗜好文学,也因有音乐的天才而偏富于韵文。”[2]348而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则将这种创作动机归结为“传世欲望”,此外作为书场文本的弹词本身具备的娱乐、教化作用也是弹词小说承接的重要文学功能。因此无论从内在动因,抑或艺术形式,女性弹词小说的发展都即满足了女性书写的特点而得到广泛的认同。这一点也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清代著名谴责小说家吴趼人曾公开承认弹词文学对女性的重大影响,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的第二卷第七号《新小说》“小说丛话”中说:“弹词曲本之类,粤人谓之‘木鱼书’,此等‘木鱼书’皆附会无稽之作,要其大义无一非陈述忠孝节义者……妇人女子习看此等书,遂时受其教育。风俗亦因之以良也。”[3]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弹词在今日,在民间占的势力还极大。一般的妇女们和少识字的男人们,他们不会知道秦皇、汉武,不会知道魏征、宋濂,不会知道杜甫、李白,但他们没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没有不知道左仪贞、孟丽君的。那些弹词作家们创造的人物已在民间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了。”[4]也正因为在市民阶层、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普遍接受程度,弹词小说成为了女性宣传与政治诉求、道德教化最好的传声筒。晚清著名翻译家徐念慈曾鼓励作家创作适介于普通女子之心理、专供女子观览的作品[5]。狄平子在《小说丛话》中说:“今日通行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如《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安邦志》、《定国志》等,作者未必无迎合社会风俗之意,以求取悦于人,然人之读之者,目濡耳染,日积月累,酝酿组织而成今日妇女如此之思想者,皆此等书之力也,故实可谓之妇女教科书。”[6]316可见弹词小说正是以它的宣传教育功能获得了当时知识文人的青睐,也使清末民初的弹词写作呈现了繁荣多彩的局面。以广大女性为服务指向的女性期刊也考虑到这一女性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在民初时期的女性期刊中刊载较多,这其中又以秋瑾的《精卫石》最为突出。
近代女性第一人秋瑾以充满革命气息、激情澎湃的笔触及痛彻心扉的个人经历为基础,叙写了弹词小说《精卫石》。相比较以往弹词小说往往以虚构人物为中心,《精卫石》具有鲜明的自传性质。《精卫石》创作于秋瑾求学日本的1905年到1907年,首先在《女报》刊出两期,署名汉侠女儿,本来要在《中国女报》逐期刊布,但因为资费问题报纸停刊而中断。《精卫石》正文前有序及二十回目录,“精卫石”的象征正是取材自《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故事,寓意女性解放也应该有精卫填海的持之以恒和坚忍不拔。尽管因为秋瑾的被害而导致《精卫石》的失传,原本计划的二十回今仅残存六回,但这六回正与秋瑾的东渡日本前经历吻合,从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参照意义。
从弹词规格而言,《精卫石》前有“序”抒发了秋瑾为文的原因。其中也孕育着“契约”,即在文本的开头就和读者订立一种约定,用以辩白、解释、提出先决条件、宣告写作意图,而最终达到与读者建立一种直接的交流。
故余也谱以弹词,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逐层演出,并写尽女子社会之恶习及痛苦耻辱,欲使读者触目惊心,爽然自失,奋然自振,以为我女界之普放光明也[7]122。
正是要启蒙女界、开启女智,同时又要吸引最广大的稍有知识的女性,因此才采取了“弹词”这种为广大女性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序之后,有目录二十回存目、仅存的前五回与第六回残稿。以弹词的体例创作,前面是诗词开场,中间则停顿或穿插作者的议论。“唱”“白”结合、韵散结合。唱词部分以七字句为主,加三言衬字,有时形成三、三、七言而成的十三字句,句尾押韵。并穿插了很多成语、俗语、谐语。叙事部分则接近古代白话、浅白通俗,听之即懂。
弹词假托东方华胥国,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尤其重男轻女之恶俗使得女性受尽身心虐待、婚姻枷锁,王母于是派众女杰下凡救世。而主人公名为黄鞠瑞,生有英侠之气,诗书满腹、志高存远,并且结识了梁小玉、鲍爱群、江振华、左醒华等闺中好友,同气相生。黄鞠瑞的父母欲将黄鞠瑞许配给富商苟巫义之子苟才,而黄鞠瑞却心怀远志,与众女伴变卖首饰金银,共赴日东,并结识陆本秀、史竞欧,商议加入光复会参加革命推翻鞑虏政权的过程。
《精卫石》弹词,因为其所书与秋瑾人生经历十分贴切,因此带有一种自传性质。而自传创作恰恰是近代女性在写作时最常使用的创作方法*参见杜若松.前五四时期女性期刊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创作[J].海南大学学报,2014(9),文章分析了近代女性期刊中女性创作中经常使用自叙体来进行小说创作的情况。。判断《精卫石》的创作动机,应该说和秋瑾的性格特质、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二
1905年(光绪三一年已巳),秋瑾赴日留学第二年,自日本返回绍兴省亲,回忆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对丈夫王子芳的厌恶,在给长兄誉章的信中写道,“怨毒中人者深,以国士待我,似国士报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报之,非妹不情也。一闻此人,令吾怒发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待妹之情义,若有虚言,皇天不佑。”[8]32此时的秋瑾已经和丈夫王子芳决裂,而此前,1896年5月17日,20岁的秋瑾听从父命嫁给王子芳,她就表示“以父命,非其本愿”[8]20。那么王子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秋瑾的婚姻不幸的原因是否完全归咎于王子芳?这种婚姻不幸又怎样影响了《精卫石》叙事?在对史料与弹词的比较中可以一见端倪。
秋瑾与王子芳的婚姻关系经历了一个由“怨”而至“恨”的过程。1895年冬或翌年春,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与湘乡王氏联姻,将瑾许配给王子芳。王子芳,字廷钧,他的父亲王黻臣,是湘乡神冲(今属双峰县)人,经营当铺发家,当王家迁至湘潭时,已经十分富有,王时泽在《回忆秋瑾》文章中说,“廷钧之父在湘潭由义街开设义源当铺,积资巨万。”[9]199因此王家成为当地豪富三鼎足之一。王氏闻瑾“丰貌英美”,由李润生作伐,厚礼聘之。但是秋瑾的心目中的理想丈夫却并非是王子芳这样的男性。据赵而昌的《记鉴湖女侠秋瑾》中记载“夫名子芳,状似妇人女子,而女士固伉爽若须眉者,故伉俪间颇不相得。”[10]102陶在东的《秋瑾遗闻》却更大加褒赏其为“子芳为人美丰仪,翩翩浊世佳公子也,顾幼年失学,此途绝望,此为女土最痛心之事。”[11]109而据日本的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女士》中回忆“秋瑾的丈夫也跟了出来,白脸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温顺的青年。”[12]175尽管各家立场均有不同,但是对王子芳的总体评价介乎一致,长相清秀,而性格比较软弱。此外囿于家庭熏染和自身性格,不自立自强,带有一些纨绔子弟的习气。
反观秋瑾的性格与之可谓截然相反。秋瑾少有才名,“十一岁已习作诗,‘偶成小诗,清丽可喜’并时常‘捧着杜少陵、辛稼轩等诗词集,吟哦不已’”[8]13同时秋瑾喜名士做派,自成一调,“女士首髻而足靴,青布之袍,略无脂粉,雇乘街车,跨车辕坐,与车夫并,手一卷书。北方妇人乘车,垂帘深坐,非仆婢,无跨辕者,故市人睹之怪诧,在女士则名士派耳。”[11]109因此,虽然王子芳长相清俊,但是内在的缺乏和性格的软弱使得秋瑾对之不甚满意。故此才有“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之句。
当然此种不和谐当时并未直接导致两人婚姻走向破裂。从现有数据来看,应该说有三件事加速了夫妻的分化。第一是在1902年,“秋家和王家在湘潭城内十三总开设和济钱庄,因用人不当,经理陈玉萱利用职权大肆贪污肥己,岁末钱庄倒闭。自此秋家即告破产,瑾在王宅也更受冷遇。”[8]22第二件事就是秋瑾跟随王子芳捐官户部主事,于是来到北京。“交游中桐城吴芝瑛,与廉惠卿(泉)伉俪甚笃,每言之,至声泪俱下,多所刺激,伉俪之间,根本参商,益以到京以来,独立门户,家务琐琐,参商尤甚,吾家陶杏南、姬人倪荻倚,及予妻宋湘妩,无数次奔走为调人,卒无效,由是有东渡留学之议”[11]109。吴芝瑛是吴汝纶的侄女,工书法、善诗文,思想比较倾向维新,而如吴芝瑛、陶杏南、宋湘妩等友人的相识和促动,北京新思想、新报刊的思想汲养,使得秋瑾破除家庭束缚、争取个人自立的观念愈发明确起来。而第三件事应该是王子芳阻挠秋瑾留学计划,甚至采用了私扣秋瑾首饰的方法。
在后人的回忆中,对历史真实的描述似乎发生了“奇妙”的分岔。比如在服部繁子的文章《回忆秋瑾女士》记录中,王子芳曾经亲自登门恳求她带秋瑾赴日留学。在服部繁子的描述中,王子芳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性,而其态度则是“惶恐而又害羞”的,当王子芳恳求服部繁子带秋瑾去日本时,他说:“我妻子非常希望去日本,我阻止不了,如果夫人不答应带她去日本,她不知如何苦我呢,尽管她一去撇下两个幼儿,我还是请求你带她去吧!”*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C].见: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179-180.也正因此,服部繁子得出了秋瑾在家里面是一个“家庭女神”的判断。服部繁子还记述过秋瑾对于丈夫的评价:“夫人,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足,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不不,这并不是为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人屈服。夫人,我要做出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12]174
固然这只是服部繁子的一面之词,并且由于她的立场和对秋瑾的观感而决定了其言词的倾向。秋瑾和王子芳的和睦究竟是否是一种表象?这可以参照当时秋瑾其他诗词为证。尤其是1903年中秋秋瑾与丈夫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尚发生于秋瑾准备留学之前。
王廷钧原说好要在家宴客,嘱秋瑾准备。但到傍晚,就被人拉去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收拾了酒菜,也想出去散心,就第一次着男装偕小厮去戏园看戏,不料被王发觉,归来动手打了秋瑾。她一怒之下,就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炉边琐记》,(上海)建设出版社,1943年。此据陈恭象《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引录”,以上材料转引自夏晓红.秋瑾与谢道韫[J].北京大学学报,1999,36(1):97.。
对于秋瑾与王子芳的这段公案,陶在东曾说,“寝假王子芳而能如明诚子昂其人者,则当过其才子佳人美满之生活,所谓京兆画眉,虽南面王不易也。徒以天壤王郎之憾,致思想上起急剧之变化,卒归结于烈士殉名,可云不幸。然革命成功,名垂国史,宁非大幸。”[11]109陶在东似乎对两人的离异非常遗憾,并做了这样的假设,如果王子芳能够有充分的才华,那么秋瑾也可以夫唱妇随,幸福美满。但实际上,秋瑾个人的名仕风流、人格理想、婚姻憧憬都显然不是王子芳能够达到的,因此两人由性格的差异所导致的婚姻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精卫石》作为秋瑾的自传体弹词小说,在主人公黄鞠瑞与其丈夫苟才的婚姻问题上持有特别激烈的态度。可以说,虽然秋瑾曾经一度在众人面前也曾经表现的与王子芳琴瑟和鸣,但在婚姻后期,这种怨愤已经到了不可调节的程度。以至于在日本动笔书写《精卫石》时,怨恨之情,溢于纸上。这也正体现了自传在精神分析角度的建构特征。“自传表现出某种姿态;其次,自传不经意间提供了可供阐释的回忆和自叙内容……”[13]87王子芳相貌清秀、性格温和的优点在《精卫石》完全未曾提及。同时用“狗才”通“苟才”的命名方式正是秋瑾发泄愤懑的途径之一,文中描述“苟才”:“从小就嫖赌为事书懒读,终朝捧屁有淫朋。”[7]146甚至不止连王子芳,他的父亲也遭到一并羞辱,在小说中起名为“苟巫义”。对其描述则为“为人刻薄广金银”,“家资暴富多骄傲,是个怕强欺弱人。一毛不拔真鄙吝,苟才更是不成人。”[7]146
可以说,秋瑾对于王家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而其决绝的态度也是让人感到其性格中间暴烈的成分。对王子芳父子二人的诋毁性虚构也正是通过叙事而形成了一种情绪发泄和心理治疗过程。即(女性的)自传总是包含着一个全球性的、深层的病理治疗的过程:组创女性的主体。以“苟才”“苟巫义”对应现实中的“王子芳”“王黻臣”,在公开发表的期刊上去昭示自己对其的不满,通过小说的情节去影射王家父子的薄情寡义。而小说一再描写主人公黄鞠瑞的“英气”,这种英气在一定方面上也是秋瑾处理问题上态度决绝、干脆利落的反映。
与“英气”相辅相成的则是秋瑾性格中的“侠气”。陶在东回忆,“宁河王筱航(照)戊戌一折而去礼部六堂者也,亡命数年,忽投拘步军统领狱,女士与筱航无素,以廉惠卿介绍,入狱存问,谈甚恰,适王有所恋爱,欲完成而绌于资,女士倾囊中所有增之,其仗义疏财如此”[11]109。而且当时王并不知此事,等到他出狱后知道此事时,秋瑾已经赴日了,所谓助人不图回报、侠肝义胆在秋瑾是个性使然。夏晓红在文章《秋瑾与谢道韫》中这样评价秋瑾性格特征:“秋瑾之以决绝的态度对待王子芳,亦是其所以为秋瑾的至性表现。而知行合一,勇于任事,无论待人还是爱国,均出之以尚义精神,这也是秋瑾由家庭革命转向社会革命一以贯之的人格底蕴。”[14]97这种评价是十分精准的。
三
以秋瑾的“闺怨”与“豪侠”为线索,则更能捋清《精卫石》的内外线索,在前五章,《精卫石》所叙述的是一个“闺阁世界”,而在闺阁中有女儿的各种愁怨,正所谓“写尽女子社会之恶习及痛苦耻辱”(《精卫石》原语)。
在第一回睡国昏昏妇女痛埋黑暗狱中,假借华胥国痛诉中国女性的黑暗处境:在社会统治层面,推行的是“天赋男尊女本卑,家庭中,又须夫唱妇方随”的伦理道德,重男轻女的恶俗,三从四德、七出这些旧有礼教传统极大侵害女性的成长;而缠足则从身体上戕害了女性的肉体,婚姻的不自由使得女性往往沦入悲惨的人生境遇。在这样的处境中,黄鞠瑞托仙胎下世,但是她一出世,就遭到赋闲在家的黄父的怒骂:“生个女儿何足道?也许这样喜孜孜。无非是个赔钱货,岂有荣宗耀祖时?”在黄鞠瑞成长读书时,也遭到父亲的阻拦“怎么鞠瑞也读起书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何必读什么书?这又是她母亲的混账主意了。待我去讲她一顿,叫进鞠瑞去学针线。”听了俞夫子的劝解,也不过说,“但是纵教学得才如谢,亦无非添个家人薄命诗!”之后违背黄鞠瑞的意愿贪富贵将之嫁给苟巫义之子苟才。
弹词的叙事线索则主要介绍另一个女子梁小玉。在前五回,梁小玉可谓重要人物,若论及人物叙述份额,甚至比黄鞠瑞还要多。梁小玉因此也成为与黄鞠瑞对照的另外一种闺秀典型被描述。梁小玉本“为庶出,嫡母生有三弟兄,性情嫉妒多严厉,侍妾妆前未克容,打骂时加凌虐甚,小玉父生成惧内又疲癃。此妾亦由嫡母买,人前欲搏量宽洪,内中看待如囚婢,在外面自道看成姊妹同,善工掩饰人难晓,外施揖让内兵戎。小玉生来多命苦,在家胜是鸟居笼,嫡母看承多刻薄,二兄相遇更狂凶。”[7]139后来又叙述梁小玉因为为生母买药之事而遭受兄长毒打,并遭受“今朝打死小淫娃,拼的我来偿了命,免气娘亲挑拨爷”的恶毒咒骂。可见女子在闺阁内、大家庭中生存之不易。
《精卫石》一方面记述女子闺中之怨,另一方面极力描摹了闺中之蜜。今时女子好友称为“闺蜜”。秋瑾之闺蜜,在现实中有徐自华、徐小淑、吴芝瑛等人,其文字有《致徐小淑书》、《寄徐寄尘》等文,而徐自华、徐小淑本是姊妹。可见秋瑾与至交好友的交往也是局限在一种小范围的,虽有知己不过寥寥,正像秋瑾自陈的,“人皆云我目空一世,与子相处月余,当知余非自负者,庸脂俗粉,实不屑于语。余之感慨,乃悲中国无人也。”[15]63秋瑾的闺蜜原则是志同道合、酬唱应答、富有才学之女士。而后来徐自华、吴芝瑛等人埋葬秋瑾骸骨、树秋瑾碑陵、开女学的壮举也印证了秋瑾择友的慧眼。
秋瑾在《精卫石》前五回也极力书写了这种“闺蜜”情谊。梁小玉本是庶女,按照当时的礼教规范,黄鞠瑞本可以对其冷淡视之,但是黄鞠瑞却将梁小玉引为知己。梁小玉为黄鞠瑞的不幸婚姻通宵不寐,而在黄鞠瑞提出留学海外的主张时,梁小玉因没有钱财忧虑,这时黄鞠瑞慷慨解囊,黄鞠瑞不以个人金钱为私,资助其他四女共同留洋,此种行为正是解他人危难之举。
不仅黄鞠瑞能与“四美”建立闺蜜之情,与鲍爱群的丫鬟秀蓉也能建立起主仆情谊。她对鲍爱群的丫鬟秀容非常赏识,称:“如此人才真屈辱,名花落溷恨难平。若得与君受教育,何难为当世一名人。他年若有自由日,必誓拔尔出奴坑,结为姊妹相磋切,造成必是女中英。”[7]44由此引起了秀蓉的知遇感恩之情,在后面的五人借鲍母寿辰之际离家出走,都是由秀蓉在当中通风报信,起到重要作用。
而其“寡”,则所谓为大义,很多事及人就不能或者也无暇考虑,这或许可称之为成大事者的“寡情”。
按照秋瑾的自身生命历程和弹词相对比,我们明显发现秋瑾在《精卫石》中进行了乐观化、精简化的情节处理。这种后来在革命文学中经常使用的“革命浪漫主义”在弹词中有充分体现。首先就是一种遮蔽性叙事*菲力浦·勒热纳在《自传契约》艺术中认为这是一中非常经验化的记忆现象学。而遗忘被视为对生活意义的某种遮蔽或者是揭示。见参考文献13的第69页。方法,试举以下几例:
例一,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嫁给王子芳,并生一男一女,此事在弹词内完全没有描写,后来的与王家发生冲突,变卖首饰情节自然未提及。例二,秋瑾到日本,水土不服,亦不适应当地饮食(见: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语言文字学习困难,留学资金困难。此等种种艰难弹词也并无提及。例三,在日期间,秋瑾与同学因革命政见的不同发生过诸多矛盾,其中与胡道南发生争论,“女侠于众人间骂胡为‘死人’”[16]162,以及与陶成章的不合,这些留日期间的故事都未曾提及。这体现了自传叙事的特征,“自传不能只是发挥叙述才能,把往事讲得生动的叙事,它首先应体现一种生活的深层的统一性,……自传需要做出一系列取舍,这些取舍有的已由记忆做出,有的则有作家对于记忆提供之素材所做出。……尽管这种关联性要求可能导致简单化和图解化倾向。”[13]11其实,此类情节十分曲折,且更有教育警醒之功能,但出于隐私避讳,抑或复杂的心理原因(本文第二部分有过分析),秋瑾并不愿描写此内容,于是弹词在这里进行了虚构。
其二,黄鞠瑞和梁小玉的家世情况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典型化描述,如黄鞠瑞之父虽然贵为知府,却具有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对黄的存在大多是责难,且荒唐好色,在济南署理期间就纳了两房妾,其中一人还是妓女出身;而黄的母亲对于女儿不愿的亲事也采取忍让劝说的态度。梁小玉的家庭则是嫡母阴狠毒辣,三个弟兄视梁小玉为眼中钉,甚至以“淫娃”“祸胎”来称呼,亲生母亲软弱无能,父亲则惧内软弱。两个落后黑暗的家庭使得两个女性愤然离家,此后也未见丝毫后悔留恋之意。
这种将主人公典型化的描写方式也是小说虚构的常见方式,而现实中的秋瑾,其家属因其事流落峡山村寺庙,在遭此“奇祸”的打击下,长兄于37岁壮年患病抑郁去世,而正是兄长长期与秋瑾通信,并资助秋瑾在日的留学部分资费。此外,在其女王灿芝的《读〈六月霜〉后之感想——关于先母秋瑾女士》的文章中,我们亦可得知,其“在襁褓中,乃随母行。后寄托于友人谢涤泉家,由邓性女仆携归家中,几乎冻死饿毙于中途。……先母为国捐躯,余亦因此几丧其生,后受家庭之压迫,备尝艰苦。无母孤儿,乃罹斯厄。……世态炎凉,观此诚外国人之不若矣。良可慨也。”[17]165对于秋瑾的所作为,未尝没有埋怨之意。此类种种与弹词如相对比,只能说舍去个人的家庭幸福换之民族大义,秋瑾与其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以文字鼓舞众妇女的《精卫石》将此中情节舍去,但其中的心灵挣扎与感情悖论将是这作品永远无法表白之痛。“自传写作,就是一种自我构建的努力,这一意义要远远大于认识自我。自传不是要揭示一种历史的真相,而是要呈现一种内在的真相,它所追求的是意义和统一性……”[13]77将个人舍去,换大义,将芜杂简化,换神话,秋瑾在近代“家国”系统中的选择,正是女性响应时代的一种叙事选择。
作为近代女性弹词的代表,秋瑾的《精卫石》以个体在时代中的悲欢遭际,自传性的描摹,披肝沥胆、字字血泪地发出了自己启蒙女性、激励女性的呐喊之声。当下的学者频频重视秋瑾的诗文却忽略了她弹词的存在价值,或许也是由于她自身生命的诸多悖论,使得这部弹词的解读充满了矛盾与不可知。但是弹词这种形式在即将湮没之际得到秋瑾的青睐这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我们由此去观察近代典型女性的生活重心与时代接轨时的所思所想,自然也更能体会到过渡阶段许多不可说不可解的女性心结。而《精卫石》对女性的阅读影响,对女性叙事虚构的手法探索,也在现代女性自叙传创作如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苏雪林的《荆心》中得到了传承。
[1] 阿英.弹词小说评考[M]//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第六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2]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3] 吴趼人.小说丛话[J].新小说,1905(7).
[4]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5]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6]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秋瑾.秋瑾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8] 郭延礼.秋瑾年谱简编[C]//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9] 王时泽.回忆秋瑾[C]//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10] 赵而昌.记鉴湖女侠秋瑾[C]//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11] 陶在东.秋瑾遗闻[C]//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12] 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C]//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13] 菲力浦·勒热纳.自传契约[M].杨国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4] 夏晓红.秋瑾与谢道韫[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6(1).
[15] 徐自华.秋瑾轶事[C]//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16] 绍兴逸翁稿.再续六六私乘[C]//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17] 王灿芝.读《六月霜》后之感想——关于先母秋瑾女士[C]//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哲文]
L’autobiographieenFrance:NarrativeResearchintotheTanCiNovelWrittenbyQiuJin
DU Ruo-so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e modern Tan Ci novels written by women are ignored by the research community due to their gradual disappearance. Yet as the narrative genre that modern women loved to read,Tan Ci novels bred the female “identity” verification,narration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style of feminine literature. Tan Ci novelen titledJingweiStonewas written by Qiu Jin to enlighten females and advocate women’s rights. Th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content became the important channel for Qiu Jin to produce complex creation motivation and explore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modern women. Meanwhile,the use of narrating shadow and typical narrative means ofJingweiStoneembodies th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text andJingweiStone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nsition to modern feminine literature.
Qiu Jin;JingweiStone;Tan Ci Novel;Autobiography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6.004
2017-06-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ZW038);吉教科文合字(2016)第400号;长师大社科合字[2015]008号。
杜若松(1981-),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此文为作者的东北师范大学2015博士论文《近现代女性期刊性别叙事研究》的部分成果。
I109.4;I24
A
1001-6201(2017)06-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