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恶棍的春天
东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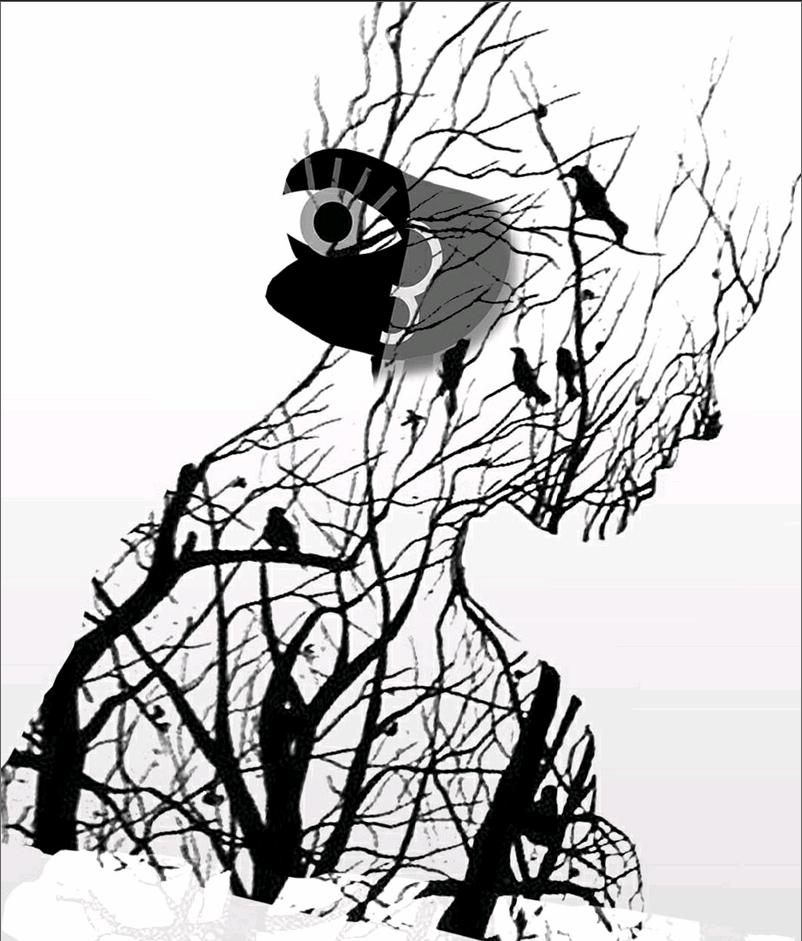
老酒汗,敢不敢喝?!马荣把杯子推到我鼻子底下问。
我十三岁的时候喝过一种高度老酒汗。老酒汗之烈,不下于东北高粱做的“烧刀子”,对南方人来说,烈酒等同于一把剜胃刿肝的刀子。但有些人到死都喜欢这种酒。被酒放倒,好比是牡丹花下死。
那天请我们喝老酒汗的人,是我的同学马荣。马荣是这样对我们说的:醉过之后,你就是男人了。马荣仅仅比我大一岁,就以男人自居了。在同龄人中间,他应该算是早熟的。他没有查过字典,也没翻过什么书,居然知道“鸡奸”是什么意思,而我们那时所理解的鸡奸就是公鸡与母鸡之间所发生的性行为。
敢不敢喝,老酒汗?!马荣卷起了袖子问我们。说话间,突然朝我吐出一道白气,如马喷鼻。我被浊重的酒气一熏,仿佛挨了一记耳光。心中有些不快,但不便说出来。
酒馆里还有几桌闲客,吃过了午饭,便坐在那里饮酒吃茶,杂谈声洇开,有了一种大概可以称之为散淡的氛围。他们如果没什么事,照例可以聊到太阳西斜。
之后我们就看见西门勇进来。他背着我们,在窗口的位置坐下。也就是说,他坐在南面,而我们则坐在东北角,中间相隔四张桌子和一扇雕花镂空屏风。
毫无疑问,西门勇是马荣最崇拜的人物。这条街的南北货市场原本是无序的,西门勇来了,很多事也便由他说了算。凡是在他势力范围之内的外地摊贩,都要向他交保护费;没有交的,也行,日后与人纠纷,他概不出面回护。但交了保护费,就等于请来了一尊保护神,剩下的事就看财神的保佑了。
马荣“嘘”了一声说,我看到西门勇背后藏着一件家伙。他的声音很低,除了我们一桌人,谁也不会听见。我们转头瞥了一眼西门勇的背影问,什么家伙?马荣说,你们猜猜看吧。长头说,好像是一把刀。李颉说,不对,刀藏在衣服里,不小心还会伤到自己,可能是双节棍。铁腰说,双节棍没有那么细,应该是一把铁尺。马荣同意铁腰的看法,认为西门勇背后那根家伙就是铁尺。那个年代,很多流氓常常操持铁尺,它没有被归类为刀具。但我坚持认为,西门勇身后插着的是一把带鞘的短刀。
马荣把脑袋凑过来说,谁如果敢掀开西门勇背后的衣裳,摸一下那件家伙,我马荣就在街头爬三圈。他的两根手指弯曲着,在桌上作爬行状。
我见过西门勇的刀,马荣说,有一回,西门勇来到我爹的打铁铺,让他把一柄有些年头的刀重新锻打一遍,血槽刻得更深一些。从马荣口中,我们略知一些与西门勇有关的轶事。他带在身边的只有刀和女人。晚上,女人睡在里侧,带鞘的刀放在枕下。刀只有一把,女人也只有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从来不许别人染指。有一回,有个小痞子在电影院里摸了一把他的女人,此人走出电影院之后,五根手指就不再属于他了。
马荣把我们的脑袋往下按了按,悄声问道,你们当中有谁敢去摸一下?李颉问,摸什么?当然是他背后那件家伙,他敲了一下李颉的脑门说,难道是他女人的屁股?怎么,你们敢不?没人应声。而我装作没听到。马荣却偏偏把目光盯住我说,有两件事证明你胆子是否足够大。一是去摸一下西门勇身后那件家伙;二是拿石头去砸林小雨家的玻璃。提到“林小雨”这个名字,我左臂的肱骨就会隐隐作痛。但我的舌头只是在杯子里吸溜着,没吭声。胆小鬼!马荣腾地一下站起来,提起那壶酒朝西门勇那边走去。他绕到西门勇跟前,哈着腰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做出一副要敬酒的模样。西门勇挥了挥手,示意他走开。马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好拣边上一张桌子坐了下来。那一刻,他就坐在离西门勇最近的位置,那神气仿佛是坐在王座边上。
大概是因为酒能壮胆,我喝了一小口老酒汗之后,内心突然涌起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勇气,也跟马荣那样腾地一下站起来,端着酒杯,走到马荣身边,十分镇定地坐了下来。酒的热气正好抵达腹部的位置。
西门勇有一张线条粗硬的侧脸,泛着淡青色的下巴微微上翘,而嘴角向下撇开,仿佛有两股相反的力量正在相互牵扯着。不过片刻,楼梯口响起一阵迟缓而滞重的脚步声,他蓦地转过脸来。进来的,正是周老师。许久不见,周老师消瘦了许多,整张脸也仿佛薄了一层,隐约透着黑气。他身上的灰色哔叽中山装显得有些宽大,好像是临时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周老師跟西门勇点了一下头,就在他面前坐下。
周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也是西门勇的数学老师。他的书教得如何,只需要看底下同学们的表情就能明白。周老师每每见大伙打不起精神,就会讲一个故事。他喜欢讲《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偶尔也夹杂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据他说,大半是在下放林场那些年亲历的。说是有一回,他夜宿林场木屋,忽然听到刀剑相交的声音,惊起。打开窗户,院子里面月光是白的,草木是黑的,四下里没有一丝人影,也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但厮杀的声音依旧不绝于耳。周老师即便捂住耳朵,也无济于事。因此,他疑心这是幻听。第二天,他早早起来,问林场的老汉,昨夜可曾听到什么动静。老汉说,他听到了刀剑碰撞的声音,但他念了几句不晓得从哪儿学来的咒语,这声音就渐渐消失了。周老师问,这怪异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老汉指了指地下说,这里原本是古战场遗址。那些埋在地下的将士大约不甘寂寞,又在地底厮杀起来了。老汉这样说着就把周老师带到一口古井边说,声音就是从井底传来的。周老师讲完这个故事,缓步走到窗口,指着外面那个落满枯叶的古井说,那口井就跟这口井一样。我们听了,都深深地抽了一口凉气。尽管我们都知道周老师所讲的鬼故事是编造的,但还是有些害怕。他为了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就在每堂课上留一点时间用来讲故事。有一个学期,每堂课临近结束时他就跟说书人一般,给我们讲关云长。铃声一响,他就立马打住,把悬念留给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忘掉了他教给我们的方程式解答,却独独记住了那些离奇的故事。周老师本人也颇有些传奇色彩。一年前,他用石头砸过一个人。那人命硬,脑袋砸出了一个大窟窿,居然没死。因为这事,周老师坐了牢。据说有两个律师因为石头是钝器还是锐器相持不下,所以周老师的案子迟迟没有审判结果。至于他在牢里有没有给狱友讲那些离奇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
马荣隔着一张桌子,朝周老师打了个招呼。周老师的嘴使劲嚼动了几下,看起来好像十分勉强地挤出一个微笑。但他终究还是没笑,只是点了点头,就迅速别转脸,跟西门勇静静地对视着。有那么一阵子,他们什么都不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西门勇递上一根烟,问,吃不吃?周老师说,我不吃烟。西门勇说,嗯,我早就听说,你是喜欢吃酒的。我今天特地给你准备了一壶好酒,加热了就送来。
我现在没心思喝酒。
一酒解千愁,这是你当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喝吧喝吧,该办的事,我是一定替你办掉的。
西门勇吐着烟圈,形状宛如上吊绳的绳圈,仿佛可以置人于死地。
我要找的人呢?周老师有些焦急地问。
西门勇咕噜一句:阿德这小子,说好这个点上来的。于是把头探到窗口,朝楼下喊了一声:黄毛,你上来。不多时,那个叫黄毛的瘦个子便走了进来。西门勇说,你把阿德叫过来,就说周老师要跟他会个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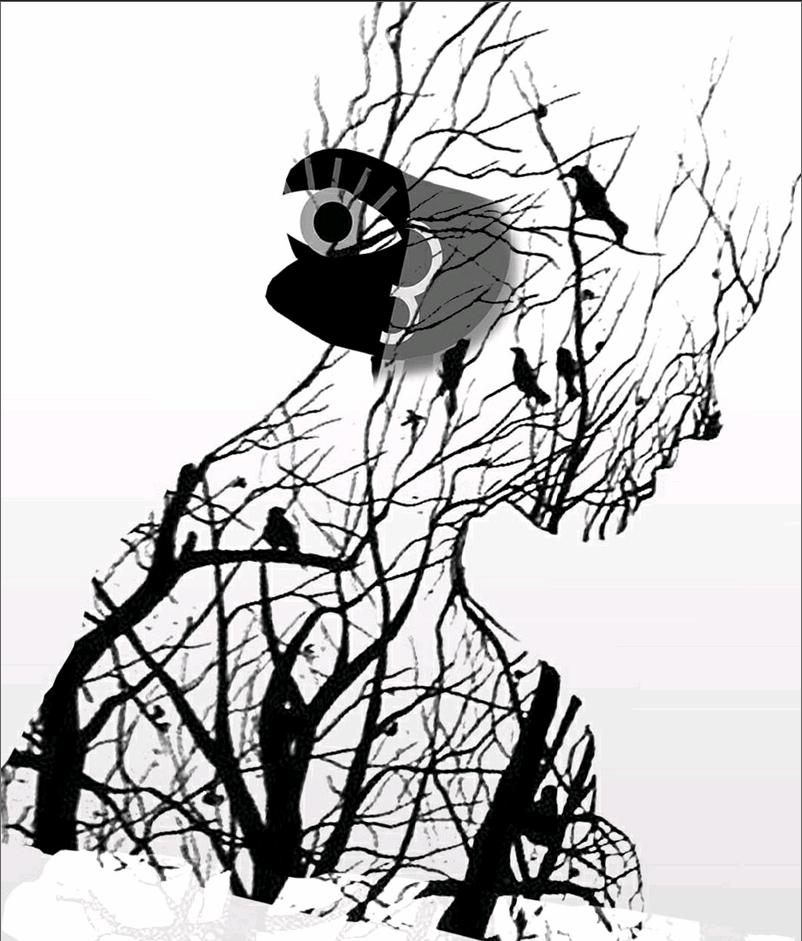
黄毛走后,一壶酒已摆上周老师面前。周老师摇摇头说,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喝酒。西门勇说,我们喝完了这壶酒,阿德差不多也就到了。说着,就给周老师的杯子里筛酒。
午后的悠长时光拉长了酒馆里面的阴影。眼下我似乎暂时忘掉林小雨跟我们之间的过节,倒是很想看看周老师与那个名叫阿德的家伙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而西门勇他究竟要干什么?事实上,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眼中,西门勇一点都不可怕。他看见街上的小孩,通常会摸一下他们的脑袋,而且非要把他们的头发弄乱不可。有一回,他曾用那只拿刀的手摸过我的后脑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摸我,还冲我扮个鬼脸。凭良心说,西门勇从来没有欺侮过小孩。
西门勇说,这一壶酒也差不多喝完了,阿德也该过来了。话刚说完,黄毛进来说,阿德说他不来。西门勇说,他不来也得来。黄毛说,阿德让我转告说,都是一些小问题,没必要惊动大哥。
但西门勇挂下了脸,明摆着就是要跟“小问题”过不去。他说,阿德如果不来,你就让他自己剁下一根手指来见我。
周老师说,我今天是从牢房里偷偷跑出来的。如果我见到了阿德,他给一个让我满意的说法,我就立马回去自首;如果他不来,愿意剁下一根手指来见我,我也就认了。从此之后,这笔账我不会再去追究。
我们意识到,一件动刀子的事就要发生了。刀可以让复杂的事突然变得简单。但也有可能会让简单的事变得越来越复杂。
黄毛转身走后,西门勇又叫了一壶酒,说,你再把这壶酒喝完了,阿德如果不来,也会带来他的一根手指。
没有人带来阿德或阿德的手指。一阵风吹过来,撩动我们的头发,就像有人摸了摸我们的脑袋,走了过去。
知道我为什么要敬你三分?西门勇举杯对周老师说,因为你是条汉子,跟那些胆小怕事的教书先生不一样。你应该还记得十多年前那个夏天的事吧。那天傍晚,你只身一人,光着膀子,进了我们郑家祠堂,从那些拿刀的人里面带走了你的学生。
不错,那个学生就是阿德。他爹打了郑家的长辈公,引发极大的公愤。他爹是跑了,可郑氏族人却冲到学校,把阿德给绑走了。我气不过,报了警。警察过去要人,也没消息。阿德他爹是我的拜把子兄弟,我岂有坐视不管的道理?放学后,我就孤身一人来到郑氏祠堂。族人说,要赎人,就带阿德他爹的一只手来。可我伸出了自己的手告诉他们,如果谁有种,就剁掉我的手。
那时我就躲在人群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觉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像你一样威风。现在我倒想问问,你身上什么家伙都没带,不怕?
正因为我身上什么都没带,所以不怕。
可你就凭一股气势,让全场的人压低了半个头。因此我还想知道,你身上的一股气势是从哪儿来的?
气势这东西,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
无中生有?我是粗人,不明白你的意思。
打个比方吧,周老师把杯子举起来说,我们喝酒,要的不是这个杯子本身,而是它空无的内里。这个内里,就叫“无”。你看到了它的“有”,偏偏没用,能用的恰恰是它的“无”。也就是说,杯子空了,才能倒這个酒;双手空着,才能生出那气势。说到这里,周老师又像是回到了课堂,正对着一个资质驽钝的学生讲解一道难题。
西门勇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你有了刀,身上不一定有那气势;不带刀,反倒有了气势。你说的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是这意思了,周老师突然做了一个摔杯的动作,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把杯子砸了,“有”就消失了,“无”也跟着消失了,一切也就完了。你在摇头,你不会明白我的。
渐渐地,他的脸涨红了,好像愤怒就隐藏在他的皮肤里,好像愤怒是红色的。喝完了最后一滴酒,他往后一靠,打了个酒嗝说,阿德还是没来。
西门勇笃定地说,他会来的。
阿德,全名叫王阿德。这条街上的人只要提起阿德,就知道是谁。阿德一直喜欢周老师的女儿,小周对他却没一点意思。周老师坐牢那阵子,就把女儿托付给阿德照看。有一天,阿德和几个朋友带着小周去爬山。其中一个朋友说口渴了,让阿德带着空酒瓶去溪那边盛水。阿德回来时,发现小周不见了。直到天黑,小周才捂着疼痛莫名的下体回到家中,把自己关进房间,再也没出来过。后来,阿德就觉察到她有点不太对劲了,但凡看见男人(包括阿德)进入房间,她就会掏出枕头底下的剪刀,在空中胡乱挥舞。周老师得知此事,在监狱里面断断续续写了上百封起诉书,要严惩那几个强奸犯,但每回寄出起诉书,都没有回音。周老师有些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就让那些出狱的人给外面捎带一句话:法律不能解决的事,只能用刀来解决。这一回,他偷偷跑出来后,没有立马动刀子,而是找到西门勇,请他出来主持公道,让阿德出来,好歹给个说法。
你放心,西门勇拍着胸脯说,我让阿德过来一下,他敢不过来?!我们知道,如今的西门勇已不同往常,不用做出狠相,都能教人膝软;不用出面吱一声,只要托人传个话,也能把事办了。那一刻,我们都等着瞧阿德的好戏。
没多久,黄毛进来说,阿德跑了,只留下一句话:他要去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西门勇说,无论他跑到地球上的哪个角落,我都会花点时间把他找出来。
周老师喝完了这壶酒,说,我没时间了,警察很快就会找到我。等我出来的时候,恐怕已经拿不动一把刀子了。
周老师把手伸进怀里,哆嗦着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刀。
在我的想象中,西门勇也会把背后那一把更锋利的刀抽出来,插在桌子上,说一句发狠的话。然后,就会有一场异常精彩的打斗。最完美的结局当然是,西门勇带着这把血迹未干的刀离开这里。
然而,我所想象的场景并没有出现。西门勇把左手伸到后腰的位置,好像要掏家伙了,但他的手指只是微微动了一下,没有掀开衣服。
周老师把刀尖指向自己的胸口说,临死前,我求你一件事,用我这把带血的刀剁下阿德的手指。
把刀给我,西门勇伸出一只手来说,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周老师把刀递了过去。西门勇接过刀,咔嚓一下,剁下了自己的一根小手指。
手指在桌子上蹦跳了几下,不动了。窗外有鸟飞过,西门勇忽然张开双臂,仿佛那一刻他听到了鸟翅扇动的声音。还要补上一刀?他问道。
周老师面色铁青,嗫嚅着,你这是何苦?!
就这样了结了?
就这样了。不过,我如果能活到出狱那一天,会请你吃一杯酒。
西门勇把那根血淋淋的断指捡起来,放进口袋,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低垂着脑袋,向大门那边阳光汹涌的地方走去。背后那件凸出的家伙,居然没有掏出来。我指了指说,那是一根夹住的尾巴。
一个胆小鬼,李颉说,就这样夹着尾巴走了。
不,马荣说,他是一条好汉。
那天下午,我们第一次干掉一瓶老酒汗,头有些重。我走到大街上时,一道阳光迎面照过来,差点把我击倒。这一路过去,我不再像往常那样清点大街上的电线杆。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搅动,酒是一种温和的火,可以让人慢慢燃烧起来。
前面就是林小雨家,你敢不敢过去?马荣指着前方说。我们三三两两,任由早春二月的风吹乱头发。冬天的荒寒迹象尚存街角,而春天依旧瑟瑟缩缩地躲在树后。这条街上,唯一绽放的花朵是花圈店里那些面朝死亡、毫无生气的纸花。
我站在林小雨家门口,铁门依然紧闭。马荣把石头交给我。我没有接。铁腰把石头交给我。我也没有接。李颉把石头交给我,我还是没有接。
我握緊拳头,积蓄力量,随时准备拿起一块最锋利的石头,朝那个黑洞洞的窗口投掷。风吹过来,我的手一点点松开……感觉拳头里凝固的愤怒被风吹散了……
话说半年后,西门勇在浙南边境一个暗旧的修车铺找到了满身油污的阿德,他跟阿德谈话时,看见一辆末班车缓缓驶来,就使劲抓住阿德的手。阿德越是不依,西门勇越是紧抓不放,结果扯破了阿德的一只袖子。一分钟后,他登上了车,顺便带走了阿德的一只手。西门勇还没回到县城,就在途中被警察逮住了。那一年,国家推行严刑峻法,因此就把西门勇列为“严打”对象,判处死刑。跟随西门勇(包括黄毛)的小兄弟全都坐了牢。至于阿德,断了一只手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西门勇死后三年,街头还有一些年轻人仍然在谈论他。
有一天,马荣说,我跟你们打一块钱的赌,西门勇之后,这条街上还会出现一个厉害的角色。
有一天,马荣像老大哥那样把刀子递到我手里。我仍然不知道自己要干点什么。
选自《天涯》2017年第1期
原刊责编 郑小驴
本刊责编 向 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