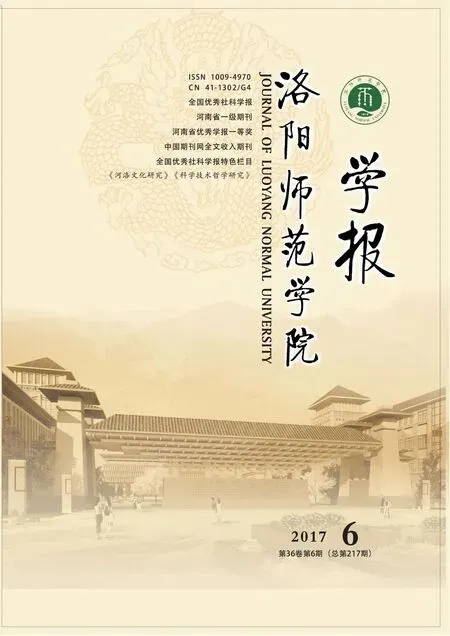唐僧圆静与洛阳恐怖袭击案关系考
陶继双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518055)
唐僧圆静与洛阳恐怖袭击案关系考
陶继双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518055)
唐僧圆静, 在唐宪宗元和十年八十余岁时, 因谋划血洗洛阳被捕, 兹由50余年前安史之乱时他对唐廷积恨所致。 他与安禄山同族, 属粟特胡, 是史思明的得力护卫。 在史朝义发动的政变中, 其家属受到牵连, 无奈之下削发为僧, 并在此身份遮掩下伺机复仇。 透过对圆静身份的考察, 亦可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 表面虽或平静, 内里却暗流涌动, 危机四伏。 关键词: 圆静;武元衡;洛阳;刺客;安史之乱
元和十年(815), 唐朝宰相武元衡死于刺客屠刀之下。 他生前因儒雅不失大将风范而备受推崇, 但死后就杀手、 主谋是谁等问题, 在当时及之后一直存在争论。 笔者拟在揭示唐朝僧人圆静身份及其与洛阳袭击案关系的同时, 旁涉其与武元衡被刺的关系, 以及唐政府与藩镇的斗争和妥协。 不当之处, 请方家指正。
一、 圆静身份探究
元和十年(815), 王师讨蔡, 李师道属下人等拟乘东都调兵驻守伊阙, 城内防守空虚之际突袭东都洛阳, 事发前日, 同伙中有人到东都留守吕元膺处告密[1]7716, 遂致败露。
“穹理得其魁首, 乃中岳寺僧圆静, 年八十余, 尝为史思明将, 伟悍过人。 初执之, 使巨力者奋锤, 不能折胫。 圆静骂曰:‘鼠子, 折人脚犹不能, 敢称健儿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 临刑, 乃曰:‘误我事, 不得使洛城流血。’”[2]3538-3539
这是所见有关圆静的最详细记述。 材料虽简短, 却为我们透露出四条重要信息:第一, “圆静”乃出家后所取之名, 本名不得而知;第二, 他曾是史思明的部将, 身手非凡;第三, 年纪八十余岁;第四, 对洛阳恨之入骨。 由于第一条没有相关记载, 无法从姓氏上推测其族属, 故只能从第二条开始考究。 因圆静是史思明部将, 那么很有必要对安史军队部伍构成略加考索。 就笔者阅读所及, 有关安史主力的讨论主要分两派。 一派认为是昭武九姓, 《大唐西域记·飒秣建国》:“其王豪勇, 邻国承命。 兵马强盛, 多是赭羯。 赭羯之人, 其性勇烈, 视死如归, 战无前敌。”[3]12此与圆静信息中透露的其身手不凡、 不畏死和个性勇烈等特征完全符合。 《新唐书·安国传》:“募勇健者为枳羯。 枳羯, 犹中国言战士也。”[4]6244圆静的战士身份也与此吻合。 当然这些也不排除存在巧合的可能, 故仅据此尚不足以断定其为粟特人。 另一派认为是奚、 契丹等少数民族。 两方孰是孰非可置之不论, 但他们都倾向于安史主力是少数民族而非汉族。 那么, 在不能断定圆静为粟特人之前, 推断他是少数民族人, 应该没有问题。
安史之乱发生在公元755—763年之间, 元和十年是公元815年, 圆静八十余岁。 推算起来, 至安史之乱结束, 他应在三十岁左右, 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段。 按正常年辈推算, 他此时不仅有妻儿, 父母也当健在。 故从事业和家庭两方面可断其没有与红尘绝缘的大因由, 那么他缘何要出家呢?从八十余岁还行恶可知他绝不是为了文化或精神追求, 可断定其一定遭遇不得不出家之变故, 最有可能是他家庭遭受毁灭性打击。 史载圆静是史思明部将, 但没提他与史朝义的关系, 顺理成章地推想, 他在史思明死后应该追随史朝义才合理, 为何史朝义逃死东垂, 他却在嵩山出家?这大概是史朝义对胡政策使然。
《安禄山事迹》所载两条看似不相干的事件, 与圆静却有不可割舍的联系。 史朝义在谋划软禁其父时, 考虑到一个关键人物, 即负责史思明卫戍的曹将军, “思明居驿, 令心腹曹将军击刁斗, 防卫甚严”。如史朝义所愿, 最终对他策反成功。 这招致史思明对曹氏变节的唾骂:“此胡杀我, 我负汝何事, 而行此逆乎!”从这骂语中, 我们可知曹将军是胡人, 相对史思明的突厥种, 他应该是粟特胡, 即昭武九姓之曹姓胡。 在叛乱之际, 史朝义心腹骆悦等“其夜, 领朝义部下数百人擐甲诣驿, 思明侍卫怪其有异, 惧曹将军, 遂不敢动”[5]44, 遂顺利俘虏史思明。 从圆静的身手和当时为史思明部将来看, 他很可能是这宿卫部伍中的一员, 曹将军是胡人, 他的队伍里包含胡人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以上看法不误, 圆静当时身在宿卫, 亲身经历了政变全过程, 仅因守将叛变未敢反抗而已。
与此同时, 史朝义派人回范阳密杀对他最有威胁的帝位争夺者史朝清。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范阳从此屠杀相继, 达到难以控制的局面, 史朝义也因此最终未能再进范阳城。 此前范阳城也经常发生部队械斗事件, 但一般是“两敌相向, 不入人家剽劫一物, 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 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 皆闲习弓矢, 以此无虞”[1]7111。 而此次却有所不同。 高鞫仁掌控局面后, 对阿史那承庆等率领的蕃胡部队及他们在范阳城内的家属下达屠杀令, “鞫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 于是羯胡尽殪, 小儿掷于空中, 以戈承之, 高鼻类胡者甚众”[5]44。 据此条, 再联系到前已推论圆静是胡人, 笔者认为他的家口在这次屠杀中遭到了灭顶之灾。
如果说此次劫难虽由史朝义肇发, 事态发展的情势非其能掌控, 圆静内心久之还是能接受和谅解的, 但事件至此并未完结。 由于高鞫仁的行动已经背离史朝义的原旨, 如果承认咎责在己, 难免接受制裁。 为规避罪责, 高鞫仁利用已经掌控范阳的事实, 逼迫史朝义接受此次事件恶化悉因阿史那承庆率胡人反叛所致, 必须对阿史那承庆等追加处置。 史朝义为不丢失其家“龙兴”之地范阳城, 被迫接受高鞫仁的威胁, 乘阿史那承庆到洛阳之时, 对部队中的胡人进行了清洗, “后朝义使招之, 尽归东都, 应是胡面, 不择少长, 尽诛之”[1]7112。 这对胡人背弃和屠杀的做法, 必然招致其他部队中胡人的强烈反对和不满。 对圆静来说, 史朝义不但不将高鞫仁绳之以法, 反而与其狼狈为奸,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时他已无家可归, 追从史朝义既不心甘情愿又有被迫害的可能, 那么选择出家是最可能的。 如此, 再结合前面的推论, 圆静的胡人身份可以进一步得到确认。 他的身手非凡与不回归范阳也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答。
二、 血洗洛阳的阴谋
洛阳号为东都, 拥有政治、 经济和地理等诸多优势, 是唐朝除长安外第二大重要城市, 圆静正是因为要血洗洛阳才落网的。 血洗洛阳阴谋有其时代迫成的因素。 唐宪宗元和年间, 政局较稳, 国力增强, 加之唐宪宗本人欲有一番作为, 解决藩镇割据成其夙愿。 元和九年(814), 淮西镇帅吴少阳死, 其子吴元济欲继任留后, 遭到朝廷反对。 吴元济欲以武力胁迫唐廷首肯, 遂挑起唐朝历史上著名的淮西战役。 次年, 吴元济战场受挫, 求援于成德王承宗、 淄青李师道, 此二藩遂以调停姿态介入此事。 “王承宗、 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1] 7711, 遭到唐宪宗拒绝。 他们转而游说宰相武元衡, 由于“辞礼悖慢, 元衡叱之。 承宗因飞章诋元衡, 咎怨颇结”[2]4160-4161, 双方反结仇怨。 李师道所养客说曰:“上虽志讨蔡, 谋皆出宰相, 而武元衡得君, 愿为袁盎事, 后宰相必惧, 请罢兵, 是不用师, 蔡围解矣。 乃使人杀元衡, 伤裴度。”[4]5592因是, 武元衡死于贼人之手。 然他们终止淮西之战的目的并未得逞, 由于唐宪宗决心已下, 加之裴度坚决襄助, 战争继续进行。 为此, 二镇又陆续实施其他恐怖袭击, “承宗、 师道之盗, 所在窃发, 焚襄州佛寺, 斩建陵门戟, 烧献陵寝宫, 欲伏甲屠洛阳”[2]3881。 从这些恐怖事件不难看出, “屠洛阳”无疑是计划中最大也是蓄谋已久的一个, 目的是削弱朝廷力量和转移朝廷视线, 阻止其对淮西的进攻。 另外还应有圆静个人的泄愤。
“屠洛阳”谋划已久, 很可能因为淮西紧急才提前爆发, 由于打乱原先步骤加之被人告发才归于失败。 “初, 师道多买田于伊阙、 陆浑之间, 凡十所处, 欲以舍山棚而衣食之。 有訾嘉珍、 门察者, 潜部分之, 以属圆静, 以师道钱千万伪理嵩山之佛光寺, 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 集二县山棚人作乱。”[2]3539从引文看, 圆静是在李师道资助下才联络山棚的, 但细思之, 或并非如此。 对李师道而言, 用八十余岁的和尚帮其笼络山棚, 肯定有其可利用之处。 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圆静在嵩山出家的五十余年中, 一直在其僧人身份的掩盖下谋划袭击洛阳, 笼络山棚是他本来就在做的事情, 这与他在被捕后所言的“误我事”即更多是其个人之事正好对应。 但凭其一己之力, 没有财力支撑, 无疑难以实现。 所以主动找李师道做靠山, 才出现二人不谋而合、 相互利用的局面。 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有山棚鬻鹿于市, 贼遇而夺之, 山棚走而征其党, 或引官军共围之谷中, 尽获之”[2]3539。 圆静等本来欲凭借以血洗洛阳的“山棚”, 却成为他们的最终掘墓人。
在此有必要对圆静执此计划的个人原因加以探讨。 按常理而论, 80余岁的僧人作此血腥的阴谋, 为名利肯定不是理由, 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复仇。 安禄山起兵直指洛阳, 攻克之后登基称帝, 以洛阳为首都, 最后死于洛阳。 史思明称帝之后, 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洛阳, 攻克后不久到陕州督战而身死彼处。 牛致功以为“洛阳的得失标志着叛军的兴亡。 叛军的两起两落, 都是以洛阳的得失为分界线的”[6]159-167。 又, 幽州“俗谓禄山、 思明为‘二圣’, (张)弘靖惩始乱, 欲变其俗, 乃发(安、 史)墓毁棺, 众滋不悦”[4]4448。 “圣”即皇帝之意。 此事之发生距安、 史称帝已六七十年, 可见安、 史在幽州影响之大。[7]34圆静对安、 史二人之笃敬, 因把安、 史二人的死迷信地归咎在洛阳似乎在情理之中。 这应该是他谋划血洗洛阳的主要动机。
不过圆静为何不与自己出身渊源深厚的幽州、 魏博这样的安史旧地联系, 而与淄青这个与其本无瓜葛的藩镇联系, 可能是淄青拥有的便利条件使然。 “初, 师道置留邸于河南府, 兵谍杂以往来, 吏不敢辨。”利用这种优势, 李师道“潜以兵数十百人内其邸, 谋焚宫阙而肆杀掠”[2]3539。 此前, 武元衡被杀之后, 朝廷监视的是成德府邸, 而对参与刺杀的李师道府邸并未怀疑, “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1]7715。这也正反映出朝廷对淄青的信任, 在此遮掩之下, 行事固然方便。
还有两事与此次谋划密切相关。 其一是洛阳城兵屯空虚, 其二是洛阳留守吕元膺没有防卫兵。 洛阳乃唐朝东都, 屯兵及留守防卫兵皆不容忽视, 这当是圆静等计划实施的主要障碍。 史载直接参与此次袭击的仅百十来人, 后来审判时“党与死者凡数千人。 留守、 防御将二人及驿卒八人皆受其职名, 为之耳目”[1]7717。 这个数据可能不实, 即便实有其数, 当有很多无辜之人被牵涉其中。 因为此次事件的大部人马本该是山棚, 但由于意外, 山棚并没有参加, 反而站在朝廷一方立了功, 因此直接参与者不可能有数千之多。 另外也可能是史载出错或存夸大之弊。 例如《旧唐书·李师道传》载吕元膺包围叛乱者只“半日”, “数月”才将他们擒获, 而同书《吕元膺传》则说包围了“半月”, 《通鉴》则说“数日”就将他们擒获, 可见存在数字错讹在所难免。 因此, 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即便加上计划中的山棚, 若想血洗洛阳也并不能稳操胜券。 但巧合的是, 此时的洛阳竟是一座没有防卫的空城。 原因在于“因吴元济北犯汝、 郑, 郊几多警, 防御兵尽戍伊阙, 师道潜以兵数十百人内其邸, 谋焚宫阙而肆杀掠”[2]3539。 伊阙一直以来是洛阳南面东西道上的咽喉, 战国时即如此, 如“(秦昭襄王)十四年, 左更白起攻韩、 魏于伊阙”“西周君背秦, 与诸侯约从, 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 令秦毋得通阳城”[8]212-218。 可见秦可越此攻击六国, 六国同样也可以据此攻秦。 唐时的伊阙同样具有这一功能。 淮西进犯汝、 郑给洛阳带来了压力, 淮西在洛阳东南, 若其攻击洛阳, 伊阙最有可能首当其冲。 据上条《史记》引文,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伊阙在“洛州南十九里”, 二地距离相当近。 唐廷利用伊阙地险优势设防, 调洛阳防御兵虎踞之, 进可击退可守, 不失为明智之策, 但对洛阳城内萧墙之祸的防御却力有不济, 给圆静等留下可乘之机。 然而幸运的是, 吕元膺提前得知叛乱将发的消息, 连夜撤回这支驻戍伊阙的部队, 迅速控制了城内事态, 稳住了洛阳局势, 也即稳住了整个东南战场的局面。 然此时仍难确定, 吴元济进犯汝、 郑是否在圆静计划之中, 以便调虎离山。 然而看上面的引文, 正是在吴元济进犯汝、 郑, 造成洛阳郊畿紧张, 城内守兵被调出之后, 圆静等才决定出击。 如果这在他们计划之中, 可见此次预谋至少是三个藩镇联合参与的大计划。
如果说调洛阳防御兵至伊阙戍守事关布防大局, 虽有漏洞不可强责, 洛阳留守不赐“旗甲”则绝对是失误。 “旗甲”是指留守应得的礼仪等级和防卫部队。 “旧例, 留守赐旗甲, 与方镇同。 ……留守不赐旗甲, 自元膺始。”[2]4104-4105令人费解的是, 如此重要的都城, 又正值战事紧张之时, 正如朝臣所议, 宪宗不赐吕元膺“旗甲”的决策未免不合时宜。 这可能是淄青、 成德等藩镇此前对朝廷的游说和施压阻拦的结果。 从血洗洛阳的长久谋划来说, 洛阳留守的重兵宿卫, 无疑是他们计划中的障碍, 因而需想方设法解除之。 而宪宗此刻攻打淮西, 力量有所不济, 争取这些反对朝廷用兵的藩镇支持或中立可想而知, 因而不无听之任之的可能。 经历事变之后, “(吕)元膺因请募山河子弟以卫宫城, 从之”。宪宗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 而这保卫宫城的“山河子弟”, 其实就是留守应得的“旗甲”的变相。
三、 圆静与武元衡被刺案
武元衡被刺之后, 凶手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那么圆静与此有无牵涉? 若有, 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厘清这个问题, 确定刺客身份是关键。
关于刺客身份, 史书有三条关键史料:史料一, 武元衡被刺后, 王承宗属下张宴等人被抓获, “时王承宗邸中有镇卒张晏辈数人, 行止无状, 人多意之, 诏录付御史陈中师按之, 皆附致其罪, 如京中所说。 ……竟杀张晏辈”[2]3610-3611。史料二, 在处死张宴等后不久, 李师道等所派遣的訾嘉珍、 门察等欲血洗洛阳事件失败, “穷按之, 嘉珍、 门察皆称害武元衡者”[2]4105。 史料三, 武元衡被刺四年之后, 田弘正从淄青李师道处“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1]7769。 史料一所记凶手属成德王承宗系统, 后两条所记属于淄青李师道系统。
史料一所记张宴等是否为真凶一直存在争议, 当时的张弘靖就存疑, 并力谏宪宗慎重处理。 后来司马光就此事作考异曰:“然则元衡之死, 必师道所为也。 但以元衡叱尹少卿, 及承宗上表诋元衡, 故时人皆指承宗耳。”[1]7715主要根据就是上文所列史料二记载, 对于司马光的怀疑, 还能找到一些史料与之印证。 王承宗诋毁过武元衡, 因而在抓捕张宴等以后, 审判者“皆附致其罪, 如京中所说”。这就是说, 他们公开矛盾使“京中”人传言并相信, 武元衡就是被王承宗派人所杀, 所以审判者在审案时无疑受此传言影响而“附致其罪”。 朝廷在抓捕刺客过程中已经有了对犯人范围的预设, 即“其伟状异制、 燕赵之音者, 多执讯之”[2]4162。 “燕赵之音”显然更符合王承宗辖地人们的一般特征, 明显是针对王承宗而非李师道。 此外, 当时舆论压力也会造成此案存在屈打成招的可能。 宰相殒命多日, 凶手仍异常嚣张, “或传言曰:‘无搜贼, 贼穷必乱。 ’又投书于道曰:‘毋急我, 我先杀汝。 ’故吏卒不穷捕”[4]4834。 刺客们故意制造的谣传, 加重了恐慌的气氛, 以致吏卒出现怠工自保的现象。 这引起大臣的不满, 兵部侍郎许孟容就是其中突出者, 谓:“狂贼敢尔无状, 宁谓国无人乎?”[2]4102-4103“于是京城大索, 公卿家有复壁、 重橑者皆索之。”[1]7714张宴等就此落网。
据上, 张宴似为替罪羊。 但此与上列史料三所记主犯王士元供词显然冲突。 王士元与史料二所记主犯訾嘉珍同属淄青系统, 且同时参与刺武元衡行动, 他在行刑前说:“士元等(与张宴会合)后期, 闻恒人事成, 遂窃以为己功, 还报受赏耳。 今自度为罪均, 终不免死, 故承之。 ’上亦不欲复辨正, 悉杀之。”[1]7769临刑之际王士元没有撒谎的必要, 故属可信。 据此可知, 王士元与张宴本是同伙, 由于王士元“后期”, 张宴才单独行动。 当武元衡被刺之后, 王士元对李师道撒谎声称是淄青所为, 无外乎是“窃以为己功”。 由于本来是合伙行动, 加之行事隐秘及张宴等被处死, 李师道在大后方不知底里, 遂把王士元等记录在功劳簿里, 为后来追查留下了罪证。 据此, 张宴等人不是替罪羊, 就是真凶。 在《诛杀武元衡贼张晏等敕》中有“擒捕斯获兵刃具存, 自相证明遂得情实”[9]682的记录, 可谓人赃俱获。 张宴在被捕之后对刺杀事件也供认不讳, 这都可认作是张宴等就是刺客的重要佐证。 然而, 《册府元龟》却给了另一种解释, 即武元衡之死的刺客身份疑案再起是由田弘正一手策划的。 田弘正在朝廷平李师道后, 欲“提承宗至关以为己功”[10]290, 即想通过说服王承宗归顺朝廷, 以达到建立奇功的目的。 这一说法不无可能, 在此之前, 元和十二年(817)朝廷“诛吴元济, 承宗始惧, 求救于田弘正”[2]3881。可见二人私交早就建立。 通过这条记载, 我们不难想象, 田弘正在发现李师道留存的刺杀武元衡档案之后, 正好为其所用, 找到了调和朝廷与王承宗矛盾的契机。 有此证据, 朝廷不但不会讨伐王承宗, 反而会撤销对王承宗谋害武元衡的指责, 王承宗归顺之路也就顺畅了。 这使得原本已经澄清的案子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以致一千多年以来论者难得究竟。 直至《续通志》的编者还愤愤地说:“(武案)史家分记属款以传疑, 亦以见唐失政刑, 如此大事不加穷治, 颛顼了狱, 则其它之不足抉奸谋而申国宪者多矣。”[11]4881
史载“(王承宗)自是与李师道奸计百端, 以沮用兵。 ……欲伏甲屠洛阳”[2]3881, 又据上文所引王士元的证词, 反映出两个藩镇在制造混乱方面是通力合作的。 既然如此, 那么二镇之间是否有统一的组织来发号施令?如果有, 圆静又扮演何等角色?从二镇合作行刺武元衡看, 有统一组织实属可能。 而王士元可能是成德镇派驻淄青具体负责此事的协作者, 当然这也是基于对他名字的推测, 王士元和王承宗的父亲王士真, 从行辈来看, 二人不无本家兄弟的可能。 王士元在淄青镇负责行刺武元衡, 不排除是王承宗特意派遣, 以便协调二镇的合作。 如果确实如此, 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会是这样的情景:他们以成德、 淄青二镇为密谋策划的根基地, 以洛阳为进退自如的中纽和接应站点, 以长安二镇进奏院为前哨行刺据点, 三位一体, 构成一个组织严密、 体系完整的恐怖集团。 而洛阳中纽站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圆静, 他在行刺武元衡事件的策划中应该起很大作用。 因为曾经承认刺杀武元衡的訾嘉珍、 门察就受圆静的指使, 故刺杀一事不可能绕过圆静。 退一步说, 即便圆静主要负责山棚事宜, 没有直接领导刺杀武元衡之事, 他对此事也应相当了解。 对圆静来说, 袭击洛阳是其夙愿, 他肯定首先考虑刺杀武元衡的风险。 如果对血洗洛阳计划会构成破坏, 圆静当会阻止, 即便阻止不了成德镇的行刺者, 阻止訾嘉珍、 门察等是可能的。 从未阻止看, 他对刺杀武元衡应是采取支持的态度。 失败之后, 圆静对同伙表达出强烈的不满: “误我事, 不得使洛城流血!”訾嘉珍等行刺武元衡和袭击洛阳都未成功, 圆静只能怪托付非人而致宿计不逞了。
[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玄奘.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4]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牛致功.从安史之乱看洛阳的地位[C]∥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0]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 嵇璜,刘墉,等.续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湛贵成]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ang Dynasty
Monk Yuanjing and Luoyang Terrorist Attack
TAO Ji-shuang
(SchoolofHumanities,ShenzhenPolytechnic,Shenzhen518055,China;SchoolofMarxism,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an)
Monk Yuanjing was arrested for planning to assault LuoYang when he was more than 80 years old in the tenth year (AD815) of Emperor Xian Zong Yuanhe in the Tang Dynasty.In the study of his identity, we find that this is because he had deep hatred for the Tang Dynasty government during An-Shi Rebellion, which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more than 50 years ago. He and An Lushan are the same family that are Sogdians, and he was Shi Siming’s bodyguard. In the coup which Shi Chaoyi staged, his family was involved. His heart was broken, and then chose to become a monk, waiting for the opportunity of revenge under this identity. Through the study we also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governors, which was calm in the surface, but behind it there were many conflicts and crises.
Yuanjing; Wu Yuanheng; Luoyang; assassin; An-Shi Rebellion
2016-09-12
陶继双(1981—), 男, 安徽明光人,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K242
A
1009-4970(2017)06-00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