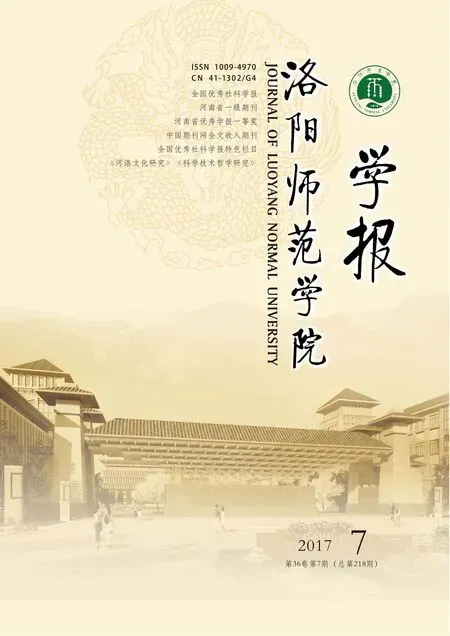观察渗透理论的心理学基础探析
袁建新, 向 莉
(1.华南农业大学 哲学系, 广东 广州 510642; 2.湘潭大学 哲学系, 湖南 湘潭 411201)
观察渗透理论的心理学基础探析
袁建新1, 向 莉2
(1.华南农业大学 哲学系, 广东 广州 510642; 2.湘潭大学 哲学系, 湖南 湘潭 411201)
心理学成就构成观察渗透理论论证的基石。 汉森、 库恩关于观察渗透理论的思想同样如此。 但两人所利用的格式塔心理学并不导致否认科学合理性的相对主义, 因为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哲学基础是表征实在论。 邱奇兰德的观察渗透理论及脑科学的最近研究表明, 观察确实渗透理论, 但这并不否认科学的合理性。 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不可靠。 关键词: 观察渗透理论; 心理学; 科学的合理性; 相对主义
自汉森以来, 观察渗透理论一直构成以库恩、 费耶阿本德及各种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相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 虽然这一理论的最初提出者汉森从来没有做出这一结论, 但汉森的结论被库恩、 费耶阿本德等各种社会建构论者作为其相对主义的基础, 并以此来反对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和认识的理性化。 对库恩等而言, 正是由于观察渗透着理论, 科学理论因而本质上是非理性的。[1]然而, 观察渗透理论并非完美无缺。 正如杰里·福德所指出的那样, 在论证这一理论的四种方式[日常语言论证(ordinary language arguments)、 意义整体论论证(arguments from meaning holism)、 本体论路径(ontology approaches)和心理学论证(psychological argument)]中, 本体论论证很少运用, 而源于心理学成就的论证是主要的论证方式。[2]我们特别强调的是, 意义整体论论证的方式并非令人信服, 因为提出这一理论的蒯因本人无疑是反对观察渗透理论的。 蒯因从其自然主义认识论出发, 认为存在外部物理世界作用的“神经纳入”(neural intake)过程, 这一过程不是理论渗透的, 因此存在纯粹的观察。[3]可见, 支持观察渗透理论的四种论证方法中至少两种不是令人满意的。 对此, 本文不可能做出深入探讨, 我们只想对这一理论的心理学基础作初步探讨, 并指出库恩及各种社会建构主义者从心理学的成就出发, 来得出科学事业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相对主义观是站不住脚的。 究其原因在于, 尽管心理学的成就一直是观察渗透理论的主要经验证据——特别是在库恩、 汉森等早期信奉者那里尤其如此, 但心理学的成就并不支持观察渗透理论所导致的相对主义结论, 由此, 即使承认观察渗透理论具有合理性, 仍然不能否认科学的客观实在性和合理性。 我们将从两部分论证这一结论。 第一部分表明, 汉森、 库恩等的观察渗透理论并不能从逻辑上导致否认科学的合理性的相对主义结论, 因为这一理论的心理学基础(格式塔心理学)是以承认科学的客观性为前提的,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格式塔心理学是以表征实在论为其哲学基础的; 第二部分表明, 心理学的最新成就虽然证明观察渗透理论的某种合理性, 但并不导致否认观察的客观性和科学的合理性的相对主义结论。 先看第一部分。
一、 观察渗透理论的心理学基础
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全盛期, 卡尔纳普等认为, 在观察词与理论词之间可做出一种严格的区分。 汉森、 费耶阿本德等质疑这种区分。 他们认为, 所有观察都是依赖于理论的,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觉要么为知觉的、 言语的及文化的差异所形塑, 要么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做出的任何直接区分都是不成功的。 也就是说, 依照汉森与费耶阿本德等的观点, 没有完全不受理论影响的、 独立于理论体系的纯粹观察存在, 即观察是负载理论的。 对库恩、 费耶阿本德等来说, 对科学理论的选择的相对主义就是可能的。 因为, 如果我们考察对相互竞争的理论的选择, 那么, 这种选择不是由观察提供的证据来判决的, 而必须到观察之外去寻找理论选择的根基, 因为科学家不可能获得不依赖理论的中立的观察证据。 即对那些信奉观察渗透理论, 信奉科学理论的选择的相对主义者来说, 科学证实的逻辑不由科学观察决定, 而是由观察之外的其他因素(例如科学家的个性、 社会文化因素等)决定, 由此, 科学事业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事业。 然而, 通过对汉森、 库恩等论证观察渗透理论的心理学基础的分析表明, 观察渗透理论所诉求的心理学证据并不支持“一切科学理论都是理论负载的”这一结论, 因为提出心理学证据(这些证据被汉森、 库恩等用来论证观察渗透理论)的格式塔心理学家明确支持表征实在论, 由此承认独立于理论的、 表征外部实在世界特征的、 不受理论影响的观察的存在。 下面以汉森和库恩的思想来说明这一点。
汉森在《观察》一文中认为, 观察报告不可能移除所有的理论影响, 观察报告不可避免地依赖理论信念。 “看”要求不仅有视知觉, 而且有理论的理解。 对汉森来说, “看”有比仅仅碰到眼球的东西更多的东西, “看”是一种经验。 视网膜的反应仅只是一种物理状态——一种光化学兴奋(photochemical excitation)。 心理学家总是能鉴赏到经验状态和物理状态之间的区别。 人们并不是用他们的眼在看, 照相机和眼球是盲的。 试图将一些被视为“看到的东西”定域在(locate)有机体的视野(sight)(或在眼睛的神经网内)之内, 是不被经验所接受的。 汉森认为, 开普勒和第谷是否确实(或没有)看到同一事物, 不能通过参照他们的视网膜的、 光学神经的或视觉皮层的物理状态来确定, “看”有比碰到眼球更多的东西。[4]汉森认为, 开普勒和第谷虽然有同样的感觉经验材料, 但看到的东西却不一致, 这种分歧不在于两人的基本的视觉材料, 而在于两人运用理论所理解到的感觉材料的不同, 因此, 在物理状态和视觉经验之间有一种区别。 为了证明《观察》A部分的这一结论, 在该文B部分, 汉森利用八幅不同图像来证明上述观点, 并在该文C部分得出其观察渗透理论的结论, 而这八幅图中的前七幅都是引用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成就。 汉森运用这七幅心理学的图像试图表明, 看同样的事物, 不同的人看到的却不相同。[4]汉森以为, “为什么一种视觉方式被不同人看作是不同的”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不过, 那种被我们看作不同检验和观察的概念同样重要:“这里或许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那样, 心理学是逻辑的符号。”[4]“那被开普勒和第谷看作不同事物的东西, 实际上是同样的事物。 对这些不同事物的看, 依赖于他们的知识、 经验和理论……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要找出观察材料、 证据和观察的差别, 那么, 或许需要比指向观察对象更多的东西。 这或许要求全面地估价某个主体。”[4]汉森由此从心理学的证据跳到观察渗透理论这一逻辑结论。 因此, 在该文C部分一开始, 汉森就提出其观察渗透理论:“因而, 有一种感觉, 其中, ‘看’是负载理论的(theory-laden)。 观察到的某物X是被先前的某知识所形塑(shape)的, 另一影响观察的东西在依赖语言或表达我们所知的记号(notation)之内, 如果没有这些, 就很少有被我们认作知识的东西。”[4]接下来, 汉森主要分析了负载理论的观察是如何在“看作为”(seeing as)及“看作是”(seeing that)之间实现的, 对此, 汉森同样借助于该文B部分的心理学图像来说明。[4]
综观汉森的《观察》一文, 来自心理学的证据构成其提出“观察负载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基础。 与此类似,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同样借鉴心理学的成就来为观察渗透理论辩护, 不过, 与汉森不同, 库恩得出了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相对主义结论。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指出, 因受到一位同事的影响, 促使他读了一些知觉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论文。[5]格式塔心理学对库恩的影响在该书第七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第七章中, 库恩认为, 科学革命是科学家的世界的改变, 科学家的世界的转变的基本原型, 可用大家熟知的视觉格式塔转换来启发性地证明。[5]
库恩以为, 求助于“直接经验”的中性的观察语言, 来证明“处于不同范式的科学家观察到的是同样的事物, 形成的是同样的感觉”是行不通的, 因为, 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性的感觉经验。 库恩指出, 尽管自笛卡儿时代以来, 哲学家就试图依赖心灵和知觉的理论, 来设计出一种纯粹中性的观察语言, 但这种企图面临心理学的无数实验的挑战, 因为心理学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 任何试图构建一种纯粹的、 中性的观察语言的努力都是不成功的。 库恩甚至认为, 现有的哲学研究甚至不能给我们以一点暗示, 以表明中立而客观的观察语言是什么样子。[5]由此, 库恩做出结论说, 不存在一种仅限于报道一个事先完全知道的世界的语言, 这种语言能够中立而客观地报道“直接所予的感觉世界”。[5]库恩由此认为, 科学观察就如孩子学叫妈妈一样, 其观察受到期待、 反应和信念的影响, 科学家的范式决定了其观察到的是什么, 不管是在常规科学还是在科学革命时期, 都是如此。[5]因为科学家的观察渗透着范式的特征。
可见, 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与汉森的一样, 也是以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作为其理论基础。 不过, 与汉森不同的是, 库恩在观察渗透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科学进化的相对主义结论, 并且认为, 不同的科学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 由此科学的进化本质上是非理性的。 然而, 汉森、 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赖以建立的心理学基础(格式塔心理学)并不支持他们的相对主义结论, 相反, 柯勒(Koher)等格式塔心理学家明确承认表征实在论, 由此承认存在独立于一切理论的中性的客观观察。
柯勒等格式心理学家借助数学集合论的同构概念, 并且继承了其先辈海林(Hering)和穆勒(Mueller)等心理学家的同构概念, 提出了心物同构论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Psychophysical Isomorphism)。 这一原理的同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心理事件与现象经验的同构, 二是被给予的现象关系与它们的心理相关性的确定关系的特征之间的同构。[6]柯勒等以为, 心物同构原理具有先验的合理性, 因为, 在逻辑上存在心理领域与物理领域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同构关系。[6]柯勒并且认为, 心物同构论是以表征实在论的认识论的二元论为基础的。 因此, 尽管知觉与物理对象不同, 然而, 由物理对象的刺激所形成的知觉仍然是客观的经验, 知觉的格式塔转换并不能否定这种客观性。[6]
当然, 库恩本人意识到了“由心理学的格式塔转换到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之间的逻辑关联的合法性难题。 而且, 库恩也看到了心理学的格式塔转换与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之间的五种区别。[6]尽管如此, 库恩仍然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由前者到后者的逻辑过渡的必然性难题。 正如西奥多罗所论证的那样, 库恩只是利用第五区别来论证任何科学家的观察都只是把外部物理刺激C“看作为”, 而这种“看作为”是由理论的范式所决定的, 因而不可能有观察的客观性。 然而, 库恩从第五区别去论证“单纯的看”(simple see)与“看作为”之间的区别是错误的。 因此, 由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并不能逻辑上过渡到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 更不能做出否认科学的合理性的相对主义结论。[7]事实上, 尽管近年来随着心理学的成就和脑科学的发展, 观察渗透理论显得具有某种合理性, 但这并不能导致“一切观察都是负载理论的”这一结论, 更不能导致否认科学的合理性的相对主义结论。 邱奇兰德的观察渗透理论及脑科学的最新成就证明了这一点。
二、 观察渗透理论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
邱奇兰德或许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著名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辩护者。 不过, 与汉森、 库恩等主要从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来论证这一理论不同, 邱氏更多地将心理学的成就与日常语言及意义整体论结合起来论证这一理论。 但是, 心理学的成就仍然是邱氏的主要论据之一, 虽然他更多地运用了以乔治亚、 布鲁纳、 卢克等为代表的“新视观”(new look)知觉心理学成就。[8]然而, 与库恩不同的是, 邱氏的观察渗透理论所导致的不是反实在论的和相对主义的, 而是科学实在论的。[9]实际上, 近年来的脑科学和心理学的成就确实表明某些观察确实渗透了理论。 这种渗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人类的知觉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过程综合作用的产物, 不存在单一的知觉过程。 埃尔·米勒(Earl K. Miller)指出, 我们的知觉和思维是自上而下的 (top-down )及自下而上的(bottom-up)信号互相作用的结果。 自下而上的信号源于感官接收到的物理信息, 而自上而下的信号则是对这些感觉信息的解释和理解。 自上而下的作用将从经验而来的信息转入综合, 并使之成为可储藏的知识, 这些知识赋予感觉信息的输入以结构和意义, 从而使它们在认知中处于中心地位。 蒂姆塔(Tomita)等的实验提供了自上而下的自发性作用的直接证据。 研究表明,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号在知觉中的作用是这样的:例如, 自下而上的信号分析告诉我们以位置、 颜色和图中的位置轮廓, 而自上而下的经验依存过程提供了认知的一致性及意义。 不过, 自上而下的自发性信号不只限于知觉中, 它们在我们转换注意以决定事情如何, 我们如何行为方面都发生作用。 因此, 它们使我们的复杂行为得以可能。 在正常的脑中, 自上而下的自发性作用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复杂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 在动物的意识活动中, 非常难以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过程分离开来。 蒂姆塔等的实验将猴子的自下而上的感觉信息从较低的颞颥叶皮层 (temporal cortex) ——这一区域涉及脑中的视觉记忆——移走, 剩下的只是从额叶前部皮层的自上而下的讯号。 他们研究了当猴子回忆贮藏在初极颞颥皮层的视觉图时自上而下自发性讯号的功能。 这一研究表明, 在没有自上而下的感觉信息输入时, 低级的初级颞颥神经元(inferior temporal neurons)被自上而下的自发性讯号所激活。 这种传输语义概念的自发性信息过程是被视觉刺激强使联系起来的, 猴子的行为在失去自上而下的自发性讯号后也严重地减少了。[10]可见, 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这一成就确实证明了某些观察确实渗透理论, 但是这并不导致相对主义结论。[11]观察确实渗透了理论的第二方面同样来自心理学和脑科学的刺激。 这些成就表明, 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不但渗透在人类的视知觉过程中, 而且在其他的观察过程和科学认知过程中同样存在, 例如, 在人的注意、 对感觉资料的评价和解释、 记忆、 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等过程中。 不过, 这一点并不导致相对主义结论, 因为当自下而上的证据强大时, 这些来自外部的物理刺激就不容易被自上而下的信息压倒(Overridden)而使之无效。[24]
由此可见, 即使我们承认某些观察确实渗透理论, 但这并不表明, 一切观察都是理论渗透的, 更不导致否认科学观察的客观性的结论, 并不导致否认科学合理性的相对主义结论。 因为, 作为观察渗透理论的重要基础的心理学成就, 虽然一方面可以作为观察渗透理论的经验证据; 但是, 另一方面, 心理学提供的这些实验并不为相对主义提供证据, 库恩等所利用的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认识论明显以表征实在论为基础, 而直到最近的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成就尽管表明观察确实渗透理论, 但这并不导致否认观察的客观性的相对主义结论, 科学的理性基础并不因为接受观察渗透理论而动摇。 因此, 人们完全可以接受库恩等的观察渗透理论, 但同时却可以正当地否认其“科学革命是科学家范式转换的结果”的相对主义结论。
[1] ESTANY A. The thesis of theory-laden observation in the light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J].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1(68): 203-205.
[2] FODOR J. Observation Reconsidered [J].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4(51): 23-43.
[3] QUINE W V. In praise of observation sentences [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3, 90(3): 107-116.
[4] HANSON N R. Observation [M]∥ROTHBART D. 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78-79, 80-88,87, 88.
[5]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iii, 110,124-126,126.
[6] MADDEN E H. A Logical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Isomorphism” [J].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57,7(31): 181-185,185-188,188-191,110-114.
[7] THEODORA P. Of the Same in the Different: What is Wrong with Kuhn’s Using of “Seeing” and “Seeing as” [J].Journal of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4(35): 175-200.
[8] CHURCHLAND P M. Perceptual Plasticity and Theoretical Neutrality: A Reply to Jerry Fodor[J].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8(55): 169-181.
[9] CHURCHLAND P M.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Observables: in Praise of the Super empirical Virtues[M]∥ROTHBART D. 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413-422.
[10] MILLER E. Straight from the top, TOMITA. H. Top-down signal from prefrontal cortex in executive control of memory retrieval [J]. Nature, 1999(401): 650-651,699-701.
[11] [24] BREWER W F, LAMBERT B L. 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and the Theory-Ladenness of the Rest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J].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2001: 176-186,184-185.
[责任编辑 尚东涛]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YUAN Jian-xin1, XIANG Li2
(1.PhilosophyDepart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42,China; 2.PhilosophyDepartment,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201,China)
The achievements of psychology are crucial experiential evidences of the 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Hanson’s and Kuhn’s theory on 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is also such. However, Gestalt psychology which Hanson and Kuhn utilize to develop the 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doesn’t lead to scientific relativism that denies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because the basis of Gestalt psychologist is representative realism. Churchland’s 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and the newly investigations of brain science indicates that observation does theory-laden, however, this doesn’t deny both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and the objectivity of observation. So the relativism of Kuhn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t are not reliable.
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relativism;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observation
2017-02-12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ZDB016)
袁建新(1968—), 男, 湖南宁乡人, 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康德哲学、 科学哲学; 向莉(1986—), 女, 湖南湘潭人, 硕士研究生。
N031
A
1009-4970(2017)07-0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