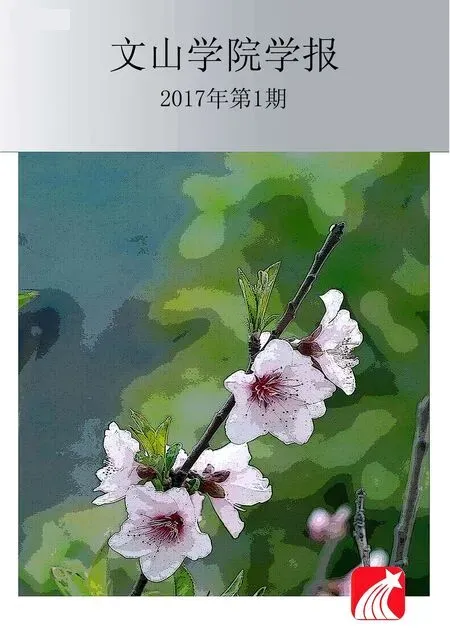楚图南在云南文化抗战中的革命斗争活动研究
冉庚文
(文山市党史研究室,云南 文山 663099)
楚图南在云南文化抗战中的革命斗争活动研究
冉庚文
(文山市党史研究室,云南 文山 663099)
1937年,在云南大学附中任校长的杨春洲特别邀请楚图南回云南任教。是年底,楚图南从战乱的上海举家退往抗战大后方的昆明,以一名云南本土学者的身份,参与和组织了云南的文化抗战。抗战期间,楚图南在青年学生、人民大众、省内外文化名流当中架起了一座座桥梁,为团结和发展云南文化抗战力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化抗战 ;云南;楚图南
一、关注学生群体,发展壮大云南文化抗战中的青年力量
1938年2月起,楚图南到云南大学附中任国文和历史教员,并在女一中、成德中学兼课。在课内和课外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办壁报、成立进步社团;支持和指导青年学生开展抗日进步活动,进行抗日宣传。使得云南大学附中、昆华师范及云南大学学生成为昆明抗日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1]279
这一段时间,楚图南关注的群体主要是云南的广大中学生。抗战爆发之前,云南社会相对平稳,抗战爆发后,特别是京、津、沪等地相继失陷后,大批难民和文化人如潮水般的涌进云南,国内一些重要的书店也搬到云南,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机关相继搬到云南,自然就使云南的社会状况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复杂起来。楚图南认为,在云南这片土地上一定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新的事态。“对于这些新问题,新事态的反应,来得最快、作用最大、影响最深的,当然是中等学校的学生。因为小学校的学生还幼稚,大学生的发展大多是有了一定的定型,加之在云南,大学生的数量还比较少;民众方面,当然由于知识的落后,和生活的牵掣,自然是感受迟滞,或甚至于不起作用。”[2]309楚图南强调,在云南开展文化抗战,首先要依靠广大的中学生这支强大的生力军。楚图南认为,“惟有用这种方法才可以使本来是健全的思想和行动,不会走入歧途,可以使本来是幼稚的,甚至于是错误的思想和行动,可以得到矫正,且强壮起来。”[2]311在抗战最紧张的时代,广大青年学生不可能有安稳的学习环境,面临着每天都要“疏散”的恐慌和窘境。楚图南撰文鼓励青年学生要把“疏散”变成一种积极的学习和积极的抗战行动。“以自己作为一个战时青年,艰苦卓越,苦干又苦学的榜样,来教育了民众,指导了民众,发动了民众,这是我们疏散的第一个意义和第一个责任。”[2]325“我们希望我们的疏散,乃是将中华民族的新的细胞,新的血液,最有力而健全的分子,注射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散布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努力作所能作的研究工作,或文化工作,这实在和前线的流血抗战,有着同一的价值,而且也是同一的重要。这是我们疏散的第二个意义,和第二个责任。”[2]326“敌人的飞机盘旋在我们的头上,所谓救亡如救火,我们还推诿什么,还等待什么呢?——疏散并不是使我们逃避或放弃了我们的工作和活动。乃是相反的,更开展了我们所能做,所应做的各部门,各方面的救亡工作和救亡活动。这便是我们疏散的第三个意义和第三个责任。”[2]327
课堂上,楚图南总是围绕文化抗战,为广大青年寻找战斗的动力和标杆。唤醒埋头读书的学生从数理化里钻了出来,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危机时,做为一个热血青年应该奋起救国。通过教学,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兴亡。[1]280
“山国的儿女们,我们是创造者的后代,我们是垦荒者的子孙……起!起!起!……美与幸福的社会,得由我们一手来完成。”[1]280这是楚图南在云大附中撰写的一首诗歌《山国的儿女们》,云大附中将其作为校歌。
在楚图南及其他文化大家、思想大家的引导下,很多青年踏上了革命的征程。抗战结束后,受中共云南省委的派遣到文山从事恢复党组织工作的岳世华,就是楚图南在云大附中所教的高中学生。岳世华在生前,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楚图南家里拜望自己的恩师。“楚图南对我影响很大,我也经常去楚图南家。”[3]这是91岁高龄安朗的一次讲述。在云大读书时,费孝通任系主任,上历史课,楚图南上大学语文课。在楚图南的引导下,安朗加入民青组织并随军进入越南参加日军的受降仪式,随后在越南任教,做华侨工作。1949年,安朗从越南回国到文山开展建立县乡民主政权斗争活动并任中共文山县委第一任书记和文山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
二、高举文化旗帜,发展壮大云南文化抗战中的群众力量
文化抗战,关乎一个国家的前途和一个民族的命运。1939年1月15日、2月1日,《新动向》连续分两期刊载楚图南《抗战与中国文化检讨》文章。全文包括5个部分。一是《几个历史上的事例》;二是《中国文化的本质》;三是《中国文化所给予中国民族的命运》;四是《中国文化的动摇》;五是《抗战前途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在《几个历史上的事例》中,楚图南以巴比伦的兴衰为例,讲述了文化的重要性。说巴比伦创建了中部亚细亚洲的第一大国,是因为巴比伦民族凭依着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让自己兴旺起来。后来,由于巴比伦民族崇拜荒淫和奢侈的低俗文化,巴比伦民族终究消失了。另外一个例子是波斯人和希腊人的战争。波斯人的文化,是以大欺小,倚强凌弱,强迫几百万奴隶远征攻打弱小的希腊。波斯人的文化是侵略文化、暴君文化、强迫文化;希腊人的文化是反侵略文化、是正义的文化、是积极的文化、主动的文化。所以,正义的弱小的希腊人连续几次打败了非正义的强大的波斯人,挽救了希腊民族的危亡,保全了欧洲文化。楚图南在该文中还列举了罗马帝国、日耳曼、印度、缅甸、安南、日本等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兴起和衰落的故事,反复强调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极其重要。说“所谓文化,乃是全民族适应环境,维持生存的物质的精神的创造的总和,则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其自身的文化,乃是一个支配的要素,是一个决定的要素,当然不是过言的了。”[2]334
在《中国文化的本质》部分,楚图南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这种文化被后来软弱、虚伪的文人利用了,软弱性、虚伪性、欺骗性、逃跑主义、卖国行为,似乎就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令人可怕的。抗战爆发了,“前方的当汉奸,顺民,在后方的则逃避,流亡,散布流言,说风凉话……”[2]339
在《中国文化所给予中国民族的命运》中,楚图南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文化的软弱性、虚伪性,一些文化人“看不见国家,看不见民族,看不见大众,不惹事,不出头,不冒险,一切不负责任……”[2]341楚图南说,中国文化的奴性特征,导致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凭借求生的本能举起叛旗,扫荡敌人,建立新国,不久,文化的奴性一出来,弊害复生,人民又没有了生气,外力一来,又要粉碎瓦解,当主子的准备着让位,当奴才的准备着投降。楚图南呼吁国人要对自己的文化尽快反省、尽快改造,指出:“中国文化若没有深切的反省、没有彻底的改造,则中国的社会机构,不会健全,中国的民力也不会发扬,在国际竞争的舞台,在真实的力与力的竞赛的历史剧中,中国是不容易生存的,也是不容易占到一个确定的地位的。”[2]343
在《中国文化的动摇》中,楚图南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认为这“动摇”,其实是一种“改变”“裂变”。“这结果,便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动摇,中国人生活态度的根本转变,中国人以应战回答了挑战,中国在抗拒暴日的神圣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站立起来了。这次的战争,当然必须以全民族的长期艰巨的牺牲和英勇的热血,来博取最后的胜利。也是来彻底的清算了中国过去的文化,和改造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的新生的命运。”[2]347
楚图南先后发表了《文艺工作者怎样充实和武装自己》《学术辩难应有的态度》《云南教育界应当怎样应付当前的事态》《抗战建国过程中云南的新使命》《怎样开展今后的文艺工作》《今后的文化运动》《防护精神或道德上的国土》《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等多篇文章,针对云南的实际,陈述了自己的抗战观点。
1938年5月8日、15日,《云南日报》分两期刊载楚图南《文艺工作者怎样充实和武装自己》的文章。楚图南认为,艺术家首先必须明白自己是一个人,是有血有肉有理性的人,因为“艺术并不是一种快乐的职业,乃是一种非常猛烈的斗争”[2]297。
其次,艺术家要认识社会、关注社会。“来至诚地、深入地注意社会,认识社会,来充实和武装自己,以此创作和产生了真实的伟大的文艺。”[2]299
第三,艺术家要具备精当、通俗、有效而又有力的创作技术。“我们的文学,并不需要装鬼吓人,我们只需要有效又有力的,准确而锐利的武具,来武装了我们自己!”[2]300,301
1943年10月,云南《动向》创刊号发表楚图南《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一文。楚图南指出,希望外来文人少一点对云南贫穷与落后的批评和指责,要多一些包容;同时希望云南人要欢迎这个时代的到来。对于外来文化在云南的选种下苗,要持谨慎的态度;禁止片面否定和批判外来文化,要见其森林之森,见其树木之大。因为当下的云南社会的总趋势是好的,外来文化对于云南社会的影响是一次变革。“比之于晋人南迁,罗马人西渡,还有着更多的积极性呢!”[4]627,629
抗战期间,楚图南积极参与和组建各种抗战文艺团体。1938年5月1日,“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易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楚图南被选为理事,与张克诚、冯素陶、徐嘉瑞等负责领导工作,自此担任该会历届理事、常务理事,参与主持领导工作,成为核心人物之一。他参与编辑出版该会刊物《文化岗位》;开展文艺普及工作、举办文艺竞赛、开办暑假文艺讲习班,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研究抗战文艺理论及技术问题;举办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如纪念鲁迅、庆祝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五四”文艺会、诗人节等等。从上海或海外回来的途经昆明到重庆的文化知名人士如茅盾、巴金、陶行知、王礼锡等,楚图南均以文协名义请他们座谈、讲演,以扩大昆明文化界的视野,活跃文化界的抗日民主运动。
1938年12月28日,茅盾到达昆明,发表了以《统一战线与基本工作》为题的讲演。茅盾从楚图南所谈昆明文化界情况中,了解到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很少参加当地文化组织的活动,与文协很少联系,便向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吴晗等提出外来人与本地文化界沟通思想,加强团结的问题,让他们找楚图南交换意见,把云南文化界的力量统一起来。大家接受了茅盾的意见,安排了些外来人进入文协云南分会任职,在全国有影响的沈从文、顾颉刚、朱自清、施蛰存、徐炳昶、谢冰心、吴晗等均在其中。团结的面更加广泛,力量更加壮大,影响深远。[1]284
1944年,文协开展了援助贫病作家的募捐活动,楚图南捐款一千元。在这之前发表文章《保障作家生活与发扬民主精神》,为贫病作家呼吁社会援助;捐赠了自己的《刁斗集》,在扉页上题写了鲁迅的“血沃中华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的诗句,以鼓励青年学生。
三、团结民主斗士,发展壮大云南文化抗战中的领导力量
1942年3月,楚图南等人在昆明秘密成立了“九老会”。虽称“九老”,这些人实际都不老,也不只九人。他们不定期地举行聚会和茶会,研判形势,共商对策。后来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各方面做工作,成为推动云南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之一,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进步运动影响日益扩大。[1]288
1943年初,中共南方局代表华岗到了昆明,首先找到楚图南,并带来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件。为了与各方面学者、文化教育界人士交换和探讨对国内时局的看法,引导各方人士团结起来,在大学教授中组织了“西南文化研究会”。这个组织的活动地点在唐继尧的别墅,每两周一次。他们轮流作学术报告,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本地人与外来人的隔阂,“洋”教授与“土”教授间的歧见,学者教授对文化人、对政治活动者的偏见等逐渐得到消除。这个组织,成为党在云南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云南文化抗战的民主斗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1943年4月,楚图南由周新民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5月,民盟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成立。翌年10月,民盟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楚图南当选为委员。1945年9月,楚图南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同年12月23日,在民盟云南省支部第一次盟员大会上被选为主任委员,闻一多为宣传部长兼青年委员会主任。为了民盟组织的发展,云南省支部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出发,主张打破“政团”同盟,吸收爱国知识分子参加。1944年9月,被全国代表大会所接受,取消了“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是年,民盟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建立青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发展了一批成员。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青年中也建立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两者发生交叉,有人主张由民盟领导,楚图南认为民青应由共产党组织领导,与民盟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他的意见得到闻一多等人的支持。
1944年7月7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三校学生自治会和西南联大壁报协会联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七七”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楚图南、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在会上提出国难当头,文人应该论政,是年,日寇发动湘桂战役,湖南、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失守,加之滇西的龙陵、腾冲仍在日军占领下,尚未光复,于是由民盟云南支部与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发动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和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云南文协等进步组织,于10月10日在昆华女中操场举行五千余人参加的“保卫大西南大会”,楚图南、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等出席。楚图南在会上讲演的题目为《言论自由与身体自由》,提出反对独裁,只有实行政治民主,才能使国家民族有所进步;保障人民的人身、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才能动员全民的力量,共赴国难。12月25日,民盟云南支部联合十余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及进步团体,举办“云南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会上喊出“拥护龙主席,发扬护国精神,保卫大西南,保卫云南!”“打倒独裁,实行民主政治!”等口号,六千余人于会前举行了游行,楚图南等走在队伍的前面。
四、结语
编著《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的云南大学教授蒙树宏说:“楚图南演讲和发表的作品,颇有真知灼见,是云南抗战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战略家。”
“楚图南是抗战时期云南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中的中坚人物。在那个时代,楚图南作为云南文化界的一名旗手,高举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旗,大声呼唤着云南各族人民向往的明天。”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王元辅在其纪念文章《楚图南在云南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贡献》中,这样评述着。
回忆起抗战的人生经历时,楚图南的心绪是极为复杂的——“我当时是凭着我的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对当时当地发生的情况,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工作。有时也由从重庆来到云南的南方局的同志传达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的指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活动是受到党的指引和领导的。”[4]340“在昆明,在抗战期间的多方面活动和经历不是这一篇短文所能写完的。”[2]825
[1] 麻星甫.一生心事问梅花[M].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
[2] 楚图南 .楚图南集(第二卷)[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
[3] 冉庚文. 文山市革命老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496.
[4] 楚图南. 楚图南文选[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娄自昌)
A Study on Chu Tuna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Cultural War Against Japanese
RAN Gengwen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Wenshan City, Wenshan Yunnan 663099, China)
Yang Chunzhou, headmaster of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 invited Chu Tunan to teach in Yunnan in 1937.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Mr. Chu and his family withdrew to Kunming, the rear are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from Shanghai and he took part in and organized cultural war against Japanese as a local scholar of Yunnan. He served as bridges among common people, literary celebrities in province and out of province and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uniting and developing Yunnan cultural war power against Japanese.
cultural war against Japanese; Yunnan; Chu Tunan
G12
A
1674 - 9200(2017)01 - 0047 - 04
2016 - 10 - 16
冉庚文,男,壮族,云南广南人,文山市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