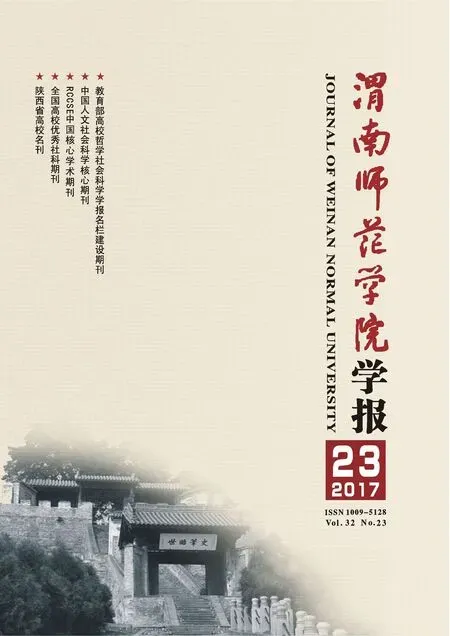论村上春树《开往中国的慢船》中的“中国”意象
李 妮 娜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
论村上春树《开往中国的慢船》中的“中国”意象
李 妮 娜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开往中国的慢船》是村上春树初期创作的重要短篇小说,其中明显涉及中国因素。通过对小说文本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小说主人公“我”对“中国”及“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的歧视与偏见,体现了作者作为日本人朴素的愧疚之情,进而深刻揭示了村上文学中现代人对自身生存困境的痛切反思。
村上春树;中国;《开往中国的慢船》;意象
《开往中国的慢船》是村上春树初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文艺杂志《海》1980年4月上。发表后,在日本学界受到了广泛关注。田中实称赞道:“读完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该作品明确地表现了村上春树作品群中最根本的主张——‘我’和世界之关系及其‘我’的世界观。”[1]日本女作家小川洋子看过这部小说后称道:“常说处女作包含了一切,的确,这部短篇集描写了迄今为止村上文学世界的所有要素——《寻羊冒险记》之‘物语’膨胀力,《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对于自我解离的恐惧,《电视人》之硬质,《奇鸟行状录》之徒劳感,《斯普特尼克恋人》之空虚的永恒性……无所不有。”[2]3-4村上自己也很看重这篇短篇,他说:“《开往中国的慢船》和《贫穷阿姨的故事》是我创作初期完成的两篇短篇。我觉得在这两篇短篇中,蕴含着某种最重要的、感觉良好的东西。同时,小说中洋溢着我当时年轻(刚过四十)而充满活力的要素。”[3]3并补充道:“做完这些修补工作之后我想:在该短篇集中已将我本人,或者说是村上春树这个作家的大体形象基本得以表现。”[4]4可见,解析这篇短篇对村上文学的理解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将从记忆与忘却的悖论、反时代的主题、场所的哲学意蕴来探讨村上心目中的“中国”意象。
一、记忆与忘却的悖论
《开往中国的慢船》是由三个在时间上有着承续关系但各自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小说共5章,1章和5章都是现在时间,1章和5章中插入2、3、4章,讲述了3个中国人的故事。小说开头以“遇到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这一“考古学式的疑问”展开。而这个疑问在开头短短四行中就重复了2次。可见第一次遇到中国人的确切时间对“我”是何等重要。“第一次遇到中国人”与记忆相关,而“我的记忆没有日期,我的记忆力很不确切”,“或前置或颠倒,或事实与想象错位”。也许是1959年抑或是1960年。总之对于“1959年和1960年”——这两个衣着褴褛而丑陋的双胞胎兄弟即使“我”坐着时光飞船倒回到那个时代也很难将他们区分开。于是“我”只记得——“那年正是约翰生和巴达生争夺重量级拳击冠军的一年”,“到图书馆去翻翻就行了”。“我”不得不骑车到了区立图书馆,想通过查阅旧的新闻年鉴体育版来确认我遇到中国人的具体年份。“我”一心想像考古学家那样把这段“记忆”挖掘出来,而“我的记忆,就是像这样非常含糊不清。有时前后颠倒,有时事实与想象交错”。
由此,一种悖论心理跃然而出。因为不确切的“记忆”暗示着“记忆的忘却”,从而凸显了一种记忆——忘却的悖论心理。
但正是这一悖论的深层心理是“我”作为日本人的真实想法:中日两国关系的和谐与否是每一个日本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应对,因为必然要与过去的历史态度密切关联。因为“忘却”是想从某段历史“记忆”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因此“记忆”也就转为了“忘却”的记忆。对于村上这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80年代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就亚洲与日本的关系之提法形形色色,表面上对亚洲蔑视的反省思潮传播开来,然而那只是表面现象。在《开往中国的慢船》中,描绘了忘却的政治不只是国家层面的而且也是浸透于‘我’这样的个人心中的事实”[5]461-462。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中国”是一个难以言状的词语,如鲠在喉。想要忘却,却始终忘不掉。正如同哈佛大学杰·鲁宾所说:“他对中国和中国人一直以来难以释怀的关注可以被视为两个民族之间难以释怀的历史记忆的一种表现。”[6]69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其实凸显了“我”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人怀有的一种罪责感。
接下来小说叙述了“我”在小学、大学和成年时邂逅三个中国人的故事。“我”在小学时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小学的监考老师。而“我”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是因为那以前我一次也没有遇到过中国人。那么后来打工时遇到的漂亮中国女孩和在咖啡馆遇到的高中时的同学,“我”仍然没能分辨出,这又是为什么呢?小说在第三章开头部分给出了答案:“(他们)虽说是中国人,也并非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并非他们具有共同特征。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固然千差万别,但这点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完全一样。”
小说中,两周后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怀着既担心又黯淡的心情去一所“中国人小学”考试。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很陡的坡路上几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朝同一方向行进”,“他们只是默默走路,没有人往地上拍皮球,没有人扯低年级同学的帽子”。这一幕与现实多么不符。如此活泼好动的年纪,为何他们这些中国小朋友如此静悄悄呢?想必虽说“他们”是二战后战胜国的后代,但却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寄居在前殖民者的土地上,因而心中失落吧。
小说中“我”在参加小学会考时在一个中国人的小学里遇到一位监考老师。作为小学生的“我”,中国人的小学是意想不到的清爽、干净、明亮、舒适的学校。“别致的铁门”“明亮的教室”“墨绿色崭新的教室”等都完全颠覆了“我”去之前的想象。而那位拄着手杖,年龄不超过40岁的中国监考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残疾总会令人产生恐惧异样的反应,加上听老师郑重严肃地宣布考试纪律,在沉默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接着老师在开考之前发表了一些与之前形象完全相反的话语:“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的和睦,每个人才能活的心情舒畅,对吧?”同时对同学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大家不要在桌面上乱写乱画,不要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面乱来。明白了吗?”老师在开考之前发表的这些话语,同时又对同学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中国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前来他们学校考试的日本小学生呢?”一个日本小学生去日本的中国小学参加考试,老师提醒说“中日两国要友好相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在日的中国人应该是少数人,并不是很受欢迎,因而会特意提到中日两国应和睦相处。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的调查,自战后以来,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始终是美国和英国、法国、瑞士等欧美国家。而在他们所不喜欢或讨厌的国家之中,苏联处于第一位,中国、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虽然在不同时期略有差别,但都属于被日本人讨厌的国家。[7]267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监考老师怕日本小学生讨厌中国的小学生,而可能会故意在桌子上乱写乱画,所以才说的那番话吧。然而,事情并非按照“我”想象的那样发展。
后来高三时,“我”第一次与一个同班女孩约会。由于是在秋天,又在同一条坡路,并且我们还在同一考场考试。“我”问女孩当时“是否在课桌上乱写乱画过”,她说“想不起来了”。“把她送回家后,我在公共汽车中闭起眼睛,试着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中国少年的形象——一个星期一早上在自己桌子上发现谁的涂鸦的中国少年。” 一个是老师不让乱写乱画,而“我”却做了与老师意愿相违背的事——在桌上乱写乱画。这是第一次“我”背叛中国老师。为此,“我”在多年后对自己在中国人小学的课桌上“乱写乱画”产生深深的愧疚感。
遇见第二个中国人是与“我”一同打工的漂亮女孩。她工作很认真,受她的影响“我”也干活认真。一起工作了两个星期后,我们逐渐熟悉起来,慢慢地“我”对女孩产生了好感。在打工结束之后的那个傍晚,“我”约这个中国女孩去舞厅跳迪斯科。跳完舞后,我们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行走。这时已经十点二十分了,她言道:“该回去了。哥哥很啰唆的。”而“我”提醒她“别忘了鞋子哦”。回家与鞋子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我”会提到鞋子?
“差不多我该回去了。11点前必须回去的。”
“这么严啊!”
“恩。哥哥很啰唆的。”
“别忘了鞋子噢。”“鞋子?”她走了五、六步以后,才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啊,你说灰姑娘啊,没问题,不会忘记。”
女孩后来在对话中提到了“灰姑娘”的“鞋子”。而灰姑娘是谁呢?灰姑娘是一个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她的母亲早逝,她的父亲给她娶了个继母,继母没有善待灰姑娘,总让她干粗活,总是灰头土脸的,因而被人们称为“灰姑娘”。读过《灰姑娘》这个童话故事一定知道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灰姑娘很想参加王子的舞会,但是恶毒的继母并不让她参加。她得到仙女的帮助得以参加王子的舞会,但是必须得赶在12点的钟声敲响之前回家,否则所有的魔法都会失效。灰姑娘在匆匆离开皇宫时一时大意遗落了一只水晶鞋子,而正是因为这只遗落的水晶鞋,王子才找到了灰姑娘,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开往中国的慢船》中的故事情节并非按照男女约会的正常路子向前发展,而是发生了转折。本来可以将她顺路送回家的,而“我”却将她送上了相反的列车,等她返回车站与“我”重逢时,已经过了门禁时间。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几个小时后“我”才发现我把她的电话号码写在了火柴盒上,在她上车走之后,“我”无意间扔掉了那个火柴盒,以致“我”以后再也找不到她。那么,最终也就没能发生同《灰姑娘》中王子通过水晶鞋找到了“灰姑娘”的美满结局。
之后的情节便是女孩不禁喊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这里终究不是我所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日本是女孩实际生活的地方,可她因为自己是中国人,依然不能真正地融入这个国家中,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让她倍感紧张失措,始终体验着自己是中国人的疏离感,甚至把这个一直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前提。而村上更是借女孩之口完成了以她为代表的不再有中国痕迹的华裔的自我否定的声音。这是“我”对中国人第二次背信。村上通过讲述“我”与中国女孩最终失之交臂的故事想必是想揭示自己对中国人的愧疚之情。
“我”遇到的第三个中国人是“我”熟悉的陌生人——高中时代“我”朋友的朋友。而“我”却在一时间想不起对方,对方反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的事恐怕还是想要忘掉吧?我是说潜在性地。”“我”只得承认“有可能”,直至他提起自己是中国人,他正在做的行当是向中国人兜售百科事典时,“我”往日的记忆才慢慢浮现。他说“我因为同样的理由,却记得过去的每一件事,一件也不漏”,“甚至当时的天气,温度等”,而“我”却对往事记忆模糊。
“人之所以会烦恼,就是因为记性太好。该记的、不该记的都会留在记忆里,而我们又时常记住了应该忘掉的事情,忘掉了应该记住的事情,所以痛苦总是那么绵长。”[8]180然而无论怎样,这个中国朋友“我”都无法与他亲近。由此可见在日中国人身份尴尬,处境窘迫。
村上叙述了战后日本都市中三个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异乡心绪,他们是中国监考老师、中国打工女孩、高中同学,他们都是旅居日本的中国人,分别出现在“我”的小学、大学、结婚生子的人生阶段中。一般说来,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往往会令人记忆深刻。且小说中角色总是拥有生动的人格,而且人名也编造的易于记忆。为什么村上在文本中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用一些符号代替呢?想必暗含着“我”内心深处实在不愿想起的往事以及对“中国人”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之情。
二、反时代的主题
村上在小说中描绘的中国监考老师、打工女孩和高中同学,他们都只是住在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并未真正融入日本的主流社会,因而异乡客的标签将他们逼回了中国人的狭窄生活圈。正是村上对这一幕的精心描绘,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对旅居在日本的中国人怀有的排斥和偏见,使作者怀有愧疚之情,在整篇小说中弥漫着一种负罪、自责、无奈的气氛。
日本国民对中国感情发生彻底转变的分界线是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的1972年。那么在这之前,在日本的日子并不好过。中国虽说是战胜国,而这篇小说发表于1980年,也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久后。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对于中国人的态度还没有完全转换,日本民族对旅居日本的中国人还存有部分排斥和偏见。
加藤典洋谈到“村上拒绝使自己与当时的社会期待同调,具体说来就是固执地提出反时代主题。所谓的反时代的主题用一句来说就是对中国的罪责感”[9]111。而明确提出这一主题是村上在2009年以色列举行的耶路撒冷奖颁奖发表的演讲上,村上提到了他已去世的父亲。
村上的父亲在二战时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战争。村上说过:“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生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而宝贵的事项之一。”[10]54
村上曾说过:“我觉得写小说,很大一部分就是一种自我治疗的行为。”[11]53或许是父亲的经历对村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村上第一篇短篇小说的主题就与中国相关。也许心中不自觉地存有对中国人这种朴素的愧疚之心,并且将这种对内心的拷问与苛责编织进了小说文本中。在这篇小说中,村上在叙述战后“我”同三个中国人之间交往的故事的过程中,不自觉中发掘了自己对中国人的某种深深的情绪,并使其在小说的文本中纵情宣泄。然而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水平上升,年轻人对社会政治丧失兴趣,且再面对中国时,是很难再有如此之痛楚,更无法理解这样的痛楚。因而村上在第一篇小说中惟妙惟肖地描写出这种隐隐的痛楚,想必会对当代年轻人有所感触吧。
三、场所的哲学意蕴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场所”是极其古老而又“新鲜”的问题。在村上文学中,赋予“场所”深刻寓意主要凸显在作为现代人“存在根据”的问题上。所谓“根据”就是现代人赖以存在的根基。因为“所有的存在,特别是人的存在旨在追求不依赖他者的自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充分地表现了近代人的这种欲求,同时也曾是为其提供根据的划时代的主张。[12]50
文本中关于“场所”问题在不同情境下出现过三次,且不同情境下赋予“场所”的寓意各不相同。第一次是中国女大学生乘错电车返回后,面对“我”的道歉,她含泪微笑地说:“行了,这里本来就不是我应在的场所。”“我不知道,她所说的场所是指日本?还是指围绕在暗黑宇宙周围运转的岩石?”对此,田中实指出:“她说这句话的意义深远,是她用受伤的体验获得的代偿性认识。不久我就会意识:是日本社会让她感到惧怕,所有的(日本人)使她将自己封闭起来。‘好吗?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的建议一旦被她接受,‘我’的梦就会对她造成更大的伤害。”[13]275-276该见解从“日本人”、日本社会的排他性切入,披露了“我”无意识中扮演着伤害他者的角色,无疑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山根由美惠认为:“这里的场所不是具体指什么,而是指此环境中存在的少数人(minority)问题。即我把少数人替换为场所,且自以为‘我’不是少数人,这种不理解直接与无意识中歧视他者的行为息息相关。”[14]该观点从“我”自身无意识中对“她”的伤害出发,披露了“部分”(日本人)的排外心理,这种解释显然缺乏深意。我认为文本中“场所”不仅指“共同体、无意识和固有环境共同拥有的、我们(意识中自我)的存在基体,而且包括存在主体和基体之间的相关性。如果用更具原型的形式表示这一力学构图,那就是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戏剧性的行动者、主角)与合唱队的关系”[13]275-276。即“她”在身临其境中喊出的“这里本来就不是我应在的场所”中的“场所”,隐喻着现代社会中,“我”无法找到自我存在根据的丧失感。正如拓植光彦指出的,村上文学的叙事特质“不是在自身内部设定一个能够和自己亲切对话的分身,并与自己互相探讨外部世界,而是认真地倾听自己无意识中发出的呼唤,且在直面这一呼唤的过程中探寻真正的自己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一行为与寻找世界的意义等价”。这就是“我”从“她”那里听到的“场所”的深层寓意。可见,村上这一短篇探讨的主题与《且听风吟》一样具有奠基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开往中国的慢船》这篇小说虽是村上的初期短篇,但是通过“我”对历史“记忆”的痛切反思,表现了二战后以“我”为代表的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的歧视与偏见,体现了作者作为日本人的愧疚之情。而正因为如此,“我”才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女大学生喊出的“这里不是我的场所”,不仅喊出了“我”的心声,而且“切身感受到她的痛楚是因来自(日本人)的压力”。因此,这艘“开往中国的慢船”不仅象征着日本社会的未来希望不是一味地依赖“美国”,同时预示着现代社会的未来走向,或者说,“我”意象当中的那个“中国”也许真的很遥远,但也许它是未来世界的曙光所在。
[1] [日]田中実.「港のない貨物船」――『中国行きのスロウ·ボート』[J].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90,(12):162-168.
[2] [日]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M]. 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 [日]村上春树.『若い読者のための短編小説案内』[J].文艺春秋,2004,(2):1-22
[4] [日]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全作品1979—1989(3)」短編集[M].东京:讲谈社,1990.
[5] 李恩民.中日民间外交1945—197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美]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 [M].王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 陆裕财.我在美国讲中老年健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9] [日]加藤典洋.村上春樹の短編を英語で読む1979—2011[M].东京:讲谈社,2011.
[10] [日]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M]//林少华.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文学世界.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
[11] [日]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M].吕千舒,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12] [日]中村雄二郎.西田几多郎.[M].卞崇道,刘文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13] [日]中村雄二郎.共通感觉论[M].东京:岩波书店,2007.
[14] [日]山根由美惠.「村上春樹『中国行きのスロウボート』論:対社会意識の目覚めー」[J].国文学攷,2002,(2):35-46.
OntheImageofChinainHarukiMurakami'sStory,ASlowBoattoChina
LI Ni-n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SlowBoattoChina, an important early short story of Haruki Murakami, touches obviously upon the “China factor”. The novel reveals the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of the protagonist against “China” and “Chinese” in his sub-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ovel.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author’s guilt towards Chinese people and profoundly reveals the painful self-examination of the modern people for their survival dilemma in Murakami’s literature.
Haruki Murakami; China;ASlowBoattoChina;image
I106
A
1009-5128(2017)23-0038-05
2017-09-25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秦东古代诗歌在日本译介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5SKZD04);渭南师范学院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MOOC平台下的日语听力课程资源优化建设研究(JG201637)
李妮娜(1980—),女,陕西西安人,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郝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