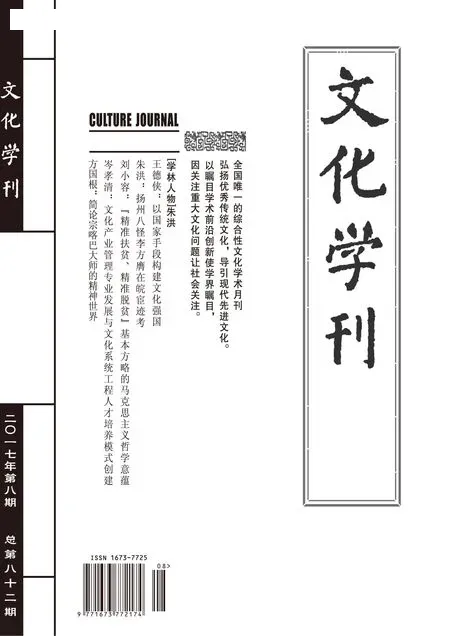霍布斯“利维坦”的建成及其内在困境
庞济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
【文化哲学】
霍布斯“利维坦”的建成及其内在困境
庞济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
《利维坦》中,霍布斯建构国家的路径,首先是从自然人的激情和理性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建立起伟大的“利维坦”。但是,由于霍布斯建构的国家体系过于庞大,其中融合了诸多复杂因素,难免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些悖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霍布斯契约建国之路中,由公民对国家的外在服从与保持其内在信仰之间的张力而引发出一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政府权力正当性的来源等问题的思考。
利维坦;自然状态;服从与信仰;权力来源
托马斯·霍布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思想家,被称为现代自由主义之父和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在霍布斯所有著作中,《利维坦》(Leviathan)可谓是论证最严密、体系最完备、影响最深远的经典之作。所谓“利维坦”(Leviathan),首先,源自希伯来神话,有缠绕扭曲漩涡之意;其次,在《圣经·旧约》中指三个怪兽之一,以海蛇、鲸鱼等海中巨兽为形象,比希莫斯也是其中之一,后来利维坦的形象转变为恶魔、妒忌、罪。《约伯记》中有这样的记载:“Upon earth there is not his like, who is made without fear”(在地上没有像它造的那样无所惧怕)。“He beholdeth all high things: he is a king over all the children of pride”(凡高大的,它无不藐视,它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1]霍布斯之所以以“利维坦”命名这部著作正是迎合了主权者应该有且仅有他所有不可分割的最高世俗强权的主张,这也说明《利维坦》是一部有关国家论的专著。本篇论文以《利维坦》的第一、二部分为文本基础,进一步分析理解霍布斯的国家建构理念。
一、“利维坦”的建构路径
霍布斯将建构“利维坦”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建构之前的自然状态,二是建构之后的国家状态,最后是国家主权丧失以后的情形。霍布斯就建构国家的理论表述上,首先认为国家是一个人为的“人造物”,其存在是以保护自然人为目的;其次,他以现代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分析国家的架构,并科学地区分出国家的各个部分;最后,霍布斯确立了通过订立契约、让渡权利来建立国家的契约之路。与神学的国家神定论不同,霍布斯十分拒斥国家是依靠神定秩序建构起来的这一理论,主张国家的建立理应起源于自然状态。在国家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有两个特征尤其令人瞩目:一是在体力和智力上,人与人之间总体而言呈现的平等;二是人人互相为战的战争状态。霍布斯认为平等是自然状态的出发点,这里的平等是指身体和心灵上(没有灵魂等级的含义)的平等。身体上真正的平等是面对死亡的平等,因为人们不知死亡何时降临,它让所有的算计都变得不可能,人越能算计越知道死亡之不可控制,故而人与人在暴死或脆弱性上来说是平等的。心灵上真正的平等则是指每个人对自己都很满意。尽管人与人是平等的,但人们通常拒绝承认这一点,相反地总是认为“除开自己和少数因出名或赞同自己的意见而得到自己推崇的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如自己”[2],所以应该占有更多,甚至可以统治他人。基于这一点,霍布斯将“权力”定义为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拥有多少权力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他人。即使自己握有的权力已经增长了,但倘使他人的权力增长的更多,那么他的权力反而就变得更少了。大多数人追求权力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自我保全,为了能够自保而落井下石,于是先发制人便成为最合理的自保之道。同时,又有些人把征服扩张进行得更为彻底,早已超出了自身所需的安全限度之外,那么其他那些不愿扩张其权势、安分守己的人们,单纯只靠防卫已无法生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这种扩张统治权的行为成为人们自保的必要条件。
根据以上一切,我们可以看出,在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使大家慑服时,人们极有可能处在互相为战的状态下,即战争状态。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将其定义为:“such a war, as is of 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3],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且更为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对暴死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们的生活贫困、孤独、残忍、卑污而短寿(which is most of all continual fear, and danger of violent death*霍布斯认为,死于他人之手是一个比死亡更大的恶,是对人自保的摧毁。; and the life of man, solitary, poor, nasty*意即:自保之力量会被侮辱。, brutish and short)。[4]对于霍布斯来说自然状态既自然又必然,是正当的(rightly)。在承认了人处于一个不可解的困境(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之后,便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政治框架,需要人为创造一个东西来战胜它,这个东西便是人造物——“利维坦”。
二、“利维坦”建构的内在困境
霍布斯凭借十分清晰的政治逻辑建构出“利维坦”,根据对人性特点的分析,指出恐惧与战争是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逃避的。人们出于对暴死的恐惧,以及自保的本能,在自然理性的帮助下,相互订立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转让出去,并授予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绝对且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就建立了国家——“利维坦”。然而,由于霍布斯所建构的国家体系十分宏大,其中囊括了各类纷繁复杂的因素,不免存在着一些逻辑上的困境。
霍布斯把“利维坦”死亡的外部原因归为受到外来的侵略与征服;内因则同个人的思想认识有关,首要的一个危险的思想观念是认为“个人(private man)是善恶行为的独立判断者”,其次是认为“一个人违反良知所做的一切都是罪恶的”,最后是认为“信仰和圣洁只能通过超自然的灵感得到,而不是通过学习和理性”。其实在笔者看来,内因中的后两个虽在具体表述上与第一个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为危险,最有可能导致其解体的事情就是“个人是善恶行为的判断者”这一思想的存在。霍布斯认为这一观念如果放在自然状态中,是完全正义合理的,因为那时没有国家的存在,个人只能凭借自己的欲望和理性来判断善恶行为,即便是后期当国家建立起来后,在国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的事务中,这个准则依然可行。但是,在法律已经规定的事中,一旦某个人出于自身的信仰或良知,认为国家不能符合或满足其利益时,那么国家就代表了恶,自己的信仰则代表了善,这个人便不会服从,或者表面上服从而内心抱持自己的观念,可以称为公民不服从,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国家的权威受到损害。
在霍布斯的建国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是授权和代表,授权是主权者能够拥有绝对且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源。但这一理论恰恰也是霍布斯困境的症结点之一。对比柏拉图的城邦理念来看,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终极目的在于城邦,个人对于国家而言,就好比人的四肢之于身体。个人对城邦的服从不仅仅是外在言行上的,更包括了其思想观念。但在霍布斯那里,个人的外在服从和内在信仰之间是存在张力的。因为在授权时,个人只能够让渡其外在的言辞行动,国家至高无上、绝对的权力只关乎外在而无法统治、教化人们的思想。那我们可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当一位主权者强使基督徒臣民说他不信仰基督,那么这个臣民应该怎么办?霍布斯认为可以表面上口头服从主权者,而内心继续坚持信仰基督。但正是这一点对于主权者的权威造成了极大的削弱损害,虽然看似很难推翻“利维坦”,而实际上却在不断蚕食、动摇着它的根基。
三、对利维坦“困境”的分析
通过分析霍布斯建构“利维坦”的逻辑困境,引发了笔者对新问题的思考:一个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何处?对于霍布斯而言,国家首先一定要去宗教化,他认为当时的基督教教会从根本上背离了《圣经》的教导,需要最大程度地削弱教会对于世俗政治的影响和控制力,减轻宗教对政治的危害。虽然霍布斯如此之后,能达到颠覆基督教教会权威的目的,但他建构的“利维坦”也同时不再具有神圣性,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世俗物。那么个人为什么要由内而外地服从一个没有任何“神圣性”的国家呢?霍布斯通过两点来试图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是根据个人的理性计算之后,普遍认为服从国家、将自身置于有序的政治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与和平;其次是由于个人对国家的恐惧,如果个人不服从国家将会受到惩罚,人们因为对惩罚的恐惧而选择服从国家。这两点中,霍布斯更看重的是后者,但无论是出于对“利维坦”的恐惧还是个人的理性计算而服从国家,始终是一种表面的顺从。可是,公民倘若只在外在言行上服从于主权者和法律,而对于善恶行为的判断依然只听从于自己的内心,那么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举的例子,当个人因为违反法律规定的事项而面临受到监禁惩罚的危险,在主权者派士兵抓捕他时,他完全可能因为内心并不认同国家的权威和法律,有着自己对于正义的判断,同时为了自我保全,拒绝被捕甚至诉诸暴力反抗,霍布斯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可以说是不义。如此一来,当为一个人开了可以违犯法律、蔑视国家权威的先河后,势必有后来人效仿,久而久之,大利维坦的内部将被蚕食掏空,国家政权将在风雨中飘摇逐渐走向倾覆。
有关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继霍布斯之后的各大政治哲学家仍然为解决该问题而不断探索着。17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接受霍布斯部分国家观的前提下,提出在人们有限地让渡除财产权、自我保存权以外的权利的情况下订立契约,构建一个人民授权的合法而有限的政府,并以此强化个人权利的重要价值,这一点是在其所处的政治动荡之时代,建构政府权力正当性的来源。洛克认为,建构政府的核心是保卫权利,他的论证大多是基于个人权利构建政府,同时通过论证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来阐释个人权利,二者互为依托。
法国17世纪伟大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研究政府权力正当性问题上也有所建树,卢梭接受了霍布斯部分自然状态的理论,把“自然状态”作为其逻辑起点,假定人类在自然条件下受到阻碍,无法凭借个人的能力生存,必须聚合在一起,订立契约,建构国家才能克服阻碍。在订立契约时,人民便可将其自然权利转让给共同利益体,将天赋的自由转化为政治前提下的自由,让自由与权利在政治社会中得以承认并受到保护。卢梭认为,社会契约为国家带来了生命,国家的意志表现为立法,政府权力成为国家行动的力量。国家代表人民,政府可以通过行使权力维系国家的生存,协调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确保社会契约的实现。总而言之,卢梭认为政府权力正当性最终的来源是人民。
但是无论洛克、卢梭如何积极且正面地建构国家,为政府权力正当性寻找来源,他们的理论无不接受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前提,即便努力将宗教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成为一种道德宗教以维系公民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但始终逃不开丧失了神圣性的国家无法对人具有真正的约束力这一困境,无法找出公民为何要服从一个没有神圣性的国家这一命题之解。
当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政治思想家没能走出这个困境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我们做出了有关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的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公共权力机构。政府权力常常以“调停人”的角色出现,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发挥着管理社会的作用,这也是政府权力的作用及其必然存在的原因。国家又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国家之暴力作为统治工具为统治阶级所专有,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对付外敌。同时,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尽管一切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一种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这样,在统治中,政府就必须履行其他一些社会管理和组织职能。因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权力的合理来源均为人民,这一点吸收并超越了卢梭的相关思想,认为主权者是人民权力的委托行使者,而不是权力的所有者。总而言之,马克思认为,人民和国家的阶级性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1]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M].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9.510-511.
[2]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3.
[3][4]T.Hobbes.Leviathan[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7.113.114.
【责任编辑:周丹】
B561.22
A
1673-7725(2017)08-0189-04
2017-06-05
庞济梧(1995-),女,天津人,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