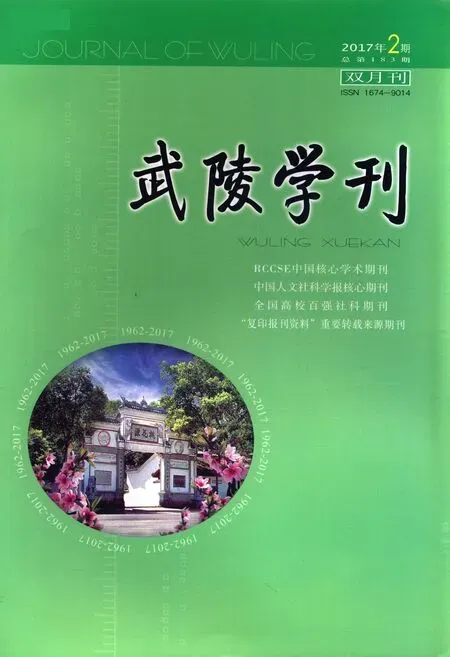声训衰落原因试析
张国良
(湖南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声训衰落原因试析
张国良
(湖南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声训在两汉时期达到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如今已少有学者使用声训解释词语。从传统语文学角度分析,声训在发展中受到经学、训诂学、语音学、词汇学和词典编纂等多方面的影响,再结合现代语源学发展和人类认知行为的研究,可以发现声训的衰落乃至消失不仅是语言发展的结果,也是学科建设的必然结果。
声训;经学;双音节化;语源学
声训是配合孔子正名思想而发挥儒家学说的主要工具之一。“流求佴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仁者人也,谊者宜也,偏旁依声以起训;刑者侀也,侀者成也,辗转积声以求通。”[1]声训的使用在先秦已经十分普遍,主要供诸子用来“依声立说”。西汉学者继承了声训之法,解释“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名词”[2],此类声训集大成于东汉班固《白虎通》。古文经学家也使用声训释词,声训正式进入语言学研究领域。郑玄提出“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的训诂理论,刘熙《释名》大量使用声训展示语源推求的结果。声训于此臻于鼎盛。
自魏晋起,声训初衰。仅刘勰《文心雕龙》使用声训解释文体名,尚有前代正文训诂遗风。虽然孔颖达疏经注、颜师古注《汉书》、徐锴注《说文》等也使用声训,但无论是数量还是主动意识都无法与先秦两汉相比。入宋之后,声训持续衰落。王安石著《字说》,王圣美提出“右文说”,把“字源”研究引入“词源”研究的层面,声训的纯粹性受到负面影响;且宋代学者所用声训多引自故训而无所创新,声训逐渐失去了生命力。清代古音学研究的成果被广泛应用于训诂,“因声求义”的提出客观上促进了语源学的研究,学者也多使用声训展示语源研究的结果,王念孙疏证《广雅》、段玉裁注《说文》、郝懿行注《尔雅》、钱绎注《方言》等使用声训尤多,且多为学者就词自释而非循古,声训一时复兴。近现代,科学语源学学科的建立,使语源的研究逐渐有了成熟的指导理论、系统的术语和严密的论证方式,不再使用声训作为语源研究结果的主要表述形式,声训之法逐渐退出训诂行列。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声训理论和具体声训语料都进行了多样的探索和研究,但由于受到训诂学学科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制约,相关研究并没有妥善地解释声训为什么会衰落乃至消失。故今从纵横两方面梳理声训发展的脉络,探讨其衰落的过程和原因,以便读者对声训和声训史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一、今文经学的衰落,导致声训使用量减少
汉初经学昌明,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立五经博士,至光武帝时博士已有十四家之多。诸家经学穷训诂、究典章、宣大义微言,仍多用声训立说。同时期之子、史亦然。如:
(1)《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
(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
(3)《史记·律书》:“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
(4)《淮南子·天文训》:“指寅,则万物螾螾也……指卯,则茂茂然。”
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开始朝着神学化发展。随着皇权的集中,统治者逐渐不能容忍今文经学家对政治的干预和批判。东汉建初四年,汉章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召集诸经学者(包括今、古文经学家)会于白虎观讲论经学。白虎观会议讨论的内容被班固记录下来,即《白虎通》。《白虎通》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对上自“三纲五常”下到婚丧嫁娶等,对有关汉代社会政治、思想、伦理的词语进行了全面的解释,最终确立了维持封建社会运行的基本意识形态。这些或充满神秘色彩或内涵丰富的词语,大多数仍采用声训来进行训释,总数超过200条。如:
(5a)《太玄·玄文》:“冬者,终也。”
(5b)《尚书大传》卷一:“冬,中也。物方藏于中也。”
(5c)《白虎通·五行》:“冬之为言终也。”
(6a)《独断》卷上:“妇人,伏于人也。”
(6b)《白虎通·三纲六纪》:“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
“冬”《太玄》训为“终”,《尚书大传》训为“中”,二说不同,《白虎通》定为“终”;对“妇”的训解,舍《独断》“伏于人也”而不取,而训为“服也”,是为了更符合儒家的“三纲五常”。所以说《白虎通》表面上是调和诸家经学分歧,实际上是在章帝“称制临决”下确立一套社会规范。此后学者对《白虎通》所释之词不敢轻易提出异议,今文经学再无明显发展;甚至古文经学家也深受《白虎通》的影响,郑玄注经、许慎著《说文》、刘熙著《释名》等都抄录了其中的部分释词。
此外,谶纬之学消失,声训失去了一种重要的载体。谶纬依附今文经学而生,自西汉末年影响渐大。其内容虽神秘驳杂,但离析章句、解释词语和今文经学如出一辙。七经谶纬颇杂声训,如《诗含神雾》:“故诗者,持也,以手维持也。”《礼含文嘉》:“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易乾凿度》:“卦者,挂也,挂万物,视而见之。”《春秋元命苞》《春秋说题辞》所用声训均多达30余条,数量可观。由于谶纬充斥着浓重的神学迷信色彩,魏晋以后屡遭禁止,到宋代已经消失殆尽。声训亦由此而失去了一种焉附的主体,使用量自然也就减少了。
二、郑学地位下降,导致声训理论影响力降低
西汉末年兴起的古文经学,继承了经学的传统,也使用声训释词,且重心逐渐转向普通词语。学者使用声训的主动意识明显加强。郑玄倡导从字音释义,提出“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的理论,并在注经中使用声训。如:
(7)《周礼·考工记》:“竑其辐广以为之弱,则虽有重任毂不折。”郑玄注:“弱1,菑也。今人谓蒲在水中者为弱2,是其类也。”
(8)《周礼·秋官》:“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郑玄注:“书‘薙’或作‘夷’。郑司农云:‘掌杀草。’故《春秋传》曰:‘如农夫之务去草芟夷蕴崇之。’又今俗间谓‘麦下’为‘夷下’,言芟夷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玄谓‘薙’读如‘鬀小儿头’之‘鬀’,书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从类耳。”
“弱1”指没入毂中的一段车辐,“弱2”指荷茎没入泥中的部分,二词音同形同意义相通,郑玄将之类比。“薙”为除草,“鬀”为剃发,二词音同意义相通,故郑玄将之类比。如此之类,郑玄为后学使用声训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范式。
郑玄注《毛诗》《礼记》《仪礼》《论语》《尚书》《尚书大传》等,今尚存者仍有十余种。清人皮锡瑞赞曰:“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3]经学一度统归于郑学。就声训的理论和实践来说,晚出的高诱、韦昭、刘熙等多受郑玄影响,尤其是刘熙《释名》系统地继承了郑玄的学说,使用声训多达1298条[4],蔚为大观。
然而,郑学“小统一”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就同时代而言,经学也并非仅存郑氏一家之说,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虞粲《尚书注》、王弼《易注》和何晏《论语集解》等多与郑说不同;稍后王肃注《尚书》《诗》《论语》《左氏春秋》和三礼等,立为官学,与郑学争胜。南北朝政权割据,经学亦分南北,《北史·儒林传》:“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虽然郑氏经注仍受推崇,但已沦为众家之一,地位和影响自然不能与昔日“小统一”时代相比。随着郑玄经注的地位下降,其提出的声训理论和所作的声训实践影响力也逐渐降低了。直到清代汉学复盛,郑玄被推到至高地位,声训才随之短暂复兴。
三、辞书释词模式的改变,导致声训的独特性被忽略
不论雅书、字书还是韵书,释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辞书的质量取决于它的释义。衡量一部辞书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的释义水平如何。”[5]汉代的四大辞书,《尔雅》《方言》偏重于直接释义,许慎《说文解字》意在解析字形以释本义,刘熙《释名》目的在于推求事物的命名之由,都属于独创性释词行为①。但魏晋以后,受辞书的性质和编纂目的的影响,释词(词头)以引用、汇集前代故训为主,原创性的训解越来越少,直接降低了新创声训产生的可能;编纂者在词头之下罗列被释词的训释,少则一两条,多则三五条,举凡雅书、字书、韵书、经史注疏都在其引用范围之内。各条训释往往兼有声训、义训或形训,模糊了三者之间的差别,抹杀了声训的独特性,使其旨趣逐渐不为人知。如:
(9)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卜部》:“卦,古卖反。《周易》:‘包羲始作八卦,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刘曰:‘卦之言画也,谓图画之也。’野王案,卦兆一等耳,分蓍布多则曰卦,灼龟见兆则曰兆。《说文》:‘卦,筮也。’《广雅》:‘挂也。卦,化也。’”
(10)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1:“诸岛,刀老反。孔注《尚书》:‘岛,海曲山人可居曰岛。’《尚书》曰:‘居岛之夷也。’《释名》云:‘岛,到也,谓人所奔到也。’《说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从山,鸟声。’”(T54p834a)
(11)宋丁度等《集韵·文韵》:“君,拘云切。《说文》:‘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一曰群,下之所归也。’”
顾野王训“卦”,引《说文》“卦,筮也”,自加按语“分蓍布多则曰卦”为义训;引《广雅》训为“挂也”“化也”,引“卦之言画也”都是声训,而未作区分。慧琳释“岛”,引《释名》声训“到也”,其他皆为义训或形训,也未作区分。此后《广韵》《集韵》《玉篇》《类篇》等辞书释义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多汇集而无分辨,收录声训多属于无意识的抄录故训的行为。另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张参《五经文字》之类,或重正音,或重正字,释义中偶见声训,本就是“副产品”,对声训的使用自然也不会有促进作用。
四、词汇双音节化和语音演变,导致声训使用的可能性降低
上古新词的产生主要依靠单音节旧词的派生和孳乳。由于汉民族思维方式具有具象性,先民在为新事物命名时会根据事物的形状、功能、颜色等方面的某个显著特征,对比已知事物,为具有相同特点的事物赋予一个音同音近的名字。正如刘师培所说:“盖古人之于物类也,凡同形、同色,则其呼名亦同。”[6]因为早期学者生活的时代,也是单音节旧词孳乳派生音同音近新词的时期,所以能够切身体验到新词产生的方式和过程,使用的一些声训往往符合语言的实际情况。如。
(12)《礼记·檀弓上》:“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
(13)《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后代学者逐渐失去了对这种新词产生方式的直接体验。自东汉始,新词的产生模式不再以单音节词孳乳、派生音同音近新词为主,而是以单音节词的双音节化为主要模式。“复音化的步伐从东汉开始大大加快。到了唐代,双音节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建立,双音节化的程度在近代汉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7]汉语词汇双音节化,无疑隔断了学者对于单音节旧词派生、孳乳音同音近新词的直接体验,使学者缺乏对词语之间同源关系的感性认识,因此在探求语源和系联同族词方面自然不如汉代及之前的学者得心应手,从而降低使用声训的主动性。
另外,汉语语音的演变,也降低了声训使用的可能。声训之所以被称为声训,是因为其主要的特点之一是被释词和训释词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若溯其源,正是因为被释词和训释词具有同源关系,二者才能够音同音近。但是语音是不断变化的,语音的演变会导致本具有同源关系的词语不再音同音近;甚至前代学者使用的声训,后代也很难认识到被释词和训释词的音同音近的关系。如:
(14)《说文·马部》:“马,武也;怒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
(15)《释名·释书契》:“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
上古“马”属明纽鱼部,“武”属明纽鱼部,音同;而中古“马”属明母马韵,“武”属微母麌韵,声韵皆不同。上古“谒”属影纽月部,“诣”属疑纽脂部,以现在的音韵学研究成果甚至没有办法证明二者音同音近。可见语音的演变对声训的理解和使用造成的负面影响。两汉之后,社会动乱,少数民族入侵,人口的流动性增大,语言的交流与融合增多,加剧了语音的演变。王力先生将公元三、四世纪作为汉语史的上古和中古阶段的过渡期[8],可见这一时期的语音变化之大。语音变化越大,确定词语之间的语音关系的难度也就越大。同源词之间的音同音近的关系被掩盖,给正确推求语源制造了巨大的困难,从而降低了使用声训的可能性。
人类在使用语言之初,不可能自觉地对语源进行研究,但“当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进展到一定深度时,都要追问语源问题”[9]。而语言学和人文科学进展到一定深度时,可能已经距离语言的产生、旧词派生孳乳新词的时代相当久远的时间,“后人对语源的探求,也就是对原初命名理据或复合词构词的理据的探索,对原来就已存在的种种模式的再现。”[10]声训就是对于旧词孳乳、派生新词模式的再现。而词汇双音节化和语音的演变断绝了训诂学家对旧词派生、孳乳新词模式的直接体验,从源头上隔断了对同源词之间“音近”“义通”关系的认识,无法自觉地推求语源、系联同族词,自然也就谈不上使用声训表述语源研究的结果了。由此可见,语言内部的因素已经决定了声训会从东汉之后开始衰落。时至清代,学者重构汉语古音系统,并将上古语音研究的成果广泛应用在训诂学上,使声训的使用短暂复盛。但古音学艰涩难懂,训诂学家中也仅段玉裁、王念孙等少数硕学之士能通其精要;再加上词语系统的研究在当时也只是初具规模,实践多而理论少,所以限于当时语源学的研究水平,声训在清代的复兴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五、字形感知的强化,导致音义关系感知的敏感度降低
汉代“缣贵而简重”,经学父子师弟授受仍以口授耳听为主。经师离析章句、训诂词语依靠口传,则弟子受教亦以语音感知为主要途径。词语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在“语音感知”情境中更容易被发现并加以利用,所以声训能够被接受并广泛使用,与它在人类的认知行为上占有优势有一定关系。如:
(16)《周礼·凫氏》:“于上之攠谓之隧”。郑玄注:“攠所击之处。攠,弊也。隧1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2。”
(17)《释名·释形体》:“胫,茎也,直而长似物茎也。”
“隧1”指钟鼓因敲击而形成的凹坑,“隧2”指甬道,二词形音皆同,无需多言。就是“胫”(人的小腿)和“茎”(植物的茎部)在以语音感知为主的情况下,首先捕捉到的信息也当是二者有一个相同读音(不计声调),从而把二者联系起来。
这种情况在纸本书籍普及之后发生了变化。“魏晋时代,纸张逐渐取代笨重的竹木和昂贵的缣帛,纸写本书籍大为流传。”[11]纸本书籍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者获取信息的主要认知方式——从“语音感知”逐渐演变为“字形感知”。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字形体的认读上,导致对词语音同音近关系感知的敏感度有所下降。两汉训诂重章句、释义而注音未详,魏晋以后则音义兼顾,盖亦由实用所需才有此变化;今人读书,识字形知字义而不能读字音的情况时有存在,古人也不外于是。
从语源学史来看,也正是从魏晋开始,文字形体在语源研究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具体训诂实践中,如晋崔豹《古今注·都邑》:“罘罳,屏之遗像也。塾,门外之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罘罳,复思也。”郭璞注《尔雅·释山》“属者峄”曰:“言络驿相连属。”都从形声字“声符”入手选择训释词;顾野王《玉篇》直接或者间接地展示具有相同声符的两个字的意义可以相同、相通。理论方面,晋杨泉《物理论》云:“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第一次将三个同源词(字)一起排比,指明同声符形声字表义的相同之处。宋代王安石《字说》以形声为会意;王圣美“右文说”总结声符表义的规律,等等。对于声符和字义关系的高度关注,无疑得益于文字形体地位在认知方式中的提高。
“字形”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语音”地位有所下降,在协调字形感知和语音感知的矛盾时,语音感知不得不做出让步。作为声训中特殊的一类,同字为训的消失,就是语音感知向字形感知妥协的一个有力证据。如《易·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孟子·滕文公上》“彻者,彻也”,《释名·释书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户口也”等,此类声训寻常可见。而魏晋之后,新创声训中使用同字相训的情况就极少见到了。同字为训,多由于声调或者词性不同,所以能取之为训,尤其在声调方面,即使具体音读不能确知,但必定是有分别的,否则不便于“耳治”。但“这种方法总是有背于以已知释未知的训诂原则,所以仅行于口耳相传的说经时代,后来一到笔下就渐渐废弃了,因目治不便也。”[12]同字为训的情况,其存在是因为在“语音感知”条件下可以区分被释词和训释词的语音差异,而其消亡则是由于在“字形感知”条件下同形字无法起到解释的作用,所以学者弃之不用。
六、近现代语源学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导致声训最终消亡
近代以来,传统小学走向科学语言学道路,训诂学中的语源研究成了新兴的课题。黄侃明确把探求语源当作“训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13]因为声训本质上是展示被释词的语源,因此开启了从语源学角度研究声训的新时期。现代语源学学科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对声训理论的研究,但也致使声训的使用最终消亡。
(18)黄侃《释兽音训》:“彙,毛刺。彙之为言也。,众也。又言也,草木孛之皃。皆肖多刺之状。孙注‘栎其实梂’云:‘有梂彙自裹,以其象比彙耳。’”
(19)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坻》:“《说文》十四篇下部云:‘陼,如渚者陼丘,水中高者也。从,者声。’(当古切。)《字通》作‘渚’。《释名》云:‘小洲曰渚。渚,遮也。体高能遮水,使从旁回也。’按成国以‘遮’释‘渚’,义为近之。愚谓渚之言著也。《国语·晋语》云:‘底著滞淫。’韦注云:‘著,附也。’《一切经音义》三引字书云:‘著,相附著也。’‘渚者,言水之所附著也。’”
黄侃、杨树达的语源学研究仍然带有清代乾嘉学者治小学的遗迹,考字(词)之同源、推求语源多用声训来表述其结果,以“之言”作为术语,每条之下附有意义相通的考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王力、陆宗达、王宁等学者先后提出一系列语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源学基本理论体系建构逐渐完成,现代语源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词族”“根词(语根)”“同根词”“同源词”“源词”“派生词”等术语为学界接受,在具体研究中使用逐渐规范。另外,语源研究的论证方面,也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推求语源、系联同族词操作范式。
(20)王力《同源字典》论证“斯”和“析”同源:
sie斯:syek析(支锡对转)“斯”“析”都是劈柴的意思,二字同源。《说文》:“斯,析也。”《诗·陈风·墓门》“斧以斯之”传:“斯,析也。”《说文》:“析,破木也。”《诗·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小雅·小弁》:“伐木掎矣,析薪拖矣。”《左传·昭公·七年》:“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15]
王力先生先证“斯sie”“析syek”音近,再以故训论证斯、析意义相同(相通),得出的结果是“二字同源”,而不再用“斯之言析”或者“斯之为言析”等声训形式来表述。又如王宁《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16]借鉴西方语义学的义素分析法论证“稍、秒、艄、霄、鞘、梢、消、销、削”等一组词语具有同源关系,把这组词语的意义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用/N/表示,是词义的类别,称作“类义素”;后一部分用/H/表示,是词义的共同特点,也就是造字所取的理据,称作“核义素”或“源义素”,因此得出同源词之间意义关系的公式:Y[X]=/N[X]/+/H/。王宁先生分析同源词的“类义素”和“核义素”,论证的结果也不再用“a之言b也”或“a,b也”等声训形式来表述,而是“a与b同源”“a是b的源词”等方式表述。
对比黄侃、杨树达和王力、王宁的同源词考证的行文即可看出,声训作为语源研究结果的展示形式,逐渐为日益严密、规范的现代语源学表述方式所取代。今人已很少使用声训,声训最终沦为“训诂学史上的一种训诂之条例了”[17]。
总之,声训是一种传统训诂方式,而古代训诂学基本上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声训受经学潮流和训诂理论的影响。声训本质上反映的是单音节同源词语之间音近义通关系,所以当语音发生变化和新词产生方式变化时,单音节词之间的同源关系难以发现和论证,声训使用的可能性就逐渐降低。声训还是一种展示语源的方式,随着现代语源学术语的完善,声训的功能被完全取代,最终消失。把声训放到训诂学史中,甚至放到更大范围的传统语文学中,从宏观把握其发展脉络,才得以看清它在历史上受到的多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衰落,最终退出现代释义学和语源学。
(陈师建初教授对本文写作进行了多次指导,谨致谢意。文中若有错谬,均由本人负责)
注释:
①刘熙《释名》因特定的著书目的,以声训作为展示语源推求结果的主要方式,所以至今若言声训,犹首提《释名》。就历代辞书的编纂来看,《尔雅》《说文》多有踵后之作,但再也没有出现一本训诂著作来继承和发扬刘熙的语源和声训研究。这其实也是声训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1]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8:2.
[2]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44.
[3]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95.
[4]陈建初.《释名》考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4.
[5]赵振铎.集韵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144.
[6]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物名溯源[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443.
[7]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节词的演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7.
[8]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43.
[9]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294.
[10]曾昭聪.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1:215.
[1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9.
[12]齐佩瑢.训诂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6.
[13]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学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81.
[14]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73.
[15]王力.语源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7.
[16]王宁.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5(2):167-178.
[17]孙雍长.论声训源流[J].辞书研究,2002(3):127-136.
(责任编辑:沈红宇)
H13
A
1674-9014(2017)02-0113-05
2016-11-23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汉语语源学史研究及汉语同源词汇纂”(200909)。
张国良,男,江苏徐州人,湖南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训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