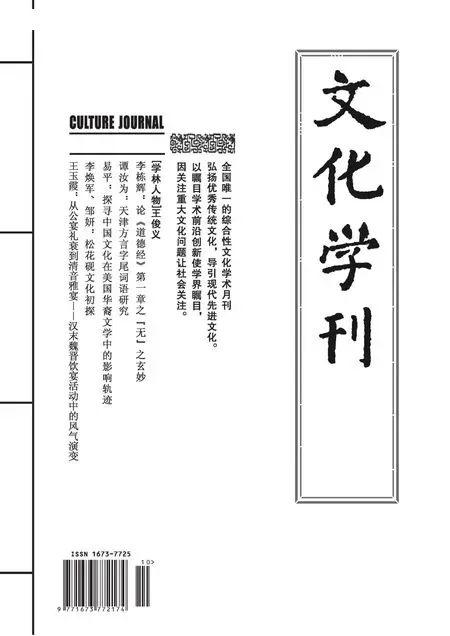我与艾尔曼教授的交往及其学术成就略述
王俊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00720)
【责任编辑:周丹】
【学林人物】
我与艾尔曼教授的交往及其学术成就略述
王俊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00720)
艾尔曼作为一名外国学人,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不懈地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其学术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其学术成就与贡献突出表现何在?在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上有何创新之举?这些问题似乎都应认真思考与回答,这从学术史与学术交流的角度说,他作为当今国际知名学者,理应多留下些学术信息档案,以资借鉴交流,即使是从个人友谊视角看,我觉得也有必要留下点永久的文字记忆。因不惴浅陋,拟就我们间的学术交流出发,就其治学之路、学术成就等方面略作评述。
本杰明·艾尔曼;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史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于1946年9月出生在德国慕尼黑,1947年随父母移民于美国,在美国各高等院校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是活跃于当代国际学术舞台的著名汉学家。他曾先后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及历史系主任。近十年来,还作为中国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兼职于复旦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他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长达半个世纪,尤长于明清学术思想史及中国科学制、科学技术史之研究。著述丰硕,成就卓著,多有拓展和创新,具有引领风气的作用和影响。此外,他还以很大精力致身于学术交流,其足迹遍及欧美及东亚各国、各地区,为推进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我与他在学术交流中建立的深厚友谊也已长达三十余年,弥足珍贵。
一、在学术交流中建立的深厚友谊
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王勃曾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深深感到我与艾尔曼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忆及我与他的交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以下简称《从理学到朴学》),于1983年来中国大陆首次学术交流。是时,我正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清代学史思想史的有关问题,已发表有《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等论文,且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见解,认为乾嘉学派(亦称乾嘉考据学、朴学)并非仅是清朝文字狱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对该学派亦多持正面评价。这些见解未料与艾尔曼的观点恰不谋而合、遂以此为契机,进行了愉快的会晤交流。从此相互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学术友谊也日益加深。1989—1990年,他与黄宗智教授联名邀请我到洛杉矶加大讲学,为该校历史系、中国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开设“清代学术思想史”与“清代学术思想文献选读”两门课程。此间还一度住在他家中,朝夕相处,切磋交流,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谈吐风趣幽默,博古通今,使我受益良多,友谊更深。在此次讲学过程中,我还访问了不少高校的清史研究专家,如加州理工大学的李中清、加州大学尔湾的王国斌等教授,特别是时任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魏克曼教授(亦译名魏斐德)还邀我到该校作专题讲演,我讲演的题目是《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潮及宣南诗社的几个问题考辨》。讲演针对学术界的有关论述,特别是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鸦片战争时期中的经史思潮中有一个宣南诗社,林则徐是宣南诗社的领袖,龚自珍和魏源都是宣南诗社的成员,该诗社倡导经世思潮,是鸦片战争抵抗派的母胎”等,这些论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曾率先对这种说法撰文提出质疑,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海内外学术界仍沿用这种说法不误,包括魏克曼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援引了这种说法。我在杨国桢教授质疑的基础上,用更多的事实和材料,无可辩驳的进一步论证,鸦片战争前的北京文坛上确有过宣南诗社,成立于嘉庆九年,林则徐只是诗社的一般成员,而并非是领袖,不久即离京外任。龚自珍和魏源都没有参加过宣南诗社。同时,此诗社属于封建社会中一般的文人结诗社。并非是经世思潮的源地和抵抗派的母胎。主持会议的魏克曼在讲演结束时十分谦虚坦率地说:“王教授讲得很好!过去我对宣南诗社的认识显然是错了,谢谢他的纠正”。从此,我与魏克曼也建立了学术联系,由于他还兼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美国史学会会长,1991年曾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到中国访问,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要恢复一度中断的美中学术交流时,还向中国对外交流协会提出,要会见我和戴逸先生,并在会晤交谈时,向我们透露了他此次来华的意图,也希望我们能积极参与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的确,此后美国大使馆此访举行的不少活动都邀请我参加。也可能与我到美国讲学以及与魏克曼的会晤有关。由此,我不能不衷心感谢艾克曼教授,是他邀请我到美国讲学,为我搭建了对外学术交流的平台,开阔了学术视野,并使我的学术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艾尔曼的两部主要代表作《从理学到朴学》及《常州今文经学研究》,先后在美国出版后,又都由我的学弟赵刚先生译成中文,列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分别于1995、1998年在中国内地出版,也都在国内学术界受到高度评价和强烈反响。艾尔曼鉴于赵刚的专业学术水平和翻译质量的考评和了解,他还将其吸引到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而今,赵刚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早已是在美国高校任教的教授,这些都得益于艾尔曼先生的培养教导。
我与艾尔曼在多年的学术交往中,有时也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如对庄存与在清代中叶兴起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原因问题上,他认为是起因于庄存与及庄氏家族,为反对乾隆朝的宠臣和珅,我则仍持传统观点,认为乃是援引《公羊春秋》,为乾隆时的“大一统”作论证,甚至还在2007年与2009年各自发表文章,公开进行过商榷,但由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各自都是从追求真理出发。相互尊重,丝毫不损害原有的真挚友谊,仍一如既往的进行学术切磋,他在学术讨论中反映的高尚学术风格,也着实令人钦佩。
至2009年,我们还曾共同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的学术座谈会,就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及由裴德生教授任分主编,艾尔曼参与编撰的《剑桥清代前中期史》,二者在史学观上的差异与研究方法的变化,进行对话研讨,艾尔曼在会上曾发表了勇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的精彩讲话,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当时媒体也曾有公开报导。
近些年来,艾尔曼的学术著作更加丰硕,学术成就愈来愈大,学术地位和影响也日益提高,异常活跃的呈现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却仍然谦逊如常,并未忘怀我这个学无长进的故交,直到近两年(2016、2017年)他还陆续应邀到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钱穆学术论坛”作高层次的学术讲座时,都与邀请在香港的我与会,并和香港学术界的朋友聚晤交流。
我通过与艾尔曼先生的长期学术交流,对其刻苦勤奋的治学态度和诚恳待人的为人风范,有了更多的直接感知,对其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及其思想开阔敏锐,不断提出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方法,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在回顾我们的学术交往的同时,也想就他的学术成就与研究方法,做些粗疏的评述。
二、艾尔曼学术成就述略
艾尔曼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追求中,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仅在中国内地出版的著作就有《从理学到朴学》《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帝制中国晚期科举文化史》《中国近代的科学文化史》《自有其理:科学在中国》(1550—1900)、《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等。
其学术成果除文字著述外,他作为一位长期在各个高等学校执教的教授,在教学与学术交流方面的成就也功不可没。我们通过其著作中阐述的内容和思想观点,及其在教学与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可以窥见,其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大致可概括如下几点:
其一,系统梳理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转变,推进了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其《从理学到朴学》《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两部代表作之中。
《从理学到朴学》于1984年首次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迅即在美国、日本、及中国的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1985年荣获费正清提名奖,1990年又出平装本,1995年被译成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出版,在此前后还有日语本,韩文本在东京和汉城出版。
一本学术著作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强烈反映,主要是该书内容翔实丰富、它系统分析总结了从宋明理学到清代考据学(又称“朴学”)的转变,充实了这一研究课题的空白;再者其思想观点新颖独到,具有开风气的作用和影响。从内容上说,源源本本地论述了这场学术转变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形成转变的内在理路和外部原因;总结了乾嘉考据学派的社会机制及其在当时社会文化教育、图书与出版等方面的蓬勃发展;肯定了考据学的特征及其各个学术领域的贡献和影响。此前学术界对于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的研究,均不乏有影响的著作和有成就的学者,但对于从宋明理学向清代考据学的转变,做出如此系统的梳理总结则不多见;再就书中阐述的思想观点讨论,它客观公正地分析了清代考据学崛起的原因,并非是清代文字狱导致的必然结果,认为其产生形成与清政府倡导的学术文化政策的正面作用也分不开,特别是充分肯定了考据学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鲜明指出,“现代中国学术固然受西方学术和科学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现代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曾受惠于清代学者的考证成果,如闫若璩的古文尚书研究、戴震的声类研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研究、王念孙、王引之的训诂学研究,而且没有清代金石学者奠定的基础,中国考古学者恐怕不可能读懂“甲骨文”。[1]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该书出版的1984年那个年代,则尚属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在中国内地长期受极左思潮和一些历史成见影响,对乾嘉考据学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几乎是学术研究的禁区,此书出版当时,中国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界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已有人指出新的看法,则尚不多见。艾尔曼作为一名外国学者,少受意识形态约束,其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客观分析,及对该学派作用和影响的高度肯定,无疑具有引领风气的作用。惟此之故,该书的出版问世,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共鸣和影响绝非偶然。
《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论述了明清学术思想史上又一场学术思想的转变,即从长于考据的东汉古文经学向擅于阐发微言大义的西汉今文经学的演变。曾沉寂近两千年的今文经学,为何在清乾嘉时期再度兴起,并形成“掩胁晚清社会百年风气”的一个重要学派,自然应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然而,学术界的研究较多的是被称为能反映清代学术特征的考据学派,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至今,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常州今文经学的研究专著,仅此而论,艾尔曼之此著,就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尤其是全书采用学术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学、政治与宗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视角,详细论述了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兴衰,更是作者的首创。该书以常州今文经学为经,以常州的庄氏、刘氏两大家族为纬,广泛搜集了庄、刘两大家族的族谱、家乘、方志、个人文集等大量文献史料,并以该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为核心,追溯了常州地域经文经学派的渊源,论证了庄存与在清代重建公羊学的经学思想,及庄存与之后,又经庄述祖、宋翔凤、刘逢禄的传承,梳理了该学派的演变和发展,亦可谓翔实系统,源源本本。[2]因此,其中文版问世后,亦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学者引为同调,在自己的论著中引用本书的观点和材料,但由于作者在书中着重强调了庄存与及其家族在乾隆时期兴起和发展今文经学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与乾隆朝的权贵和珅的对立和斗争,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并引起公开讨论,至今仍无一致定论。我想不同意见的讨论,属于正常研究中的百家争鸣,各种意见对活跃学术气氛,繁荣学术研究都有积极作用。艾尔曼关于常州今文经学的研究,对推动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同样功不可没。
其二,深入研究中国科举制与科学技术史,拓展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艾尔曼在研究从理学到朴学及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的基础上,又逐渐将自己的研究中心转向中国科举制及科技史方面。这种研究中心的转变,一则是科举制与科技史与其此前侧重研究的儒家经学关系十分密切;再者是他感到这些领域尚有不少有待深入研究的空间。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基本制度的确立,考试原则的制定,到考官的选派,试题的选择,都以儒家经学为中心,但随着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变化,儒家思想的表现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致使科举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时有变化,在选择试题时也各有侧重,如自宋代之后,程朱理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科举试题也完全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为准绳,但到清中叶乾嘉考据学兴盛后,科举试题也向考据学重视的经学原典的古文经转移。再致同治、光绪之后,伴随西学输入,新学兴起,包括天文、历算、数学、地理、水利等经世之学,也逐渐被纳入试题和策论范围,这些变化都是儒家思想不断变化的具体反映。因而研究科举制,就能更具体深入研究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演变的表现。艾尔曼将研究中心转向科举制,实际上也是其此前以儒家经学的纵深发展。另外,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同样是因为科技史与儒家经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作为儒家经典本身的《诗》《书》《易》《礼》《春秋》都包含有天文、历算等科技内容,自古以来许多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者都很关注科技,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一些学者,如王锡阐、梅文鼎、江永、戴震、阮元等精通天文、历算和数学,并将之运用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话、注疏之中。因此,后人要研究儒家的经典,如不熟知天文、历算,就很难弄通儒家经典中的某些内容,也很难弄清楚精通天文、历算的戴震、阮元等学者的思想和著述。对此,艾尔曼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实践中深有感知。与之同时,他还感到中外学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虽然有李约瑟等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师,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杰出贡献。然而,“至今人们对1900年以前中国自然界的了解还处于模糊状态”,[3]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艾尔曼将自己的研究中心,转向中国科举制和科技史方面,且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令人钦佩的成就和贡献。
艾尔曼在科举制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及一些论文之中,如《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制度》《明清科举与经学的关系》。他在这些论著中系统阐述了科举制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深刻分析了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其适应了帝制官僚政治的需要,维持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也是封建帝制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与广大社会民众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影响十分广泛。进而指出已往有关科举制的著作,对之有过多否定的偏向。
艾尔曼对科举制在内容阐述方面也有个人特色。过去多数科举制主要的著作内容多着眼于考试中的状元、翰林、进士等中了高榜的人物。他则另辟蹊径,将重点移向大批落榜的士子,并用数据说明,明代的考生约一、二百万人,到清代则有二、三百万人,但考中者则不过二、三万人,其中95%以上的士子落榜[4]。这些落榜的士子命运如何?流落于社会何处?直接关系到社会治乱安危,因此,他用了很大精力,挖掘搜集了各方面的史料,说明许多落榜士子,依据其原有的儒家文化素养与一技之长,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去书院任经师,或充任官僚、富商之家的家庭教师,或去做民间的医药师,衙门的讼师小吏,也有的去经商,或以文学才能写小说,编剧本、绘画。其中,也涌现出一些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如编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撰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都曾是科举制度下屡试不中的落榜士子。这些落榜者充当的各种社会角色,都丰富了社会的文化生活,提高了民众的教育知识水平,在调整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是到1905年清廷废止了科举考试,这些人也能适应社会转变,在社会上担当了相应的角色。因此,他不同意李约瑟等论者所说的:“科举制扼杀了中国人在自然探索方面的兴趣。”“科举制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障碍”。[5]
总之,艾尔曼对科举制的研究,从宏观论述,到微观分析,从陈述的内容到提出的思想观点,都丰富充实了科举制的研究。
如前所述,艾尔曼在转向科举制研究的同时,也以很大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和贡献,主要反映在其代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史》《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两部著作,还有学术论文《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科学》之中。其《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史》系统阐述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和演变,而《科学在中国》(1550—1900)这部著作并不是要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科学进行逐项综述,而主要关注的是1550—1900年这一时间跨度内中国的自然研究,以及文人对欧洲自然之学的掌握,尤其是要展现满洲统治者和汉族学者是如何通过朝廷、文人与耶稣会士、新传教士之间的接触,拓宽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医学的研究”。[6]因在其在著作中列举了各门学科如何拓宽的具体情况的同时,还有针对性的以专题讨论的形式阐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
如有些西方学者及某些受西方教育影响的中国学者有种共同的论调“中国在西方影响之前未能发展出科学”,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科学”。对此,艾尔曼则据理以驳,他认为并非中国没有科学,只是在近代之前没有“科学”这个词语,因为“科学”这个词是很晚才从日本传入的,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自然知识的探讨是用“格物致知”(即探究而扩展知识),或用“博物”(即有关事物性质的广播知识)来表达,后来又称“格致学”,“博物学”,有些学者还编写了《格致丛书》《广博物志》。[7]这就是说中国人是“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对自然研究的兴趣”,[8]亦即他常说的“自有其理”。他还以大量具体实例,说明早在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就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知识来观察世界,而且在天文、数学和医学等领域,都已达到很高水平,并非是传教士输入欧洲科学后,中国才有科学。只不过是西学东渐后,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中,中国人吸收了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学,中国的自然科学进入了新的阶段,发展到新水平,但却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没有科学”的结论。这些分析论述都以历史与逻辑的说服力,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近代话语。
综观艾尔曼对中国科举制和科技史的研究,都拓展了研究领域,结合中国的历史特点,以新的研究视角及相应的话语表达方式,丰富了研究内容,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不愧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又一创新性的成就和贡献。
其三,勇于向传统与权威挑战,探索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观点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和灵魂,任何一个在学术事业上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无不在学术创新上有所贡献,艾尔曼也不例外。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长期探索中,总是勇于向传统与权威的陈旧观点发起挑战,并不断探索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学术思想观点。他在这方面的突出事例,反映在其参加过由费正清先生作为总主编,又由裴德生教授担任分主编的《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撰稿工作的过程中。
大家知道,由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卷帙浩瀚的大型史学丛书,也是反映世界中国史研究最新水平的巨著。其中由费正清亲自主编、撰稿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又由裴德生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的编写与出版,前后间隔有十多年。由于时代变化,学术界在学术观点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和不同。艾尔曼曾在一次以“美国对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为题的座谈会,发言中,就总结了其中的变化和不同。他说:“费正清先生的《晚清史》和我们的《清代前中期史》态度一不样,甚至有冲突。因为时代不一样,他们的《剑桥晚清史》写在20世纪70年代,反映的是50年代、60年代的研究。我们的《清代前中期史》写在20世纪90年代,反映的是80年代的研究”。又说:“他们是前辈,是老师,我们很尊敬他们,但是后辈可以也可能超过他们”。艾尔曼这里所说《剑桥中国晚清史》与《剑桥中国前中期史》的不同与冲突,背后反映的正是美国学术界对清史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与思想观点上的转变与不同,即由“冲击——反映论”向“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而费正清正是“冲击——反映论”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费正清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或循环往复的状态,只能靠西方的冲击,才能打破固有的秩序而走向现代化道路,中国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和动力,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对冲击的反映”。[9]由于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些论述逐渐形成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理论模式和框架,且成为在美国居主流地位的思想观点,并反映在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实事求是地说,费正清作为一代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其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有重大贡献,但由其主导的“冲击——反映论”,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解,却有严重的片面性,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历史的客观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越战后美国政治局势的动荡因素,国际史学界兴起了冲破中西方中心论思潮的趋势,一些美国史学家,如魏斐德(亦名魏克曼)、孔飞力、施坚雅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逐渐以新的历史取向,用动态变化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直停滞往复循环的,即使到了明清时期也不断有新的增长点,进而反对用“冲击——反映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而酝酿着用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反映了美国史学界正在由“冲击——反映论”向新的理论模式转变,而艾尔曼正是这场思想理论转变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正是在上述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柯文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思潮转变的学术成果,撰写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正式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所谓“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主张世界要以中国为中心,更不是要恢复封建的“中国中心主义”,而只是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取向,主张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把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因。它也不排除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只是反对将西方的冲击视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10]应该说这种研究中国历史的取向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因而此书出版后,在美国和中国学界都引起强烈反响,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和肯定,并形成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新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卷的主编裴德生,及包括艾尔曼在内的如史景迁、马若孟、王业健、曾小萍、罗威廉、柯乔燕、曼素恩等,也都是“中国中心观”的主张者和支持者。这说明“中国中心观”已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种主要趋势和走向。
我们从“冲击——反映论”到“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的转变过程的评述中,可以印证艾尔曼所说的“超越前辈”,这种向传统和权威挑战的精神,是建立在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基础上的。同其在《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秉持的理念和写作态度一样,他在撰写《从理学到朴学》等著作时,也都坚持“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取向,从中国社会历史内部的变化,去分析各种思潮和学派,论证中国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是建立在中国内部学术思想变化中新的增长点基础上,并非是由于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传入,中国才出现了现代学术思想。所以,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文本《前言》中说:“如果要对该书的最后一章——《近年来美国历史研究之趋势》有所补充时,我会提到本书出版后的几本重要著作”。他所补充的几本重要著作就包括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以及“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社会》等。这说明他所采取的研究取向与研究成果,已经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艾尔曼的学术研究,虽在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和变化,但总的研究范畴却始终围绕中国历史文化这个大方向,而且一直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运用,其在1992年就写过《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尔后,又将此文稍有修改,作为其《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的《中文版序》。他在这篇文章中,尖锐批评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严肃指出他们“质疑历史的权威与其理性”,“根本否认有客观历史研究”。“这些后现代主张无疑地过于夸大,但史学家不能不理会”。因进而指出“随着西方后现代时期的来临,我们前辈所守的旧的方法论,日益显得不合时宜”。他所指的不合时宜的方法论,主要是指海内外学术界的“社会化约论”“目的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观念史论”,这种“观念史论”大多是从思想到思想,“独到观念的内部开展,做为阐明传统中国思想和缺乏的方法论框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和美国的一些同行建议中国思想史研究应采取新的方向,将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史相结合,代替思想史的单向分析,以使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内容更加客观和丰富。[11]
艾尔曼对其所提出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的建议,身体力行的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与著作之中,他所撰写的《从理学到朴学》及《常州今文学派研究》,都摒弃了过去学术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方法,将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方法,而是把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紧密结合起来,正如其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的《著者中文版序》中所说:“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注意本书综汇学术史与社会史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它采取了欧美最近出现的新文化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摒弃了传统学术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作法”。同样,他在《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的《序论》中也宣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者互动的过程,并由此说明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研究一旦结合起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将会是何等丰富”。
由于艾尔曼学术研究的侧重点,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但其无论是在研究中国科举制、中国科技史、或者是在研究中日关系交流史的过程中,都不断在探索研究方法,进而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和观点,这里不一一列举。
为了使学术研究事业代代传承,持续发展,艾尔曼不仅自己勇于向传统和权威的陈旧观点和方法发起挑战,而且也将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体会,向年轻一代学者传授。如他在接受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者的访问时,就语重心长的说:“从事历史研究,对史料与近人研究的阅读都不可偏废,阅读近人的著作主要目的是了解前辈学者研究过什么题目,如果不知道前辈的研究,怎么能超越他们。”他认为“年轻研究者将来必然会超过前人的成就,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年轻学者必须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有所不满,有所怀疑,才能开展新的探索与研究”。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资深学者,热切期望年轻一代的学人,要有抱负、有志气、勇于超越前辈,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故人。正是学术事业传承发展的规律。
以上,我从几个方面评述了艾尔曼先生的学术成就,事实上他的学术成就还有许多,这里所说的还很不够,如他作为一位长期在美国各高校学校任职的著名教授,既为本科生讲课,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移民国家,在美国就读的学生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他在长期执教的过程中,培养的学生,多至成千上万,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另外,他也很重视对外学术交流,多年来他在学术交流中,足迹也遍布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等学府,担任兼职教授或讲座教授,讲学传道,为开展和推动国际间学术交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杰出贡献,广受称道和赞扬,这里兹不详述。
在撰写本文过程中,常常自然联想到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理解其意思是说在学术层面,不分国别和地域,相互都是心理相同,道术相通的。在当今政治格局多极,思想文化多元的时代,学术文化交流必然会更加频繁,世界文化要走向中国,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则是必然趋势。我从与艾尔曼教授长期的学术交往及从其学术成就中对此深有感受。我盼望艾尔曼先生,老当益壮,在学术研究事业及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取得更大成就,做出更多贡献,也衷心祝愿他的学术之树常新常青。
[1][2]艾尔曼.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
[3][5][6]艾尔曼.原祖杰,译.科学在中国·译者絮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29.636.
[4]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6).
[7][8]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学科[J].中国学术,2010,(28).
[9]费正清.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0]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艾尔曼.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之《代中文版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K23
A
1673-7725(2017)10-0028-08
2017-09-15
王俊义(1936-),男,河南人,教授,主要从事清代学术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