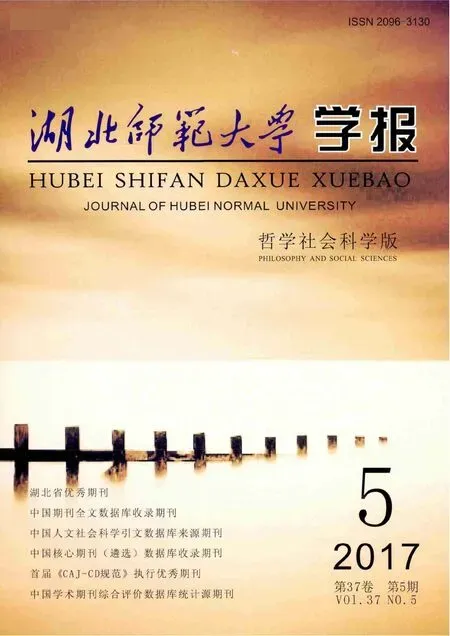浅析原始彩陶线条艺术的审美意蕴
赵 莹
(湖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浅析原始彩陶线条艺术的审美意蕴
赵 莹
(湖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在原始社会时期,陶器纹饰不但是装饰艺术,而且也是族的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从最早有些象形意味到到完全脱离形象走向独立的形式,这是一种思想认识上的概括,亦是一种意识活动的轨迹和社会变相。线条表达的不仅是对象本身,更重要的在于其背后潜藏着先民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精神及物质的各种复杂原因,以及与此相联的原始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宇宙情调。
彩陶纹样;线条;生命精神;审美意蕴
《易·系辞传》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人类从流荡游牧的生活改变成农业的定居生活,安分于一块土地上。不但利于这块土生养百谷、牲畜,也利于这块土制作了器物。陶器正是这“安土敦仁”的文明产物。[1]器物上的纹饰是原始人类造物精神的审美启示,采用“线”来作为主要的表达方式,纹饰不仅再是装饰,它更承载了远古人类几千年来的审美观念和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本文旨在通过彩陶纹饰中线条艺术的审美变化,探讨其背后哲学审美意味所表达的内在的精神本质。
一、和谐的行云流水
(一)象形纹饰的意味
彩陶纹饰的装饰主要采用象形纹和几何纹。象形纹饰在彩陶早期居于主导地位,数量较小,后来随着几何纹的不断发展,象形纹几乎消失殆尽。具象性的造型手法,是象形纹的最大艺术特色,也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艺术成就。它的表现手法多样,以线条造型为主的白描式的线描型绘制手法,线条疏密有致,能抓住对象的形态特征;平涂型则以单色平涂作类似剪影式的描绘方法,造型概括、动态活泼,并从特定的角度把握对象的形态特征;河南临汝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淘缸是先用白色在缸腹涂出一块竖长方形色块作底色,然后用黑色绘出鸟、石斧和鱼形。鸟、鱼、石斧的描绘极具绘画性。第三种是以线描和平涂两种手法相结合,称为综合型描绘方法。这种方法与前两种相比,刻画细腻,追求生动的绘画性效果,形象富于变化,图像本身的对比形成了比较强烈的装饰意味。
虽然象形纹饰的表现手法很多,但总的风格是统一而明显的。不以某一具体对象作为描绘的参照物,而是对某一类对象特征、动物形态的的多次感受,凭记忆所作的综合型创造。 其中有些纹饰是为了记录生活中的对象,另外一些则是原始艺术家凭借自己的想象、情感所创造的模式,来表达某种观念意识和审美习惯。对于这些对象的记录,原始艺术家不是机械地表达,而是“屈尊”地持“以己度人”的态度,把它们当做有情感、有灵魂的同类来看待的和表现的。在对这类动物的特定形态和运动的观察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记忆,从而做出了创作性的描绘。由于作者将自己的情感和对象沟通起来,所以他们创造的象形纹样中的形象不是冰冷冷的漠然物象,而带有一种“人的神情”。[2]所以,这些形象虽有一定的确定性,但又不囿于某一具体的对象。
(一) 几何纹饰的韵律
由点、线和各种几何形搭配组合而成的图形或纹样,称之为几何纹。“几何纹”是相对于“象形纹”而言的,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点和线的结合是彩陶早期的装饰方法,最初单纯线的构成元素及联结方式的规范,使陶器看起来规整而统一,当点以较大的圆形见于陶器外壁,用于环带分割、划分和联结中时,点则成为了纹饰结构中最活跃的部分,成为了构成的重心,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无论是水平的线条或垂直的线条,给人的感觉是平稳甚至是呆板的,对于水平放置的器物来讲,有着相似的恒稳感觉。不同方式线的出现打破了横竖方向的呆板,形成了装饰纹样的运动感,线的不稳定感恰恰又与器物的稳定感形成了对比,从而丰富了彩陶纹饰的艺术效果。对于早期的彩陶几何纹饰来讲,无论是将线排列成“锯齿形纹饰”,还是将其柔化为“水波型纹饰”,它们都能保持平稳的运动态势。它们跌宕起伏所造成跳动的感觉,以及循环运动节奏,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图案构成骨架,以至于后来的“曲折”成了最重要的审美评价准则之一。[3]
彩陶到了马家窑类型时期,几乎全部以线条为基本构造,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称为“线的世界”“线的艺术”。这一时期的彩陶,不仅在整体布局上重视对比和照应,同时,在每一个具体纹样的刻画上也非常注意变化与和谐。线条的粗细与间距、线条间的留白、线条的特定组合等不同手法的运用都会给画面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些线条构成的几何纹样,可能并不表达某种确定的含义,而更注重由它们造成的感受、情绪与气氛。图案与敦厚有变化的器形、细密而光洁的陶质结合,都为线条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器物肩、腹等开阔平缓的表面上,线条细柔、密集且变化较多;而在劲和下腹等较陡峭、较狭窄的表面,线条则较粗率、疏朗,较少起伏。这样,整个器物与纹饰就在视觉中产生了一种匀称有式、平稳和谐、流畅而统一的感觉,造成这一时期彩陶艺术的总体风格。
彩陶发展到这一阶段,原始人如此热衷于线条构成的纹饰,很难说它是取决于某些具体对象崇拜的观念,它们主要是在于人们特定的审美需求的相互作用中,装饰手法的进一步发展所致。不能排除在它们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基本纹样中,包含并传达了某些确定的或模糊的观念,纹样的产生,更多的大概不是图腾崇拜,而是水流和云霞一类与自然、气候相互关联的观念所致。从这个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象征,从形到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自觉的地创造和培育了比较纯粹的美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感。正因为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已积淀在其中,于是,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也正因为对它的感受有特定的观念、想象的积淀,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成为特定的“审美情感”。[4]在彭吉象主编的《中国艺术学》里也说到彩陶的几何纹饰,他认为彩陶几何纹是具有一定内涵的,它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中国原始意识形态的演化轨迹,即“由实到虚”正好符合了“由神到气”的演化思想体系。这些都表明远古时代的彩陶纹饰是一个灵动的画面,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优秀而古老的文化。[5]
二、“线”性特征的思维基础
原始艺术“线”性特征,一是指在原始思维相似律支配下的诸事物之间的秩序感;二是指以线条为最基本造型手段的原始艺术,装饰手法简洁而概括,鲜明的把握了对象事物的外轮廓线,从而再现事物的面貌特征。原始彩陶中动、植物以外的大量几何纹,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认为,这些抽象的纹饰由具象写实的纹饰演化而来,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他列举了鱼和鸟的演化过程,那些写实的纹饰所具有的含义最终都归为一条有意味的线。他认为彩陶上那些点、线、面都是“有意味的形式”。[6]图案中的线来源于纹样艺术的装饰,线表达的不仅是人们从自然感受中抽象出来的“纯粹形式”,同时也是人们的审美创造,赋予了情感和意识观念,独具艺术魅力。
列维—布留尔说:“原始人用与我们完全相同的眼睛来看,但是用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原始思维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秩序感的线性思维,而这种线性思维是建立在生存目的和认知目的的基础上的秩序原则。[7]在原始艺术中,人们所运用的直线排列和线性展开则是最直接、最稳定的秩序感,因为它便于认知、记忆与掌握。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熟悉和掌握的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唤醒了人们的知觉,这种表达反映在艺术上,便构成了艺术中的秩序感:节奏、韵律、匀称、均衡、统一、和谐....。 在某种意义上说,原始艺术是一个“秩序”表现的过程,艺术中的秩序感不只是自然秩序的外化,同时也是个体生命秩序的对象化。
对线的审美感受是通过在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中所掌握和熟练了的合规律性的自然法则本身而实现的。劳动、生活和自然对象与广大世界中的节奏、韵律、对称、均衡、连续、一致、变化、统一等种种形式规律,逐渐被自觉掌握和集中表现在这里。[8]奥地利作曲家恩斯特.托赫在论音乐与艺术的“线”性特征时指出:“线条首先是视觉印象最简单的形式,因为它是单维延伸的最基本形式。”[9]对于原始艺术来说,“线”的刻画和“线”性结构是最普遍运用的形式,也是最能表达人们意识、情感和审美的直接方式,这也许就是早期的刻画符号一直以来主要采用线为表达方式的主要原因吧。
三、宇宙意识与生命情调
(一)“诗性智慧”
维科称呼原始人的审美精神为“诗性智慧”。他在《新科学》中说,“自然”就是“生育”与“诞生”,对民族而言,最原始的民族精神是自然形成的,也是最接近自然的,它表现为在西方人看来略显粗糙的、野蛮的、原始的诗性。[10]中国传统造物的精神强调表现自然的、质朴的对象,这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体现。追求自然美,不习惯于纯理性的方式,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法则,原始彩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1]“天地养万物(颐卦)”,不能设想人离开自然还能生存,更进一步说,人不但从自然得到物质的给养,而且他的道德精神和一切活动,都能同自然达到最高的统一。《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唯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音。”音乐本是社会的审美方式,本拟按照人的情感需要来制律,但按中国音乐传统,它取的是自然的节律,其效果非同凡响,它不仅能实现天和,而且也能实现人和。[12]这里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马家窑彩陶上的纹饰我们清楚的看到,它是由圆圈和曲线构成的,圆圈内部大部分面积的空白,周围布满了曲线,形成虚实对比。这些有序列的曲线往往是围绕多个圆圈铺开的,这些曲线在开始部位是围绕一个圆圈,结尾的地方又围绕下一个圆圈,构成了一个无止尽的漩涡图案,同时圆圈里绘制的黑色圆点好似鸟的眼睛,给人以神秘感。正是这种表现方式解答了远古的文化根本,万物互渗,宇宙同一。[13]
纹样空白处的陶质底色总是与彩绘部分一起构成纹样的,所以空白也是纹样的组成部分。早在半坡期彩陶中,就出现了有意利用空白构成纹样的做法:人面纹中人的鼻子用黑色平涂,而嘴却用留空的方式,在用黑彩画的三角形中,用留空的方式空出一个倒三角形来,这明显是有意利用空白对比来造成装饰效果;另外这类彩陶鱼纹盆多在内壁安排四个单位纹样并使之两两相对,口沿的八个纹样以“米”字形分割了器口周围。类似的还有诸如“九宫格”“米字格”“花瓣形”等。不同形式的纹样阴阳互转,除了与原始人类精神内涵有关外,也隐含了史前早期的阴阳八卦思想。卦象虽然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但它的基本构成同样沉积了从许多彩陶纹饰中形成的基本审美规律。它的基本思想也反映出许多彩陶纹饰造型表述的基本观念。彩陶纹饰中三等三等分圆周的构图,三条排线构成的手指或蛙爪,回形线中的一波三折,我们不联想到“卦象”中乾、坤等并排的三列短画及最初导致“三生万物”这一哲学思想产生的那种观念的力量。[14]“鱼跃于渊,通乎阴阳”,从半坡彩陶盆以鱼表现旋转,经马家窑彩陶罐抽象规范的旋转鱼纹图案和屈家岭彩陶纺轮上的抽象旋转鱼纹,逐渐简化、规范化,把运动的的双鱼以对比色统一在一个圆中,在对比中求平衡,在统一中求变化,涵盖了一切的对立统一运动规律。[15]《易传》把阴阳的互相结合和互相作用,看成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始基,而阴阳的平衡统一是自然和人类社会能够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只有这种平衡统一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宁和快乐。[16]
人与自然形成诗性的关系,人恢复为自然人。因此,“合目的”指合道的目的、自然的目的,而否定人的欲望和人为的目的;“合规律”指合道的规律、自然规律,而否定智慧的规律;“自由”指彻底的精神自由,不再受物的系绊;“直觉”指超越道德层面的伦理精神,获得道的精神境界,感受到美的愉悦,悟到智慧。[17]较古的时代说“天地”,隐然已有时空的意识。宗白华以希腊美学为例说:“心灵必须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之流动演进不相违背,而同为一体一样。”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将这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流动演进,灿烂呈露,同体共美。[18]
(二)天人合一”:人的生命的自然美
封孝伦的《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完整而科学的阐释了人的生命。他认为,人是生命的个体,人具有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人是三重生命的统一体。[19]彩陶文化作为先民精神文化的创造,体现的不仅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更完美彰显的生命美学的内涵。审美创造的成果总是关联着人类的存在方式,体现着人类的生命追求,在创造成果后面,隐藏着对生命的热切关注,体现着人类的生命理想。刻画在陶器中的线,首先第一个存在条件是,人具有了生存所必需的实用工具—陶,在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的精神生活也发生着变化。线不仅再具有“物”的属性,原始人类更多是通过线来传承民族信仰、审美情感,而这些都是涵盖着早期人类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体验。其中的“天人合一”、“和”旋律,通过“线”这种纹饰的形式,暗涵着先人对生命的感悟,对美的追求,对生命未知的探索,虽是混沌,但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一种穿透生命之外的力量,这种力量给生命以精神的内核,具有审美和文化的意蕴。
人的生存环境—自然之所以美,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命追求。人与自然形成诗性的关系,人恢复为自然人。宗白华以希腊美学为例说:“心灵必须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之流动演进不相违背,而同为一体一样。”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将这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流动演进,灿烂呈露,同体共美。[20]史诗《格萨尔》中所表现出的对自然的无上崇拜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是这一思想的美好实践,正是由于最初的的然崇拜思想,才出现后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天人合一”这一理想状态正是生命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具有列维.布留尔所谓“神秘互渗”的文化性格。原始彩陶艺术中的“天人合一”正是生命美学审美境界的理想写照。
结语
人与自然的统一是指人能依照自然规律,全面地感觉、感受或享有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又能自由地理解和思考,拥有广大而深邃的理性空间,既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为自己营造一块独特的天地,又能将自己融入群类之中,融入整个自然界。人以生命的忘情状态投入到对象世界,对象世界以忘情状态投入到人的怀抱,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的反映,也是生命所追求的的审美理想状态。[21]远离了茫昧的渔猎社会剧烈的生存竞争,史前陶器的形制和纹样都展现着一种进入较缓和的农业社会时的优美心情。那些延展的曲线、连绵、缠绕、勾曲,像天上的云,又像大地上的长河。因为定居了,因为从百物的生长中知道了季节的更替、生命的从死灭到复苏,中国陶器中的纹饰除了图腾符号的简化之外,又仿佛有一种静下来观察万物的心情。[22]
封孝伦认为:“艺术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捉住了生命,也就捉住了美的真正内涵,当我们把人的生命的秘密全部揭开,美的秘密也就自在其中了。”[23]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精美的彩陶,是对彼时彼地活生生的感觉记录。它所传达的信息不是对自然物的恐惧和忧患,不是对崇拜物的卑微乞求与消极屈从;它给人的是一种自信的稳定,是一种欢乐的律动,是一种坦达的包容,一种朴实的和谐,是对生命美好的写照,是原始人的生命精神、审美观念和宇宙情怀共同融入这一生命美学的境界中。
[1]蒋 勋.美的沉思 [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23.
[2]王朝闻,邓福星.中国美术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116.
[3]王朝闻,邓福星.中国美术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143.
[4]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4.
[5]朱大维.原始彩陶纹饰的文化蕴涵初探[J].佛山陶瓷,2007(9).
[6]朱大维.原始彩陶纹饰的文化蕴涵初探[J].佛山陶瓷,2007(9).
[7]陈龙海.论原始艺术的“线”性特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3).
[8]李泽厚.美学三书[J].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
[9]陈龙海.论原始艺术的“线”性特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3).
[10]葛 辉.老子美学思想是史期研究[D].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59.
[11]高 原.原始彩陶造物精神启示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6(6).
[12]陈望衡.中华民族童真的魅力——中华史前审美意识本质论[J].社会科学战线.美学,2014(3).
[13]朱大维.原始彩陶纹饰的文化蕴涵初探[J].佛山陶瓷,2007(9).
[14]王朝闻,邓福星.中国美术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77.
[15]王 超.中国原始彩陶纹饰之“神性”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4.
[16]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274.
[17]葛 辉.老子美学思想是史期研究[D].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64.
[18]刘 墨.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54.
[19]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0]刘 墨.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54.
[21]韩 伟,庞泽华.‘格萨尔’生命美学思想论[J].中国藏学,2008(2).
[22]蒋 勋.美的沉思[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23.
[23]封孝伦.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M].贵阳:贵州出版社,1995(5).
(责任编辑:胡光波)
J211.23
A
2096-3130(2017)05-0039-04
10.3969/j.issn.2096-3130.2017.05.010
2017—06—12
赵莹,女,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