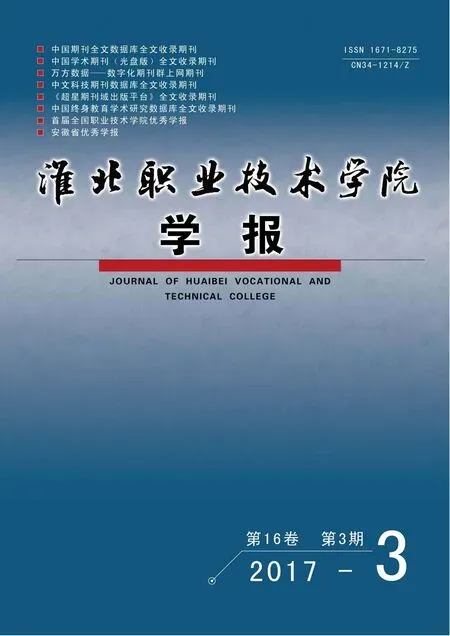《浮生六记》叙事视角探析
崔 萍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浮生六记》叙事视角探析
崔 萍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浮生六记》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转向夫妇之间,柴米油盐、布衣蔬菜的琐事完成情节建构。这种叙事角度与方式不仅展现出一幅下层文人夫妻恩爱的生活图景,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的融入亦使作品呈现出极大的情感张力。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大量描写,既是在晚明小品文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对传统宏大叙事的变革,反映出市井文人的生活气息,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浮生六记》;沈复;叙事方式;审美情趣
《浮生六记》为沈复生平唯一的一部著作,作者的人生面貌、审美情趣、情感体验都凝聚其中。近几年,尽管该书研究日盛,但大部分研究都注重文体辩说、叙事形象、艺术特色,对《浮生六记》的日常生活内容却很少有细致的研究。事实上,这种日常琐事的描写,对叙事情节的建构、清代下层文人审美情趣的表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日常琐事的叙事方式
《浮生六记》以时间线条为顺序,从青梅竹马式的爱恋写起,到相知相携的婚姻生活,以妻离子散的悲苦结尾,展现了作者大半生的悲欢离合以及人生如梦的独特体验。从叙述内容来看,可分为“乐事”“趣事”“愁事”“快事”四事。
在“闺房记乐”的十八篇和“闲情记趣”的十五篇中,主要记述了以“乐”和“趣”为主的琐事,涉及生活各处。吃食方面,如拌卤腐:“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许拌卤腐,亦鲜美。以卤瓜捣烂拌卤腐,名之曰双鲜酱,有异味。”[1]47为了方便食用,他们自制菜盒,“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附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1]64生活的其它方面,作者也不遗余力去描述表现。在贫困潦倒时,他们巧妙利用各种废弃物,即节省开支又不落俗套。比如做活花屏、做阑干。关于活花屏:“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约长四五寸,作矮条凳式,虚其中,横四挡,宽一尺许,四角凿圆眼,插竹编方眼。”[1]61关于阑干:“用竹数根黝黑色,一竖一横,留出走路。截半帘搭在衡竹上,垂至地,高与桌齐。中竖短竹四根,用麻线扎定,然后于横竹搭帘处,寻旧黑布条,连横竹裹缝之。”[1]64在这部分中,作者主要是为了表现乐、表达趣。因此,沈复极力描写他们的幸福恩爱,而把愁苦淡化。“坎坷记愁”主要写了作者与妻子是如何一步步与家庭产生间隙以致离家出走过着寄人篱下的凄惨生活,直至妻离子散的经历,悲苦令人动容。如其中写到生活的艰难,“隆冬无裘,挺身而过”[1]68由于贫苦,终导致陈芸撒手人寰。“浪游记快”写作者46岁时的游历,此时作者已做过多处幕僚,走了大半个中国。本部分的开头,作者写到“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1]83可见其游历之富。其中,乐事、愁事、趣事皆不记,只记浪游之感。到杭州,畅游西湖之胜、赴寒山,登高寻偕隐之寺、至海宁,观潮之汹涌。此地结构之精妙、此园布置之工巧、此山宜远观,宜近视、此园之幽静,作者一一列举。从这些秀美景色的描述中,既看出作者游历之胜,又可看出作者游性之浓!
关于烹茶、消夏、插花、叠石、赏月、畅游这类题材的文章,前代早已有之,尤以明代晚期众多小品文所描写的为最,其已不再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那样写山水抒心中块垒。如袁宏道的不同特色的山水小品、陈继儒对具有“幽韵如云”的茶的描写,要么表现个性之美、要么表现生活情趣。但也仅此而已,对于表现夫妇的生活,却是很少涉及。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赞《浮生六记》为一大例外创作,全书所呈现出的琐事内容可谓其最大的创新之处。这是与沈复作为市井文人密不可分。沈复虽是生于衣冠之家,但一生都奔波于各地做幕僚,从未做官,因此他不可能接触到王公贵胄,《红楼梦》中元妃省亲的热闹盛大场面,是他的眼界所达不到的。另外,由于沈复只是一个下层文人,少了为官者应有的为国效力君君臣臣之类的大抱负大思想,只是把普通百姓生活作为自己的审美所在,而正是这种对一件件小事的描写,不仅把作者对亡妻的追悼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
二、日常琐事中对叙事情节的构建
(一)通过日常小事推动情节发展
全书完整地交代了作者与芸娘相识、相知、相携,直至芸娘去世的夫妇生活的面貌。从幼时“余”随母归宁,得以初见陈芸,感叹其才思隽永,顿起怜惜之意,即此订婚。从回外婆家的事情写起,既交代了作者与芸娘两小无猜的感情,又交代了其婚姻的起始,为整篇内容做铺垫。全书所叙具围绕婚姻家庭之事展开层层铺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如一粥事,写了四次,在“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中分别提到,既是他们夫妇感情的见证,又是作者生活由“乐”到“苦”的最好体现。
第一次吃粥见于卷一,沈复回娘家送亲返回夜半时,“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1]38既表现了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感情,又可看出陈芸的贤良淑惠;第二次见于二人燕尔新婚,“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即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1]40,表达他们夫妇之间的浓情蜜意以及芸的孝上之德;第三次见于二人婚中闲聊,“余笑曰:幼时一粥犹忘不了;若来世不昧今生,合卺之夕,细谈隔世,更无合眼时矣”,表达夫妻二人琴瑟和鸣以及对永生永世不分离的祈盼;第四次见于卷三“坎坷记愁”中,当时芸因憨园之事而血疾加重,生活入不敷出,导致公婆心生间隙,不得不与儿女分离。粥事正是他们夫妇晓寒登州前的临别悲痛之言,“将交五鼓,暖粥共啜之。芸强颜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矣。’”[1]71从合到离,从乐到苦,以一粥事贯穿其中,表现了作者生命的曲线,是作者生活过程的真实反映。
就叙事学角度而言,“坎坷记愁”可谓是故事的高潮,作者通过一件件小事交代出他们夫妇怎样被父母误解、嫌弃、离家以及妻离子散的情节,作者用了二十篇勾勒出清晰的故事轮廓。在本卷的开始作者这样写道:“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拙。谚云:‘处家人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女子无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即交代了“愁”之源,又暗暗有悔恨与劝诫之意。余下皆是作者对这一“愁”之始末以时间为线索,徐徐道来,直至陈芸逝去“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1]76心伤泪涌,绵绵此恨,曷其有极!至此,感情达到最高处,故事达到高潮。后几篇则写芸之后事及作者对妻子深深的哀悼之情。“坎坷记愁”一卷既是叙事的高潮结尾,同时又是沈氏夫妇婚姻的终结。在这一部分中,既没有叙述者创作的白日梦幻想,也没有铁马冰河般的磅礴气势,涉及到的只是在贫困和礼法下挣扎的一对相濡以沫的小夫妻。悲喜亦或离合都通过生活的日常来表现,从而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清晰的叙事结构。
(二)纵横交错形成情感张力
《浮生六记》一书四卷,每卷都有一个情感的着力点,即“乐”“趣”“愁”“快”,叙述都是围绕这一感情主题。如“闺房记乐”中只记乐事,其他都淡化甚至不写,尽管其中有寥寥愁语,但对于读来来说还是一种愉悦的的感觉。在“闲情记趣”中则写盆花、焚香、交友之趣,令人喜爱,在“坎坷记愁”中则主要描写婆媳间隙、陈芸之死、家庭财产纠纷,令人悲痛。第四卷则只写游历之快,愁与苦都融入到山水美景之中。
与此同时,每一卷中都按时间线索进行铺写,且每一卷又都交错补充。同时间同地点发生的事依据思想主题进行主次分配。如沈氏夫妇寄居萧爽楼两载,在“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皆有提到,但分布的轻重却大有不同。在“闲情记趣”中作者用了两大段记述了夫妇二人与客往来,品诗论画的闲情,在“坎坷记愁”中则仅仅提笔带过表明沈父的谅解,“浪游记快”中则主要写了随友人去岭南的游历。再如陈芸养病于锡山华氏,在“闲情记趣”中只写了夏日芸作活花屏的雅兴,突出生活的乐趣,而在“坎坷记愁”中则用了浓重的笔墨表现离家远子的悲痛以及冒雪跋涉索债的经历,由此可见他们夫妇二人被逐,寄人篱下的悲苦。“浪游记快”中对于“愁”情只写道:“是年冬,余为友人作中保所累,家庭失欢,寄居锡山华氏。”[1]104余则尽写苦中作乐之游;
另外,四记虽对事件描写的力度不同,但篇幅的长短却是彼此相谐,又因每一段的情感体验不同而使得“哀”与“乐”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又相互补充,既加深了作者“扰扰攘攘,不知梦醒何时”的人生无力感,又表现出故事的情感张力,这样的叙事结构明显看出是作者的有意安排。
四记中每一记都对所看所思所见所做的事情进行细细的描绘,同时又把这些琐事与“乐”“趣”“愁”“快”的心理相交融,不仅展现了作者的生活图景,而且把自身独特的生命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
三、日常生活题材的审美价值
沈复对日常生活题材的叙述,既是在晚明小品文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对传统宏大叙事的变革,同时又反映出当时市井生活气息。
可以看出,沈复对古文了解通透且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吟诗作画皆得心应手,按照古人文人就应该“致君尧舜上”的思维逻辑,沈复似乎不应该屯于底层或闺房之乐。即使创作也应该写像《楚辞》亦或《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宗旨,或表达黍离之悲,家国之恨;或表达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或表达尊卑矛盾,社会悲苦。“与女性的‘主内’相对应,由于男性是‘主外’的,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所以男性作家惯于投入一种史诗性的追求,面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和社会生活,要写重大的题材、主题,进行宏大叙事,似乎这样才和男性身份相匹配。”[2]写政治,写战争,写主流成为历代男性文人心照不宣的准则,即使哀悼妻子,也应该表现其品行端正之类。“古人写夫妇之情,多少都要受限于各自特定的文化背景,书写者既不可能毫无缘由的自爆私情,写作中也不存在任意创新的自由。”[3]因此,对于那些夫妇燕昵之情、家庭柴米之事,都是鄙之弃之。但沈复偏逆向而行,自爆私情。陈寅恪曾对此书评价“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敌,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唯一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4]毫不避讳的夫妻恩爱,直率的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与传统的叙事无疑是背道而驰。在《浮生六记》中写道:“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1]83可见其独特的个性以及审美思想。
对于《浮生六记》的文体,历来争论不休,各持己见。但无论是自传体小说还是忆语体散文,都是属于一种叙事文体。其故事虽没有让人新奇的狐妖神鬼,没有江湖侠客的快意恩仇,但让我们倍感亲切,爱不释手。很大程度上,这与作者贴近现实的生活描写有关系。如“坎坷记愁”中涉及到的底层情状、家庭矛盾以及财产纠纷,都是下层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沈复在叙述这类日常琐事时,并没有落入俗套成为流水账式的连篇累牍,把他市井生活与高雅的情趣结合起来,给人带来雅趣的感官体验。
自晚明小品文以后,文人似乎不再把科举当成人生唯一的追求,开始转向眼前的一景一物,由外转内进行细细的观察品评,从而把生活艺术化。如张大复的《泗上戏书》中写道“一卷书,一塵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溪水,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5]即是对自己起居生活的情趣化描写。再如《红楼梦》中精致的吃食。但从这些书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只是文人的自我陶醉、上层社会的豪华奢靡,沈复则突破文人对自我生活艺术化的描写,把生活的聚焦点转向与妻子之间的燕昵之情,如前面所述的几次吃粥,在全书中此种夫妇之间琐事的描写比比皆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变系乎时序”《浮生六记》即反映了普通百姓家庭生活,同时又与文人的雅趣相结合,共同反映了当时市井的生活气息。
综上所述,沈复将对日常可见的琐事描写与传统文人艺术化、情趣化的审美相结合,不仅使情感抒发更加真切感人,也为作品添上了一分典雅之色,体出现当时市井文人独特的审美方式。
[1] 沈复.浮生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 谭军强.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09.
[3] 康正果.悼亡和回忆:论清代忆语体散文的叙事[J].中华文史论丛,2008(1):359.
[4]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93.
[5] 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88.
责任编辑:之 者
2017-03-23
崔萍(1992—),女,河南驻马店人,古代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I207.62
A
1671-8275(2017)03-007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