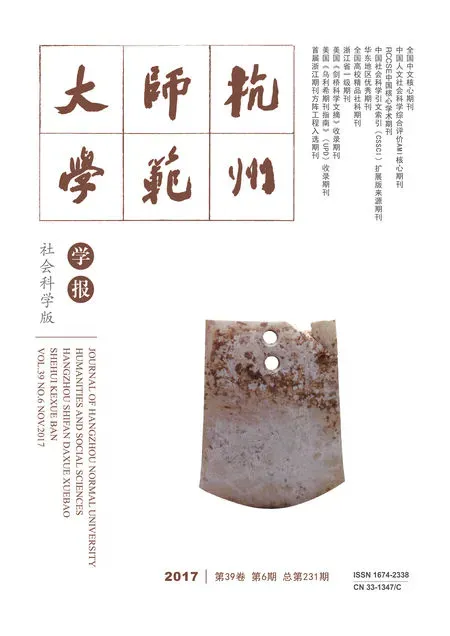“伞式社会”与中国古代工商业经营
张继焦,李金操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2.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伞式社会”与中国古代工商业经营
张继焦1,李金操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2.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
“伞式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政府与经营主体之间的“伞式”关系即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主要社会关系,也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我国政府与经营主体之间“伞式”关系由来已久。在古代,我国最主要的三种工商业经营体制——官营、包商经营、私营体制下的工商经营活动均在政府管控之下。因政府在不同经营体制中的参与程度不同,政府对经营主体实施的庇护政策也有所不同。总体上看,政府对官营工商业实施“父爱式庇护”,对包商经营工商业采取 “亲戚式庇护”,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朋友式庇护”。这种庇护差序现象对我国古代的工商业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工商业经营;伞式社会;官营;包商经营;私营;资源配置
一、研究的意义
美国汉学的开创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中提出一个“费正清之问”,即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依附于政府。[1](P.46)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一种经济社会结构。自古以来,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以及由政府直接经营的诸多经济活动,在我国社会经济领域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2](P.46)在古代,官营、包商经营、私营三种经营体制互为补充,构成我国工商经营结构的主要特点。①“官营”之“官”指政府而非官僚,官僚经营工商业多是为一己私利,与官营工商业有本质区别。参见宋国恺《唐朝禁官商合流政策之社会学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21-122页。实际上,古代的三种工商经营体制与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以及现当代公有、公私合营、私营等企业经营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传承性。探讨我国古代三种工商经营体制的联系与区别,既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特点,又有助于分析近现代中国企业经营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理论准备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创新呈蓬勃发展之势。李培林于1992年提出“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变动弹性,当社会的利益格局和运行机制发生结构性变动时,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潜在的能量,从深层影响资源配置并推动社会发展。*李培林关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基本命题主要体现在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三论”的3篇论文中:《“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的“结构-功能”理论,是对西方古典“结构-功能”理论的创新与发展。[3](P.7)在该理论框架下,张继焦于2014年提出“伞式社会”概念,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当今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仍是一种“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这种“伞式”关系对各地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伞式社会”理论,当今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庇护模式主要有三种:对下属企业是“父爱式庇护”,对合资企业是“亲戚式庇护”,对私营企业是“朋友式庇护”。[4]实际上,政府与经营主体之间的三种庇护模式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工商经营结构与当今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伞式”格局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
195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史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有关古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何种角色、施加何种影响的学术成果为数不少。例如,齐涛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对官营工商业着墨颇多,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我国古代工商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5](PP.353-441)刘秋根强调,中国古代不存在国家是否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存在干预程度深浅和干预方法是否得当的问题。[6](PP.338-365)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侧重历史事实的描述,以“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我国古代工商发展的学术成果寥寥,相关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三、“伞式社会”与中国古代三种工商体制的产生及经营领域的嬗变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伞式社会”,[7]无论是官府直接参与经营的官营工商业、官府监督下的包商经营工商业,还是官府参与度较低的私营工商业,均在政府的管控之下。
(一)古代三种工商经营体制的产生及其与政府的“伞式”关系
历史学者曾为官营工商业下过定义,指出官营工商业是“官府直接控制工匠和商人所进行的手工业和商业经营活动”。[8](P.395)在夏商周三代,官营工商业是我国工商经营的主要形式。无论是中央王国还是周边诸侯国、方国,均有大批在国君控制下从事工商经营的工匠、商贾。[9](PP.19-24)恩格斯认为,在牲畜变为特殊财产之前,氏族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主要通过氏族首领完成。[10](P.156)中国学者进一步指出,夏商周三代政府垄断工商业之现象,乃氏族部落时期氏族首领代替集体践行商品交易权之余绪,[11](P.143)笔者亦持此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官营工商业足以满足贵族与国人日常需要,故工商业几乎为政府垄断,“留给私人经营的余地很窄”,[12](P.12)政府实无干预私营工商业发展之必要。后来,私营工商业益发繁荣,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详下),官营工商业被赋予更多的经济干预职能。[8](P.395)总体上看,古代官营工商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为事关国家安全、市场秩序者,如铸币、兵器制造,这些行业基本由官方垄断;*与财政收入密切相关的盐、铁行业曾数次采取官营形式(主要发生于国家财政危急时),但中唐以后多采取包商方式经营。参看佐伯富等《中国盐政史研究》,《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类为满足统治阶层生活、公务需要者,如古代宫廷提供衣被的官纺机构。[13](P.14)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官营工商业,政府均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经营,不仅直接分派工匠、调拨劳动力,还通过行政手段直接配给财物,基本包办了官营工商业的一切经营资源。故笔者认为,政府对官营工商业实施的是“父爱式庇护”。
此后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至春秋战国,私营工商业开始呈现繁荣景象,并逐渐产生重大影响。[14](P.148)春秋时期,私营工商业的负面作用尚未凸显,加之当时诸国林立,各邦国欲积累财富,急需本国私营工商业者的扶持,故政府对本国私营工商业庇护程度之深,较官营工商业亦不遑多让。例如,郑卿子产曾坚决抵制晋国命卿韩起(时韩起主持诸侯会盟,权势极盛)强买郑商玉环,借此维护本国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15](PP.1378-1380)但随着私营工商业规模的扩大,其社会弊端日渐凸显。如大奸商在饥荒年代囤积居奇,“乘民之不给”而“百倍其本”,剥削百姓,扰乱市场秩序;此外,随着势力膨胀,资本雄厚的私营工商业者形成一股社会离心力量,引发了“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的问题,导致出现“一国而二君二王”的社会窘境。[16](PP.1264-1426)故而,各诸侯国均不同程度地出台某些规范或限制私营工商业的法令,魏国李悝曾让国家干预粮食贸易,通过“平籴法”打击私商囤积居奇行为;[17](PP.32-33)秦国商鞅不仅强调“壹山泽”,还主张国家垄断粮食贸易。[18](PP.108-111)总之,私营工商业的繁荣与中央集权下政府主导全国经济的意愿相违背,限制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思想逐渐占据主流。虽然之后历代王朝也出台了若干扶持私营工商业的法令,但它们多是为了体现政府对“细民”之关爱,政府极少刻意配给资源。总体上看,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施的是“朋友式庇护”。
包商经营是一种官府监督、特许商人经营的经营体制。相比于官营、私营体制,包商经营的运转模式更为复杂。在包商体制下,政府一般规定某些商品为专利商品并垄断供应,只有获得政府许可的特定商人才可参与经营。*关于“包商制”之定义,参见陈直《从秦汉史料中看屯田采矿铸钱三种制度》,《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第100页。包商经营兼有官营、私营的特点,其前身应是官民合营、利润共分制。据记载,管仲相齐时,齐国用“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当为七之误)君得其三”的方式冶铁,[16](P.1448)便是采取官民合营的方式。但自秦以来,“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观念代表了政府对工商经营态度之主流。在该背景下,政府很难采取“合作”姿态与民间力量共同经营工商事业,故而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包商制而非官民合营制。甚至到了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官商合办企业在现实操作中也几乎绝无仅有(代以官督商办形式)。*仅基隆煤矿筹划过实施官商合办方式经营,但亦未成功。参见王晓燕《评洋务运动的企业体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32页。笔者认为,包商制是政府吸收民间经营力量参与经营的结果,其产生应晚于私营工商业。陈直、杨剑虹、陈长华等认为,秦朝政府之所以从煮盐、冶铁等行业获得“二十倍于古”的利润,即与包商制施行有关。*参见陈直《从秦汉史料中看屯田采矿铸钱三种制度》(第100页);杨剑虹《从云梦秦简看秦代手工业和商业的若干问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第91页);陈长华《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史林》1995年第2期,第134页)。按秦中央实行“壹山泽”政策,盐、铁供应由政府垄断,确有实行包商制的条件。但在中唐以前,包商经营体制尚未推广。我国包商制真正获得普及发生于唐代刘晏改革盐法以后,在刘晏之前,政府多从产、运、销各环节垄断食盐贸易,采取官营方式经营。在“父爱式庇护”下,政府往往强制从民间筹集运输工具,向百姓摊派收装、运输徭役,致使民间苦怨之声不绝。[19](卷2,P.269)刘晏针对时弊,采取“(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的方法,[20](P.7404)协调了政府、盐户、商人的利益,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减少政府开支,从而提高了盐政利润。刘晏之后,包商经营体制大行其道,宋代扩展到茶、盐、香、矾等领域,[21](P.89)元代进一步将醋、矿产品纳入包商经营范畴。[22](P.94)历史上,采取包商经营的商品,如盐、茶等,多是利润较高、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之商品,故包商经营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虽然不直接参与经营,但政府十分注意通过财政优惠与补贴政策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总体上看,政府对包商经营的庇护程度介于官营与私营之间,可视为“亲戚式庇护”。
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者费孝通曾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颇似石子投入水中所泛起的涟漪,以己为中心向外愈推愈远,关系也愈来愈淡。[23](PP.27-28)中国古代工商经营领域的“伞式”现象,恰是工商经营主体与政府间关系疏密程度的差序化体现。
(二)三种体制下工商经营领域之嬗变
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政府会采取不同的工商管理政策,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期不同工商经营体制经营领域的消长与嬗变。
古代官营工商业逐步发展为事关国家安全、市场秩序与事关统治阶层生活、办公需要的两大经营类别,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西周以前,官营工商业几乎垄断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私营工商业兴盛,对官营工商业造成很大冲击。如何合理限定官营、私营经营领域,统治者曾进行了长期摸索。秦朝曾实行国家全面管控经济的政策,限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秦亡后,西汉政府以秦代经济政策为弊政之鉴,不仅“弛山泽之禁”,甚至连铸币权都下放于民,但很快引起了“钱文大乱”的问题。[24](P.41)西汉初年下放铸币权引起市场混乱一事证明,事关国家安全与市场秩序的行业最好由政府垄断经营。故汉武帝时,中央收回铸币权。此后历代政府均十分注意对铸币行业的把持,对其管控之严,丝毫不逊于兵器铸造业。*参见叶世昌《中国古代货币管理的指导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2期)。先秦以来,历代政府均垄断兵器铸造业,参见王兆春《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管理机构的演进》(《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0年第3期)。抛开为统治者日常生活服务之类的官营工商业不论(此类官营工商业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通过官营体制对铸币、兵器制造等行业的垄断是合理的,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非惟古代,近代洋务运动时期军工企业采用官办形式,现代纸币发行权归中央银行、国防工业采取国有体制,也出于安全、稳定的考虑 。
不似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之果决,政府对盐、铁、酒等利润丰厚、与国家财政关系密切的行业应当采取何种体制经营,一直举棋不定。先秦时期,这些行业向民间私营力量开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贾,但也引起了社会离心的问题。[14](PP.153-154)秦朝建立后,此类行业多采取官营或包商经营体制经营。[25](PP.87-91)西汉王朝建立后,以秦代工商政策为弊政之鉴,政府开放山泽之禁,放任私营力量涉足相关经营领域,官营、民营力量以相对平等的姿态共同从事盐、铁经营,私商再次财累万金。汉武帝时,国家外击匈奴、内兴建设,引发严重财政危机,但大商人专顾私利,“不佐国家之急”,导致“黎民重困”。[26](P.1425)故而汉武帝实行禁榷政策,规定盐、铁、酒由政府垄断经营。以大官僚为代表的私人力量不愿使此等厚利行业为国家垄断,通过朝堂辩论等方式驳斥官营体制下的禁榷政策。至成帝、哀帝以后,禁榷便“一弛再弛”,至东汉,盐铁放任政策终于又“居于主导地位”。[5](PP.367-384)魏晋时期战乱频仍,财政收入事关国家兴亡。即便如此,盐铁官营政策也“时兴时废”,并不持久。[22](P.94)隋至唐中期,此类行业均向民间开放。在此期间,政府甚至长期免收盐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出于平叛需要,再次采取官营体制经营此类行业。*参见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9-381页);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147-150、160-162页)。可见中唐以前,工商管理经验还未积累到一定程度,政府尚未明确经营盐业等行业的具体方式,官营、私营力量在相关领域长期角逐,影响了工商政策的稳定。刘晏改革榷盐法后,官、民力量不再对立,以分工式的包商体制共同经营相关行业,既保障了国家财政,又维护了民间经营者的利益。此后,盐业等与国家财政关系密切的行业便一直采取包商经营体制。中唐以前官营禁榷制度的“时兴时废”与中唐以后包商经营体制的稳定实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官营、私营都不是盐业等行业的理想经营体制。*虽有部分学者指出包商经营体制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经营体制之一,但学界大多将包商经营模式视为官营体制。考虑到包商经营与近代的官督商办和现代的合资体制间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笔者认为应将其单独划分出来,视为与官营、私营并行的工商经营体制。
私营工商业是我国工商经营体制的重要补充,且其经营领域与官营、包商经营体制间存在明显的互补及消长关系。前文指出,在私营工商业兴起之初,其经营领域十分广泛,甚至连铸币等重要行业也允许民间力量经营。但私营工商业主多追逐一己私利,少有为公为民之考虑,故而政府需对其经营领域进行规范。西汉景帝时,政府开始禁止民间铸币,汉武帝更是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此后民间力量便很少涉及该领域。包商制推广之前,私营力量曾凭借朝中当权大官僚,与官营力量在盐业等行业进行反复争夺。但包商制推广后,虽然民间工商力量被引入相关领域,但私营体制基本被排斥于此类行业之外。
笔者认为,官营、包商经营、私营三种体制经营范围的消长与型塑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自有其合理性。事关国家安全的兵器、铸币由政府垄断,有助于国家安全;*为统治者生活、公务服务的官营工商业更多地体现了阶级社会工商经营的特点,其与近代的官办和当代的国有体制工商业的传承性不如铸币、兵器铸造业明显。事关国家财政的行业采取包商经营体制,有利于缓和官、民工商经营力量对峙的局面;一些大宗贸易行业与次要行业,无采取官营、包商经营之必要,此类行业由民间经营,有助于活跃市场经济和保障民生。
四、“伞式社会”与中国古代工商经营资源之配置
“伞式社会”理论十分关注当今政府与企业间“伞式庇护”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4](P.56,61)在古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较今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社会资源配置领域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
(一)政府“父爱式庇护”下官营工商业的资源配置
前文指出,官营工商业或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或与统治者日常生活与公务需要关系密切,故历代统治者均对其十分重视。
首先,政府对官营工商业的“父爱式庇护”体现在劳动力配置方面。有学者指出,劳动力资源是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历代政府均重视通过劳动力资源配置影响经济结构及其运行。[2](P.46)在古代,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征集劳动力,以维持官营工商业庞大的生产经营需要。工匠是官营工商业中素质较高的从业人员,有官工、私工之分。为保证官、私工匠能世代为官府服务,古代政府为他们单独编造籍册,令其职务世代相袭。如北魏政府规定百工子息务必“习其父兄所业”,违者“师身死”;[27](P.97)唐代官营作坊“业作之子弟”一旦成为工匠,便“不得别入诸色”;[28](P.222)明代“以籍为定”的匠户若“诈冒脱免”,不仅本人杖八十,连“妄准脱免”的官员也要一并治罪。[29](P.2277)通过匠籍制度,政府控制大量官、私工匠,并将其运用到官营手工业生产中。除工匠外,官营工商业的日常运作还需要大量劳力,政府往往通过发配刑徒、官奴婢,征调士兵、丁夫的方式满足其经营需要。汉代铸钱、冶铁“一岁工十万人已(以)上”,为满足劳动力需求,诸铁官“皆置吏卒徒(刑徒)”以“攻山取铜铁”;[30](P.3075)唐代官营诸司存在大量奴婢,以满足官营工商业需要;[31](P.166)元代“应配役人”也被政府安置在冶炼、屯田、水利工程处“就作”;[32](P.2656)明代在苏州遵化铁厂劳作者除数百名工匠、士兵外,还有“民夫”千余名。[29](P.2640)
其次,政府对官营工商业“父爱式庇护”体现在财物供给方面。官营手工业生产规模大、工艺复杂,需要消耗大量财物。如汉代仅少府下属的三工官年耗官费数额便多达五千万之巨,[30](P.3075)如果没有国家力量做后盾,如此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恐难维系。政府通过赋税、土贡征收的物资与财富,为官营工商业生产提供了大力支持。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封占山林川泽的形式,满足官营工商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如唐代政府控制下的金属冶炼场所有168处。[33](P.1383)但即便如此,仍不足以满足官营工商业的需要,故政府开放某些矿山“听百姓私采”,但“若铸得铜及白蜡”,须“官为市取”,[28](P.749)优先满足官营作坊需要。
除了在人力、物力供应方面优先保证官营工商业经营需要外,政府还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统筹官营工商业的经营。[34](PP.278-280)另外对于某些事关国家安全的特殊行业,政府往往采取垄断方式经营,严禁民间力量参与经营。正是在政府的关怀与扶持下,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才保持了数千年的繁荣。
(二)政府“亲戚式庇护”下包商经营工商业的资源配置
包商经营行业利润丰厚,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故政府虽不直接参与经营,但通过采取经济、政治措施维护经营者的利益,从而促进了相关行业发展。
政府对包商经营工商业的庇护主要体现在对生产、销售者的经济扶持上。在清代,政府为提高食盐生产者——灶户、煎丁的劳动积极性,多次蠲免“灶地税”、“灶锅税”,遇到“晴干日久,产盐有限”的年月,政府还特许钱粮税款缴纳时间推延至“产旺”以后。此外,为防止贫苦煎丁因借贷受制于人,政府准许他们赴官府供领钱物,每年春借冬还,不必加息。[35](PP.201-202)专卖商人与政府的关系较灶户煎丁更为密切,政府对他们的经济扶持力度更大。为了解决专卖商人资金短缺的问题,古代政府出台纳代钱购物的政策。如唐代曾规定“商人纳绢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33](P.1379)明政府亦许商人“输粟二斗五升”便可“支盐一引”。[36](P.101)除了在代钱折算上给予优惠,政府还利用金融政策调节工商业经济利益。清代中央政府曾平抑盐价,为免盐价过低引起“商情失望”,政府特意规定每引加余息(利润)二三钱。[37](PP.3092-3095)此外,政府还注意维护专卖商人的垄断地位。如唐代十三巡院创设初期的主要职责便是“捕私盐者”,[33](P.1378)明初政府甚至严禁官僚“令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29](P.626)清代也严禁“失业穷黎”肩挑食盐四十斤以上。[38](PP.16-17)
总之,政府对包商经营工商业的发展十分重视,通过实施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扶持其发展。
(三)政府“朋友式庇护”下私营工商业的资源配置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所指之“商”,即私营工商业者。笔者认同之。[39]不过,历代政府均明白,单靠官营与包商经营的力量不足以满足官民日常所需,故需要私营工商业者参与经营,以补官营、包商经营之不足。
工匠、商人是古代“士、农、工、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出于爱民护业的考虑,出台了若干惠工、惠商政策。如西汉政府规定“弛商贾之律”、“弛山泽之禁”;[26](P.1418,3261)唐初“官不采”之山川资源“听百姓私采煮”;[28](P.749)宋初政府强调“官市之租”与“征算之条”务须“当从宽简”;[40](P.145)清代政府也规定,官员于正税外“不许额外苛索”。[41](P.305)此外,政府还注意打击假冒伪劣,营造良好市场氛围。早在先秦时期,法令中便含有用器、兵车(指运送军赋之车)、布帛 “不中度”者不可鬻于市的规定。[42](P.372)唐代政府规定贩卖“行滥”、“短狭”商品者处以“杖六十”之刑,[43](P.425) 宋代政府也有“禁造行滥物帛”的相关法令。[44](P.7742)不仅如此,古代政府还“详定秤法”,防止不法商贩通过“增损衡量”的方式影响市场交易公平。[45](P.725)
不过,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庇护”效应更多地体现了执政为公的“博爱”形象。私营工商业在获取社会资源方面并不占优势,政府即使“听百姓私采煮铸”,也多出于“官为市取”的考虑。故在古代,为获取更多资源,私营工商业者多从当权者中寻求“庇护伞”。先秦时期吕不韦曾厚结秦国公子异人(子楚),即为了有朝一日异人能成其庇护者;[46](PP.76-77)汉代邓通之所以能富甲天下,与汉文帝将“严道铜山”拨与其经营有关;[30](P.3723)唐代诗人元稹《估客乐》中所载商人之所以能“富与王家勍”,与其贿赂当权宦官和公卿大臣不无关系;[47](P.493)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之所以从一个落魄财主变成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亦离不开当权者的庇护。[48](PP.23)
虽然部分私商因“找伞”成功而获得大量资源,但这并不代表古代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在古代,私营工商业只是官营、包商经营体制的补充,政府对其发展不够重视,在资源配给方面的扶持力度远不及官营、包商经营工商业。
五、“伞式”关系对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影响
无论在任何时期,资源配置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伞下庇护”造成的资源配置差序现象,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明孔指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保证官府手工业会有比较充足的人手和原料”,这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比较发达”的重要原因。[13](PP.14-15)确如其所言,政府“父爱式庇护”下的资源配给维系了古代官营工商业的经营发展。若古代官营工商业仅涉及事关国家安全与市场秩序之行业,政府对官营工商业资源配置政策的倾斜无疑会为国家稳定提供重要助力。遗憾的是,在阶级社会,与统治者生活密切相关的官营工商业也是资源配置的受益者,此类行业以奢侈品生产为主。对此类行业,统治者往往过分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忽视商业利润,不仅割裂了官营工商业与市场的关系,还造成了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5](P.15)政府包办一切的“父爱式庇护”固然造就了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的数千年繁荣,对事关国家安全行业的垄断业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因过分追求某些产品的使用价值,在人力、物力配给方面不计成本,甚至不惜侵夺民间经营资源(详下),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古代工商业的整体发展。[49](P.285)
包商经营表现为政府利用民间商人的资金与经营管理才智为政府获取财富,而商人利用政府给予的政治、经济特权,垄断相关行业经营权,与政府一同分配超额利润。[50](PP.25-28)包商体制践行后,政府在相关领域的财政收入急剧上升,体现了社会结构合理转型背后蕴含的巨大能量。*刘晏改革榷盐法后,盐政收入一度高过田赋,史载“天下贡赋,盐利居半”,政府服饰、军饷与百官俸禄开支“皆仰给焉”。见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8页。在包商体制下,专营商人凭借种种特权,把持大量经营物资,轻松攫取巨额财富,中唐以后的著名商贾大多具有专营商人身份。财富的过分集中同样导致了资源过量浪费的问题。固然专营商人会将所获部分利润通过救济灾荒、筑路修桥、抚恤孤苦的形式回馈社会,但其用于奢侈挥霍的财富更多。[51](P.273)此外,商人专营地位的获得是靠政府支持实现的,故对政府依赖性极强,其经营地位并不独立,很难引领工商经营领域的变革。[50](P.25)
与官营、包商经营工商业相比,私营工商业在获取经营资源方面不占优势,其发展历程也最为坎坷。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政府制定若干惠工、惠商政策,体现了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姿态,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往往在执行过程中违离初衷。如古代曾长期推行和买、和雇政策,原本是为了减免百姓土贡、徭役之负担,但在执行过程中,渐渐沦为掠夺民间人力、物力资源的政策,且不少朝代袭此弊政。*参见唐任伍《论唐代的和籴和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第60-62页),非惟唐代如此,之后历代均不乏官僚借和籴、和雇巧取豪夺之事,如元代“京师岁所需物”多“郡邑列买于民”,但政府往往拖欠百姓,“其直(值)旷欠不给”,见许有壬《至正集》,载新文丰出版公司编《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57页。不仅善政在执行过程中渐渐演变成暴政,在某些朝代,政府甚至会公然掠夺民间财物资源。如明代中后期,政府不仅利用采办、买办、应行、当行、佥派等制度掠夺商民,而且通过重捐叠税的方式横征暴敛,导致晚明私营工商业急剧衰败。[19](卷3,PP.848-852)虽然古代有若干“找伞”成功的私营业主,因结交权贵获取部分资源,但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代,他们的经营地位得不到持久保障。如西汉邓通在文帝朝备受恩宠,蒙赐严道铜山,邓氏铜钱有“半天下”之誉,邓通因而称富一时。但汉景帝继位后,将严道铜山收回,邓通迅速破产,晚景凄凉。[30](PP.3722-3724)故有学者认为,中国私营工商业在古代受到多方压迫、限制,从未真正独立发展过。[49](P.287)
六、结语
政府与经营主体间的“伞式”关系影响了我国古代的工商经营结构:政府对官营工商业实施“父爱式庇护”,基本包办其经营所需的一切资源,造就了我国古代官营工商业的非正常繁荣;政府对包商经营工商业实施“亲戚式庇护”,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为包商经营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施“朋友式庇护”,通过制定若干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努力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经营环境。但我国古代私营工商业难以获得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其中为数不多的大商贾大多是“找伞”成功者,他们的富足并不能代表私营工商业的总体情况。
我国古代三种工商业经营体制长期共存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由政府经营,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事关国家财政收入的行业采取包商经营体制,既保障了政府收入,又维护了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利益;事关民生的大宗行业与次要行业,单靠国家与少数商人的力量难以完成,这些领域采取私营体制,不失为一种便民手段。笔者认为,政府对经营主体的“伞式”庇护差序格局有助于维持国家安全与市场秩序稳定,但也造成了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2] 吴太昌等:《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3] 张继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 张继焦:《“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
[5]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刘秋根等:《有所作为与无所作为——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国家经济职能的研究》,江锡东主编:《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
[7] 张继焦等:《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8] 漆侠:《中国改革通史·综合卷·丹青难写是精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9] 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1] 朱红林:《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12] 吴慧:《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十二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1年。
[13] 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绪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 杨善群:《春秋战国时期私营工商业简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
[1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6]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7] 郑鹤声:《李悝变法》,《文史哲》,1974年第3期。
[18] 严国海:《中国古代国家所有制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
[19] 吴慧:《中国商业通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20]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1] 尹向阳:《试论唐宋市场管理模式的变迁》,《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22] 晋文:《略论桑弘羊理财对后世禁榷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3] 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
[24] 刘玉峰:《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评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5] 杨剑虹:《从云梦秦简看秦代手工业和商业的若干问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26]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7]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28] 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29] 李东阳:《大明会典》,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
[30]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1] 李秀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2]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33] 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4] 张晋藩:《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35] 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36] 陈际泰:《已吾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90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37] 仁和琴川:《皇清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86册,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年。
[38] 吴坤修等:《安徽通志》第25册,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39] 雪耳:《中国政商关系的前世今生》,http://www.adfaith.com/zxxx/newsId=1872.html。
[40] 马端林:《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41] 允裪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第12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
[4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3] 岳存之点校:《唐律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44] 刘琳等点较:《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5] 韩邦奇:《苑落志略》,文津阁四库全书第7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46] 洪家义:《论吕不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47] 谢永芳:《元稹诗全集》,武汉:崇文书局,2016年。
[48] 曹炳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9] 郑世明:《工业文明与中国——企业制度比较分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50] 刘德仁等:《略论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与利用》,《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1] 于云汉:《海盐文化研究》第1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
“Umbrella-styleSociety”andAncientChineseIndustrialandCommercialManagement
ZHANG Ji-jiao1, LI Jin-cao2
(1.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Umbrella-style society” is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The “umbrella-styl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operators is an important wa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s well as a major social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ancient time, thre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s in our country (government-run business, contractors-run business, and private business) were all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Due to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operating systems,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on asylum for business operators are also different. In general,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paternal love asylum” for official business, “relative’s asylum” for contracted business, and “friend’s asylum” for private business. This different sanctuary phenomeno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attern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Business management; umbrella-style society; official business; contracted business; private business; resource allocation
山 宁)
2017-07-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2016-2020)、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6A070705031)的研究成果。
张继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企业人类学研究;李金操,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C911
A
1674-2338(2017)06-0118-08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6.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