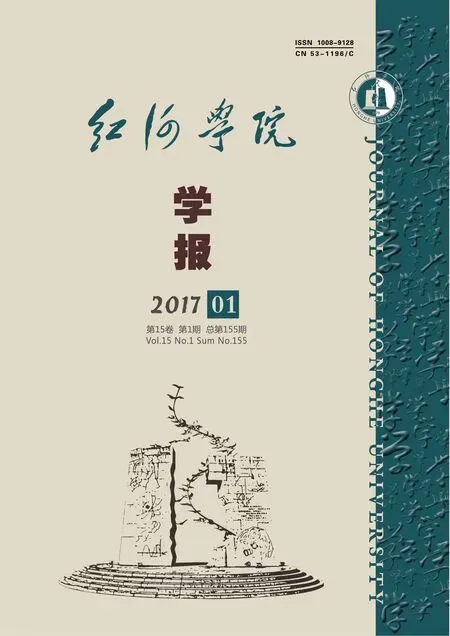去殖民化:《荒原蚁丘》中对语言的弃用与挪用
唐晏凤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500)
去殖民化:《荒原蚁丘》中对语言的弃用与挪用
唐晏凤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500)
《荒原蚁丘》中阿契贝在标准英语中嵌入未被翻译的词汇,句法融合和语符转换等策略对帝国中心语言进行重写和改写,一方面是说明他使用的“英语”即地方英语是有别于标准英语的一种“新英语”,以此彰显文化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说明地方英语文学文本中使用的方言口语的词汇、语法形式本身就是文化真实性的体现,从而颠覆帝国中心语言所体现的文化“真实性”和“中心性”,达到重塑非洲文化身份和特征的目的。
去殖民化; 挪用; 弃用;文化身份重构;《荒原蚁丘》
一 引言
《荒原蚁丘》是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代表作之一。以独立后的非洲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坎根,在获得民族独立后,精英阶层治理国家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对于文化身份重构的主题,付文丽认为在《荒原蚁丘》中,阿契贝是通过刻画比阿特丽斯这一人物形象的反抗精神,揭示出要摆脱霸权文化对非洲知识分子的束缚,就要重塑非洲传统文化和非洲形象,找回自我。[1]而于彬认为阿契贝是通过还原真实的非洲图景,直面殖民历史和帝国中心语言的本土化以重塑非洲的尊严。[2]于彬虽然谈及了帝国中心语言的本土化,但是对《荒原蚁丘》中帝国中心语言如何本土化以重塑非洲尊严的问题并未作论述。因此,本文要讨论的是:在经历长期的殖民统治之后的非洲,是怎样通过语言的去殖民化实现思想的去殖民化,最终重构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
20世纪中后期,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虽然已在国家主权上获得独立,而作为殖民遗产、代表帝国中心的“真理”“秩序” 和 “真实性”的语言文化却植根于殖民地人民的社会生活中,继续统治着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和文化。因此,找寻他们已经边缘化的语言和断裂的历史,重构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成为殖民地人民的首要任务,而这一重任毫无保留地落到了本土作家的肩上。然而作家的书写需要语言,继而如何对待帝国殖民语言遗产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许多作家主张用殖民前的语言进行创作,“通过‘土著’的声音来寻求 ‘真实的’ 灵感”,[3]26摒弃他们的殖民特色,实现文化和主权的完全独立。然而,因为后殖民社会文化融合的不可避免性和回归殖民前语言创作的不可能性,另外一些作家则认为后殖民写作要重构帝国中心的语言,将其重置于殖民后的本土文化话语之中,而且应将这一殖民遗产视为后殖民作家创作的特殊力量的源泉。显然,阿契贝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认为不但要掌握帝国中心的语言,而且要将其改写成一种新的英语以表达自己的文化经历,正如他所言,“于我而言,没有别的选择。既然已赋予我这种语言,那我也愿意使用...我觉得英语完全能承载我作为非洲人的经历。但是这种英语必须是一种新的英语,不但始终与英语的传统保持密切联系,而且通过改变(altered)又能适用于表达非洲的文化环境”。[4]阿契贝这里所说的“改变”,就是对帝国中心语言的弃用和挪用。弃用是对标准英语“优势的摒弃和否定,是对都市权力凌驾于沟通方式之上的拒斥,是对帝国文化类别的拒绝,包括其美学、规范性和‘正确’用法的虚拟标准,以及渗透在文字中的传统和固定含义的假设。挪用和重构帝国中心语言,这是一个获得并重塑语言新用途的过程,它标志着这一语言脱离了殖民优势地位。通过挪用,语言被拿来承载自己的文化经历”“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灵”。[3]34《荒原蚁丘》中阿契贝在标准英语中通过直接嵌入未被翻译的词汇,将伊博语句法和英语词汇相融合,以及方言变形音译等策略对帝国中心语言进行重写和改写,一方面彰显了文化之间差异,另一方面说明他使用的“英语”即地方英语,是有别于标准英语的一种“新英语”,从而对帝国中心语言进行一定程度的颠覆和达到重塑非洲文化身份和特征的目的。
二 嵌入本土词汇
在文本中有选择性地直接使用未被翻译的本土语言词汇,目的在于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从而阐明话语在诠释文化概念时的重要性。在阿契贝的《荒原蚁丘》中,最明显的语言特征之一就是将伊博族语言中的词汇不加注释或者不经翻译地嵌入到英语写作中。直接在英语文本中嵌入的本土词汇本身承载着本土人民的文化经验,而且这种文化经验是由本土环境形成的,是本民族所特有的。如表示着装的词汇danshiki, 指的是美国、非洲西部和加勒比等国家和地区黑人穿的短袖花套衫,lappa尤指利比里亚等非洲国家妇女所使用的缠腰条布,在领口,胸部,袖口和褶边处都绣了白色精巧图案的连衣裙adire;又如非洲尼日利亚人作为主食的“garri”“cocoyam”,与玉米一起吃的一种水果“ube”, 以及非洲人都喜欢的可乐果 “kolanut”。又如阿契贝在文本中穿插使用的伊博语词汇,“kabu kaboo” 指在社交场合“被冷落的人,被晾在一边的人”“jagajaga person” 指“寒碜的人、老派的人”或 “吝啬鬼”,“女士”称作 “ogli”,“先生,大人物” 称作 “oga”,以及西非国家尤指小孩的“pickin” 等。这些词语的使用明确地说明了小说所使用的语言是“他者”的语言,是不同于帝国中心语言的。而嵌入“Nneka” (超越一切的母亲的纳南卡),“Uwa-t’uwa”(一个世界里的世界里的世界),以及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口语“Kabisa”(就这么办, 到此为止),“Isé (是),名词wahala (麻烦, 搞糟的事情)这些不加注解的词汇不仅彰显了伊博族的文化特性,而且迫使读者参与到赋予这些词意义的文化领域。注解的缺位使读者不得不从连续的会话语境中去理解这些词的基本意义,但是如要获知更深层次的意义则需要读者关注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阿契贝使用这种不经翻译的伊博词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构成了后殖民话语的特殊符号,它们展现着非洲文化的真实性。从而将这些伊博词语确立为代表伊博文化的文化符号,以此表现出帝国中心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这种注解的缺位构建文化之间的差异,把隐藏在注解中的“他性”更加明朗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注解的弃用“把语言从文化真实性的神话解脱出来,表明了语境对语义的至关重要性”。[3]64
另外,文化源头上的差异也通过注解的缺位表现出来,如伊肯在巴萨大学做演讲时打趣说, 他未来的岳母是一位女商贩,她在盖勒市场上买扎染的布(tie-die cloth), 而且他可以将她所有的货品都顶在头上( in one head-load) ; 以及克里斯在逃亡时所见到的“原木窗户”(plain-board window),与海边新富们的宏伟建筑形成鲜明对比的“铁皮顶水泥墙的房子”(iron-roofed and cement-walled houses),外层刷一层水泥的泥土墙的铁皮顶屋子(iron roofs on the shoulders of mud walls plastered over with cement),“微红土质的墙”(reddish earth walls)和“圆顶草舍”(round thatched huts),这些都是后殖民时代的尼日利亚所特有的经历: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混杂。作者直接对本地的真实经历进行描述,其目的在于说明,虽然用的是帝国中心的语言,但是因为所描述文化环境不同,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也就不同。阿契贝对英语的这种挪用,否定了帝国中心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真实性”,凸显本土文化的身份,而且使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加隐秘化了。
三 伊博语句法和英语词汇相融合
在《荒原蚁丘》中,除了直接嵌入未经翻译的本民族言的词汇而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以凸显文化差异之外,作者还融合伊博语言和英语两种语言的结构,将伊博语言的句法结构引入到英语中,而这两种语言结构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中。例如,一名出租车司机从他在工会的中央委员会的朋友那里得知伊肯是国家公报的编辑,曾经写文章揭露肮脏不堪的出租车场地,因此改善了出租车的停车环境,便一起特地到伊肯家中表达敬意时,并对他们登门致谢的原因做了陈述:
I want answer that question which Madam ask my friend: to call one thing we done read for Gazette. Me self I fit call hundred things but time no dey. So I go talk about the one every taxi-driver know well well. Before before, the place we get Central Taxi Park for Slaughterhouse Road de smell pass nyarsh. Na there every cattle them want kill come pass him last shit, since time dem born my grandfather. Na him this oga take him pen write , write, write sotay City Council wey de sleep come wake up and bring bulldozer and throway every rubbish and clean the place well well. So that if you park your taxi there you no fit get bellyache like before, or cover your nose with cloth. Even the place so clean now that if the akara wey you de chop fall down for road you fit pick am up and throw for mouth. Na this oga we sidon quiet so na him do am. Na him make I follow my friend come salute am. Madam, I beg you, make you de look am well. Na important personality for this country.’
......That day I come pick madam from here I think say them make small quarrel.....’[5]131
这段文字中体现了地方英语的特点,动词want后接动词原型,want answer,want kill;过去时用现在时表示:ask, get, take 在句中本应该为 asked,got,和took;重复使用副词:know well well,beforebefore,look am well well;两个实意动词连用,之间无连词或者不定式to连接:come wake up,come pass,come salute,come pick;no否定动词:no fit get,no worry;介词for的通用,以介词for代替介词in,on,into,about;不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如for Gazette--in the Gazette, for Slaughterhouse Road--on the Slaughterhouse Road,make small quarrel--make a small quarrel;形容词用作副词:sidon quiet;另外,动词用作形容词,once battery de give trouble you suppose to buy new one,代词宾格用作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或者代词主格用作宾格也比较常见。这些表达都是受到伊博语表达习惯的影响,都不符合标准英语的表达习惯,但确实又都是用英语表达出来的。阿契贝用伊博语的句法结构对标准语进行颠覆性的改造,用na 代替主语和系动词,done+v. 原型表示现在完成时态;de+v. 原型表示一般现在时态;go+v. 原型/ go+de+v. 原型表示将来时态,不仅解构了体现权力结构的英国英语语法,而且体现了语言变形的转喻作用。这种弃用“英国英语”“标准”规范的策略,在体现差异的同时又保留了便于理解的相似性。
四 方言变形音译
变形音译是将伊博语言的声音和节奏纳入英语中,也是英语变形保留便于理解的相似性的一种体现,其作用依然是转喻的。《荒原蚁丘》中,伊肯和他女友艾勒瓦的对话中,这种英语变形和“标准”英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语言是一种人类行为,言说的方式决定了言说者的身份和地位:
Look here, Elewa, I don’t like people being difficult for no reason at all. I explained this whole thing to you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Didn’t I?
You explain what? I beg you, no make me vex...Imagine! Hmm! But woman done chop sand for this world-o...Imagine! But na we de causam; na we own fault. If I no kuku bring my stupid nyarsh come dump for your bedroom you for de kick me about like I be football? I no blame you. At all.
.......
The woman dem massacre for Motor Park last week na you killam.
......Nobody will kill you, Elewa. Why you no drive me home yourself if say you know arm robbers done finish for Bassa. Make you go siddon.
I can’t take you home because my battery is down. I have told you that twenty times already.[5]31-32
这里作者用英语变形的转喻表现了一场恋人之间的争吵,依肯一再强调他已经解释过了,不理解艾勒瓦不依不饶的责问,体现了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权力话语的不平等。而艾勒瓦的抱怨和责问是对男权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反抗。事实上,依肯所讲的标准英语是未受教育的艾勒瓦所不能及的,这本身就是权力话语的代表,是阶级、身份和地位的体现。然而,作者安排艾勒瓦用地方英语言说自己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英语“标准”的拒斥,对标准英语所承载的不平等的价值观的否定。除了标准英语和地方方言的相互穿插使用之外,变化英语文字的拼写方法使其具有地方口音感,也是阿契贝对语言进行挪用的技巧之一。如比阿特丽丝和“阁下”派去接她的士兵之间的对话,这种变换文字的拼写方法的特点就十分的明显:
...... she came to the door of the bedroom to inform me that one soja-man from President house de for door; he say na President sendam make he bring madam.
Tellam make he siddon, I said, I de nearly ready.
......
No be like dat madam, he said gallantly. ..... She tell me make I siddon, she even ask wetin I wan drink. ...... Na me one refuse for siddon. You know this soja work na stand-stand work e be.
.....
Guest House for Abichi Lake na there dem say make I take you. And dat must correct because why? The President de there since yesterday. He no dey for Palace at all.[5]67
这种变形音译的策略将标准英语转换成具有伊博语口语的声音节奏的地方英语,不仅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能力,而且也是作者对帝国中心语言掌控的能力的象征。此外,这种语言变形表现了强烈的颠覆性,将地方英语挪用为重要的文化话语,并无情地将边缘性作为一种规范。从而避免在用别人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文化经历时,被其所承载的文化“真实性”所湮灭。作者通过语符之间的转换,生成文化差异和文化挪用的俗语来宣称,自己使用的“英语”是不同于帝国中心的英语。地方英语和标准英语并存,并不断地对英国英语“标准”的权威性加以质疑和否定,将自身确立为一种对照性或对抗性话语,从而说明了两种对立言说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帝国中心所认为的“不真实的”和“边缘的”概念都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地方英语文学文本中使用的方言口语的词汇、语法形式本身就是真实性体现”。[3]37
五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标准英语的挪用策略,将帝国中心语言移植到殖民地的文化语境中,将英国英语(English literature)逐渐变为地方英语(english literature),避免了完全使用别人的语言表达自己文化经历的尴尬与不适,使地方英语成为一种对抗话语。不仅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否定了帝国中心语言承载文化“真实性”的神话。证实了使用地方英语书写的可操作性,成功地将地方英语挪用为文化话语,从而实现了重塑本民族的文化身份的目标。
[1]付文丽.从《荒原蚁丘》看钦努阿·阿契贝对本土文化身份的建构[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4): 116-117.
[2]于彬.重塑非洲的尊严——阿契贝的殖民批评与反殖民书写[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2:1-28.
[3]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 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理论与实践[M].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Achebe·Chinua. 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M]. London : Heinemann. 1975:69.
[5]Achebe·Chinua.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M]. Penguin Books. 1987.
[责任编辑贺良林]
Decolonization: Appropriation and Abrog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enter in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TANG Yan-f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In the novel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the author rewrites the metropolitan language --- English by directly using untranslated words of Igbo language, fusing the syntax of Igbo language into the lexical forms of English, and transcribing the English into dialect forms. Such rewriting has two purposes, one is to illustrate that the “english” he uses is “a new english”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tandard English. The second is to declare that the use of vernacular, Igbo words and syntax themselves give expression to the African cultural authenticity. By appropriating and abrogating the privilege of the standard English, the author subverts the cultural “authenticity”and “centrality” that the standard English represents and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reconstructing the African cultural identity.
Decolonization; Appropriation; Abrogation;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I106
A
1008-9128(2017)01-0072-04
10.13963/j.cnki.hhuxb.2017.01.021
2016-03-11
唐晏凤(1986-),女,云南昭通人,硕士生,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