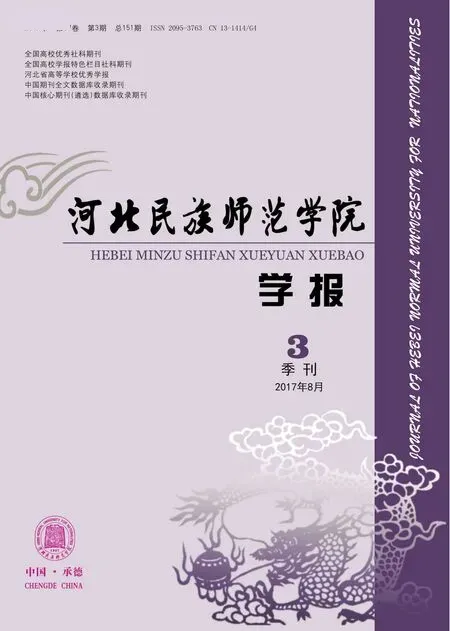论纳兰性德词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差异
罗 茜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论纳兰性德词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差异
罗 茜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及其创作实践之间有诸多吻合,但细究可见,纳兰性德重比兴讲寄托的词学主张和其直抒性灵的创作实践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与矛盾。这些差异的形成来自于纳兰性德对儒家诗教的接受,及其提高词体地位的主张,更受到其个人性情和生活经历的影响。
纳兰性德;词学理论;创作实践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与同时期的浙西词派盟主朱彝尊、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并称为“清初词坛三大家”,是清词中兴的重要力量。晚清词家况周颐把纳兰性德誉为“国初第一词人”[1],王国维更是称赞他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2]。纳兰性德以词作名世,因此研究者多关注其词作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以及纳兰生平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始有论者开始关注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并探究其词学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毋庸置疑,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及其创作实践之间有着诸多吻合,但细究可见,两者之间亦存在着一些差异与矛盾。也就是说,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与其创作实践并不是完全重合,而是存在着若干偏离。本文就将着眼于这些偏离及其成因的探讨。
一、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及其价值
纳兰性德涉及文艺理论的文章主要有《原诗》《赋论》《填词》《名家绝句钞序》《渌水亭宴集诗序》《与梁药亭书》《与韩元少书》,以及散见于《渌水亭杂识》的若干断片式的论述。这些论述虽然短小零散,却涉及到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文学的发展,文学的体裁,文学的风格和表现技巧等一系列问题。然而,由于其未曾像朱彝尊、陈维崧等人那样开宗立派,加上其英年早逝时间所限未能形成系统的创作理论,因此纳兰性德的文艺思想往往较少得到关注。
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尊词体;重比兴;主情致;求独创。
元明两代,词学衰微而曲学兴起。到了清代,词学中兴,伴随着词的创作盛况的出现,不少词人和词论家开始制造舆论,竭力为词体争取历史地位。与纳兰性德同时期的浙西词派盟主朱彝尊、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都曾致力于词体地位的提高。朱彝尊通过论证词体特性来说明词之不可或缺,他认为词“盖有诗之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3],指出了词善于表达诗之难以表达的内容。然而,他却没能走出词为“小技”的传统看法,并且认为词只是“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4]。因此,在尊词体方面,朱彝尊显得较为保守。而阳羡派领袖陈维崧则是个激进的尊词体者。他竭力提高词体的地位,不过与朱彝尊不同,他认为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为经为史,曰诗曰词”,“谅无异辙”[5],词同经、史、诗、赋一样,异曲同工,没有贵贱之分。他把词推尊至经和史的地位,认为词能“存经存史”[5],批判了“词为小道”和“词为艳科”的观点。陈维崧的观点虽然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但其论证却失之单薄,缺乏说服力。
纳兰性德则是从文体的发展演变和词的渊源上来为词张目。他认为“《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赋变而为乐府,乐府之流漫浸淫而为词曲”[6],“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7]纳兰性德认为词的渊源高于律诗,可以上溯到《诗经》。他注意到《诗三百》“句读参差”“换头转韵”的现象与词的格律、句读、用韵等形式体制方面的血缘关系。可见词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加之脱胎于乐府的声律音韵,使之具备了独特的艺术形式而与其他文体并行于世,这就批判了以词为“诗余”的世俗之见,把词从传统的“诗余”的附庸地位推举为超越近体格律诗而直接上承《诗经》和古乐府的正宗嫡派。此外,纳兰性德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肯定词体。严绳孙《祭文》中曾说纳兰性德“每言诗词,同古所尚,古诗长短,即词之创,南唐北宋,波澜特壮,亦犹诗律,至唐而畅,屈为诗余,斯论未当”[8]。纳兰性德认为词是诗亡之后继而兴起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文体发展链条上自足的一环,“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9]。这些论述清楚地勾勒出诗词兴废的基本脉络。纳兰性德把词放在与诗、骚、赋、乐府同等的地位,从文学发展的高度来肯定词体、推尊词体的词学思想,显然要高于朱彝尊虽重视词体的地位,但仍执守“词者诗之余”,把词当做是“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的“小道”之偏见。与陈维崧仅从词“存经存史”的功用来肯定词体,缺乏论据地提高词的地位相比,也显然更胜一筹。
“重比兴”是纳兰性德词学思想的第二个方面。他在《渌水亭杂识》中云:
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辞从《国风》出,纯用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板腐少味。[9]
纳兰性德认为比兴是自“国风”以来一直为历代作家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应该积极倡导。他认为唐人诗之所以高于宋诗和明诗,就在于其继承了《风》《骚》的传统,多用比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比兴作为古老的诗学观念,兼有比喻和寄托两层含义。纳兰性德所言比兴,强调于寄托和“风人之旨”。 他认为,词既为诗之后继而非诗之余绪,就应该接续《诗经》传统,重比兴、讲寄托、抒忧患,以“风人”为指归: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风蜡红巾无限泪。芒鞋心事杜陵知,只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7]
在这首以《填词》为名的诗歌中,纳兰性德有意把词体与《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教传统联系起来,认为词的创作应该继承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需要“托意比兴”,寓“风人之旨”,词人不必把这二者视为诗家专有,而应措意于此。屈原的《离骚》,描写美人香草、春花秋月,以寄托无限的忠君爱国之思。“美人香草”已成为忠君爱国的传统比兴意象。“芒鞋心事”出于杜甫的《述怀》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寄托了杜甫忠君爱国的情怀。纳兰性德力尊屈、杜,赞赏他们的“可怜春”“无限泪”及“芒鞋心事”,均为表明填词跟作诗一样,要以比兴之法寄托作者的理想、追求和性情,故而说“比兴此焉托”。纳兰性德认为世人轻视填词,并非词体本身之过错,乃俗眼不明作词也要有“风人之旨”的缘故;若昧于此理,非独词落下乘,诗亦如此。诗词创作必须“意有寄托”,才能“使故事灵”“高远有味”。
所谓“风人之旨”,是指诗歌创作的社会意义而言。即诗人应宅心忠厚,关心世事,作诗应存微婉深奥、若隐若现的讽劝之意,这是传统的儒家诗教。从“风人之旨”的现实主义出发,纳兰性德认为要致力于“忧患作”。这与同时期的朱彝尊是完全相反的看法。朱彝尊认为“黎子曰:‘欢娱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娱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4]在词作为“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的年代,朱彝尊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对词体的普遍看法。而纳兰性德强调填词必用比兴之法,寄托作者的理想、追求和不平,抒发自家性情,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性情,是纳兰性德词学思想的核心。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为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9]
中国诗歌自古就有言志说和缘情说。“诗言志”是就诗歌的社会功用而言,强调诗人运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志或思想。“诗缘情”出自陆机的《文赋》,是就诗歌的抒情特点而言的,强调诗歌主要用于表达作者的感情。作为寄情写意的诗歌作品,言志和缘情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纳兰性德接受了儒家的诗教传统,出自《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构成了纳兰性德性情说的内在精神。但作诗光有“性情”和“礼义”是不够的,诗人还必须有“才”和“学”。纳兰性德认为诗人有了“才”,才能挥拓自如地抒写性情,表达礼义;有了“学”,写出来的诗才能深刻而不浅薄,没有杜撰的痕迹。所谓“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一语道破了“才”“学”对于诗人的重要性。但纳兰性德认为创作虽不废才学,但必须以言情为本,才学不能妨碍情志的表现。如果离开了抒写性情、言志达义,单纯地去驰骋“才”与“学”,在纳兰性德看来,就是走上了诗歌创作的歧途。于诗,他批评韩愈逞才,苏轼使学;于词,他认为苏轼诗伤于学,词伤于才,不如辛弃疾言情自然真切。
正基于这一词学主张,纳兰提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9]
“贵重”“适用”和“烟水迷离”的境界,成为纳兰性德词学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与梁药亭书》中说:“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一个“情”字,一个“致”字正是纳兰性德毕生填词追求的目标,他从致语、言情、音调三个方面肯定了《花间》词,这些是其“贵重”的内容,但纳兰性德填词要求有比兴,有寄托写出真性情,强调富于意趣地表现真情实感,肯定情感因素在词创作里的中心地位,词应该着重抒发感情,表现感情,要具有“风人之旨。”这些方面、《花间》词显示出了明显的不足,故被认为“不适用”。《花间》词婉雅思深,言情入微,音调铿锵,宋词则长于寄托性情心志,这就较《花间》词适用。所以他推崇李后主,“也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因为后主词能写真情,擅白描,超逸自然。南唐、北宋词大都真率自然,朴拙浑厚,很少典丽藻饰,较为适合其“艳”而“悲”而“雅”的标准。
纳兰十分鄙视文坛临摹仿效的陋习。《原诗》一文,劈头就说:
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有高髻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其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老之衣冠,又成积习矣。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岂不悲哉![10]
纳兰把专事模仿之徒比喻为新丰鸡犬,鲍老衣冠,矮子观场,是切中时弊的金玉良言。明代以及清初,因袭模仿的颓风相当盛行。明代起伏的复古风,标门立户风,清初的忽而宗唐忽而宗宋风,严重地阻碍了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不能不让有识之士深恶痛绝。恰如纳兰所言:“自《草堂》《词统》诸选出,为世脍炙,陈陈相因,不意铜仙金掌中,竟有尘羹涂饭,而俗人动以当行本色诩之,能不齿冷哉。”[9]
纳兰在尖锐批判模仿颓风的同时,热情呼唤文学的独创精神,他认为诗歌创作应遵循“诗之本”——述志言情的宗旨,象陶、谢、李、杜那样,从自己身世经历、生活感受、性格气质出发,创作出自有面目的作品。诗人不必拘于宗唐宗宋,而要勇于破“积习”“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然而,纳兰强调创新但并非反对继承,他对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原诗》在抨击了“因袭模仿颓风”之后说:
客曰:“然则诗可无师承乎?”曰:“何可无也?杜老不云乎:‘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凡《骚》《雅》以来,皆汝师也。今之为唐为宋者,皆伪体也。能别裁之,而勿为所误,则诗承得矣!”[10]
在《渌水亭杂识》中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这两句话表明纳兰提倡的创新,并不是排斥继承的创新,并不是要割断历史。相反,他认为,风雅以来的一切优秀传统,都应当学习,古人的一切有益的创作经验都应汲取。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种盲目的崇古仿古,而又标门立户,专门模仿某人某派的偏狭态度,如明代的前后七子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形而上学的主张,这些人拜倒在他们崇拜的古人的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终生在乳母胸前过日。”他们的“师古”不是学习古人成功的创作经验的精髓,而只是师其皮毛和形式、不继承古人进而超越古人,而是做了古人的奴仆。纳兰认为学习古人,必须如诗圣杜甫那样“转益多师”,善于“别裁伪体”。有了这样的科学态度,才能博采众长,脱颖而出,风格独具,创作出自有面目的创新之作。
“艺贵独创”的思想,古已有之,不是纳兰的发明。他的贡献在于结合当时的文学创作实际,有的放矢,大声疾呼,救治时弊。在清初的纷纭杂沓的文艺思潮中,具有积极意义。
二、比兴寄托与直抒性灵: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一位作家的作品,往往实践着其文学思想。可以说是其文学理论指导着创作的开展,也可以说是其文学理论来源于创作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对比纳兰性德的词学理论和其词作创作,可以发现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融合一致的。
例如,纳兰词论“主性情”,其词正是有着真切自然、以情动人的特质。无论是“知否那人心,旧恨新欢相半。谁见,谁见?珊枕泪痕红泫”(《如梦令》)“彤云久绝飞琼宇,人在谁边,人在谁边?今夜玉清眠不眠?(《采桑子》)“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欢期,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采桑子》)的相思曲,还是“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翦银灯自泼茶”(《沁园春·代悼亡》)“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缸”(《青山湿遍·悼亡》)“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浣溪沙》)的悼亡词,抑或是“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他生里”(《金缕曲·赠梁汾》)“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金缕曲·简梁汾》)的赠友词,都体现了纳兰“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的词学主张。
又如,纳兰性德主张“求独创”,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点。或许是由于才情、气质的关系,纳兰性德在清代著名词人中应该说是受“花间派”影响较深的一位。纳兰性德将自己经常读书和与好友、文士雅集的处所自题为“花间草堂”,其对花间词之推崇即可显见。但纳兰并未因此落人窠臼,陷入苑囿,而是在继承的同时,非常注重创新,表现出“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10]的强烈愿望。
虽然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和其创作实践有着诸多吻合,但是其中亦存在若干差异与不平衡。如果用纳兰性德的创作实践来检验他“重比兴”的词学思想,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差异。
悼亡词是纳兰性德词作的一大主题。用词来抒写痛思之意、哀悼之情,北宋苏轼开其端,而纳兰性德可谓集其大成者。在纳兰的笔下,悼亡词有了另一种表现,即以白描为形式,以真情为内容,彻骨的哀痛、绵绵的思念、无尽的清泪直接流露。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共银。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咫尺玉沟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斜阳。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尽寸裂柔肠。(《青衫湿遍》)
这首词作于卢氏亡故后半月,是性德第一首悼念亡妻之作。“词情凄惋哀怨,真可说是一曲声声血,字字泪的悲歌惋唱,读来令人为之泣下”[11]。上片起笔即“青衫湿遍”,直接道出伤痛而又难忘之心境。紧接着叙述和回忆,如泣如诉,尽情宣泄,自然流露。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已。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金缕曲》)
开篇“此恨何时已”,直接带人进入了哀怨离恨之中,紧接着一路下来,层层深入,虚实相间,字字句句透出情恨缠绵,感情尽情宣泄却又完全出自肺腑。正如以上两首一样,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善用叙述和白描,直抒胸臆,篇篇低回缠绵,哀惋凄切,如诉如泣,如怨如恨的悼亡词,直接唱出了词人字字血泪的心声。
又如小令《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衡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聆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全首小令几近白描手法,将一位仆仆道途,顶风冒雪,深夜远行之人的身影和心态表现得生动形象。他的情词更是如此,每一首都是以极其朴素淡远之语,直接倾泄出肺腑真情,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以往写情的词作中,词家一般喜欢运用婉约绮丽的语言,而纳兰却能以自然朴实之语言情,比起“杨柳岸,晓风残月”“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诸句来更觉真切,有“不隔”之感,从而形成他独特的词风。正如王国维所评:“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人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昨夜个人曾有约,严城玉漏三更。一钩星月几疏星,夜阑犹未寝,人静鼠窥灯。 原是瞿塘风间阻,错教人恨无情。小栏杆外寂无声,几回肠断处,风动护花铃。(《临江仙》)
词写青年与姑娘的约会。夜已三更,新月如钩,疏星几点,爱人却久候不至。面对凄凉夜景,烦乱焦虑,无法入眠。纳兰性德描写失恋者心情的词,低徊婉转,别具韵味。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试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娥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金缕曲·赠梁汾》)
出生于高门的纳兰性德,称自己是不拘小节的人;身为皇帝的近臣,竟然说“缁尘京国”;对平原君礼贤下士、阮籍以青白眼待不同人,持赞赏的态度;对有才华而不得见用反遭诽谤的人,发出不平之鸣。直抒胸臆的手法,尽出肺腑之情,不假雕饰、真切自然地表达了质朴的友谊。
纵观纳兰词作,不难发现,纳兰词最大的特色,不仅不是他自己所说的意在言外的“比兴”和寄托,而是其直抒性灵的自然直接。
诚然,纳兰性德也偶而采用因物起兴,指物比事的表现手法。如写远在塞外,思念爱人的《菩萨蛮》一词:
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相催,由他好处行。 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照大旗。
词一开篇即以比兴的手法,写极自己对爱人的强烈思念之情。“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强劲的朔风吹散了三更雪,却吹不散自己对爱人思慕眷恋的缱绻之情。纳兰那首著名的悼亡诗《蝶恋花》也运用了比兴的手法: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夕夕长如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词中借明月少圆长缺、燕子呢喃、蝴蝶双栖,表达对亡妻深挚的爱情和相思的痛苦。然而,这种比兴的手法在纳兰的词作中并不多见。他的作品大多是直抒性灵,真率地写出自己的爱,自己的愁,除了少数几篇咏物之词。例如,下面的一首《眼儿媚·咏梅》:
莫把琼花比澹妆。谁似白霓裳。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冰肌玉骨天付与,兼付与凄凉。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
这首咏梅词通过赞赏白梅雅淡孤高的品格和对它孤独凄凉处境的同情,有所寄托,但并不遥深;意在言外,但不存劝讽,与其所说具有社会功能的“比兴”亦有所差距。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词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偏离呢?下面本文将讨论这个问题。
三、理论背景、权宜之计与个人因素
那么,应该怎样解释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呢?实际上,理论有其自足性,一般首先会与之前的理论有一个对话关系,或继承,或逆反,为了达到效果,一般会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而创作则和个人才气,生活经历等因素有更大关系,因此,当理论体现到创作实践中,则会显得较为温和,甚至会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这种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的不平衡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在理论上推崇汉音与儒学道统,在创作上却表现出魏响特色的曹丕,又如戏曲理论和创作往往背道而驰的李渔。和他们相比,纳兰性德的词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之间的差距,实为微小。但其差异中蕴含的某些缘由,却具有很高的讨论价值。
首先,纳兰性德对比兴传统的重视,来源于他对儒家诗教的接受。纳兰性德虽为满族词人,却系统接受了汉族儒家文化。纳兰性德出生于顺治年间,成长在康熙初年,他思想的形成与康熙初年重满用汉的政治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康熙亲政后,提出了“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推行了诏举山林隐逸、荐举博学鸿儒、重开国史馆等笼络汉族士子的措施,因此在康熙前期形成了提倡汉文化,重用汉族士子,促进满汉融合的风气,这为纳兰性德学习汉文化与结交汉族士子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纳兰性德老师徐乾学记载,纳兰性德天资聪慧,才华出众,从小喜爱读书,年岁稍长,“益肆力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古人文辞”[12]。除了得到汉人徐乾学的指点和教诲,纳兰性德还结识了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江南士人,并逐渐染上汉人风习,系统接受了儒家思想。
清初诗学对比兴传统的重视,亦对纳兰性德重视比兴的诗学观产生了影响。赋、比、兴历来被视作是《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汉儒往往把《诗经》与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自然赋、比、兴也与政教联系在一起。其中,比与刺相连,兴与美相连。这样就形成了比兴表现美刺的象征传统。到了清初,在诗学政教回归的主流中,冯班兄弟、吴乔等人均主张比兴,希望回归汉儒的比兴美刺传统。纳兰性德不可避免受到这方面影响。纳兰性德与许多优秀的汉族诗论家接触,受到他们的启发,亦推崇重视比兴的诗学观。
第二,虽然纳兰性德接受了儒家诗教观点并将比兴作为文学的重要因素,但笔者认为,这并不代表着纳兰性德真正认为比兴在词的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实际上,纳兰性德强调词要重比兴,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提高词体地位的“权宜之计”。我们知道,《诗经》成为儒家经典以后,就被偶象化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不乱,哀而不怒,温柔敦厚,这才是风人之旨,也是诗歌及一切文艺的正统一脉。纳兰性德深受儒家文化薰陶,他要为词争正统地位,也就不得不以正统的观念为武器,但这并不等于他真正服膺这一正统,把它当作自己词学思想的基点并身体力行。如果因此而说纳兰性德把继承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当作振兴词学的先决条件,认为他填词必心存风人之旨,或者据以论证纳兰词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寻找其中寄托所在,为之索隐,作种种猜侧,就将误入歧途。
实际上,虽然纳兰性德在理论上说词和诗一样应该“比兴寄托”,但是在创作中,他的诗与词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比兴寄托”明显要多。这更加显现出,纳兰性德强调词要有比兴有寄托,实际上只是一种提高词体地位的权宜之计,在实际操作中,他很清楚词与诗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别。
那么,纳兰性德为什么不“权宜”到底,将比兴作为他词作的主要方式呢?文学史上存在着两类作者,一类作者往往理论大于实践,其实践完全是在其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某种程度上其创作或者可以说是其理论的注脚,这类作者的作品,文学价值不一定高,但一般会具有较大的文学史价值。而另一类作者则是实践大于理论,他们虽然也提出理论,但其理论与其说是其创作实践的指导,不如说是其创作的总结,来源于创作实践。他们的创作不受任何理论的制约,秉承着作品至上的原则进行创作,这类作者的作品,往往比前者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而在文学史价值上常常逊于前者。纳兰性德则属于这第二类的作者。他的创作与其说是在其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不如说受到他自己的个性气质、生活经历的影响大一些。
[1]况周颐.蕙风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21.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17.
[3]朱彝尊.红盐词序[M]//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四○.
[4]朱彝尊.紫云词序[M]//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四○.
[5]陈维崧.陈迦陵文集[M].四部丛刊本:卷二.
[6]纳兰性德.赋论[M]//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十四.
[7]纳兰性德.填词[M]//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三.
[8]严绳孙.祭文[M]//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十九.
[9]纳兰性德.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十八.
[10]纳兰性德.原诗[M]//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十四.
[11]张秉戌.纳兰词笺注[M].北京出版社,1996.
[12]徐乾学.墓志铭[M]//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十九.
Abstract:Nalan Xingde’s Ci theory and his writing practice have been consistent in many aspects, but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his Ci writing practice and Ci theory. The formation of these differences are from the in fl uence of Confucian poetics that Nalan accepted, his idea of improving the position of Ci, and also the individual temperament and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Nalan Xingde; Ci theory; writing practice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alan Xingde’s Ci Theory and Writing Practice
LUO Xi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I207.23
A
2095-3763(2017)-0021-07
10.16729/j.cnki.jhnun.2017.03.004
2017-06-26
罗茜(1987- ),女,江西赣州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