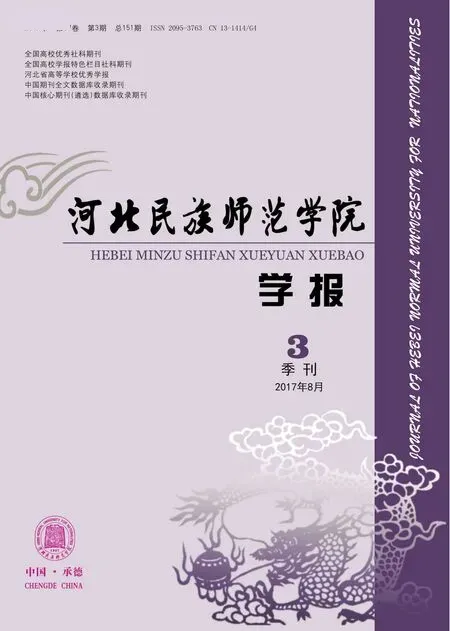论赵大年《公主的女儿》的京味儿语言特色
王晓燕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传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论赵大年《公主的女儿》的京味儿语言特色
王晓燕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传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满族作家赵大年的创作具有浓厚的京味儿艺术。在其小说《公主的女儿》中表现尤为突出。小说以北京特有的京味儿语言为叙述载体,以遗民独特的心理及其日常文化为叙述对象,既有满族本民族的语言风格,又融合了北京汉民族的语言说话方式。呈现出一种京腔京韵的艺术魅力,彰显了满族小说的独特的文学风格与审美特性。
《公主的女儿》;京白语体; 京味儿幽默
20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变幻,文学思潮峰涌,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作为满清贵族后裔的赵大年,在其创作中以游离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满清没落贵族后裔为对象,通过北京特有的语言风格,着重表现满族遗民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赵大年(1931-),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一生经历坎坷丰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文革,被下放过农村,曾在北京市农机局工作,这些经历使他更加熟悉知识分子和科技界,也为他之后的创作提供了厚实的生活基础。他从1980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女战俘的遭遇》《大撤退》,中篇小说《公主和女儿》,短篇小说《女帮办》等。其中《公主的女儿》是赵大年作为满族作家的一部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力作。作品描写了清代宗室后裔一家三代的曲折遭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社会历史生活的变迁。尽管作为满族后裔,他所承袭的是来自关外的满族先人奋斗留下的业绩,但面对京城浓厚的京味儿文化,赵大年在其小说创作中,无不体现“京味儿”的艺术性。关于“京味儿”, 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和界定。崔志远认为“京味小说指的是以北京市井生活为题材,以独特的京味语言描绘出北京独特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的小说创作。”[1]
赵园则认为,“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2]P14概括来讲,“京味儿”的内涵,首先体现在要具有浓郁的北京气息,反映北京文化及北京人文心理的内涵特性;其次,京味儿体现的是一种人的生活体验方式。“京味”作为对北京文学的概括,其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运用北京语言;二,描写北京的人和事;三,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四,挖掘北京人特有的心理素质”。[3]P79-80这四点中,其中首要的便是语言。如若没有这一条,便无法生动的描写北京风土人情,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更不能恰如其分的体现 “京味儿”艺术。“京味文学最外在、最鲜明的特征便是语言。”[4]p160可见,“京味儿”语言对于满族“京味儿”文学的重要性。赵大年作为20世纪重要的满族小说家之一,其语言艺术在清王朝定都北京的历史背景下形成,既有本民族的语言风格,又融合了北京汉民族的语言说话方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京味儿”的语言艺术,彰显了满族小说的独特的文学风格与审美特性。
一、京白语体
千百年来,中原文坛多视白话为粗俗之物,难登大雅之堂外,故多避之。17世纪中叶,满族进入中原,在之后的两三百年内,随着对汉族文化接触的与日俱增,满族中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也逐渐增多。但由于满族人在文学修养与艺术品味与汉族文化的差异,所以在创作中对语言的运用主要以天然、浑朴著称。加之清王朝以北京为主要的生活地,其语言表达更是与京味儿语言息息相关,这种简单直白的白话语言用的多是些平朴流畅浑似坊间言谈的白话语词。但经过满族作家们长期对自身民族特性的继承与对北京文化的接受与打磨,满族作家们营造出了新的价值观,体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对北京语言的接受及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中,满族文学作为满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语言。满人擅口语表达,“满人最会说话”。[5]p171这种京白语体的艺术表现一直延续至20世纪的满族文学。
20世纪的满族小说家,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文学思潮、战争、文革等一系列的政治的、历史的缘由影响,其语言也更加平实、白话的反应社会变化,人情风俗。赵大年作为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满族小说家,他的语言更是继承了这种京白语体的艺术形式,小说中更凸显出北京话直白、口语化、随性等特点,形成了其小说的京腔京韵语言特色。
《公主的女儿》是赵大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一经发表便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赵大年小说中的京腔京韵在这部作品中体现的尤其精到。小说主要描写了满族后裔祖孙三代公主的生活经历,以北京方言为主要的叙述方式,真实再现了满族后裔在历史历史变迁中的沉浮命运。在北京这座文明古都,每一种行业,每一种职业,每一类人物,都自有其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独特的语言,并历史的积累中散发着北京市民特有的生活气息和文化底蕴。赵大年精准的把握了这一特点。他在小说创作中,十分注意把握不同行业及不同人物身份的语言,比如车夫、裁缝、官员、小姐、商人等各有各的语言习惯。作者通过设置符合每个人不同的身份与性格的个性话语,把这三代人在鲜活的描绘出来,真切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老公主叶紫云,是赫赫有名的叶赫那拉氏的后代,被成为“和硕格格”,用汉语来说就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她的语言总是带有象征地位的权威,又有被生活经历打磨的平实。比如谈到,按照规矩,该如何感谢大红门里的恩人时,叶紫云一听“规矩”,便来了神气儿,在床上盘腿一坐,字句清楚的说道:“按老规矩,你要有(钱),送额送匾、整猪整羊不为过;你要清寒,登门磕头,几支檀香、几朵绢花不为少。这新社会嘛。不如叫上你女婿,一块走到大红门里去三鞠躬吧!”[6]p140
黄秋萍是“大红门”里的一个裁缝,作为一个精通顾客心理,又十分聪明细心的裁缝,黄秋萍的言行举止精明、世故、老练,…….而同时作为公主的后裔,在身居北京这座城,她又时不时的拿“咱是北京人,要讲礼貌!”[6]p155“咱们都是北京人,在公共厕所见面都得说两句儿客气话儿”[6]p162这样的京腔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她的言语既市井生活,又清高自尊,在进入大红门后,儿子曾告诫她别到后院去,但她进入院子里,心理却想“为什么不能去?这是我的家。”[6]p154这种对皇家居地主人翁的感情,也许只有曾身居于此的人才能有吧!通过叶紫云和黄秋萍这两个人物及其语言习惯我们可以略窥一些北京市民所特有的性格,如爱面子,重排场,怕被别人瞧不起;注重礼仪,重礼尚往来,念恩情等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者”,正是通过这样鲜活的人物形象,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北京社会历史的变迁,这其中也包含了作为一名满族后裔对先辈文化遗失的惋惜与悲凉之情,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和喜爱。
赵大年的小说,没有用大量的笔墨去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但却在特定的场景中,通过三言五语的和盘托出,将最常见的家常话点石成金,赋予其无限的表现力。在写张铁腿与余院长吃饭,张铁腿说:“好嘞,我一不拿你当首长,二不拿你当恩人,要问我的祖宗三代,你有啥只管问吧!对你,我信得过!保证竹筒倒豆子,一粒儿不留。”[6]p169从吃饭这一特定的场景中,三五言语便将张铁腿这一人物性格刻画出来。作为娶了了公主的一个普通蹬三轮儿的底层劳力,张铁腿看似没文化,不会讲话,但在给余虎讲解家世的过程中的典故都经得住历史学家推敲考证。叶明珠是第三代公主,在她的身上有新社会青年的思想,而同时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把自己当成全家的“小不点儿”他的语言嬉笑怒骂,自然天真,又不自欺欺人。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一味地照搬生活语言的原始样态,而是在其小说中,根据人物的身份心境,通过多层面的,多角度对人物语言的设置,选取雅、俗、文、野各不一样的口语让人物去说,从而更加真实全面的塑造人物形象。小说对于黄允中的描写不多,但通过其语言,鲜活的将这一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了。黄允中看到张铁腿被调派,说:“你地道儿熟,调车派活儿麻利快,早该管这摊子事儿啦!凭本事吃嘛,谁靠谁呀?”[6]p167“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新社会啦,自己没本事怎么行哩。”[6]p242“饥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6]p229小说中,这些言语,对于很少说话的黄允中这一人物来说,非常简明精道。黄允中不仅是正黄旗,还是皇室宗族的后裔,少年和青年生活在欧洲,曾在驻英公使馆工作过,有学问,会开车,能专研,是誉满全城的黄掌柜。因此,在他的语言中,既有既有对八旗子弟无知无能的腐败气息的批判,也有对自食其力肯定与赞扬。而在此,这样的京白语言的精气神配合着原文关于黄允中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故事,把这一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北京人的气质,精神,灵魂,不加任何雕琢,活脱真实的呈现出来,京味儿十足,且他语言中“儿化韵”更凸显出京话方言的清脆韵律跟诙谐气质,小说中,他虽言语少,却俨然是一个有见解,严谨且富有气韵张力的“京片子”。
赵大年在语言上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注重用京白俗语的鲜活气儿来表现人物性格的灵活。在小说中,无处不见的俚词俗语,被作者精心撷取,精准应用, 将书中的公主、裁缝、掌柜、车夫、政府官员、千金小姐、战士、保姆、小青年知识分子等等,状写的纤毫毕现。赵大年对北京口头俗语的偏好,足可印证满族文学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接受。比如“咱们”“您”“哩”“妮子”“招(惹)”“败家子儿”“经饿”“发面”“(回府)克”“半彪子”“乌拉”“软拉巴几”“和硕格格”“嚼谷”“松货”(体积大、比较小的东西)“硬货(砖瓦灰石、废铜烂铁之类)”“考工定额”等,这些都是非常口语化的北京口语表达方式,在小说中,作者随手拈来,随口而出。这种简白的小说语言,既通俗易懂,又不显得枯燥单调,使人读来朗朗上口,让人感到亲切、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话中的“您”字。北京人爱讲究场面,一般说话都彬彬有礼,话语间经常带个“您”字,这是最纯熟的北京腔调,体现了老北京市民的口头语言特点。80年代的京味小说家邓友梅曾说:“好的小说语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时代性,一个是性格化,再一个是地区特点。没有地区性的语言常常是没有特色的。”[7]
方言是一个地区独特的交流工具。任何方言都与特定的地域文化形态相关。赵大年在《公主的女儿》中,充分表现出对语言区域性特征的重视。他大量运用北京日常生活化的口语,“不仅把纯正的京味语言运用于他的人物之口,同时也熟练顺畅地应用于他自己的叙述语言之中。”[8]p168所以他笔下的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时代性、职业性等特点,并具有质朴、简练语言风格,作者往往通过简单的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并从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情世态,更能适当地糅合汉满两族的文明,在通俗的生活口语中透露出传统的文化气息,从而真实的反映了一种老北京文化,并在满族小说的京腔口语艺术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
二、京味儿幽默
20世纪的满族文学,大多以半带调侃的语气讲述满清遗少的腐朽、无能、寄生和虚荣等等心理状态和所作所为,从而批判满清文化的腐朽。而作为一名京味儿作家,赵大年与其他满族作家一样,起初都有对满族文化的批判以及文化认同的挽歌相交融的矛盾情感,但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创作主题也发生了转变,虽然也有对于满族文化的调侃与批判,但更多的是同情与惋惜。小说《公主的女儿》,所写的是满族家族在历史变迁中的景况,用京语描写自然逼真,人物命运真实明活。而在呈现历史变迁中的人物命运的同时,由于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语言在具体的表现中必然会带有一些作者的独特审美心理。维克纳格在《诗学、修辞学、风格论》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作家的创作风格离不开语言的艺术表现。赵大年自己曾把“京味儿”语言艺术定义为幽默诙谐。故而在其小说中,除了京白语体的直接、明快外,还有颇具幽默风趣的文学审美风格,使人倍感亲切,忍俊不禁。
从语言角度来看,赵大年小说的幽默诙谐首先体现在对人物名字的设置上。在《公主的女儿》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标签性的姓名,以职业命名的,比如蹬三轮儿的“张铁腿”,做衣服的“黄裁缝”、维修各种汽车的“黄掌柜”;以性格命名的,如“赖猫小姐” 叶明珠,“苦行僧”张兴;以德行行命名的,如余小虎继承了他爹余虎的“光荣传统”等等。赵大年擅于用标签性“特称”的词汇,既充分体现出人物的职业、典型性格,道德品行,又给人以亲切感,拉近了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幽默又不失人文情怀。
其次,赵大年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还体现在对幽默的环境氛围的设置中。在《公主的女儿》中,把土匪的投降与公主叶绿漪联系起来是作者独特的场景设置。战士们认为是公主叶绿漪声色俱厉地向土匪喊话,土匪头子鉴于公主的“威仪”三跪九叩的投降了。为此,指导员还为公主写了一首打油诗:
“凤凰山寨密林中,
公主擒王亦英雄!
自古战场多佳话,
枪炮隆隆谈笑声。”[6]p185
自这场战役过后,战友们对于叶绿漪这位“公主”又增添了颇多好感与认同。尽管湘西剿匪时公主喊话可谓捕风捉影,但作者却营造了幽默的氛围,在幽默之中又对叶绿漪的表现倍感赞赏。作者正是通过这样幽默的语言艺术及氛围尊重与肯定其笔下的每一个主人公,赋予他们丰富的形象和完好的灵魂。赵大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业写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满族人,他对北京的了解、观察,深刻入微,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写重大的阶级斗争或者生产斗争,而是以市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来书写北京的风土民情,通过人情事态来折射时代的光芒。所以在《公主的女儿》中,他的幽默,一方面给人以亲切感,另一方面滑稽而又不失分寸,比如对张铁腿下馆子场景的描写:
吃饭,这种最平常的事儿,也是张铁腿的一种享受。他在外蹬三轮儿,每天都会到小馆子里去吃一顿午饭。一进门,就用那瓮声瓮气儿的大嗓门嚷起来:“快快快!饿的我肚皮儿贴了脊梁骨罗!”服务员大都是认识张铁腿的,也爱跟他逗嚷:“知道你是个纸糊的驴——大嗓子眼儿,大肚量儿!今儿个想吃什么呀?”张铁腿则照例大喊一声:“不吃发面!”惹得四座欢腾。……
“咱可不是文人书生,吃一口发面馒头还得喝口汤!要照他们那样吃一顿儿,咱还敢顶着西北风蹬车出德胜门吗?哼,四两发面馒头,一泡尿就撒没啦!我是属鸡的,胃里能化石头子儿!吃发面?我恨不得一顿嚼它二斤铁蚕豆,那才是经饿哪!”[6]p228-229
这段描写,是赵大年京味儿语言艺术的精华段落。首先,通过日常口语化的对话,将张铁腿一个社会底层的老北京人儿的身份凸现出来;其次,“肚皮儿”“ 三轮儿”“ 嗓子眼儿”“ 大肚量儿”等儿化韵的使用又是京腔京韵的典型表现;再次,“一泡尿就撒没啦!”这样的看似很俗的语言,却真实的衬托出张铁腿粗犷、壮实的性格;而服务员的“知道你是个纸糊的驴——大嗓子眼儿,大肚量儿!今儿个想吃什么呀?”这句话在流畅的对话中,突出了赵大年京味儿语言的幽默滑稽的审美风格。在此,对王室后裔张铁腿这一形象的刻画,作者用辩证的思维看待这一个老北京人,一方面通过其幽默又“接地气”的语言,揭示张铁腿身上的保守、落后的小市民的气息;另一方面又通过他的自食其力的养家经历和淡然的生活作风,肯定他的进步性,并冠以他“新一代进步青年”的称号,从而塑造了一个极富北京味儿的北京老人的形象,既批判他的甚至愚昧,又赞美他那种对艺术热烈的挚爱与付出。再如,每当黄秋萍拿着皮尺给年轻人量体裁衣时,都要说一句从她八十岁父亲那里学来的风趣话儿:“奇装异服有什么不好?这四个字还是屈原发明的哪!”逗得这些青年男女开心大笑,争着说:黄阿姨真有学问。这里,既显示出黄秋萍老练,擅于抓住顾客心理的精明,又有对其风趣儿性格的赞赏。
可以说,赵大年幽默的语言风格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又是其“京味儿”艺术的重要表现。作家刘心武曾说:“一个作者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不可能社会生活的每个部分均等地起一种创作刺激作用,他的创作愿望的产生往往取决于他对社会生活的某些部分特别敏感。而这个东西是超行业的,超职业的。”[9]这是他对“生活敏感区”的解释。刘心武自己的“生活敏感区”指的就是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他将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文化深深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去。而赵大年的“生活敏感区”在于对京旗贵族遗民的关注与刻画。作者用纯正的北京话,略带幽默的语气给我们讲述了京旗遗民的生活及心理。虽然,会有遗憾、失落与惋惜,但更多的是为读者展示了一副富有底蕴的京旗族裔生活风貌。
另外,赵大年的语言的幽默还来源于对 满语谐音或者意译得到运用,在发挥行文语言多样化的同时,对于小说故事、人物的真实性给予了印证,并在对语义深意的推敲中,感受作者的幽默艺术。满族在清之后的年月里,逐渐被汉化,语言从“满汉兼”到“纯汉语”,而实际上看似“纯汉语”,却依旧带有“满汉兼”的语言风格。在满族作家的创作中,都免不了利用把或满文或汉文名称嵌入汉语中间的巧妙表达方式,从而将满汉两种语言的词汇连缀得天衣无缝。赵大年本人的姓氏便是如此。赵大年的祖上爱新觉罗袞肇浩是位王爷,由于世事变迁,他这一支子孙便都随“肇”而“赵”,改为汉姓。八旗子弟的堕落无能曾使他感慨万千,于是写了小说《公主的女儿》。小说中,具有满汉混合语性的词汇随处可见,比如“小炊巴”(打下手的)“杂合面”“布衣千金”“净室”(厕所)“回克”等。作者通过这样的谐音或者意译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描写场景,从而达到一种幽默的审美心理,使得小说语言更加生动,而又有别样的文化情趣。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语言艺术对于文学的主题,表现方式,文化内涵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文学区别与其他艺术形式的重要手段。作为典型的京味儿作家,赵大年在小说创作中,充分地借用了具有鲜明北京地域色彩的语言,并注意这种语言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意义,这一方面显示了作家对语言操纵的深厚功力,另一方面又拓展了北京方言口语的表现力。作者通过纯熟的京白语言,把极富京味的环境、故事、人物、民俗渊源等浑然一体的描绘出来,既为其小说增添了浓郁的京味儿,又在这简单的北京方言中,蕴含着深厚的民俗风情、生活情趣等;在既加强了小说通俗易懂的市民气息,又显示出京味文学所特有的亲热、简洁、爽快、风趣与幽默的特点;既是对京旗白话的发展,又体现了满族文学中京腔京韵的艺术成就,兼具华美与朴素之长,对于之后京味儿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崔志远.论京味小说[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5).
[2]赵园.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赵大年.看绿[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4]王一川.京味文学第三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关纪新.清代满族文学与“京腔京韵”[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6).
[6]赵大年.公主的女儿[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7]邓友梅.谈短篇小说创作[J].山东文学,1982(5).
[8]刘建斌.但语言情[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9]刘心武.小说创作中的几个内部规律问题——在昆明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J].滇池,1983(2).
Abstract:Manchu writer Zhao Danian’s literary creation has a thick artistic fl avor specially belongs to Beijing, which is prominent in his novel Princess’s Daughter. This novel is written in a typical Beijing dialect. Taking the special thinking style and daily culture of Manchu survivors as the object of narration, it has both the Manchu natives’ language style and that of Beijing Han people. The novel shows an artistic charm in language that specially belongs to Beijing; it also shows the special literary style and aesthetic feature of Manchu novels.
Key words:Princess’s Daughter;Beijing dialect; the humor of Beijing styl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istic charm of Beijing language in Zhao Danian’s novel Princess’s Daughter
WANG Xiao-ya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067000)
I207.9
A
2095-3763(2017)-0035-06
10.16729/j.cnki.jhnun.2017.03.006
2017-06-18
王晓燕(1986- ),女,山西阳泉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2017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项目“20世纪民族政策调整对满族文学发展的影响研究”(20170305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