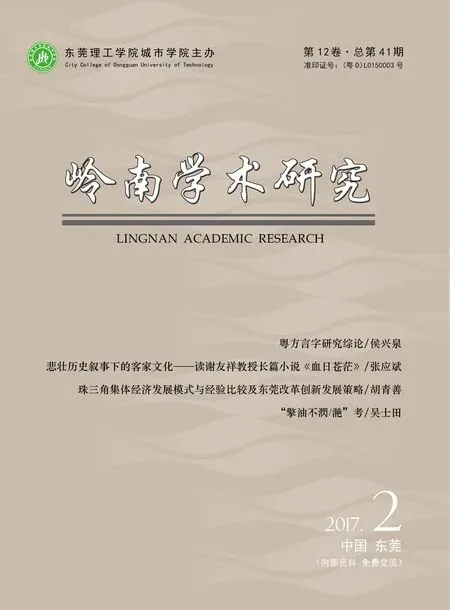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内在理路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是他其他一切批判的基础,他的宗教批判思想进程与其克服旧哲学确立新世界观的进程是内在一致的。马克思不曾纠缠于纯粹的宗教批判,相反他从对德国宗教改革不彻底性的批判开始,而后剥茧抽丝逐步深入到哲学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具体到哲学维度上,马克思在深化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实现了世界观的变革。追踪这一思想行迹,梳理其方法论脉络,对于当前搞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世界观教育都有所助益。
一、马克思宗教观的精义
(一)揭批宗教世界观
宗教力量由形成为思想体系的精神力量和组织为宗教团体的物质力量两方面构成,因此它不仅争夺着真理的化身身份,也实在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现实领域,马克思宗教批判的主旨在于使人回归人的本质,为此他聚焦的问题之一是剥开宗教世界观的信仰核心做科学检视。
宗教建构了存在于彼岸世界的至高无上、力量无限的终极神圣,掌控着此岸世界。它向人敞开永恒无限性以满足人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欲求。它将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神圣化,要求人笃信神、服从神以祈求神的宽恕与赐福。它确立了普遍的、高于人的神圣价值尺度,成为衡量人的标尺。简而言之,宗教世界观即存在神、神代表真、善、美并全知全能掌握世界,因而掌握人的命运。马克思否认神这种超越性力量的存在,只承认人在实践中改造世界和自身的命运。关于世界的本原,马克思批评上帝创世说,提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指德国-笔者注)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1]3,颠倒了的现实世界是宗教产生的土壤,裹挟着颠倒的世界观的宗教被创造出来以使从们对颠倒的国家、社会现实表示顺从,宗教转移人的注意力,将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转为对神灵与天国的关注。关于人的本原,马克思讲“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1]3,是劳动创造了人而非宗教,劳动才是人生存与发展的保障而非宗教。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一系列的虚假观念,宗教人物创造这些观念并使其他人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如宗教使人相信,灵魂(精神)是先天的,而不是通过人的实践才成为可能的。宗教作为一种非物质存在,却使物质世界在它面前低头,变成非实在,宗教被赋予道德价值权威的角色,以许诺来世的幸福来使灵魂匍匐在它的脚下,恰是苦难的尘世生活迫使无精神活力的人们匍匐在虚构的神灵面前,甘愿为其主宰,向其奉上灵魂,并奉之为价值源泉和最终归宿。马克思通过对宗教世界观的批判,揭开了宗教这种非物质存在的神秘面纱,使其显露本真面目。
(二)揭示宗教本质
学界关于马克思的宗教本质观解读纷纭。其中“鸦片论”长期占据国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流地位,一方面源于马克思揭露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3,它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1]3,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4另一方面由于列宁所下“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2]的论断,已有反对者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否定“鸦片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基石地位[3]。宗教不仅是鸦片,更是以超验形式存在的作为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不是独立的,而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1]525阶级社会中,宗教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的政治权威性衰落,意识形态功能却并未丧失,“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4],一些人据此成为宗教意识形态说的拥趸。但视宗教为意识形态揭示了其政治功能,而非对本质的把握。吕大吉提出宗教文化论,认为宗教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5]也有同样问题,即文化功能只是宗教属性的体现而非本质。基于“非理性就是神的存在”[6]的宗教非理性说不足显明马克思较启蒙思想家的区别与超越,基于宗教“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1]204的宗教异化幻觉说强调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继承,却忽视了宗教只是人的异化产物之一而非唯一,“异化”只是宗教的属性而不足以称为本质。最能代表马克思宗教本质观的当属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论断“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7]这一表述与二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1]587内在相通,互为注脚,既点明了超验性是宗教的形式规定性,又指出人间力量是宗教的现实内容。可以说,宗教是人间力量的超验形式。
马克思的宗教观连同他的哲学思想,经历着不断成熟的蜕变过程。循着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马克思对宗教世界观的批判越发透彻,对宗教本质的考察越发清晰,自身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也越发明朗。
二、马克思宗教批判的演进历程
(一)继承与发展
起自文艺复兴的对宗教神权的反对与批判,主张追求现世幸福,反对为来生而禁欲,将人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旨在恢复人的地位和权力。马克思在继承该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博士论文期间和《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将理性、“自我意识”、自由视作人和世界的准则或本质,对于宗教的危害性认识停留在不承认自我意识的至高神性层面,具有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色彩。一般认为,马克思《德法年鉴》期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初次对其无神论宗教观作了较系统阐述,该文常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奠基之作(也有反对意见),阐明了马克思对宗教社会根源和本质的一些见解。他肯定了德国宗教批判理论的彻底性表现在“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得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主张和提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的任务。[1]11但同时马克思表达了对代表着德国国家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黑格尔法哲学的不满,认为它抽象而不切实际。他指出革命理论须与革命实践相统一,彻底的德国革命依赖于无产阶级对革命理论的掌握。
(二)悖离与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指出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自我意识、绝对观念,而是物质生产,强调了解宗教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推动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因为后者的唯物主义观点——自然界是本原的,观念才是派生的——消除了黑格尔体系中自然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是派生的这一令青年黑格尔分子彷徨的矛盾。对此恩格斯有所记述:“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8]随着马克思思维广度与深度的拓展,渐渐对深深影响自身的费尔巴哈思想产生质疑,终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进行清算。他肯定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将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同时指出费尔巴哈失误在于未能进一步追击,借对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分析去理解它并促发革命,由此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错误地归结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本质,而不懂得“宗教感情”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形成了对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的全新认知,并据此判定宗教是社会的产物,必须从其世俗基础的矛盾中去理解,同文,马克思还批判费尔巴哈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作用,指出脱离实践去争论思维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决计立脚于人类社会实践去理解社会生活,到实践中去考察包含宗教问题在内的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出发,把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式进行考察,认为宗教尽管是对社会存在虚幻的、歪曲的反映,它仍然是人的历史生活的产物,研究宗教必须以现实的人和他们的活动为出发点,至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确立,其宗教观基本成型,宗教批判任务届已完成。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4完成对宗教的揭露之后,马克思转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尘世批判强化天国批判。资本主义的世俗仅是表面的,实质上其已经充斥着各种迷信。金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偶像,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偶像崇拜就是对商品、金钱、资本的狂热追求。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信息的畅通并未使祛魅成为必然,相反却使造神变得更容易:“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由于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9]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求诸于宗教,特别是新教,但宗教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不过是使矫饰问题使之合理化的一套世界观。资本主义试图将宗教与自己绑在一起求得支持,这种把戏被马克思无情拆穿,剩余价值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存续的世俗基础的内在矛盾,宗教不过是“一种让人们沉溺于资本主义之中的药品”。马克思看来,不存在脱离现实的至高理念,不存在抽象的永恒规律,任何规律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也不例外,他预言资本主义社会终将为科学社会主义所取代,届时人类将获得解放,包括宗教解放。
三、马克思宗教批判的方法之维
马克思先破后立,在解构宗教中积极地建构了积极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那么,马克思采用了哪些科学依据、哲学依据和人类实践依据,又是循着怎样的方法路径破除宗教及其世界观呢?
(一)以利益为切入口揭示宗教产生根源
为什么缺乏科学依据的宗教会产生,人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幻想进入自己头脑并信仰?马克思不承认神秘的“天命”,而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蕴于经济关系,是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启示,马克思发现“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0]。物质利益是人的第一需要,群众对宗教的需要是次生需要。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及其条件的反映。由于生活中的偶然性因素、人能力的局限性、资源的匮乏性,人的需求指向的理想境遇与现实力量之间存在矛盾,人寻求借以解脱苦难的依靠,人渴求保护、帮助、抚慰和激励,正如恩格斯所讲:“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11]宗教产生正是源于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人对神秘力量的寄望。现实越不能令人满足,人就越依赖宗教。人的宗教感情从何而来?——正是“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1]31刺激出人们对宗教的狂热。
(二)以人的本质为依托揭露宗教实质
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视为独立的个体的抽象物,视为一种内在的、将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成“类”的普遍性,马克思质疑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论,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包括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宗教作为人们的思想关系,是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由物质关系所决定。“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9]547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再去审视宗教,就看得更加真切。
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这个神要求人们顺从谦卑,面对苦难要逆来顺受,并许诺现世的忍耐美德会换得来世的报偿。人们对苦难的忍受和顺从对谁对有利呢?对施加苦难的社会主导性的经济力量,即资产阶级。本身处于压迫剥削者角色的他们借助宗教合理化这种压迫,为压迫辩护,从而宗教也实质上是以压迫者的身份存在,只是具有更高的威权,让人臣服。宗教以一套虚幻的观念制造偶像崇拜,归根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劳动者却以之为寄托,幻想着在非人的生存状况中求得宗教的庇护,如此一来,统治者加固了牢笼和锁链,而被统治者找到了精神安慰剂,宗教成了减压阀和稳定器。这就是宗教神秘面纱下的真相,它不过是以超验形式存在的人间异化力量。
(三)以实践为立足点指明宗教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统一
“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1]587,马克思强调研究宗教的世俗基础,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非相反,认为解决宗教问题不能仅从理论上战胜它,还必须斩断其赖以存在的现实根基。启蒙时期思想家的努力使人产生挣脱教会这种宗教物质力量的自觉,但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11,要根本上撼动宗教思想体系的根基,必须依赖于更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一力量蕴于生产实践,承载于联合的无产阶级身上。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01马克思以实践为立足点,寻找解决宗教问题的办法。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其现实根源在于劳动异化,要摆脱宗教异化,必须改变宗教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扬弃劳动的异化。他立足于对当下现实的解构性批判,在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完成了批判尘世世界从而强化对天国世界虚幻性批判的双重任务。宗教批判任务的完成消解了真理的彼岸世界,但只要私有制、商品拜物教等非人性状况在现实社会中不能消除,只要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仍存在冲突,则宗教问题不可能彻底消除,因而接续的任务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这有赖于对尘世的法、政治、经济的系列批判来完成。所以,马克思以宗教批判为基点,生发出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批判,进阶到人类解放根本途径的思考。
马克思的宗教观在对唯心哲学、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清算中渐趋成熟,它将哲学的批判功能从本体论哲学的纯思辨领域的“解释世界”转向揭露和变革现实生活的“改变世界”,因此对宗教的批判不再循着理性、自我意识展开,而着力于寻找“神圣世界”的世俗基础,由此确立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立足实践的思维方式和置身历史的基本路向,在持续深入的宗教批判中逐步确立新世界观。这一世界观鼓励人依靠自身的主体力量改造世界,打破宗教这一幻想、观念和教条的存在物的枷锁,它昭示人们只有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完全融合,人才能摆脱外在的一切束缚——包括物质力量的束缚和含宗教在内的精神束缚,真正实现自我解放。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M]//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3]牛苏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应关注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州学刊,2015(12):94-10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