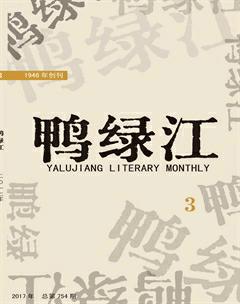卓尼杜鹃(组诗)
阿信
天色暗下来了
天色暗下来了。乌云
低低压迫山脊。
我在山下的屋子,灯光尚未亮起——
那里现在:无人。
我不必急于回到那里去。
我可以继续听着风声,愈来愈疾
掠过身边的草木。
就算天已经完全黑定,下山的路
看不见了,我也想
再逗留一小会儿。
我倒不是在等待星群,我只是
有一种
莫名的、难以排遣的伤感。
河曲马场
仅仅二十年,那些
林间的马,河边的马,雨水中
脊背发光的马,与幼驹一起
在逆光中静静啮食时间的马
三五成群,长鬃垂向暮晚和
河风的马,远雷一样
从天边滚过的马……一匹也看不见了
有人说,马在这个时代是彻底没用了
连牧人都不愿再牧养它们
而我在想:人不需要的,也許
神还需要
在天空,在高高的云端
我看见它们在那里。我可以
把它们一匹匹牵出来
桑珠寺
桑珠寺供养的神,脸是黑的
这是长年被香火和油烟浸润、熏染的结果
崖畔的野杜鹃花瓣缀满露水。槛边
一株丁香树枝条探进雾气
水声溅响却看不见来路
我的司机当智,在昏暗灯前
认出表弟。那个穿袈裟的孩子
脸是黑的,鼻尖上面有一点白,但眼神清澈
他哥俩悄声说话,我在佛堂燃香、点灯
这里的神
脸是黑的,鼻尖上面有一点白。神的
肩头和袖间,落着几粒鸽子的粪便
入门看见,几只灰鸽,在廊下空地
跳来跳去。鸽子的眼神,清澈无邪
与那孩子的一般无二
疲 倦
这疲倦有如微醺,让我迷恋。
这疲倦不名姓字,既感陌生,又觉熨帖。
这疲倦的浪花一波波袭来,竟是无由拒绝。
这疲倦的花园,关着一头野性的豹子。
这疲倦,如此深沉,充满诗意的魅惑。
这疲倦的物,疲倦的眼神,疲倦的岸,
如夜的渊面,令人,沉醉。
这疲倦的春天,仍叫作春天。
词条:卓尼杜鹃
杜鹃花科。高山杜鹃亚属。
生长地:甘南卓尼,光盖山脉之阴坡。
坡上:雪松、苔原、砾石和冰川;
坡下:砂岩、灌木、隆隆作响的峡谷。
月光舞台,听众是松鼠、蓝马鸡、雪豹……
宁静的音乐响起,内中,隐隐有一种狂欢。
信奉地方主义、原教旨主义,
拒绝异地嫁接和栽培。
不取悦人类。
性器官,只对自然界打开。
灿烂、放肆、如火如荼——
濒临窒息的美,分明是向死而生。
我不幸靠近了它们,从此
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花痴。
达宗湖
没有人知道
达宗湖
没有人牵着马
在群山之中
走三天三夜
夜幕降临
达宗湖
几乎是透明的
三面雪山,整整一座天空的星星
全倒在湖里
它,盈而不溢
湖边草地
帐篷虚置,空气稀薄,花香袭人
就这样抱膝长坐
就这样不眠不宿
就这样
泪流满面
发着呆。直至天明。牵马
悄悄离开
一小片树林
一小片树林。
暮色中的,一小片杨树林。
只有朝向河水一侧的叶片还闪着光,
其余的部分,渐次沉入灰暗。
我刚从那里散步回来,没走出多远
回头时,原来的路径
已模糊不清。树木和树木,
紧靠在一起,没有缝隙
仿佛有更深的黑暗在那里潜伏。
夜色很快统治了这里——
黑暗中的树林,完全是一个闭合的整体
没有一丝光渗出来。它
比四周的黑夜还黑。
它让我觉得陌生,感到惊讶,
隐约有一丝不安。
如果多给我一点时间,也许
我会等到它慢慢发光,甚至
变得透明。
也许会相反。
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
继续逗留。它是我遇见的
黑暗中沉默的事物——
不出声,蹲伏在那里,模糊的一团。
比沉默还沉默,比黑更黑。
一小片树林,
它究竟在抵抗什么?
植物园记事
在兴隆热带植物园,我发现
诗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
上帝其实是默许的——
可可的果实,被淘气的孩子
随手粘贴在粗糙的树干上;龙眼鸡的固执
简直不可思议:它拒绝荔枝和梧桐,拒绝
除龙眼树之外所有的枝条。
同行的诗人兼生态摄影师李元胜说:
“惊喜已经太多,足够了。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蒙恩者!”
而我的想法是:哪有个够啊!
怎么能拒绝杨桃家族可怕的生殖力
和千层蕉从高空累累垂向大地的谦逊和敬意?
信
在海南陵水的这几日,我没有
想起你。你和你妹妹在一起,
在兴隆山滑雪营地。
一下午,我在植物园
认识了可可树、无花果、见血封喉
那只树叶一样紧贴树干的昆虫:龙眼鸡。
又一个下午,和臧棣、西娃、郑文秀
登上南湾猴島。看见土拨鼠一样在水里
游泳的猴子。西娃惊叫一声:“哎呀!”
吃着海鲜。喝了
不多点酒。
海风真好。
我们熟悉的番茄、黄瓜、尖椒和空心菜,
在陵水设施农业基地的大棚里,以一种
不可思议的速度生长。
我没有想起你。没顾上细察
贝壳、螺蛳和停靠在海湾里的船。
日子犹如鞋袜,塞满细沙,又近乎虚度。
第三日,分界洲岛,遇雨。
半山亭中,与元胜、潘维分吃完一只椰子。
晚上睡眠充分,几乎没有做梦。
我发现:我们之间
除了爱、怨恨,
似乎还有友谊,短时间的分开、忘却。
当我在满屋月光和椰树婆娑的影子中醒来,
我突然意识到,我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你。
一枚橘子
有时候,无端想起
帆布提包中掏出的一枚橘子。
不新鲜、起皱……微觉干涩。不是
曾经熟悉的饼干或糖果——
点亮我们的眼睛。
浑圆、金黄,渗出酸酸甜味,
弥漫开来……满屋子都是陌生水果的味道。
那可以剥开、依旧新鲜、每个孩子分到的
新月一样的三瓣
——舍不得撕下缠裹它的缕缕绒絮,舍不得
一下含入口中。哦,飞溅四溢的汁液!
把一枚橘子
从走过长路、敝旧的帆布提包中掏出
于瞬间点亮孩子们眼睛的父亲的手,
不会在这个世上出现了……
牵马经过的树林
落叶这么多。
居于高处的,在向低处偿还。
踩在上面,阵阵疼痛、破碎、尖叫。
……密如阵雨。秋天深处
有人使劲擂鼓。
生长草莓的山谷
像海洋植物般柔软、湿滑、贴地,
允许我的手指在这里阅读和探寻。
在此之前,这是未经整理的荒芜山谷。
在冬天,一匹马逡巡不前,啃着谷口积雪下裸露的草茎。
充满渴意的浆果,从遮蔽处一一现身,找到春天的嘴唇。
孤 独
知道月亮里面有一扇开向桂树的门。
知道大河奔流受制于一种神秘的自然宗教的驱使。
固执地想把大海写入诗歌,想把一种
人类无法根治的毒素,植入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