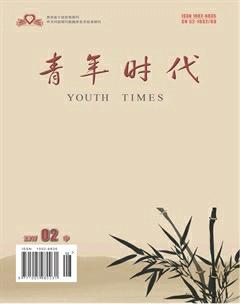政治科学的软、硬方法论之争
叶颖
摘 要: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是从历史、哲学与法律的角度来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这被称为政治学的软方法。而在现代政治学中,受到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成功经历的影响,主张采用量化统计、数学模型、控制性实验等硬方法,以期发现政治现象背后规律性的声音愈加凸显。但是,由于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一个由普遍规律严格控制着的决定论世界,也不是一个毫无规律可循、完全偶然的非决定论世界,因此,单独采用硬方法并不适合政治科学的研究。
关键词:政治科学;方法论;软方法;硬方法
《分裂的学科――政治科学中的阵营与派别》[1]一书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著作,回顾了现代政治学在20世纪后半期所经历的方法论之争,并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于政治学研究所应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看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阿尔蒙德对于现代政治学所包含的各种理论流派的认识,局限于政治学所经历的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发展和学说争论、以及这种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直接延伸的范围之内,而对于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绵延至今的政治哲学在政治学理论中的复兴、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于政治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因应这种变化而生的政治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的改变等则较少涉及,甚至完全没有得到体现。首先,政治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它的复兴。这一方面得益于出色的政治哲学家,例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等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和二战后经历了“政治学革命”的政治科学(在与政治哲学相对的意义上)――也就是阿尔蒙德所关注的政治科学――的表现不尽人意有关。其次,政治理论的左派与右派之争在阿尔蒙德关于现代政治学的论述中占有显著地位,而20世纪8、90年代发生的国际局势剧变则已经显著淡化了现代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并由此带来了政治学学术景象的改变,例如公共政策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等。
阿尔蒙德认为,可以将现代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各个学派按照意识形态和方法论这两个维度加以归类。在意识形态维度上,可以将现代政治学分为倾向于左派、激进观点的政治学理论和倾向于右派、保守观点的政治学理论。属于前者的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倡导“批判政治理论”的学者、依附论学者、以及倡导“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等。他们的共性是认为不能将知识与行动分隔开,认为政治科学应当服务于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属于后者的包括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权力最小化的新保守主义者。
在方法论维度上,可以将现代政治学分为软、硬两种。前者认为,适合于用来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只能是历史的、哲学的以及法律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适于研究政治与社会现象。坚持这一观点的一个典型是Albert Hirschman,他称赞John Womack所作的关于墨西哥游擊队英雄Emiliano Zapata的传记具有丰富而且重要的理论内涵,尽管这部传记完全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当具备的概念化、假定、命题证明等等内容。与这种极端情况相比起来更加注重经验证据和逻辑分析、但仍然坚持以软方法展开政治学研究的是一些政治哲学研究,例如Michael Walzer关于正义[2]和义务[3]的研究、Carole Pateman关于参与[4]和义务[5]的研究等。与软方法相对的硬方法指的是量化统计、数学模型、控制性实验等方法,其中最极端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它把数学模型、统计分析、实验、以及计算机模拟等手段相结合。在政治学理论中,以这种硬方法展开研究的包括选举研究、联合政府研究、委员会和官僚机构中的决策研究等。
硬方法受到不少政治学研究者的青睐,甚至被视为唯一正确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在这些研究者看来,通过运用与自然科学所运用的数学化、实验化方法相类似的这些方法,政治学研究有望成为真正的科学,有望实现“发现政治现象背后的规律”这一目标,进而对政治现实的走向作出预测和指导。但是,阿尔蒙德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指出,“在政治科学中有一场长盛不衰的争论,争论的一方将这个学科视为一种硬科学――系统的、数学的、统计的、实验的――并致力于积累受到过检验的“说明性规律”,另一方则没有这么乐观,更为折衷,将所有学术方法,既包括科学方法,也包括更软的历史、哲学和法律方法视为恰当有用的。我属于后一阵营[6]。”
阿尔蒙德认为,对于这种硬方法在政治学中成功运用的信念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政治科学的目的是发现社会和政治过程中的规律;二、科学的解释意味着从某项规律中演绎推导出个别事件;三、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中,唯一具有科学相关性的关系是与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联系相对应的关系。这三项相互联系着的假定依托于一个共同的核心信念:政治过程如同自然界一样有确定不变的规律可循。只有在认定存在着与自然规律相应的“政治规律”、“社会规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将政治科学的目的确定为发现这种规律,也才有可能依据所发现的规律来对个别事件进行解释。同时,与本质上在于揭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的自然规律相对应,“政治规律”或“社会规律”被认定为应当揭示出社会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然而,政治世界是否严格遵循某种规律,政治现象是否完全依照特定政治规律来进行,这却是有疑问的。阿尔蒙德借助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的哲学思想来进行论证。
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一些事物,例如钟表和太阳,其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另一些事物,例如云层的形状变化和一群昆虫的活动,则是随意、无规律可循的。波普用钟和云来分别比喻这两种观念。这样,整个世界就呈现出“钟”和“云”并存、一部分事物是“钟”、另一部分事物是“云”的这样一种景象。
但是,随着牛顿物理学取得巨大的成功,人们开始认为物理世界就象一架巨大而精密的钟表,严格遵循着由各种规律所规定的演变路线;只要掌握了某一事物的运动规律,就可以对它的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根据这种决定论观念,那些看似毫无规律可循的事物运动,例如云层的形状变化、一群昆虫的活动轨迹等,实际上仍然是有规律的,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发现其中的规律,恰恰说明了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而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就可以对这些看似随意的运动依据它们的运动规律进行预测。换句话说,在这种决定论观念看来,整个世界都是由“钟”构成的,即使最为变化无常的云,实际上也是“钟”。
随着量子物理学的出现,牛顿物理学的决定论观念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决定论观念,认为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并无规律可言,偶然性对于所有自然过程来说是更为根本的。在这种观念看来,世界不是“钟”,而是“云”;原先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事物运动规律被认为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并不存在,偶然性主导着一切。这种世界观令很多人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它似乎把人们从原先那种决定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自由选择。
波普认为上述两种世界观都是有缺陷的。“如果决定论是真实的,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一部运行完美、毫无瑕疵的钟,包括所有云、所有有机体、所有动物、所有人。另一方面,如果皮尔斯的或海森堡的或某种其他形式的非决定论是真实的,那么纯粹的偶然性就在我们的物理世界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是偶然性真的比决定论更加令人满意么?”[7]波普的回答是否定的。“对于理解理性的人类行为――甚至也包括动物行为――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某种介于完全的偶然性与完全的决定性之间的东西,某种介于完美的云与完美的钟之间的东西……因为我们显然想要理解诸如目的、思考、计划、决定、理论、意图和价值这样的非物理事物如何能在产生物理世界的物理变化中发挥作用[8]。”
波普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控制问题,也就是人的观念对行为和物理世界的其他方面进行的控制。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解释自由;而且也必须解释自由如何不是纯粹的偶然性,而是在某种近乎任意和偶然的东西与某种类似于有限或有选择的控制的东西――例如一个目标或标准,但这种控制决不是一种严格的控制――之间发生的微妙互动所带来的结果。”于是,可被接受的解决方案就必定“既合乎将自由与控制相结合这一观念,也合乎与‘严格控制相对立的‘弹性控制的观念”。[9]人们通过观念实现的行为控制就是这样一种弹性控制:“我们并不强制自己服从于来自我们的理论的控制,因为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批评性的讨论,而且,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理论不符合我们的规范性标准,我们可以自由地拒绝它们。不仅是我们的理论控制我们,而且我们也能控制我们的理论(甚至我们的标准):这里有着某种反馈”[10]。
政治现实总是包含着人们的目标、决定、选择等等精神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以及这些因素带来物理世界中的改变的过程不是完全由规律来决定的。这当中存在着控制,但不是“必定如此”的严格控制,而是在人的自由意志的参与下发生的弹性控制。与严格控制不同的是,这种弹性控制并不保证在相同前提下出现相同的结果,而是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例如,在那个著名的“薛定谔猫”的实验中,所有的前提条件都相同,但猫的结局却有可能截然相反,因为实验粒子的运动方向是任意的,不受任何规律的预先决定。我们在这个例子里看到了规律与自由的同时存在:当实验粒子业已向一个方向运动之后,各种自然规律开始显现出它们的作用,其结果就是猫的生存或者死亡;但是在实验粒子的运动方向确定之前,规律暂时隐退,在场的只有量子的自由。与此类似的是,在政治过程中,当人的选择与决定作出之后,我们可以在实际发生的政治行为与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之间找出可以用普遍规律来加以解释(亦即由普遍规律加上各项所需条件推导出个别事件);但在此之前,政治学研究所面临的对象却是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政治世界既不是一个由普遍规律严格控制着的决定论世界,也不是一个毫无规律可循、完全偶然的非决定论世界。就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过程而言,它在“是否遵循一定规律”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是要么只能象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然现象那样严格遵循自然规律、要么只能象量子理论所揭示的微观世界那样只有偶然性,而是在人的自由意志的密切参与下呈现出遵循某些“软规律”或者说演变倾向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哲学的、法律的、以及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某些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形成某种关于社会和政治发展趋势的认识,并据此对于未来作出一定的估测。这是我们通过政治科学这一学科所获得的关于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与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严格决定论为特征的知识是不同的,它所包含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不具有自然现象间的因果联系那样的必然性,因为人对社会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参与和介入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社会现象和政治过程本身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其复杂程度绝非一架精密钟表所能比。一个现实中的政治系统更类似于一个现实中的天气系统或者一个自然生态系统,而不是通过实验控制手段所创造出的天气模型或者生态模型。但是,这种类似并不能抹煞政治系统与天气系统间的本质差异:作为政治系统的参与者,人以其思考、选择、决定在时时刻刻影响、改变着整个系统的发展演变,而这些因素是不受严格规律支配的,也无法对其进行准确预测。我们的知识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对于这些自由因素的某种总体性认识。例如,我們可以在哲学人类学关于人性的认识的基础上,对于人在市场或政治行为中的“经济人理性”作出假定,但却无法知道每个人是否与如何运用他的“经济人理性”,而正是这些无法确知的因素会对事件的实际结果带来无法确知的影响。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科学倘若完全专注于寻求束缚着选择的规律性,就将错过政治现实的特有方面,亦即努力摆脱束缚、并为处于束缚环境中的问题找出能实现价值优化的解决办法。”[11]换句话说,政治科学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导向的。然而,对于硬方法的过度推崇却使政治科学背离了解决问题的导向:对于一项政治学研究来说,是否运用了符合硬方法标准的研究方法――量化分析、统计分析、实验方法等――成了判断这项研究是否科学、是否有意义的标准,而它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却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沃格林指出:随着将某种方法的运用与否作为科学的尺度,“科学作为关于现实结构的真实描述,作为人在其世界中的理论导向,以及作为人借以理解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伟大工具的含义就都丧失了。……把理论相关性从属于方法,这从原则上颠覆了科学的含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