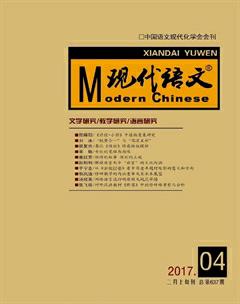论《檀香刑》中暗含的暴力美学因素
王红丽++吕颖
摘 要:《檀香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中暴力书写的代表作品之一,文本通过对酷刑的描写以及对酷刑实施过程中人物本性的揭露,描绘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暴力世界。莫言以作家的“大悲悯”来雕塑这些酷刑,使作品饱含了某种深层次的审美意味。文章试从暴力美学视角出发揭示作品中暗含的暴力美学因素。
关键词:莫言 《檀香刑》 暴力美学
暴力与美学的衔接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初,“暴力美学”并不是一个被广大学者接受的严格的理论术语,而是作为一种遵循从某种形式感觉出发而形成的批判术语。而后“暴力美学”这一专有名词在美国出现,香港导演吴宇森把这一美学范畴带入到电影行业。之后,对于“暴力美学”的电影批评逐渐增多,“暴力美学”的概念似乎也成了一个电影艺术的专用批评话语。在我国,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涉及“暴力书写”的作品也变得越来越多。暴力美学的范畴也逐步从电影行业转移到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中来,在这其中,伤痕文学以来的众多作品首当其冲,特别是当代作家莫言,其作品中多有涉及“暴力的书写”,无论是从话语描写的角度,还是从历史描述的角度,都是对“暴力美学”这一范畴的完美阐述。
“暴力美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话语,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暴力”通过形式化、社会化手段改造后,本身的攻擊性得以软化,暴力变得容易被接受,甚至于被应用到一些正面人物的身上,通过对其实施暴力的描写来隐匿暴力的侵害性;另一种是直接地描述暴力过程以及展现血腥效果,渲染暴力的感官刺激。这种描写虽然在表面上呈现一种暴力的场面,但是经过了作者的渲染,反倒呈现出了一种美感,进而又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
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便是“暴力美学”的代表作。本文拟从《檀香刑》的形式化、人性化暴力美学书写角度,对其暗含的“暴力美学”因素进行解读。
一、形式化的暴力美学书写
暴力美学的形式大多与电影艺术有关,往往是把暴力或血腥感十足的场面变成纯粹的形式感。而文学中对于暴力美学的形式描述,主要通过文字传递一种意味,而这种意味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关于“暴力书写”的文字内部产生的。在文学作品中,暴力常常通过形式化书写来展现,把血腥的暴力场景转化为纯粹的形式之美,借助语言、表演等手段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式,从而赋予那些暴力书写过分的作品存在的可能性。
“《檀香刑》这部小说完全是以一种喜剧性的话语方式来展示悲剧性的精神内涵,且悲与喜在小说中都叙述得浓彩重抹……”[1]作品本身有浓重的民间叙事痕迹,它常常运用具有地方色彩的、充满喜剧性的话语叙述方式行文,这种叙述方式便减弱了暴力过分书写给人带来的不适。
首先,通过具体人物展现出来。文中几乎每个人物身上都有喜剧的成分,在此举出一例:就眉娘来说,这个在乡村出生,在茂腔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少妇,嘴里会时不时地说出来一些极具喜剧性的话语,像“没有蛋就没有鸡”“黄鼠狼日骆驼,尽拣大个的弄”“睁着眼打呼噜,装鼾(憨)”等等,不难看出她是个乐观的人,而这个非常乐观的人下场却十分残酷,浑身充满了一种命运的无力感,因为大脚嫁给了懦弱无能、心智不全的小甲;追求“真爱”却成为钱丁满足肉体需求的对象;本想借助情夫势力救出亲爹,却抵不过情夫对仕途前程的追求。“眉娘追求自由、敢爱敢恨,但也仅仅是获得了身体上的性爱解放。她其实和钱夫人一样,并未真正走出男权中心的樊笼”[2]。
其次,是酷刑实施过程中的喜剧性语言,比如周聋子被德国兵挑了肚子,花花肠子就像鲤鱼一样钻出来;斩首的舅舅的尸体像个酒坛子一样倒下;腰斩的人的辫子像蝎子的尾巴一样翘起来……可以发现,在酷刑中的喜剧性语言往往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展现,作者把那些恶心到极致的东西运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描绘出来,可能当时感觉可笑,但细想一下,又会不寒而栗。
第三,对实施酷刑的场面进行大力渲染,带有表演的性质。书中带有表演性质的场景非常多,比如叫花子节、万猫合唱等。若把文中六次惨无人道的行刑场面和五种独创的、富有新意的酷刑抽取出来,都是极具有画面表现力的舞台艺术。在施刑前,便对各种酷刑进行了或精细或粗略地描述,把读者“带入”酷刑现场,从而使读者产生心理上的求知、生理上的不适。檀香刑进行之前那一些繁琐、精细、耗费巨大的准备工作,就足足有二十二页居多,似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形势,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而檀香刑本身就是一部戏,在这场戏里,几乎所有人都报着一种卑鄙心态观看着,“在书中第一个酷刑场面中,刽子手若活儿做得不利索……人群就喝倒彩起哄般甚至愤怒出现要把刽子手活活咬死的奇特狂欢景观。”[3]刽子手为了满足那些拥有恶趣的看客,把酷刑的实施演绎成了戏剧。再者,对受刑者表现欲的书写也充满了表演的意味。酷刑的承受者,多为触及统治者权力的“叛逆分子”,文中被施以极刑的人很多,尤以抗德的孙丙最为突出,他本身就是以演戏为生的“演员”,孙丙也曾袒露心声,他认为自己受刑而死正是保全了名节,因为举旗抗德刚刚进行一半,如果他中途逃脱,就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他也认为身体上的受虐恰恰能够凸显出精神上的强大和胜利,是摆脱平庸通往英雄乃至神明,被写进戏里的必由之路。所以檀香刑与其说是摧残他,不如说是成全他。正如莫言说的那样:“孙丙本来有逃跑的机会,但他没有逃跑。他是唱戏出身,已经形成了戏剧化的思维习惯……”[1]。在其他受刑者身上,这种表现欲也有涉及,比如库丁在刑场上,看客们越对他的行为喝彩,他就越疯;钱雄飞在经受凌迟时,虽然肌肉颤抖,但仍旧展现出临刑不惧的高贵姿态等等。酷刑的承受者们,在封建的土壤中生活、成长,服从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常态,他们本身思想的不健康性,也决定了反抗的不彻底性以及悲剧收场的结局。
也就是说,作者是通过描写具体人物本身交织的喜剧悲剧因素,酷刑描写过程中的喜剧性话语以及带有表演性质的酷刑场景与受刑人物,来展现《檀香刑》的话语书写对于暴力美学形式化作用的。
二、人性化的暴力美学展现
人性化的暴力弱化往往有以下几种形式:一,通过展现施暴者的合理人性使暴力合理化。但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化往往是基于人类的共性而言的。二,通过文本叙述视角的转换来弱化暴力,直接描写的画面冲击远远比听到施刑过程的人的转述大得多,当然有些作家因为个人功力的问题,反而将两者颠倒,这也不足为怪。
在文本中合理人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看客的视角来展现普通大众的人性。笔者发现与莫言一贯注重原始力的爆发相同的是,看客们所表现的状况正是对人类本能攻击欲掩藏的一种表现。康拉德·洛伦兹在其《论攻击性》一书中认为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也同样具有攻击行为的本能。人类面对外部环境的威胁时,都有一种应对的本能,会因仇恨和压抑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运用含有暴力因素的手段来战胜外来的各种威胁。赵甲的师傅余姥姥说他执行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凌迟美人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烈女,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身体,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刺激看客们虚伪的同情心,满足着内心见不得光明的邪恶的审美心。在晚清的社会秩序中,暴力侵犯是被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身体中的本能攻击欲就只有通过旁观、高喊等途径得以发泄。而且随着人类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与视觉有关的活动产生了更高的审美要求,他们不仅在观看,还在品评、鉴赏。所以说,在《檀香刑》中人们对于行刑的观看,并不是对生命的漠视,反而是原始生命力的另类展现。就像我们会为一连串的子弹发射声和机关枪发出的火光而兴奋,这是因为这样的场面及声音激起了观众内心的攻击欲,他们是为看到生命力的张扬、展现、逐渐消逝而激动。《檀香刑》中对看客的描写也一样,让读者感觉到:这些“看客”不仅是在关注生命,也是民间说唱演出中的听众,不只是听众,他们还“帮腔补调”,每个在场的个体都以其情感投注参与其中。而这些观众在把自己假想成为攻击或被攻击的一方的过程中,体验到一种与生命本能产生共鸣的快感。
二是通过施暴者的变异价值观展现拥有特权的人的人性。自古以来,生活在锦衣玉食中的封建统治集团便极尽残暴地在肉体和精神上百般折磨受刑人,而酷刑就是供封建当权者消遣娱乐的节目表演。他们认为各种血肉飞溅的場面,不同的撕心裂肺的哭喊,残缺不全、姿态各异的躯体,是权力的威严,是身份地位的胜利,甚至是种族的优越。封建统治集团对酷刑的变态偏爱让酷刑的执行者也可以拿朝延的俸禄,甚至得到皇太后、皇帝的接见和赏赐。
文本中叙述视角的转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准确地来说,檀香刑的行刑过程是通过小甲的视角来展示的,“檀木橛子已经进去了一小半……橛子恢复了平衡,按照爹的指引,在孙丙的内脏和脊椎之间一寸一寸地深入,深入……终于,檀香橛子从孙丙的肩头上冒了出来,”[2]这样的行刑过程是复杂的、缓慢的、精细的,就像在显微镜下观察腐烂伤口上的蛆虫一样,令人难以忍受。而最压抑的场面却通过一个单纯的、毫无成人视角的小甲来展示,这样的手法区别于那种单纯的暴力性语言的描写,使作品更易被读者接受。
作品本身暗含的暴力美学因素,在形式化、人性化的书写过程中,慢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读者除了感受血腥、暴力的场景之外,也能感知当时社会背景下不合理的人物命运和社会制度,让读者走出文本限制后,有所顿悟。当然,《檀香刑》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文中展现的酷刑本身是“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的”[4]。文章也“深深地被繁冗的酷刑描述”[5]掩盖、弱化了血性的祖先的阳刚精神,所以在阅读含有暴力书写的文本时,对社会是有要求的,“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必须是: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后现代社会,高度法制化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6]。可以这样认为:若社会达不到要求,阅读这部作品时就会存在争论。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莫言的暴力书写就认为他是一位非正常的作家,更不能因为文本对社会和读者有要求,就忽略了它本身的价值意义。
再者,近年来,以“暴力美学”为出发点的各种艺术创作,在所谓前卫思想和科技的陪衬下,使现代艺术似乎弥漫着一种夸大描述暴力实施过程的病态,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谴责。而如何借由暴力阐述来展现美学的意义,从而转化读者认知,使美感在作者体会客观事件后更深、更广的思维下生发,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对《檀香刑》中暗含的暴力美学因素的研究意义所在。
(本文系宁夏社科项目“新时期以来宁夏女性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NXBZW01)
注释:
[1]莫言:《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2]莫言:《檀香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3]赵先锋:《狂欢化的酷刑与变异的权力——<檀香刑>的主题意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62页。
[4]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第40页。
[5]张坤,李云莉:《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暴力现象探析——在当代审美文化的理论视域中探索“暴力”》,阴山学刊,2008年,第1期,第22页。
[6]吴娟:《大众文化冷思考:“暴力美学”真的那么美?》 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27296/2292269.html2004-1-12.
参考文献:
[1]李海彬.酷刑“戏”的背后——论莫言《檀香刑》[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3,(4):10.
[2]黄瑛,李艳.男权文化屏风上的翠鸟——析《檀香刑》中女性人物的生存状态[J].安徽文学,2013,(6):28.
(王红丽,吕颖 宁夏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