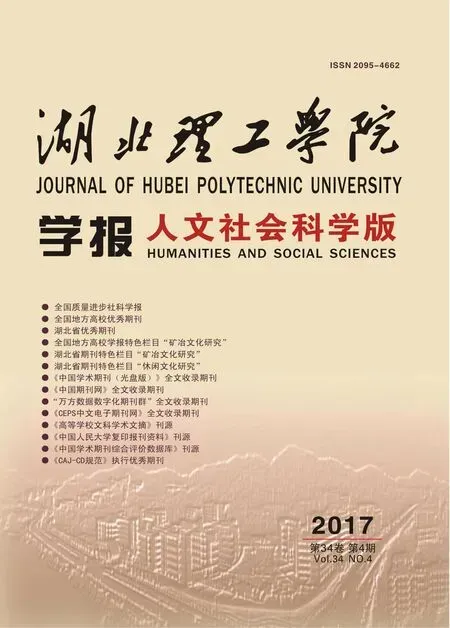王渔洋“神韵”说
——以《唐贤三昧集》为中心
李小雨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王渔洋“神韵”说
——以《唐贤三昧集》为中心
李小雨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王渔洋所倡“神韵”,主要体现为诗歌“清”“远”的艺术风格。正因为以“神韵”来概括盛唐诗歌气象,故而《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二家诗。此外,王渔洋自作诗虽喜用僻事、多用地点,然而他自觉追求诗歌创作的“清”“远”风格,因此与“神韵”说并不相悖。
王渔洋;唐贤三昧集;神韵
王渔洋论诗以“神韵”为则,历来受人重视。查其“神韵”说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目前普遍认为他五十余岁丁父忧乡居所编的《唐贤三昧集》是“神韵”说完成的标志。此外,王渔洋还编过《神韵集》(今已不存)、《古诗选》《十种唐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等选本。这些选本充分体现出王渔洋对于“神韵”的重视,这种态度使“神韵”说不仅为自身所尚,更对当时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他对“神韵”毕竟又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论述,有必要对其进行考察。
20世纪以来,对于王渔洋“神韵”说的研究可谓风起云涌:郭绍虞、方孝岳认为“直取性情,归之神韵”,用个性来解释神韵;钱锺书认为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优游、痛快,各有神韵;近年来更有将神韵作为一个系统的诗学概念来进行探讨,将其分创作论、风格论和鉴赏论三个层面;也有从“神韵”概念溯源及标举神韵原因方面进行探讨的文章。既然《唐贤三昧集》标志着王渔洋“神韵”说的完成,那么不妨以该书为基点,探讨王渔洋晚年所尊崇的“神韵”是怎样的。
一、王渔洋“神韵”说内涵探究
《然灯记闻》是王渔洋弟子何世璂所记,专录渔洋与人所谈初学作诗之道,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载了王渔洋如何论《唐贤三昧集》:
吾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语,而自命高华,自矜为壮丽,按之其中,毫无生气。故有《三昧集》之选。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其中蕴藉风流,包含万物,自足以兼前后诸公之长。彼世之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等语,果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乎?抑亦优孟、叔敖也。茍知此意,思过半矣[1]122。
王渔洋编选《唐贤三昧集》之意,原本是想“揭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显然,王渔洋对世人所以为的盛唐面目颇为不满,认为他们只是从表面学唐,而没有探索到盛唐真精神。那么,王渔洋所谓的“盛唐真面目真精神”是什么?首先看《唐贤三昧集》的篇目:全书分三卷,主要取盛唐人诗,自王维起,至万齐融止。共42人,400余首诗。其中,选录王维诗多达110首,超出全书总数1/4;选录孟浩然、岑参、李颀、王昌龄4人的诗分别为48首、37首、36首、30首;选录裴迪、常建、储光羲、崔颢4人的诗,分别是13首、13首、12首、12首;其余诗人所选均在10首以下。由数目统计可知,在王渔洋心目中,王维诗作无疑是能够代表盛唐诗的。
其次从题材方面分析,《唐贤三昧集》又多选田园、山水、送别、怀人以及边塞诗。表面上看,前四种题材与“神韵”概念相契度较高。而引人注意的是,边塞诗的选入也不在少数。如所选岑参诗共36首,其中边塞诗至少有6首,约占1/6。那么,豪迈酣畅的边塞诗,又是如何体现王渔洋所提倡的“神韵”?边塞诗是盛唐诗的代表之一,那纵横千里、驰骋沙场的气势,表现军中忧乐、闺中人怨的题材,既反映出盛唐人生活真实的一面,也体现了盛唐阔大的气象。王渔洋直言他爱高适诗“悲壮而厚”、岑参诗“奇逸而峭”[1]159,欣赏“燕台一望客心惊,箫鼓喧喧汉将营”[2]110“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2]157这类酣畅淋漓的诗风。可见他把边塞诗也作为“盛唐真面目真精神”的一方面。
《唐贤三昧集》所选诗篇最多的,集中在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这类诗。渔洋所谓“神韵”,更多地也是针对这类诗而言。作于康熙辛未年(1691年)秋的《池北偶谈》“神韵”条云:
汾阳孔文谷(天胤)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3]。
王渔洋原本自认为以“神韵”二字论诗,是“首为学人拈出”,其实明人薛蕙已经指出,在“清”或“远”这种诗歌艺术风格中,具有“神韵”之妙。王渔洋对此表示认同。那么,“清”“远”又分别指什么?薛西原举南朝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来说明“清”,二句写景,对仗亦工,营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境界,给人一种“清”的审美特征,“清”概括了诗人所描述的景物与景物所带给人的感觉这两方面的特征;又以谢诗“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来说明“远”,则重在传达诗人的一种情怀,带有一种“言不尽意”的韵味。准此,“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二句,既有景物的描写,传达出一种“清”的意境;又表现出主体蕴含着的高远情怀。
由此看来,王渔洋编选《唐贤三昧集》,意在揭出的“盛唐真面目真精神”,一是边塞诗的驰骋纵横之气势,反映出盛唐人积极向上的精神;一是山水田园诗的“清远”特征,可作为“神韵”诗的代表。
姜宸英为《唐贤三昧集》作序称:
盛唐之诗,实有不同于中晚者,非独中晚而已,自汉魏及今,有过之乎?盖论诗之气运,则为中天极盛之运。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则常有不极其盛之意,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辟之于禅,则正所谓透彻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规模于浮响漫句以为气象而托之盛唐,此明嘉、隆以来称诗者之过也,于前人乎何尤①?
姜宸英此处细述了王渔洋为何独拈出盛唐来。盛唐诗,不仅不同于汉魏、宋元之诗,亦与初、中、晚唐诗不同:盛唐气象,不是托于表面之“浮响漫句”,而是有边塞诗的真实、宏阔作为依托;是由山水田园诗所体现出的“清远”的神韵——这二者两相结合,才是一个“真”的盛唐。
二、《唐贤三昧集》不选李、杜原因窥测
翻阅《唐贤三昧集》则不免心生疑虑:既尊崇盛唐气象,为何不选李、杜二家?王渔洋自称这是依照王安石选《唐百家诗》体例的缘故②。然而,除此之外,王渔洋不选李、杜二家,其实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
《师友诗传录》中,王渔洋有论称“有宋以来谈诗家,乃祧盛唐诸人,而专宗少陵。然考之唐人之绪论,及唐人选唐诗,因未始有宗少陵之说。即在盛唐诸家与子美抗行者,子美亦多所屈服。”[1]145如此说来,王渔洋先是体会到盛唐诸人的独特面貌,有些即使是诗圣杜甫也不如的。编选《唐贤三昧集》正是要展示盛唐诗的面貌,不选李、杜,是因为李杜之诗本非盛唐人眼中盛唐之诗。方孝岳对此亦有论述,他认为所谓盛唐之音,“自为一种绝后空前的境界;表现这种境界的人,是王维、孟浩然等而不是李、杜。李、杜这些大家,本不可以时代限;言盛唐而皈依于牢笼今古的李、杜,结果必定迷眩”[4]。张明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唐贤三昧集译注》前言中说:“集中不录李白、杜甫诗,王士禛表面上说仿照王安石《唐百家诗》的做法,实际上是同他标榜‘清远’的宗旨有关。”[2]3也有学者从王渔洋的生活处境去推究这一原因,称“王士禛毕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推崇《沧浪诗话》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说,以为‘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香祖笔记》卷一)。由此出发而提倡写作脱离现实的作品,也就势必会对关心现实的杜甫表示不满,并旁敲侧击地底之为‘村夫子’了”[5]121。其实,若仅由王渔洋论诗好尚而认为他“提倡写作脱离现实的作品”,且“对关心现实的杜甫表示不满”,是不能够服人的,略论如下:
王渔洋提倡“神韵”,只是提倡一种诗歌“清远”的艺术风格,并非要不写现实内容,否则那些写实的边塞诗何以入选《唐贤三昧集》?而至于后来“神韵”说甚嚣尘上,模仿者多作有音无义之诗,表现出一种“神韵”偏执,恐怕并不是王渔洋的初衷,并且,王渔洋自作诗也并未脱离现实。认为他对杜甫的关心现实表示不满,其实是一种误解。《然灯记闻》记载王渔洋论杜诗:“唐人乐府,惟有太白《蜀道难》《乌夜啼》,子美《无家别》《垂老别》以及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1]121可见王渔洋认为杜甫的《无家别》《垂老别》这类乐府诗,能够推陈出新,而又继承了乐府批判现实的真精神。以“真”乐府来评价这些诗歌,本身就能够说明王渔洋并非对关心现实的诗歌表示不满。《师友诗传录》载:“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冠古轶今,则人有大成之号;不有拟古浮辞,而风谣俱归乐府;不有淫佚艳靡,而赠答悉本风人。故登吹台于是梁、宋,则支离东北风尘;栖江阁于夔州,则漂泊西南天地。故浑脱浏漓,只如其自道,顿挫独出,能此者几人?诸体擅场,绝句不妨稍绌,吾亦不能妄叹者。”[1]145可知王渔洋对于杜甫那些纪录、感慨时事的诗篇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正是这些诗歌的存在,为杜甫赢得“诗史”的称号,也使得诗歌风格更加浑脱浏漓。
总之,王渔洋编《唐贤三昧集》不选李、杜,并非只是仿照王安石《唐百家诗》的体例,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李、杜二家诗歌并不是盛唐人眼中具有盛唐气象的诗歌,并且李、杜二家诗不具备“清远”的特征,故而不取;且李、杜二家诗集确实流传甚多,在王渔洋看来,实亦不必再选。
三、渔洋自作诗与“神韵”说是否相悖
王渔洋论诗提倡“神韵”,而他自作诗“喜用僻事新字,倾于修饰,而神韵之旨反晦”[6]“渔洋自作诗,亦好搬弄地名”[7],种种现象,表面上似乎给人以王渔洋作诗与其所倡“神韵”相悖的印象。这一点也已经被学者注意到:“王士禛篇章杂沓,每到一处必有诗,未必像他说的那样都出之于真实感受,实际情况可能还是在多方面修饰上暗下功夫”[5]122,认为渔洋的大部分作品乃强作而成,并且在“下笔之时,藏头露尾,欲吐还吞,借以显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样子,追求‘神韵’的妙处。袁枚批评他‘一味修饰容貌’,则是掌握到了王诗弱点,说他装腔作势写作‘假诗’”[5]122。其实,造成这种看似矛盾的原因,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1)渔洋作诗用“僻字新事”“用地名”,一是与诗歌题材,即所要表达的内容相关;一是与诗歌创作手法(即诗歌用典)相关。这些现象在一定表达范围内,与诗歌“神韵”是不相矛盾的。兹举一例:
别万大屏杨胜林[8]111
别鹤念湖海, 离群秋夜心。
风声郧口暮, 江色御亭深。
去路分吴楚, 相思各滞淫。
关门今夕雨, 萧飒动寒砧。
这是一首送别诗。前两句以“别鹤”比将要离别之人,“离群”与“别鹤”互文见义,继标题之后再次点明此诗主题是与友人送别。三四句以郧口、御亭点明送别地点,并写出在江边上送走友人,暮色已临江面,友人身影望不见,唯有耳边风声呼啸这一送别场景。最后是说友人这一别,不知何日再见,相思之情当愈来愈浓。在这首诗中,出现了“郧口”“御亭”及“吴”“楚”这些地名,然而地名的出现,并没有妨碍整首诗歌意欲“清远”的风格。写到的地名,一是送别地点,一是友人将至之地,是由诗歌主题决定的。而王渔洋用“风声郧口暮,江色御亭深”二句,写出送别之时的场景,截取的意象与自然风景相搭配,体现出一种“清”的意境。且诗人在表达自己感情时,含蓄蕴藉,清词丽句,又让读者体会到一种“远”的情怀。
另外,说王渔洋作诗“喜用僻事新字”,与其喜用地名有关,如《蠡勺亭观海》[8]34“日主祠前水蕭瑟,仙人台上云嵯峨”中,“日主祠”于《史记·封禅书》记载:“八神,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鬥入海,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8]35据《乐史·寰宇记》:“仙人台在莱州膠(水)(木)县东北五十里青山下。”“只今指顾伤怀抱,黄腄(巾弦)缾尽荒草”[8]34,35中,“黄”“腄”“(巾弦)”“缾”均为地名。这也许就是胡去非先生所谓的“僻事新字”了吧。
王渔洋作诗,确实用地名较多,有些涉及到用典、用古地名等等,出现僻事新字是自然的。而一般说来,王渔洋的这种用法,在某种限度内,不与其诗歌之“神韵”发生冲突(因“神韵”由其对自然的描写而产生),而至于太多太滥时,比如“曲阿之北京口东”“扬州西去是真州”[8]182,192等,则又当别论。
2)“神韵”虽为王渔洋一贯诗学思想,但也是逐渐形成的。翻看王渔洋15岁时所作《落笺堂集》便知,渔洋自幼作诗,便有语句清新、意境取远的艺术倾向,自觉追求诗歌“清”“远”的艺术特征。正如蒋寅所指出的,“神韵”始仅为渔洋作诗风格,后为门人(徐乾学)提醒,而拈出作为已之论诗核心[9]。可知王渔洋作诗,并未以“神韵”为准则,只是追求“清远”的艺术风格而已。且当时诗坛的情形,“清初文人已经厌倦于明代的拟古模仿和门户纷争,王士禛自出手眼,排除以时代和家派论诗的陈腐风气,写作清闲可咏的作品,能够一新时人耳目”[5]122。再联系其时政治形势,康熙朝正需要这种诗风,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王朝必须加强其‘文治’之整饬,以辅助‘武功’来进一步稳定其政权,进入‘太平盛世’”[10]494;且神韵说标榜“清”“远”,这种诗风必定与现实产生一定的距离,亦即严迪昌先生所言王渔洋提倡“神韵”说有客观上的“淡化‘国是’”的“淡化效应”[10]494。严迪昌先生用“皇权政治与诗坛的深层潜在的制约性和影响力是何其显豁”[10]472的感叹来表达他对“神韵”说发展的看法,亦得之。
四、余论
王渔洋所倡“神韵”,主要体现为诗歌“清”“远”的艺术风格。这一艺术风格,与王渔洋所认为的“盛唐真面目真精神”相一致,故王渔洋编选《唐贤三昧集》,以盛唐为归宿。
“神韵”说的提出,一方面矫正了当时不良复古之风,开辟了康熙诗坛新风;另一方面又迎合了当时康熙朝统治的需要,使得“神韵”说风靡一时。然而随着诗坛风气的发展转向,“神韵”说也逐渐显出其流弊,这也是符合理论的发展规律的。
注 释
① 王士禛著,《唐贤三昧集》,清康熙刻本。
② 王士禛著,《唐贤三昧集》原序中有“不录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此外,在《师友诗传续录》中,王渔洋也坚持这种说法。
[1] 王夫之,等.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2] 张明非.唐贤三昧集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8[M].靳斯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430.
[4]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56.
[5] 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 胡去非,选注.王士祯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3.
[7] 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4.
[8]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M].李毓芙,牟通,李茂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 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6,58.
[10] 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龚 勤)
On Wang Yuyang's "Shenyun"——Focusing on "Tangxian Samui Collection"
LIXiao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00)
The connotation of "Shenyun" used by Wang Yuyang is "Qing" and "Yuan".Wang Yuyang didn't include poems of Li Bai and Du Fu in "TangxianSamuiCollection" because of their poetries style.Furthermore,Wang Yuyang's poetries embody the connotation of "Shenyun",despite of many place names in his poetries.
Wang Yuyang;"TangxianSamuiCollection";Shenyun
10.3969/j.ISSN.2095-4662.2017.04.011
2017-04-11
李小雨,博士生。
I207.2
A
2095-4662(2017)04-0062-04
——成功男士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