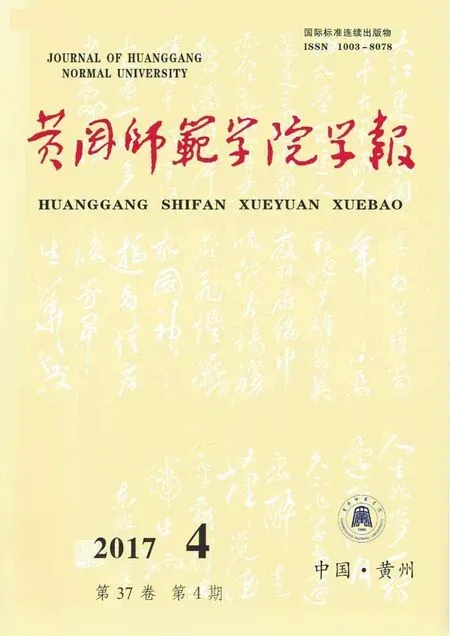中国园林作品的写意性翻译
——以《中国园林》和《中国名园》为例
马文丽,杨婷婷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中国园林作品的写意性翻译
——以《中国园林》和《中国名园》为例
马文丽,杨婷婷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写意”系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表现法则,是中国园林艺术审美活动中的最高境界。中国园林作品的写意风格既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性中,又体现在具体的写意形式标记中。通过以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园林》和《中国名园》及其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园林作品的写意符号体系。认为,园林文本的写意风格移译具有重要的现实传播意义,且只有以写意为原则的翻译才能引导西方读者领悟中国园林所蕴含的文化品位。将写意翻译原则二分为“形意结合”、“虚实结合”,并赋予其具体内涵,包括利用英语在构建画面方面的词法和句法特点,找准“形”与“意”的契合点,通过写意形式标记的写实转换以及避实就虚等“虚”化处理,把握“虚”与“实”的表现度等。
写意;翻译;《中国园林》;《中国名园》
中国园林系世界三大造园系统之一,在世界造园艺术中独树一帜。从整体上看,中西园林由于在不同的哲学、美学思想支配下,其形式、风格迥异。中国园林如诗如画,集建筑、书画、文学、园艺等艺术的精华,注重意境的营造,园林之美通过造园师写意式的安排与布局得以实现,并被世人用优美、凝练的语言将其移植到文字之中。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园林的建造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大背景之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园林作品被译成英文。如何准确地再现园林作品写意式的独有文风,将中国园林独特的文化品质表现来,这一话题值得翻译实践者和研究者探讨。关于原文风格的再现研究由来已久,且大都集中在文学翻译领域。本文选取《中国园林》[1]和《中国名园》[2]及其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该类作品的写意性符号体系和传播价值的基础上,从风格移译的角度论证写意性翻译的必要性及其内涵。
一、写意作为一种文本风格
(一)园林的写意与写意的文风 “写意”系中国古典美学术语,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表现法则,广泛地运用于文学、书法、绘画、戏剧等艺术创作中,它不要求创作者写实地再现客观对象,而是抓住并突出客体中与主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以此来表现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思想,抒发感情、意兴,其中虚实结合、情景结合是其常见表现手法。中国园林的发展与中国主流艺术在哲学、文学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园林,尤其以江南古典园林中所表现出的写意美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学文化。中国的士大夫,即园林的主要建造者与享有者,希望能够通过园林表现和完善理想的人格。园林艺术位于写实与抽象之间,让人们怀着对隐逸文化崇拜的心理去感受园林的“意趣”。正是士大夫的这一目的,才使得“写意”成为园林艺术审美活动中的最高境界,并在几千年生生不息。
中国古典园林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佳作,有些为“精美绝伦的惊世之作,令后世望尘莫及”。[1]20任何风格理念必然会被赋形于语言,这些经典园林多年来经历了无数文人骚客的阐发与解读,其见解与领悟也被相关文字或以书籍、或以随笔、或以册子的形式加以记录,美的意境因为优美的文字得以“感性的显现”。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园林风格因此被语言符号化,写意也自然成为园林作品的文体风格,文字所描述的近景远景的层次、亭台榭轩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题咏楹联的提点等等,无不在读者脑海里形成生动的画面。本研究对象为知名建筑学者楼庆西所著的《中国园林》(该书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之“人文中国”书系)和著名造园学者陈从周所作的《中国名园》(该书入选2010世博系列图书)及其英译本,两位大师的原作均以高度优美、凝练的语言引导读者畅享于绝世的中国经典园林之中。
(二)园林文本的写意性符号体系 现代文体学表明,文本的风格具有可知性,可见诸表现风格的符号体系,其中包括非形式标记和形式标记。非形式标记主要表现为整体性,即借助于审美客体的总的语言风格、语境来唤起人们审美意识中的印象、体验、感觉等心理活动,如园林文本的写意性总体印象。园林文本作者往往极力捕捉中国园林“形”与“意”的统一,虚与实的结合,讲究小中见大、动静结合、讲究深远与近景,俯视与仰看的别样天地,将诗情画意融贯于园林形态之中,语言表达形象,画面感强。
形式标记由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以及修辞标记六类属性标记组成。就词法与句法而言,园林文本的写意形式标记常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四字表达提炼美感,二是使用画面感强的词汇,三是拟人修辞的运用。例如,《中国园林》在描写拙政园时用“径缘池转,廊引人随,妙在移步换景”来引导读者感受拙政园的动态美,用“朝餐晨曦,西枕烟霞”来描绘其静态美。优美的四字成语、形象生动的动词,辅以拟人修辞的运用,园林的动静之美感呼之欲出。
标题的抒情特征是园林文本写意表现的又一形式标记。比如《中国园林》以“纵情山水”为引来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园目的;《中国名园》以“二分明月在扬州”等诗句来渲染中国名园的文学意境与历史感。《中国名园》整本书的标题均以写意畅神的风格拟定。另一形式标记是楹联题咏。文人、画家的介入使得中国的造园艺术深受文学和绘画的影响,园林的设计常常出于文思,园林的妙趣常赖文以传,园林与诗文、书画彼此呼应。好的楹联题咏往往表达了园主人的情趣爱好和人生追求,同时还具有点缀堂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中国名园》引用诗词32次,题咏28次,造园理念23次,它们均在文中起到了重要的提点意境的作用。除此之外,有关造园理念术语,如“借”、“皱”、“透”、“漏”等往往以简洁的方式表现中国造园艺术的奇与巧,也是园林文本独有的写意形式标记。
二、写意作为一种翻译原则
(一)写意风格移译的现实需求 写意风格移译的现实需求首先来源于园林作品本身的写意创作风格(如本文第一章所述),需要补充的是保留该风格的现实传播意义。中国古典园林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力不言而喻,国外的相关学术论文也呈现一定的规模(这一点从国际期刊搜索可以看出)。但是,与其重大影响力不相对称的是,相关外文书籍,即全面介绍中国园林建筑思想与艺术造诣的外文书籍或译本却极为有限。本研究收集到的有英译本的园林书籍,共计15本,《中国园林》和《中国名园》是具有代表意义的高质量之作。正如《中国名园》的译者李梅所言,其译本“力图将我国登峰造极的园林艺术呈现到跨越文化的高点”。[3]
综合考察这两本书的内容和出版背景,该类作品首先面向的是对中国经典文化有兴趣且有一定了解的中外读者。同时,因其内容的全面性、高度凝练性以及类似文献的稀有性,它们必然会吸引西方专业人士的目光,并可能成为国外相关专业(建筑、园林、艺术等)教学、研究的必读或参考文献;同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东方生活情趣与生存智慧也会为西方史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不言而喻,以反映园林精髓为目标,再现园林意境的高质量的园林译本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即新一轮的文本创作。既是创作,就存在创作原则。本研究认为,写意——这一中国造园灵魂之所在,只有以写意为创作原则的翻译实践才能最大限度地得以再现。
(二)写意性翻译的实现基础 写意作为一种翻译原则前人少有提及,《中国名园》的译者李梅教授曾撰文指出,“内涵的写意性”是其术语翻译的策略之一[3],但她并未对写意这一策略进行专门阐述。然而,有关原作风格移译的探索早已存在于翻译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发源于文体学的翻译风格论。风格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模糊性的行文气质或素质,如本研究的“写意”。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风格具有可知性,翻译研究者已基本达成共识,风格具有可译性,风格的可译性随着对风格的科学论证工作的发展而得到保证。[4]文学作品的风格再创造一直是翻译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但如何再现原作风格也是翻译实践中的一大难点。翻译风格论认为,作品的风格既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性中,又具体体现在其语言形式中,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作品的形式结构做出合理的分析和鉴别,使原文抽象的风格得以具体把握。
在风格翻译的框架之下,大多数作品可以通过模仿来传译作品的风格,用风格形式标记的分析和转换来完成对应式的换码。以此为基础,往往还需要风格转换的高层次即重建式换码或者淡化式换码。由于写意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表现手法,首先被中国文字所记录,因此所谓的写意性风格再现这一话题主要存在于中译英的翻译实践中。虽然园林作品本身的写意符号体系提供了写意性翻译的可能性,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告诉我们,风格的移译远非单纯模仿原文的形式标记那样简单:一方面,对应式的风格标记转换会面临转换本身的困难,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转换效果是否失真的问题。
因此,作为译者,一方面要充分领略园林文本所体现的写意的精神以及具体的写意形式标记,熟悉中国园林的常见手法和布局,用心体会背后其规律;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英汉语言文化的差异,在目标语中找准“形”与“意”的契合点,“虚”与“实”的表现度,引导读者突破时空、语言的障碍,实现审美想象,领悟中国园林所蕴含的文化品位。正因为如此,本文将写意翻译创作原则二分为“形意结合”、“虚实结合”,并赋予其重建式换码的具体内容。
三、写意翻译之“形意结合”
写意翻译之形意结合指的是通过画面感的语言实现“形”(画面)与“意”(通过画面激发的联想)的融合。
(一)巧用转义词 中国园林作品的写意风格整体表现为语言表达的画面感。画面是读者通过语言文字在头脑中形成的,通过阅读具有画面感的英语表达,西方读者才有可能在大脑中激发起有关中国园林的联想,引发审美共鸣。
译者应该意识到,汉语和英语实现画面感的方式并不相同。讲究意合的汉语长于用名词刻画意境,例如,在中国古诗里素来有“物象陈列,勾勒画境”的传统。英语则不同。从词汇层面来看,英语的形象性即画面感主要体现在其转义(比喻义与联想义)词的使用上。因此,汉译英译文的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转义词的成功运用[5],成功的转义具有程度不同的“言外之力”。[6]在英译园林作品时,译者虽没有了汉语名词的意境表达优势,但可以利用英语灵活自如的转义词的使用来弥补这一不足,以简洁而生动的词汇再现画面,获得“词外力量”,增强译入语的表感功能,这也正是风格感应力之所在。在这一点上,《中国园林》和《中国名园》都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例1:从高处俯瞰荷风四面亭,但见亭出水面,飞檐出挑,好似满塘荷花簇拥着一颗明珠。(《中国园林》)
译文:Viewed from above, the Pavilion of “Lotus Breeze from all Sides”, rises out of the water with upturned eaves, like a pearl surrounded with a pond full of lotuses.
该译文以a pearl surrounded with保留原文“荷花簇拥的明珠”的生动形象,巧用rise一词的转义将景物拟人化,配以 upturned eaves再现原文“亭出水面”“飞檐出挑”的美丽又生动的场景,寓情于景,展现了荷风四面亭的人造景观和自然景观完美结合的画面,意境与原文一样呼之欲出。当然,在这方面,两个英译本都有提升的空间,如下例:
例2:走进寄畅园西部,古树、幽谷、泉声使人如入自然山野。(《中国园林》)
译文:Walking into the west side of Jichang Garden, ancient trees, secluded valleys and the sound of the springs gives you the illusion of the nature in wild.
为获得更佳的意境,建议将the sound of the springs换成the singing springs。这样一来,给人欢快感觉的singing一词(转义)配以 springs,不仅与古树、幽谷形成严谨对应,更重要的是勾画出一个层次分明、活泼与幽静反衬的画面,其写意效果水到渠成。
(二)利用句法优势再现意境 园林文本在介绍园林构造或分布的同时也包含有景色的描写。在翻译时,要找准视觉定位点,充分运用英语组句灵活的句法优势,善用从句,通过合理的句子框架,让语言更具层次感与画面感。
例3:中部北半区是水景区,水中有大、小二岛,岛上用土、石筑山。(《中国园林》)
译文:The northern area of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garden is the water scene area, and built within the water are two islets on which hills are built with earth and stone.
例4:(中部南半区)虽然建筑集中,但由于建筑有厅、堂、亭、舫各种不同的形态,又有廊、桥、假山的穿插组合,再加上琵琶、海棠等各具特色的植物点缀,园林的景观便错落有致,毫无单调之感。(《中国名园》)
译文:Northwest central part, although an area concentrated with architecture, has a variety of architectural forms of halls, mansions, pavilions and stone bridges, interspersed with corridors, bridges and artificial hills, and decorated with crabapples lower trees and loquat trees. The garden scenes therefore give no sense of monotony, but rather a sense of richness and diversity.
以上两句充分利用英语主从句的立体架构,利用其造句灵活,便于表达复杂内容(此处为不同景物的方位架构)的句法优势,有效展现中国园林空间多个方位的变化韵律,营造山高水低、高低错落的变化意境美。
例5:名园如珠,从南到北散落在各地,无不讲述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园林》)
译文:Famous gardens a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Chinese landscape like so many pearls, and give silent testimony to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从画面定位效果来看,这里的处理还欠妥当,建议运用英语的插入语优势,将前半句改为Famous gardens, like pearls, a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Chinese landscape,这样处理后,译文画面效果更明显。
四、写意翻译之“虚实结合”
虚实结合是写意表现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园林文本翻译的“虚实结合”策略,旨在创造明晰而晓畅的译文风格,营造丰富而不繁琐的园林意境。
(一)形式标记与细节描述的写实转换 写意翻译之实,是针对原文中的形式标记和细节描述而言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翻译要精准,二是指避免不恰当的删减。一方面,原文中的写意形式标记是构成作品畅神文风的重要因子,对于这一类的翻译需要落实到精准。例如,将“拙政园是江南的另一座精美的私家园林”中的“精美”一词译成outstanding(《中国园林》) 就显空泛,如果将之改成exquisite就更能体现其精致细腻的特征,更为写实。另一方面,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恰到好处的重点浓墨和细节铺垫是写意不可缺少的环节,缺乏重点和细节的场景往往因缺乏足够的烘托而显得画面空泛而缺乏吸引力。再者,西方是讲究理性的解析思维,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每一个结论都需要有说服力的支撑。
写实转换重点之一是对抒情标题以及楹联题咏等形式标记写意功能的准确转换。尽管对于这些内容的翻译有一定难度,研究表明,两本书的译者都选择以直译或意译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它们的写意功能(《中国名园》的对应翻译达到百分之百),虽然总体来说并未达到完美,但却不乏精准之处。例如《中国园林》一书中将“倒影楼”译成Tower of Water Reflection,不仅将原文中信息倒影译出,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点出了盖楼选址及设计之巧所营造的意境美。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题咏(主要是指景点名称),《中国名园》的译者选择音译(为的是“找得着”,译者注),《中国园林》的译者选择直译或意译。客观来讲,二者各有优势。但从写意效果来看,建议二者结合,正如《中国名园》将“殿春”译成dianchun, meaning late spring的处理方式,从而实现该类术语意境的提点作用。
重点之二是对细节铺垫的写实转换。就本研究的两个英译本来看,一些被译者省掉(《中国园林》的省译较多一些)的细节描述实际上是整个文本必不可少的部分。
例6:“那时的人们乐于造园,并把造园与做人联系在一起:造园须曲,交友贵直,造园是为了修身养性,园能寓德,子孙后代在园林的意境中读书、吟咏、书画、拍曲,品味人生道理,培养正直高贵的人格。园中寄情、园中寓理,真可谓意蕴深远”。(《中国园林》)
译者只选择译出“那时的人们乐于造园……交友贵直,”,其他部分选择省略。然而,省略后的译文不仅让读者失去了对于园林功能的进一步了解,人与园,情与景交融的画面也随之消失。
例7:西面的岛山顶上建有“雪香云蔚”亭,与远香堂遥遥相对。(《中国园林》)
译文:On the western end of the islet is built a Fragrance Snow and Clouds Pavilion.
从纯信息的角度来看,此句里面的“与远香堂遥遥相对”看似一个简单且不重要的一个信息,也许是为了保持译文的简洁性,译者选择将其省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远香堂遥遥相对”具有非常明晰的画面效果,显现盖楼选址及设计之巧所营造的意境美,建议以英语现在分词的形式将之译出。
(二)“虚”化处理:写意中的留白 这里的虚,一方面是指语言表达的适当精简,留下想象的空间,是故意而为之的艺术创造,另一方面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即针对由于难以克服的语言、审美差异而采取的意译或省译的淡化处理。在这一点上,两本书的译者总体上都有较好地处理。
例如,《中国园林》中的副标题“移天缩地入君怀”,被译成“A vision to move the Heaven and condense the Earth”。“入君怀”在英语中无法找到对应词,译者将其创造性地简化为A vision to…使译文具有一种别样的大气、简洁、轻松之美。
例8:水池北端为“倒影楼”,面水的一侧,柱间装有通透玲珑的长窗,景物倒影如画,尽入眼中。水中揽月,池面飘云,波光月影,景色绝佳。(《中国园林》)
译文:At the north of the pond there is a Tower of Water Reflection, decorated with exquisitely-made long windows at the side facing the water and between columns. You can catch the moon in the water, and see clouds floating on the pond surface, all from the glittering ripples.
此处对“景色绝佳”的省译可以说恰到好处,前面部分成功的铺垫足以使“景色绝佳”不言自明,不译反而更有意境。
以《中国园林》有关宋代园林之最“艮岳”的介绍为例。对于原文中的关键信息,如园林的大小(十余里),以及题咏、楹联(“天下之美,古今之举”等),核心造园理念(如“聚盆”,移步换景等),重要景点及其文化内涵(如陶渊明笔下的梅池,传说中的八仙馆等)都得到细致的翻译,做到了“实”。其“园虽小而诸景皆备”的“壶中”范式渲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诸如“是一座浓缩了自然山水、植物精华的人造园林”等评价或结论性的话语选择适当的省译,就像在画面上留白的空间,反而凸显了整体意境之美。
中国园林通过写意的手段,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沉淀了丰厚的园林文化,它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环境美学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样本。由于中国园林多年来经历了无数文人骚客的阐发与解读,还由于当今介绍中国园林的作品常出自于造诣深厚的大家之手,其优美凝练的“畅神”文风使其成为与园林艺术品质珠联璧合的叙述媒介。中国园林作品的翻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译者需要准确领悟写意这一造园理念的内涵并将之融入到翻译实践中,通过运用画面感的语言和虚实结合等手段实现中国园林的再次写意,再现中国园林极具东方哲学意味的优雅、细腻、抒情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格调,让世人领略中国古代造园者的匠心独运以及中国造园艺术的巧夺天工。
[1]楼庆西.中国园林[M]. 张蕾,于江,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
[2]陈从周.中国名园[M].李梅,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3]李梅. 《中国名园》英译策略探讨[J]. 中国翻译, 2012(1)83-86.
[4]刘宓庆. 翻译风格论[J]. 外国语,1990(2)51-57.
[5]刘宓庆. 翻译美学理论[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139.
[6]潘卫民,焦亚萍. 转义词语的理解与翻译——2004年TEM8英译汉阅卷有感[J]. 中国翻译,2005(1)67-70.
责任编辑 张吉兵
2016-12-13
10.3969/j.issn.1003-8078.2017.04.20
马文丽(1968-),女,湖北孝感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杨婷婷(1993-),女,湖北荆门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H059
A
1003-8078(2017)04-00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