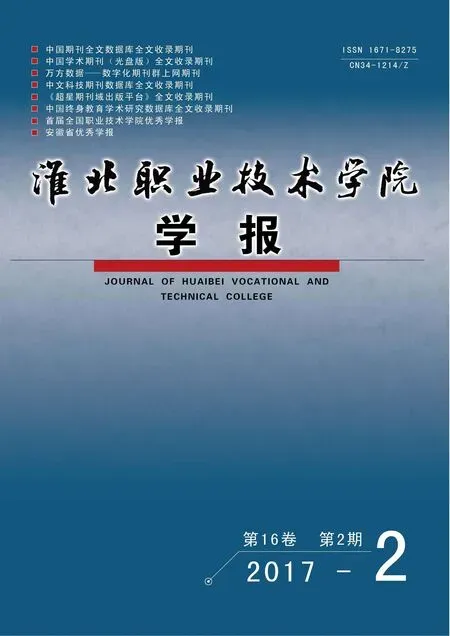浅析《林海雪原》对革命的合法性论证
黄梦芸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浅析《林海雪原》对革命的合法性论证
黄梦芸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革命通俗小说”《林海雪原》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虽在政治上没有进入主流,但却拥有广大的读者,是一部不容忽视的佳作。小说给革命战争赋予了浪漫色调,并通过“阶级”这一想象共同体、革命本体化逻辑和狂欢化叙事这三方面得以完美呈现。
《林海雪原》;想象共同体;本体化;狂欢化
基于文学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作品需鲜明反映时代精神面貌这一观念,通常我们会把“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认为是“十七年文学”中成就最高的作品,然而,一些“革命通俗小说”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与传播上也占具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其中,曲波创作的《林海雪原》最具代表性,这部小说的创作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小说中关于革命的叙述处处彰显着浪漫性因子,将革命浪漫化自然是为了冲淡我们民族对于革命的“黑暗记忆”,同时,也是对革命所做作的合法性论证。
一、“阶级”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之于革命
美国学者安德生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主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对“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作了阐释:“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基于这样的共同的想象,通过如此想象的思维和方式,我们可以对不同的共同体进行区分,同时可以更好地加深不同共同体内部的团结。由这种想象方式的相关话语构型所建立起来的民族,虽然在内部会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但通过想象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民族友爱关系总会“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2]。“民族被想象成为一个共同体,即使在民族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与剥削现象,平等的同志还依然被认为是民族内部的主旋律。”[3]将“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置换到“阶级”的想象中也是如此,“阶级”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对于革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林海雪原》中革命者对党和人民群众衷心耿耿,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宝贵生命,其坚定意志充分建立在对共产党这一“阶级”的想象的话语构型之上。作为“阶级”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在思想上达成高度共识,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与此同时,对立的阶级——敌人也必然形成。这样一来,在明确了目标和对手后,对于革命的进程势必起到推动作用。在小说中,杨子荣将党与敌人鲜明对立起来,“这仇人的概念,在杨子荣的脑子里,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他们是旧社会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祸首,这些孽种要在我们手里,革命战士手里,把他们斩尽灭绝”[4]183。在这里,仇人的概念由杨大头这个个体的概念上升到一个群体的概念,“他们”“我们”明显呈现出“二元对立”。杨子荣对于“阶级”的区分有清晰的界定,作为敌人这一共同想象体对立团体——党组织下的一员,杨子荣表示:“要把阶级剥削的根子挖尽,让它永不发芽;要把阶级压迫的种子灭绝,叫它断子绝孙”[4]183-184,这样的“想象方式”始终支撑着杨子荣将“剿匪”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想象的共同体”内部成员对于自己的信仰是矢志不渝的,工作队同志们在面临匪首侯殿坤、马希山的杀害时,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向同志们宣传,不要受骗,不要害怕,要打倒反动的革命党匪徒”[4]382。由此可见,“阶级”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建立对于革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二、革命浪漫性想象下的“本体化”逻辑
革命历史小说能将革命的浪漫性想象充分地展现出来,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功能,“本体化”就是对革命的合法性进行有力论证的重要体现。“文学的叙事是用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的过程,叙事的内容是社会生活事件,即人的社会行为及其结果,其价值就在于显示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意义。”[5]153革命胜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永无止尽,局部的胜利不过是斗争的开始,紧接着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战斗,而革命取得大规模胜利之后,还需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为即将打响的革命随时做好准备。因此,革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充分体现出“本体化”这一在今天看似荒谬的逻辑。
在《林海雪原》的创作中,遍布了这种革命“本体化”的图景。从整个故事情节来看,革命斗争这一线索贯穿始终,且丝毫没有表明革命会有终结的时候。由团参谋长少剑波、侦察英雄杨子荣、战斗英雄刘勋苍、攀登能手栾超家等组成的小分队自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剿匪”的重任。第一站是乳头山,消灭了势力强大的许大马棒。可是这并没有意味着革命的胜利,而只是革命的开始,战士们时刻都得做好战斗的准备,随时待命。在少剑波的策划和指挥下,革命战士依次消灭了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三股国民党残余势力。尽管如此,也只能说明由少剑波带领的小分队本次革命任务了完成,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画上了句号。小说的结尾处:“新的斗争开始了!……”这是革命的“本体化”逻辑: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文学版的再现。
三、“狂欢化”叙事对于革命话语的建构
“狂欢化”是巴赫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意思是对刻板的、等级化的日常生活秩序的颠覆,其特征是一种全民化的纵情表演。“狂欢化”的理念对于革命话语的构建提供了依据和模本,伴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战争,而战争就必然意味着流血牺牲,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在“狂欢化”之上的关于革命的浪漫性想象对消解革命暴力、血腥的一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狂欢文化本身具有全民参与性、自由平等性、颠覆性和再生性,是一种与理想,与生活相平行,不交融的游戏式的生活理念。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当革命被赋予了浪漫色彩,具有了神圣化、乐观化、理想化时,通过浪漫性想象建构起来的革命话语能够使人们产生高昂的战斗热情,全身心进行革命斗争,怀着对革命美好的愿望,将内心深处积蓄已久的狂热和狂情充分地展现出来。
“狂欢化”叙事对于革命话语的建构体现在情节的叙述上。《林海雪原》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富有传奇色彩,描绘了一幅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的图景。小说的开篇,我们看到的村庄是一片令人胆寒的“触目惊心的惨状”:“村中央许家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床上,几个人的尸体一段段乱杂杂的垛在铡刀旁,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个尸体却都没有了头。……狼藉地倒着二十多具被害者的遗体,有老头,有小孩……”[6]5-6。群众被残忍杀害的惨状是作者从叙事层面上使这群匪徒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的有力论证。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每一次剿匪行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狂欢活动,敌我双方的暴力拼搏彰显出我军英雄人物的大无畏精神。
此外,关于巴赫金对于狂欢节的描述:“狂欢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庆典文化,是一种非常强的生命力。狂欢节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活动,没有边界,无论高低贵贱都可以自由地参与其中”[7],这一分析也完全适用于革命战争的叙事,激烈的战争场面最能表现出这种狂欢的意味和效果。在革命小分队与匪徒九彪的交锋中,敌我双方进入对峙的局面,我军前方指挥员和小分队、民兵阵容、医疗兵等形成壮阔的狂欢广场:“刘勋苍小队负责在山神庙前布火、摆雷”“孙达得、马保军负责四挺机枪的安排”“李勇奇的民兵,主要负责外围捕捉”,战斗在我方谨慎而又轻快的节奏中以胜利告终,军民进入了一场狂欢:“每人举一块燃烧正旺的大松明子,照得满屯通红,扭着,唱着,广场上又烧起欢乐的篝火。直达通宵。”
《林海雪原》通过“阶段”这一“想象的共同体”、革命的“本体化”逻辑、“狂欢化”叙事建立起来的关于革命的合理化论证,给革命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外纱,从而消解了革命在现实世界中残酷性的一面,使每个个体所遭遇的流血、死亡等残酷事件被给予了合法性的解释。这样一来,革命成为人人心向往之的事,革命战争的痛苦情然隐退,彰显出一种革命的快感。
[1] 武永东.苏格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
[2] 王宗礼.论多族群背景下的国家建构[D].兰州:兰州大学,2005.
[3] 陈思.比较史学视野下《想象的共同体》[J].青年文学家,2016(9).
[4] 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 姜辉.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王作东.曲波在齐齐哈尔创作《林海雪原》的前前后后[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6).
[7] 吴雯.“2008奥运”中国人的狂欢节: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J].新闻世界,2008(11).
责任编辑:之 者
2017-01-03
黄梦芸(1993—),女,贵州安顺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I247.4
A
1671-8275(2017)02-00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