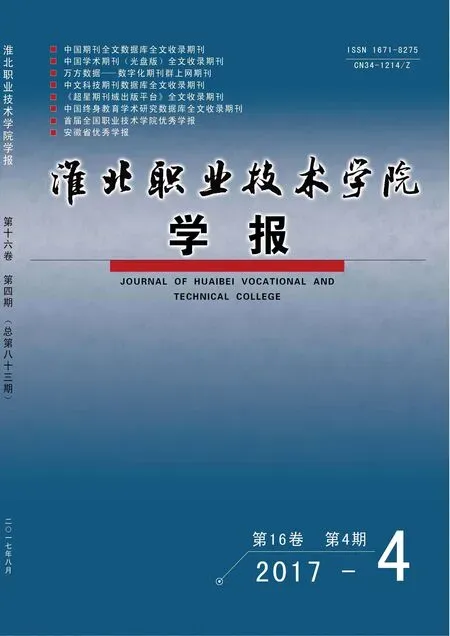畸形抗争下的女性命运
——《玫瑰门》主题新解
余梦林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畸形抗争下的女性命运
——《玫瑰门》主题新解
余梦林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是一部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品。它通过对司猗纹、姑爸等女性的命运书写,表现她们的畸形抗争及悲剧命运,揭示了女性困窘的生存状态及传统封建文化和社会性别秩序对女性的压迫。她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反抗着这一处境下的自身命运:或企图通过性别越界进入男性世界,或想通过家庭、社会的认可来追求自己的生命价值。然而,她们最终不过是遭受着家庭、政治及性压抑而畸形、变态地生活着。她们的抗争虽然最终以失败收尾,但她们却引导着女性逐渐觉醒。
《玫瑰门》;性别越界;家庭秩序;政治话语;女性命运
女性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交进入重要转型阶段。铁凝作为一位有着自觉女性主义立场的作家,始终关心女性的社会处境,注重社会批判、文化反思以及女性经验的反省。其长篇小说《玫瑰门》就是一部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品。以往对《玫瑰门》的研究大多注重传统封建文化以及性别秩序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压迫。笔者认为,小说中女性的畸形抗争过程以及性别意识觉醒在今天更具有触动性。
一、《玫瑰门》中女性挣扎反抗的两种典型形态
《玫瑰门》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男权文化对女性传统角色的要求,写出了女性人性 “恶”的一面。铁凝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女性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审视、批判女性自身的缺点,为我们再现了女性真实的生活处境及在这一压抑的生活环境下,女性为获得自身生命价值所做的不断挣扎及被扭曲的人性和人生。她“冷峻地透视了女性生存状态中的阴暗面,惊心动魄地揭示出“文革”特殊境遇下几代女人生存竞争中的较量厮杀,其中不乏狡计、卑琐、丑陋和血污。”[1]在男性对女性生存处境的百般压抑下,在女性的社会化自我和本真化自我的不断摇曳中,姑爸和司猗纹或逃离、或抗争,以期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诉求。
1.姑爸——性别越界的悲剧
作为庄家大小姐,姑爸的身份地位本应使她这朵养尊处优的生命之花灿烂开放,但她的悲剧却缘于一场只有三天的婚姻。作品中写姑爸出嫁前的心理时说到,她还偷看过他两眼。她喜欢,她满意,为做他的妻子充分地准备着。对这样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贤妻良母”依然是她最乐意认同的女性角色。然而,姑爸走时欢欣气派,回来时却惨淡凄清:“她披头散发地被抬下汽车抬进家门抬进她做姑娘时的闺房。”[2]38导致姑爸这一悲惨下场的原因竟是她长了个大下巴这一瑕疵。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空间被规定在家庭内,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可是,这唯一的出路在姑爸这里也变成了死路。
为了反抗这一不幸命运,姑爸选择了主动逃离自己的性别身份,希望进入男性序列。她一躺多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便宣布自己改名为姑爸,为与称谓匹配,她开始寻找男性的外形特征:“黑油油的两条大辫子剪掉了……旗袍、长裙换成了西装、马褂;穿起平跟鞋并且迈起四方步,烟袋终日拿在手中”[2]40她把人们所认可的男性成规拿来完成对自己的观照和改造。姑爸在遭受婚姻挫折后迅速坦然地“变”成了男性,她认为“世上沾女字边的东西都是一种不清洁和不高雅。”[2]35她以一场性别越界的闹剧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演绎。姑爸在自我畸形和扭曲的改造中,并没有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符合男权社会规范的男人,而成了一个人们眼中不男不女的怪物,一个无所事事的寄食者,一个被社会抛弃的零余人。当然,姑爸的悲剧既有心理原因,也有文化原因,姑爸对女性生命本相的自我扭曲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而是男性观念被女性自觉内化,从而丧失性别主体地位的女性普遍的悲剧,这是长期以来男权文化“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变成的”这一理念冠冕堂皇地强加给女性的悲剧。
2.司猗纹——婚姻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泥泞行走
铁凝曾说过:“司猗纹身上的‘恶’的背后是强烈的想被认可、被承认,有着女人的、人的一面和极为强大的生命力。”[3]在父权制文化社会中,女性始终是一个受强制、被统治的性别,即使是新女性,也终将逃脱不了“第二性”的命运,是永远的放逐者和异乡人。“她只是一个孤独的、冠着男人姓名的次生物,充当着男人(丈夫)欲望的对象与男人(儿子)的抚育者。”[4]243所以,司猗纹的想被认可、被承认的过程注定是艰难甚至是没有结果的。在司猗纹的前半生中,她为庄家生下了儿女,但却因年轻时与华志远的一个“错误”,并未受到夫家的重视,一直活在与庄家父子的纠缠中,这可谓是家庭秩序对她的严重迫害。
司猗纹在遭到婚姻和家庭的拒绝后,又产生了要社会认同的渴望。“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又让她重新燃起希望。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想方设法地“站出来”,表现自己的进步,自导自演地没收自己家的家具以及祖上留下来的财产,甚至不惜伤害身边的至亲。司猗纹幻想着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获得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承认,但她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司猗纹和罗大妈的纠缠表现了政治话语对女性人生的戕害。为了迎合特定时代的政治以及政治话语,女性往往要压抑、藏匿、掩盖、甚至抹煞自身生命中最原初的思想。司猗纹的悲剧在于她不是张爱玲所塑造的“绣在屏风上的鸟”那类没有真实的岁月,甚至被剥夺了一具血肉之躯的女性,而是一个要以自己真正女人身份生存的女性,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社会生活中,她都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平等而独立的个体得到别人的认同,渴望别人承认她的生命价值。在被历史与时代的塑造中,司猗纹由一个健康纯情的少女变成了龌蹉而又畸形变态的女人。
二、《玫瑰门》中女性反抗的类型
1.反抗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欲望的压抑
男性社会将女性定义为永恒的客体,女性在压抑下表现出病态、扭曲、异化等特征。在姑爸性别越界的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曾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依然渴望在“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中安稳度日,但新婚之夜新郎的抛弃让她在由女性成为母亲这一最大社会功用的道路上迷失了。接着,姑爸想以改变自己的外在及生活方式来寻得新的出路,但这一改变恰恰是她自我分裂悲剧的开始。这一点鲜明体现在她和大黄的关系上。她将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大黄身上:“自从她被称作姑爸后,是大黄又给了她一个机会,一个能关怀、能惦念、能爱的机会。”[2]110当大黄因偷吃了无产阶级罗大妈家的一小块儿猪肉被罗家大卸八块时,姑爸彻底丧失了分裂的自我中仅存的一点平衡和清醒,她的精神彻底错乱了。姑爸终因对罗家的咒骂招来了报复,被罗家惨无人道地戕害至死。姑爸以死亡作为对女性走出生命之门后所遭受的历史命运的彻底逃离。她的悲剧是试图逃离女性的宿命而进行的自我扭曲、自我分裂的悲剧。
司猗纹在初恋情人音信全无后被迫嫁到门当户对的庄家。在夫家,她精明能干却得不到婚姻和家庭的认同。新婚之夜,她默默忍受丈夫对她“不洁”的声讨。在生下一双儿女后,她带着孩子开始“扬州千里寻夫”之旅,而丈夫对于她们母子的到来无动于衷甚至有些恼怒,甚至把“花柳病”传染给了她。至此她终于看清事实:自己对丈夫而言,不过是他发泄的垃圾桶。丈夫不曾带给她恩爱的夫妻生活,给她的只有侮辱和鄙视。在经历了丈夫和男权社会对自己身体欲望的压抑以及家庭秩序对她的伤害后,她开始反抗和报复。“在毒水里泡过的司猗纹如同浸润着毒汁的罂粟花在庄家盛开着。”[2]166她决心拿自己的肉体对人生来一次亵渎的狂想,她赤条条地出现在庄老太爷的面前,“强奸”了自己的公公。新婚姻法的颁布,让司猗纹有了一块明朗的天和一个明亮而又朦胧的未来。然而她头顶那块明朗的天却因朱吉开的死再次暗淡了。司猗纹在反抗男性对女性身体欲望的压抑中也失败了。
2.反抗男权政治话语对女性的压抑
在中国数千年来的男权制度下,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和社会配角地位,中国的历代男性文人大都将女性看做审美活动的客体,女性必须顺从男性的欲望。 “这个无法抛掷、既成史实的客观条件,已经演变成‘集体无意识’,将男性的意志和男性审美趣味灌输在女性审美意识的各个角落。”[5]所以,女性心甘情愿地按男性的妇女观自觉地进行自我关照和自我改造。司猗纹的畸形、变态就是男权中心文化以及男权化身的政治话语压迫女性的例子。
新中国接纳了司猗纹,她以“吴妈”的身份工作并深知“此刻没有真的她自己,她从来都是一个专在有身份人家做佣人的有身份的佣人。”[2]47司猗纹作为一个做过大奶奶的家庭妇女没有从家庭里站出来,尽管她渴望“站出来”的路被暂时封住了,但她仍不曾放弃,并且一直让自己与时代同步。“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又为她提供一个被认同、被承认的契机。她主动奉献家产,并给附近小将写了一封言辞谦恭,语气恳切的信,要求他们来没收她的几间房子和一点祖上不劳而获的财物。当居委会主任罗大妈搬进庄家被没收的房子时,她又处处讨好罗大妈。为了让自己被革命接纳,被社会认可,司猗纹甚至不惜陷害自己的亲妹妹。为了有尊严地站在罗大妈面前,她跟踪儿媳竹西和罗大妈长子大旗,并设计利用外孙女眉眉一起“捉奸”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男权化身的政治话语给司猗纹的人性所带来的异化,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导向灵魂的升华,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是值得骄傲的资本,扭曲的内心可能依照受害者的模式继续施虐者的角色。”[6]司猗纹的不幸既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不公平,同时也是女性因这种不公平而扭曲变态的结果。因此,司猗纹在争取女性权利的同时,却促使自己成为疯狂的帮凶。
三、女性反抗的文学意义
“经历了两千年混沌的服人、从人的过去后,五四时代那些‘父亲的女儿’们以一声严肃的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叛离了家庭,开始了她们从物体、客体、非主体走向主体的成长过程。”[4]32但这并不足以撼动男性中心社会的基础,在“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女性的群体自我连同她那未被人真知过的性别真实和历史无意识,一起处于一切父系秩序的规则、角色、符号体系之外。”[4]27-28执着于改造国民性的鲁迅,其笔下的女性也普遍表现出一种自我奴化的特点,这表明女性命运并没有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得到大的改变。《明天》《祝福》《离婚》中的农村妇女虽受着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思想的毒害,但她们自身的弱点更值得我们深思。《祝福》中的祥林嫂始终挣扎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这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下,却连一个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资格都争取不到。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女性的地位渐渐有了好转,而且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时代的感召下觉醒了过来,开始有了主体意识、性别意识。
女性话语自“五四”时期提出,但一直处于被抹煞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铁凝为我们揭示了新社会中“男女平等”口号下依然不平等实质,为我们揭开了平等的虚伪外衣,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一个解放、翻身的神话中,既渐渐完全丧失了自己,又完全丧失了寻找自己的理由和权力”[4]268的悲剧所在。《玫瑰门》中女性畸形变态的性格不仅是中国传统家庭秩序导致的,更是特定的男权化身的政治话语以及社会压迫的结果。铁凝以新的视角和观照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畸形抗争中肉体的觉醒、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渴望,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女性困窘的生存状态。对女性经验、女性缺陷进行批判反省,反过来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影响着后来女性文学作家的创作方向,并形成一种自审意识,向女性解放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1] 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97.
[2] 铁凝.玫瑰门[M].北京:作家出版作家出版社,2009.
[3] 缪爱芳.构建女性未来话语:论小说《玫瑰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中的意义[J].电影评介,2007(11):94-95.
[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5] 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微[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8.
[6] 刘莉.玫瑰门中的中国女人:铁凝与当代女性作家的性别认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3.
责任编辑:之 者
2017-04-01
余梦林(1992—),女,河南驻马店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I206.7
A
1671-8275(2017)04-01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