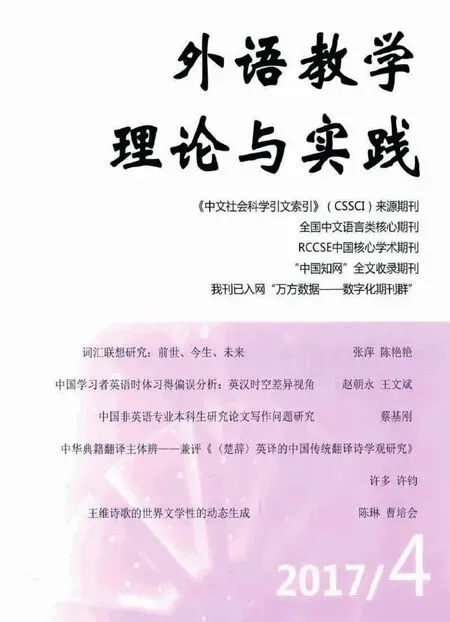于“评论”中见真知
——本雅明“纯语言”概念的贝尔曼解读*①
南京大学 张晓明
在《结论: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德·曼将本雅明这篇广为人知的文章视为衡量翻译研究者声名的试金石:“如果你不就这篇文章说点什么,你就无法立名。”(De Man,2003:13)德·曼的这一观点,与其说是在劝诫后来的研究者不可忽视本雅明此文,毋宁说是在揭示如下事实:自《译者的任务》(以下简称《任务》)于20世纪70年代被纳入西方译学界学术视野以来,举凡翻译研究领域赫赫有名之人物如斯坦纳、德里达、贝尔曼、梅肖尼克、拉德米拉尔、韦努蒂等,皆概莫能外地参与到对此文的评述和解读之中。这其中,若就评述与解读的详尽程度论,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堪称翘楚:从1984年冬到1985年,贝尔曼在法国国际哲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以研讨课的形式,分十讲对《任务》一文进行了逐段分析与评论。令人遗憾的是,贝氏生前未能实现公开出版这十讲讲稿的计划,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曾详尽评论《任务》的情况逐渐不为人知。直到2008年,其遗孀在友人协助下,将贝尔曼当年书写在十本学生练习簿上的讲稿整理出来,并以《翻译的时代——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评论》为名出版,我们才得以窥见贝氏如何以异于他人的方式走进本雅明这一玄奥文本所折射的理论世界。
当然,译学界并不是非要等到此书面世才得以了解贝尔曼对《任务》一文的看重。贝氏英年早逝,其留传后世的三部代表性著作,即《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_时代的文化与翻译》化母语表达能力为诉求的翻译冲动的错误升华(Berman,1995:21-23)。而在《远方的客栈》中,贝尔曼对《任务》的评价显然又偏向了积极的一面:本雅明提出的“不能将翻译目的等同于信息与意义的传达”和“对原文的忠实即意味着对其文字层面的忠实”两个观点被其援引,以在观念层面为翻译伦理观的建构奠定基础(Berman,1985:86-87、89-90)。这一立场前后抵牾的有趣现象,因为“纯语言”概念同“对原文文字层面的忠实”这种翻译取向之间前者为因后者为果的(1984)、《翻译和文字或远方的客栈》(1985)、《翻译批评论:约翰·唐》(1995),遂成为其翻译思想的主要呈现。在这三部著作中,本雅明均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一种参照。其中最明显的,是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中,明确指出本雅明的批评理论是其试图建构的翻译批评理论的两大理论根基之一(Berman,1995:15)。如果说此著作主要是就本雅明的另一重要著述《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而言,同《任务》并无明显关联,那么分别出版于1984年和1985年的另两部著作则足以表明《任务》对贝尔曼译学思想的重要启示。不过,我们注意到贝尔曼在这两部著作中对《任务》所持态度却截然相反。在《异的考验》中,他为了反衬翻译伦理观(visée éthique)的正确,将本雅明在《任务》中阐述的翻译思想概括为一种以追寻凌驾于所有自然语言之上的“纯语言”为本质的形而上的翻译观(visée métaphysique),认为其“反巴别、反差异、反人类经验”是对译者以优关系,而变得叫人费解,不禁令我们对贝尔曼当年到底如何评论《任务》心生好奇。《翻译的时代》为我们探究个中真相提供了可能。
一
编著者选取了贝尔曼的《我在“学院”的研讨课》一文作为该书序言,从中我们得知,关于《任务》的十讲是贝尔曼于1984年到1989年期间在法国国际哲学院以“翻译”研究课题负责人身份开设的若干期研讨课中的一期。耐人寻味的是,与其他几期的主题(“翻译中的直译概念”、“翻译:母语和外语”、“翻译的缺憾”、“法国翻译史”、“翻译的巴别塔——专业翻译与文学翻译”、“约翰·丹纳与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译作评论”)或较为笼统而不做具体指涉或属于典型案例分析不同,关于《任务》的十讲看似主题明确而具体,却是在“哲学与翻译”这一宏观议题下展开的。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对《任务》的评述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探讨哲学与翻译关系的一种进路?
贝尔曼没有在《翻译的时代》中给出正面解释,但一些“蛛丝马迹”还是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在上面提到的《我在“学院”的研讨课》一文中,贝尔曼引述了自己为了向法国国际哲学院领导层论述“翻译”课题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撰写的报告,其中说到:“翻译对于学院的重要意义,就更深层次而言,在于我们所关注的各种知识和活动(无论是已经体系化的知识门类如哲学、精神分析、科学、法学、文学和文学批评,还是仅仅以学院为存在之所的交叉科学)都会与作为一种问题的翻译相遇”(Berman,2008:10)。具体就哲学而言,在其得以与翻译建立关联的众多层面中,贝尔曼首先阐明:“现代哲学将自身定位为对言语和语言的(多种)思考,因此迫切需要同作为一种问题的翻译相遇。”(同上)可见,语言问题是其审视哲学与翻译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其实,贝尔曼对《任务》的关注,并非仅以翻译问题作为切入点。他在第一讲中即言明:“除了对《任务》的阅读外,我们的评论也以对本雅明另外两个文本即《论总体语言和人的语言》与《论模仿能力》的阅读为前提”(同上:21—22)。对这两个并非以翻译为核心论题的文本表现出的重视,表明贝尔曼意识到应当在一个有别于狭义翻译问题的范畴内来理解《任务》的理论旨趣。这个范畴便是本雅明致力于探究的“语言的形而上之维”(métaphysique du langage)(同上:21)。贝尔曼对此分析道,“语言的形而上之维”根植于本雅明从未深入阐发但却笃信不疑的“语言是家园(demeure)”的基本设想。这一设想是本雅明对语言的交际工具论和符号系统论提出批判的理据所在:既然语言是“家园”,那便不再是人们借以实现某种目的的途径或工具。本雅明在此并不回避语言作为交际行为介质的客观事实,他所强调的是语言并不因此而混同于交际行为本身。换言之,作为“家园”的语言,指涉的是“语言的形而上之维”的本质,即“纯语言”(同上:24)。“纯语言”是本雅明最早在《论总体语言和人的语言》中提出的概念,在《任务》中则成为核心概念之一。他借翻译之名论及这一概念,是因为在他看来,要想达致“纯语言”或者说找寻到“家园”,翻译乃是不二法门。在本雅明的语言哲学语境下,翻译的目标被设定为对“纯语言”的无限接近和对“语言的形而上之维”的叩问。
贝尔曼随即又将本雅明置放在德国哲学的传统中继续分析。他指出,“语言的形而上之维”是对德国18世纪哲学家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针对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纯粹理性”而提出的“理性即语言”这一观点的引申,所谓“语言的形而上之维”,实际上也就是“理性的形而上之维”亦即“纯粹理性”。由此,作为“语言的形而上之维”的本质,“纯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哲学所追寻的“纯粹理性”的本源所在,并就此成为哲学思考的终极目标(同上)。
至此,围绕“语言的形而上之维”以及“纯语言”概念,哲学与翻译之间建立了深层的理论关联和共同的目标指向,我们也理解了贝尔曼在何种意义上将翻译“作为一种问题”。《任务》一文堪称现代语言哲学同翻译的一次经典相遇,这一相遇赋予了《任务》在20世纪翻译学文献中极为特殊的地位,一如贝尔曼在第一讲中开门见山指出的那样:“我们将这一文本视为20世纪关于翻译的核心文本,这样的文本或许每个世纪只会有一个——一个无法超越的文本,其他任何关于翻译的思考都以之为出发点,哪怕是为了对其加以反驳”(同上:17)。
二
《翻译的时代》一书的副标题为“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评论”,其中“评论”对应的是法文“commentaire”一词。选择这个词并非该书编者的随意之举,而是为了点明贝尔曼切入《任务》文本的方式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批评”。同中文语境下“评论”和“批评”两个概念区别不甚明显不同,“commentaire”和“批评”所对应的“critique”一词在贝尔曼的语境里大异其趣。贝氏曾专门著文剖析两者的区别,他指出,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两者同对象文本文字层面(la lettre)的关系完全不同。“评论”是从文本的文字层面出发,“一个词接着一个词地、一句表述接着一句表述地、一行文字接着一行文字地,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极富耐心的缓慢节奏,循着文本边前行边探究,依托文本的文字来阐明其意义”(Berman,1984:90),还经常伴有对此前评论内容的回顾和对相关话题的发散性引申,但它“从不超前于当下所评论的内容,也不以任何所谓对整个文本的先期理解为基础”(同上:91),它从不追寻那种可以脱离文本文字存在的意义,它所致力于揭示的是“文本文字本有的意义”(同上)。与此相反,“批评”却赋予自身以“自我完备性”(autonomisation)(Berman,2008:18),着眼于文字之外的意义和文本的整体,其宗旨是“剥离出仅仅显现于整体之中的意义”(Berman,1984:92)。
“批评”的这种取向,使得它在面对《任务》时极易步入“歧途”。贝尔曼归纳了本雅明思想的若干特点,其中之一便是“任何一位读者都会对其文本的晦涩难懂留下深刻印象”(Berman,2008:28)。这种晦涩使得“批评”主体往往趋易避难地绕开对文本文字层面的细致探究,转而尝试从宏观层面把握整体,抑或引用其中某些看似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和表述,来为自身的论证张本。然而,贝尔曼认为,“(《任务》的)任何论断一旦脱离原文本就会立刻变得毫无依据”(Berman,2008:31)。这种说法乍一听来似乎有些夸大其词,然而努斯在《〈译者的任务〉在法文语境下的接受》一文中曾详尽分析了本雅明此文遭法语国家和地区研究者断章取义的现象(Nouss,1997:71-72),说明贝尔曼所言并非危言耸听。袁筱一也曾指出,中国学界“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读’过本雅明,读过《译者的任务》,在这样的前提下,引用本雅明,包括使用他所奠定的语汇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袁筱一,2011:89)。可见,贝尔曼选取“评论”视角,目的就是为了直面《任务》文本的本真面貌。除了作为铺垫的第一讲外,其余九讲则按一段德文原文配以相应的法文译文以及对原文和译文所做之分析这样的节奏,对组成《任务》的十二个段落依次加以评论,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对《任务》文本的一种“深度耕犁”。在此过程中,贝尔曼实际上赋予了“评论”以双重使命:既有对《任务》德文文本的评论,又有对其法文译文传译原文文字效果的分析与评价。这种在原文文字和译文文字的放大比照下进行的“评论”,有助于揭示一些原本不易察觉但却对于深层理解《任务》极有助益的细节。
贝尔曼首先从《任务》的文本属性和标题意涵层面阐明了回归文本原初语境、紧扣文本文字层面带来的三重发现:
首先,众所周知,《任务》是本雅明为其选译的波德莱尔《恶之花》德文译本所作之“译者导言”,但鲜少有人对此做进一步思考。贝尔曼则指出,作为“译者导言”的《任务》,其内容同以之为导言的译文毫无关联。对于这一不合常理的现象,他认为不应将其归因于本雅明个人翻译实践同翻译观之间的不匹配,而是本雅明刻意为之,其目的在于彰显翻译思考同翻译实践之间的一种脱节(Berman,2008:35)。传统的翻译话语以意义的传递为翻译的目标,主要着眼于解决如何传递的问题,与翻译实践密切挂钩,带有方法论的显著特征。本雅明此举旨在表明翻译话语可以不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对翻译的本质做出思考,是对仅仅关注意义传递的传统翻译观的质疑与解构。
其次,本雅明将文章命名为《译者的任务》,贝尔曼则指出文中真正涉及“译者”的内容很少,“所有提及‘译者’的地方,似乎都可以替换成‘翻译’”(Berman,2008:36)。他对此剖析道,传统翻译观视翻译为一种透明地传递意义的行为,而这种透明在于翻译主体即译者的隐身。然而,任何以翻译文本为对象的分析都不容置疑地表明译者主体性的在场。本雅明以“译者的任务”而非“翻译的任务”作标题,正是为了标榜译者主体性乃是翻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有学者指出,贝尔曼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于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关注(Oseki-Dépré,2007:43)。应该说这与本雅明的启发不无关系。相比于此前翻译研究对语言层面(以穆南为代表)、诗学层面(以梅肖尼克为代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以特拉维夫学派为代表)的侧重,这种对翻译主体的关注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使翻译“参与到主体彰显性思想的建构之中”(同上:39)。
再次,同在中文语境中一样,《任务》德文标题“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中的“Aufgabe”一词在法文语境中也约定俗成地被译作表示“任务”的“tâche”一词,令人联想到该词所含有的“责任”、“职责”之意。针对这一看似顺理成章的译法,贝尔曼回到本雅明的语境,提出了另外的理解进路。他指出,本雅明笔下的“Aufgabe”一词不应被置放于“责任”、“职责”所指向的道德伦理层面来理解,因为熟谙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本雅明非常清楚,这个词因为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的缘故而同德文中的另一个词“Auflösung”(意为“解决”、“消解”)紧密关联。在德国浪漫主义语境中,“Aufgabe /Auflösung”这组关联所牵涉的仅仅是浪漫派文艺理论所关注的哲学、诗歌、批评与翻译四个范畴。换言之,涉及这四个范畴时,应当在“解决”、“消解”的意义层面来理解“任务”一词。那么,“消解”的对象是什么呢?诺瓦利斯提出的“诗歌在其本质中消弭异质元素”的观点成为解答这个问题的一种参照。贝尔曼将此解读为“诗歌的任务就是要消解其本质层面即语言层面中的异质元素”(Berman,2008:40)。对浪漫派而言,语言是哲学、诗歌、批评与翻译四者的共同要素,深受浪漫派文艺理论影响的本雅明在拟定《译者的任务》这一标题时,依循的不是“任务”一词的常规语义,而是为了表达“消除语言中的原初不和谐”(同上)的理论诉求。按照贝尔曼的这一深度剖析,“纯语言”成为《任务》一文的核心概念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三
在译学界对《任务》一文的关注中,“纯语言”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本雅明的“直译”观往往成为争论焦点。常有学者以之为据,将本雅明此文论旨定为带有反动倒退意味的对于人类语言多样性现实的拒斥和对唯一一种“人类原初共同语”的眷恋与向往,抑或是对作为实际翻译方法的“直译”的绝对捍卫。事实果真如此吗?贝尔曼以“评论”视角对《任务》文本所做之深度耕犁,令我们得以窥见“纯语言”概念和“直译”主张在本雅明的翻译思想和语言哲学中不易把握的复杂特质。
贝尔曼首先从“纯语言”概念的德文原文“die reine Sprache”在法文中应当如何翻译的角度,展开对其实质的剖析。德文与法文之间的转换问题貌似与中文无甚关联,实则对我们亦有颇多启示。贝尔曼认为,德文“Sprache(语言)”一词在法文中应当译成表示具体语言概念的“langue”一词,而非侧重于表示笼统与抽象语言概念的“langage”一词。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它从属性层面将“纯语言”划入了非抽象概念的范畴,表明其并非嵌藏于各种具体语言表象之下的“逻各斯”,而是有着明确具体的指涉对象——“既是失落的语言(在人类语言被上帝变乱进而走向多样化之前的语言),又是终将到来的语言(langue-qui-vient)”(同上:115)。如果说贝尔曼对“纯语言”实质的探究止步于此,那么客观地说,很难在“纯语言”的诉求同“消弭人类语言多样性,回归语言大同”的反动倒退立场之间划清界限。事实上,贝尔曼对本雅明的思想脉络有着更为深入的透视。他继续分析道,法文中“langue”和“langage”的区分在德文中是模糊的,两者都指向“Sprache”一词,而“纯语言”概念因为康德哲学对本雅明毋庸置疑的影响,必然受到“纯粹理性”的启发,但是若仅看到这一点,“纯语言”就会无可避免地和“纯粹理性”的终极指向“逻各斯”划上等号。贝尔曼在此提醒我们,虽然不可能将对一种“普适性逻各斯”(logos universel)的指涉完全排除在“纯语言”概念的意涵之外,但本雅明力求通过这一概念传达的是对一种“不传递任何意义”(incommunicatif)和“不承载任何内容”(in-transitif)的非工具属性的语言的向往(同上)。
为了深化这一认识,他接着又从“纯语言”概念的另一要素“纯”入手,揭示了本雅明提出此概念的两个理论源头。其中之一即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康德哲学。贝尔曼指出,1916—1920年代的本雅明,其思想正属于一种广义的康德哲学范畴。由于康德哲学视一切非经验性事物为“纯粹”,这就决定了“纯语言”的非经验性——它并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某种具体语言。另一源头是以“纯”作为自身诗歌语言标识的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对“纯”的界定——与本源相关谓之“纯”。在点明以上两点后,贝尔曼总结道,按照本雅明在发表于1916年的《论总体语言和人的语言》一文中所做之阐释,“纯语言”即人类原初语言(langue originelle),或者说人类在亚当时代的语言,因此其本质更接近于荷尔德林意义上的“本源”,而非康德意义上的一种先于各种自然语言存在的“普适性逻各斯”。这一论断再次确认了“纯语言”的非抽象属性,但似乎又随即陷入了对语言多样性的反动。贝尔曼在此不失时机地再度强调:“但是‘纯语言’也意味着空无(vide)和不传递任何意义,纯语言就是不承载任何内容的语言,是依托于其自身的语言,而非借以实现某种目的的途径”(同上:116)。循此,则我们在理解“纯语言”概念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其“具体性”和“同一性”,而无视其“非交际性”。
本雅明在《任务》中指出,语言间亲缘性的表现并不仅限于建立在历史关联基础上的相似性,更在于不同语言对“纯语言”的共同指向,而翻译则令这种亲缘性得以显现(Benjamin,2000:250)。那么,翻译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传统翻译理论以语言间的相似性为基础,将翻译可行视为语言能够统一的例证,同时将翻译行为视为对语言多样状态的一种胜利。虽然《任务》的论旨与此几乎无涉,但贝尔曼此前对“纯语言”实质所做之剖析又明确提醒我们,视语言多样为消极现象,认为其应当被历史超越的意识确实隐现于本雅明的翻译观之中。就此而言,本雅明的翻译观同传统翻译观实有共通之处。但是在贝尔曼看来,这依然无法成为判定本雅明翻译观的终极导向是消弭语言多样性的依据。他极富创见地总结道:“本雅明关于翻译的思考同传统翻译理论并行不悖,但却对其重新加以诠释,并在这种诠释中将其导向别的可能”(Berman,2008:120)。这里所说的“别的可能”,即本雅明借助“被打碎的容器碎片重新黏合在一起以还原容器本来面貌”这一隐喻所揭示的各种自然语言之间以及它们同“纯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语言间的相似性不再有任何意义,有如容器碎片的各种自然语言经由翻译参与到对“纯语言”这一完整容器的还原和再现,并由此显现出彼此间的亲缘性。在此基础上,贝尔曼进一步总结道:“‘语言多样化的幽灵’这种夸张说法得以彻底改变,我们在本雅明那里找不到这样的夸大其辞,甚至都找不到将这种多样化完全视为消极现象,并因此依托某种自然语言抑或人造语言来超越这种现象的意思”(同上:121)。既然语言多样性不再被视为一种消极现象,“纯语言”也就不再以对自然语言的绝对超越为诉求,它是自然语言汇聚而成的一种“更大的语言”(langage plus grand),并非某种具化的世界通用语。这里的“汇聚”自然以翻译为途径,不过贝尔曼逻辑缜密地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汇聚只要经由翻译就能完成,准确地说,这种汇聚只是在翻译中被预示,而且是通过一种碎片化的方式被预示”(同上)。这一观点同德里达在其专论《任务》的长文《巴别塔》中所持见解如出一辙。德里达认为:
各种语言和各种意图在相互协作下所指向的目标,并非超验于语言之上,也不是它们从各个层面参与构建的一种现实[……]。它们各自所意指和在翻译中共同所意指的,是本身即如“巴别塔事件”般的语言,既非莱布尼兹所说的世界通用语言,亦非如各种语言那样的自然语言,而是语言的本真存在,语言的本有面貌,即令世间语言多样且每种语言都成其为语言的那种毫无同一性的统一体。(Derrida,1987:232)
可见,作为各种自然语言“汇聚”之结果的“纯语言”,实际上是一个非现实和非具化的概念,其指涉的非但不是一种绝对的“同一性”,反而是反映“语言之本真存在”的多样性。也即是说,“纯语言”只是在各种语言的互补和融合中不断被预示,但却永远无法被切实地触及。虽然本雅明声称翻译预示着“语言救赎的终点”(Benjamin,2000:251),但在德里达看来,一切都以对翻译和“终点”之间“距离”的认知为前提,而且这一“距离”只能被认知,无法被跨越,因为正是它让我们得以接触到语言之真(Derrida,1987:233-234)。
在《任务》中,本雅明是在思考“如何在翻译中使纯语言的种子成熟”这一问题时引入“直译”(littéralité)概念的(Benjamin,2000:255)。如果忽略这一前提来理解其“直译观”,就很容易仅仅视此为在实践层面上为一种具体的翻译方法摇旗呐喊。贝尔曼在评论该部分内容时,便开门见山地指出:“这里涉及的不是一种方法,本雅明没有给出任何(实际操作方面的)指示”(Berman,2008:161)。本雅明之所以宣扬“直译”,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之间的接合以及对纯语言的无限接近只有在文字层面才能实现:“译作不是要再现原作的意义,而是要精心细致地融会原作的意指方式,从而使原作和译作都能被认出是一种更高级语言的碎片,恰如碎片是容器的组成部分一样”(Benjamin,2000:256-257)。贝尔曼就此做出分析:“既然翻译的目标是达致纯语言,那么即便原作再重要,相比之下其重要性也只能退居其次”(Berman,2008:165)。不再一切以原文为基准,这一点足以说明本雅明的“直译观”并不局限于传统上以原文为唯一参照的“直译/意译”方法论范畴。本雅明认为:“以直译为前提获得的忠实,指的是作品能够表达对于语言互补的强烈渴望”(Benjamin,2000:257)。贝尔曼揭示了此中隐含的“远隔理论”(théorie du lointain),即译作对原文语言的忠实,使得作为外语的原语同译语形成互补,但这种互补是在“渴望”和“远隔”的状态下进行的(Berman,2008:167),即如本雅明所言:“翻译并不置身于语言森林的中心,而是置身于森林之外……只向森林里呼喊,对准那在自己的陌生语言中能产生原作回声的唯一地方”(Benjamin,2000:254)。如此一来,翻译便具有了相互矛盾的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无限贴合原文的语言,一方面又要保持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距离。然而在贝尔曼看来,这种矛盾性正是区分真伪直译的法门。换言之,作为具体翻译方法的“直译”,只一味追求对原文语言的贴合,因此并不完全契合本雅明的“直译观”。
在对随后的《任务》文本进行评论时,贝尔曼提醒我们,本雅明非但没有对“意义”这一原本应该被“直译”方法弃之不顾的概念避而不谈,反而明确表示:“在各种语言中,纯语言这种终极本质只与语言因素及其变化相联系,而在语言创造中,它却负载着沉重的、陌生的意义”(同上:258)。因此,如果说以重现原文意义为宗旨的翻译取向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丝毫不理会原文在文字层面的特点,那么以贴合原文文字层面为宗旨的翻译取向却必须面对“任何语言、任何作品中都有意义”的客观事实(Berman,2008:174)。尽管本雅明强调翻译的任务旨在摆脱意义的重负,但“其立场不应被理解为是要在意义和文字两种翻译取向中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他的想法并非如此,他对翻译中意义和文字的关系所做的是带有思辨性的思考”(同上:177)。贝尔曼在此所说的“带有思辨性的思考”,即在意义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因素,不会于翻译中消失的前提下,重新梳理其与文字的关系。
综上,贝尔曼的评论式分析让我们更好地窥见了本雅明“直译观”的本质,我们可以凭此断言,将这种“直译观”完全等同于作为具体翻译方法的“直译”,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解读。
结 语
至此,我们可以对本文开篇提到的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和《远方的客栈》两部著作中对《任务》一文所持态度截然相反的现象做出合理推断:本雅明的“纯语言”概念实际上将《任务》的读者引导至一个需要对该概念价值取向做进一步判断的岔路口,如果将其理解为本雅明释放出的鼓励译者追寻“人类原初共同语”或是某种人造语言用以取代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反动信号,那便就此陷入贝尔曼所说的形而上翻译观,具有了“反巴别、反差异、反人类经验”的属性。考虑到贝尔曼是在撰写于1981年5月的《异的考验》一书的前言中对“纯语言”概念提出批判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贝尔曼本人当时也身处对“纯语言”价值取向做出判断的岔路口。随着他以“评论”视角切入《任务》文本,他对“纯语言”概念在本雅明语言哲学体系中的错综复杂性才逐渐有所认识。《异的考验》作为其代表作,为译学界所熟知和研读,其中对“纯语言”概念所做之评价很容易为人援引,用作批判此概念的理据。《翻译的时代》一书令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事实上,正是对包括“纯语言”在内的《任务》一文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脉络所做的这种客观、全面、立体的把握,才使得该书在出版近十年后依然保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Benjamin,W.2000.Oeuvres complètes.Tome I.Paris:Folio/Gallimard.
Berman,A.1995.L'Épreuve de l'étranger.Paris:Gallimard.
Berman,A.1985.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Paris:Éditions Trans-Europ-Repress.
Berman,A.1995.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Donne.Paris:Gallimard.
Berman,A.2008.L'Âge de la traduction:La Tâche du traducteur de Walter Benjamin,un commenta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Derrida, J.1987.Psyché.Invention de l'autre.Paris:Éditions Galilée.
De Man,P.2003.Autour de La Tâche du traducteur.Paris:Théâtre typographique.
Nouss,A.1997.“La réception de l'essai sur la traduction dans le domaine français”.TTR 2.pp72-84.
Oseki-Dépré,I.2007.De Walter Benjamin à nos jours.Paris:Honoré Champion.
袁筱一,2011,从翻译的时代到直译的时代——基于贝尔曼视域之上的本雅明,《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1期:8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