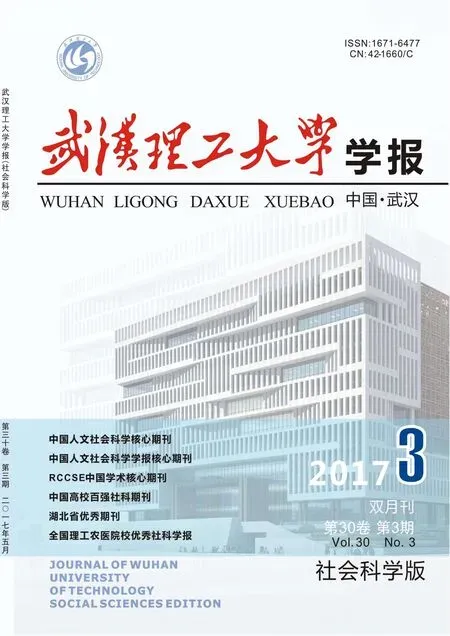黑格尔历史主义视域中的辩证法与解释学*
李永刚
(长江大学 社会发展哲学研究所,湖北 荆州 434023)
黑格尔历史主义视域中的辩证法与解释学*
李永刚
(长江大学 社会发展哲学研究所,湖北 荆州 434023)
黑格尔历史主义精神中蕴含着辩证法与解释学两大因素,前者是显性的,后者作为黑格尔思辨体系的理论基础则是隐性的,辩证法与解释学在黑格尔历史主义精神中实现了统一,由此形成了黑格尔历史理解的两大方法,即历史主义的重构方法和解释学的综合方法。但黑格尔思辨体系的封闭性禁锢了辩证法的开放性,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重新发掘出了辩证法的对话性,使黑格尔的独白逻辑发展为问答逻辑,由此历史理解的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理解的目的不是“更好的理解”,而是“不同的理解”。
黑格尔;历史主义;历史辩证法;解释学;精神
伴随着欧洲历史意识的觉醒,在反对绝对理性和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主义思潮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顶峰,因为他将一切都历史化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完全等同于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意味着只有当哲学是历史的,只有当哲学家意识到其学说的起源、背景和发展时,哲学才是可能的。”[1]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思想中蕴含着辩证法与解释学两大因素,前者是显性的,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根本特征,后者则是隐性的,只有在其效果历史中才能明确认识到其意义。辩证法和解释学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精神中是统一的,但由于黑格尔思辨体系的封闭性,开放的辩证法被禁锢在僵死的体系之中,只有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辩证法才重获生机,才实现了辩证法与解释学的真正统一。
一、历史主义与辩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在于范畴的演绎,即从前一范畴必然地演绎出后一范畴,这种必然的逻辑联系的根据在于后一范畴作为对立面而被包含于前一范畴之内,“黑格尔发现概念可以包含隐藏在自身之内的它自己的对立面,而且这个对立面可以从概念中被分析或演绎出来,并被迫起种差的作用,这样就把类概念转变为种概念。”[2]也就是说,范畴A从自身必然地演绎出作为自己对立面的范畴B,而范畴B又同样演绎出作为自己对立面的范畴C,而范畴C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回复到了范畴A,但范畴C无疑是具体化的范畴A,或者说,范畴A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范畴B而实现范畴C。由此就构成了一个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式的圆圈,若干这样的小圆圈构成了黑格尔辩证逻辑体系这个大圆圈。
黑格尔将这种辩证法应用于历史理解,但他并不认为对于历史理解来说,辩证法是一种先天的(a priori)方法,因为他认为辩证法并不是外在于世界历史而强加于它的方法,相反,世界历史应是精神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历程而呈现出辩证的性质,因而,逻辑学所演绎证明的辩证法是世界历史自我理解的恰当方法,同样是历史学家观察乃至写作历史的恰当方法。
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堆积,历史本质上是一理性的过程,因为“理性支配着并向来支配着世界”[3]14。逻辑学所演绎证明的是理性的纯逻辑的发展历程,而这一逻辑理性可以“外化”或“异化”为自然世界的理性和精神世界的理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具有自我意识,而前者是不自觉的。精神,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理性的完全自我意识,而所谓的“自我意识”就是对自身存在的意识,也就是不依赖于他物而实现的自己对自身存在的意识,这就是作为精神的实体的“自由”。由此,黑格尔的整个精神哲学就成为了精神实现完全的自我意识,即自由的历程。那么,作为精神在时间中的体现的世界历史,同样是“自由意识的进展”[4]54。这样,黑格尔就把整个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向着自由的充分实现前进的整体,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因其对自由的意识程度而被纳入这个前进历程的某一位置,由此形成了一种哲学化的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开始于东方,在这里“因为精神还没有取得主观性,所以它的精神性的外衣仍然汩没在自然状态之中。”[3]112也就是说,东方精神是一种直接的、未反省的精神,在其中,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实体的差别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君主将自己看作国家,同时也将国家看作自己,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实体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因而他是自由的,且仅有他自己是自由的,“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作为实体性存在的‘唯一的个人’,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3]105这是世界历史的“童年时期”,也是历史辩证法的“正题”。东方精神的直接同一所蕴含的两个方面,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实体,各自发展到极端,由此形成了世界历史的“青年时代”,即希腊世界和“壮年时代”,即罗马世界。从逻辑上看,这两个时期都是作为“正题”的“反题”而存在的,即各从一个方面否定了直接同一的东方精神,但它们在相互反对的同时也体现了世界精神的真正进展:主观、主体统一于客观、实体之中,由此,主体逐渐具有了实体性,实体逐渐实现了内在化。在黑格尔看来,主体与实体的真正同一,精神的完全自我意识,即自由的充分实现是在世界历史的“老年时代”,即日耳曼世界,这是历史辩证法的“合题”。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但我们应该看到,历史辩证法并不完全符合于纯逻辑辩证法,因为它并不单纯是逻辑范畴的演绎,而是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这种逻辑演绎,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根据实际的历史发展来修正纯粹的逻辑演绎,由此体现了辩证法的解释学内涵。查尔斯·泰勒称这种历史辩证法为“解释性的或解释学的辩证法”(interpretive or hermeneutical dialectics),以区别于作为纯逻辑辩证法的“本体论的辩证法”。[5]300
民族是世界精神的具体承担者,“某一特殊民族的自我意识是普遍精神在其定在中这一次的发展阶段的肩负者和普遍精神将其意志摆在那里面的客观现实性。”[6]359-360在世界精神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民族分别在某一阶段成为其具体的承担者。当世界精神落在某一民族头上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某一民族精神具体体现了世界精神时,这一民族就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成为了世界历史性民族。但这样的光荣时刻只有一次,当世界精神越过了这一发展阶段,就会有另一民族取代其位置而成为世界历史性民族,当然这一民族之所以会被取代,是因为“在这个民族中出现了一个作为纯粹否定它自己的更高原则”[7]354,也就是说,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是世界精神发展的手段和具体体现,由此,历史辩证法也可称之为“民族精神的辩证法,即世界法庭”[6]355。
既然某一民族真正的历史仅仅是当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那段时间的历史,那么,哲学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方法有两种:或者重返当时的历史时刻重构出其历史处境而历史性地理解某一历史,是为历史主义的重构方法;或者从世界精神发展的当前时刻综合性地理解世界精神的某一历史,是为解释学的综合方法。在此,我们仅论述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将在下一部分中论述。
精神的创造物总是具有历史性的,就如同每个人都具有历史性一样,“每一个体都是其民族发展某一阶段的产儿。没有人能够超出其民族精神,就如同没有人能超出地球本身一样。”[4]81由此,要真正地理解某一艺术、宗教、哲学或民族精神、世界历史个人,就必须返回到其所处的精神发展阶段,重构其历史处境。但这种“返回”并不是要摒弃我们现有的“前见”,也并不完全是浪漫主义意义上的“移情重构”,而是要我们带着当前发展阶段上的精神这种“前见”去认识不自觉的个体行为所体现的世界历史目的,从而以理性为主线理解纷繁复杂的事件和行为。比如,我们要理解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我们应首先返回到拿破仑所处的历史处境,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他为了实现其个人目的而诉诸于各种行为,这些行为在当时看来好像仅仅是为了满足其个人欲望,因而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而且由于其给他人或其他民族带来了灾难而应受到谴责,但实质上,这些行为充当了实现世界精神的不自觉的工具,是合乎理性的行为。正因为我们是带着“前见”的“返回”和“重构”,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行为和事件,真正理解拿破仑这个“世界历史个人”。
当然,这一历史主义的重构方法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历史是一理性的连续过程。整个世界历史作为精神逐步实现其完全自我意识的进步历程而成为一个连续体,真正的历史理解本质上就是精神的自我理解,因此,这种精神的自我理解不需要浪漫主义的心理学重构就能实现。同时,由于黑格尔坚持历史的进步论,每一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根据自由的完全自我意识这一“绝对真理”而得以理解,因而黑格尔避免了浪漫主义者普遍具有的相对主义倾向。这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不同于浪漫主义者的历史主义的根本之处。
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同样体现在观察历史的方法上。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其中:第一种是基于“原始的历史”考察,它源自于一种纯粹的或自在的历史意识,即对时光流逝的简单反映。在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这样的历史学家那里,“他们的叙述在极大程度上局限于他们眼前的行为、事件和社会状态,以及他们共有的精神。他们简单地将周围世界中匆匆而逝的东西转移到再现性的智力王国。”[3]1而且,历史学家本人可能也参与了他所叙述的历史,由此,时代精神决定了他观察历史的角度及所能够从历史中看到的东西,而他的叙述具体体现了时代精神,所以,历史学家的精神与时代精神是直接同一的,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正题”。作为“正题”的“反题”的“反思的历史”打破了这种原始的直接同一,时代精神已超越了历史学家的当下,历史意识自觉地意识到了个体与时代精神、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距离,是为“自为的历史意识”。这样,历史学家就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去填补这一精神鸿沟,从而能够历史主义地重构已过去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反思的历史”:普遍性的、实用性的、批判性的和概念性的。每一种都代表了“自为的历史意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反思性历史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种类,即自在的(普遍性历史)、自为的(实用性历史)和自在自为的(批判性历史);第四种类型(概念性历史)则充当一个新层面,即哲学性历史的过渡和基础。”[8]个体与时代、过去与现在的精神和时间鸿沟的真正弥补在于将历史哲学化,即完全从理性、精神的角度来思考历史,“哲学的世界历史的普遍视角不是抽象的普遍的,而是具体的、绝对当前的。因为精神对其自身是永恒的当前,没有过去。”[4]24这种“哲学的历史”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合题”,从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来看就是“自在自为的历史意识”。
这种历史观念的辩证发展同样是历史主义精神的体现。从黑格尔思想来看,历史观念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历史精神的自我意识程度;二是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精神的意识程度,因此,每一种历史观念都有其适用的特定时代和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历史观念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但一旦超越了这一阶段,假如历史学家仍固执地遵循原来的历史观念,这就犯了“时代错误”。
辩证法是黑格尔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并不是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赋予逻辑学、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而是从逻辑学、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本身的辩证性质中抽象出了这一方法,因而它就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同时,辩证法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绝对精神历史性地自我认识所应用的方法,因而浸染着历史主义精神,“黑格尔哲学本质上就是历史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价值之一就在于将历史性赋予了哲学。在他那里,辩证法贯穿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精神,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古代辩证法的发现与完成,但它深深打上了‘历史主义’的时代烙印。”[9]因而有学者径直称之为“辩证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政治和哲学思想,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文明的命运。”[10]
二、历史主义与解释学
一般来说,黑格尔算不上是一位解释学家,因为他既没有对解释学的自觉意识,更没有留下有关解释学思想的论述,但从其思想的效果历史来看,他却是解释学史上的一位关键性人物,“黑格尔在现代解释学(或解释理论)的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既丰富地继承了过去(特别是赫尔德),又大量地遗赠给未来(特别是狄尔泰和伽达默尔)。”[11]这表明,黑格尔处在解释学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方法论路线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本体论路线的分界点上,从中既可以引申出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又可以引申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但黑格尔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可以说,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深层蕴含着深刻的解释学思想,正是这一隐性的解释学思想支撑起了黑格尔的辩证历史主义体系。
青年时代的黑格尔被当时的表现主义思潮所深深打动。表现主义理论放弃了存在与意义的启蒙二分法,认为“人的生命既是事实,又是意义的表现;它的存在表现并不归结为与某个他物相关的一种主观关系,它表现了它实现的理念。”[5]22也就是说,生命的外在表现或外在行为就是生命本身的体现,生命本身的意义和目的也只能通过其外在表现才能实现,而且,其最终的结果是生命本身与其外在表现的和解与统一。黑格尔就是以这种表现主义理论来理解“精神”的:精神的“外化”或“异化”就是精神的外在表现,必须通过精神的客观化物才能理解精神。这也是狄尔泰所理解的“理解”与“解释”的含义,正是由此,狄尔泰从心理学走向了解释学,力图以此为精神科学奠定方法论基础。
赫尔德—施莱尔马赫传统的浪漫主义解释学主张历史主义的重构学说,即我们只有重构文本作者所处的历史处境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黑格尔赞成这一历史理解方法,但也认为如果我们从精神发展的更高阶段,甚至从绝对精神去回顾、俯瞰精神的历史,就能够跃出当时所处的历史局限性,更能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密纳法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7]序言,14的含义,这也就是黑格尔理解世界历史的解释学综合方法。
浪漫主义解释学的核心目的是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意,总体而言,黑格尔是反对这种理解观念的。他以表现主义的生命与生命的外在表现的本质同一为根据,认为艺术作品是其时代精神的外在表现,艺术理解的目的就是要透过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而理解其内在精神,而这一艺术作品的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在很多程度上是外在的、偶然的历史产物,因此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艺术作品本身所内含的意义,这才是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所以,理解艺术作品就在于撇开其作者的个人意愿、材质等具有外在偶缘性的东西,从而理解其内在精神。重构文本作者的原意“却只是外在的行动,类似从这些果实中擦去雨点,扫除灰尘,并且不去掌握那围绕着、创造着和鼓舞着伦理生活的现实性的内在因素,而去建立它们的外部存在、语言、历史等僵死因素之烦琐冗长的架格,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寝馈于其中,而只是为了把它们加以表象式的陈列。”[12]232因而,这种理解观从本质上说偏离了精神的自我理解。真正的理解在于从绝对精神出发的“回顾”,以绝对精神为精神辩证发展的顶点和目的,在原来的历史处境中看似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有了理解的可能性,“正如那个把摘了下来的水果捧出给我们的少女超过那直接生长出水果的自然界:自然的条件和因素、树木、风雨、日光等等;因为她是在一个较高的方式下通过自我意识的眼光和她呈现水果的姿态把这一切予以集中的表现;所以同样提供我们那些艺术品的命运的精神超过那个民族的伦理生活和现实。”[12]232这种从更高精神出发的“回顾”才是理解艺术作品,乃至理解所有精神的客观化物的根本方法。同时,黑格尔从辩证法出发认为理解并不是直觉式的“体验”,而是有“中介”的,正是由于“中介”的存在才能最终实现“和解”,即完全的理解,正如威舍默所说:“黑格尔在解释学上超越施莱尔马赫之处在于,他肯定差异是同化和占有的条件而不是障碍。”[13]因此,这种从精神的更高阶段,乃至从绝对精神出发的,精神的辩证地自我理解就是黑格尔的解释学。
在反对作者的原意方面,黑格尔无疑更接近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但黑格尔将这一思想与“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相关联,认为理解者因为理解了作者或历史人物无意识的东西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黑格尔将“更好的理解”思想应用于对世界历史个人的理解上,认为像凯撒、拿破仑等这样的“世界精神的代理人”是为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的而奋斗的,他们的敌人和追求都是明确的,“凯撒为了保持他的地位、名誉和安全,正同他们抗争。由于他的政敌的权力包括着罗马帝国各行省的主权在内,所以他的胜利同时就是征服了整个帝国,因此他在不变更政体形式的情况下成为了国家的独裁者。”[3]29这是凯撒的自我理解,根据浪漫主义解释学的重构理论,我们也是要实现这样的理解,但在黑格尔看来,更为根本的是理解凯撒的目的、行为背后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或者说,精神要利用凯撒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此,凯撒本人是不自觉的,是为“理性的狡计”。根据解释学的综合方法,理解者从精神发展的更高阶段,乃至从绝对精神出发,明确地意识到了世界历史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相较于不自觉的世界历史个人而言,理解者确实是比世界历史个人更好地理解了他自己。应注意的是,这种解释学综合方法同样需要“重构”,但不是浪漫主义解释学的心理重构,而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历史主义的重构,因为只有历史地理解了世界精神的外在表现,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世界精神,所以黑格尔要有一部哲学的历史,要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来证明逻辑学所演绎的理性辩证发展进程。
辩证历史主义的重构和解释学的综合共同构成了黑格尔历史理解的基本方法,相对而言,前者是显性的,因为辩证法是黑格尔逻辑演绎的根本方法,将其应用于时间进程中便具有了历史性特性,正是这种辩证历史主义体现了黑格尔不同于浪漫主义的根本之处。但在显性的辩证历史主义的背后起理论基础作用的则是解释学思想,因为要透过精神客观化物来证明精神的自我理解进程,就必须要“理解”和“解释”精神的客观化物,而这就是解释学的价值之所在,因而,虽然黑格尔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解释学,但他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古代解释学,特别是同时代的赫尔德—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传统的深刻影响,以服务于精神的自我理解。同时,这一隐性的解释学思想又深深浸染于19世纪的历史主义精神之中,由此形成了历史主义的解释学或解释学的历史主义化。因而,在黑格尔这里,辩证法与解释学在历史主义精神中实现了统一。
三、历史辩证法与哲学解释学
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绝对理性体系既相互适应又存在着矛盾,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相反,黑格尔的思辨观念论所要求完成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综合包含着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它以黑格尔‘辩证法’一词在词义上的摇摆不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具体来说,一方面,‘辩证法’可以视为能在一切对立和矛盾中看出整体的统一性和统一的整体性的理性观点;但另一方面,辩证法又与其古代含义相适应,即被认为能使一切矛盾尖锐化而陷入不可解决的‘绝境’,或换言之,被认为能够制造出矛盾以使思想跌入无意义谈话的深渊,尽管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矛盾共存于矛盾统一体中。”[14]110这表明,一方面,辩证法能够完成理性的绝对体系,因为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立面的统一和矛盾的和解,由此而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和解体系;但另一方面,辩证法又是开放的,其目的是要暴露矛盾以启发思考,这是辩证法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正是这一点使黑格尔陷入了深刻的对立之中,即体系本身的封闭性和辩证法的开放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体现在世界历史的理解之中,就形成了世界历史是否有终点的问题:一方面,从精神的完全自我理解,即自由的最终实现来看,世界历史是完成了的,因为各种对立和矛盾都在日耳曼世界中实现了和解,所有人都意识到自我是完全自由的,君主立宪制的普鲁士国家就是精神在客观世界中的完美体现,由此日耳曼世界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点;但另一方面,历史辩证法又有突破这一封闭体系的倾向,它既认为历史仅仅关注于过去和现在而无法预知未来,又认为“美洲乃是明日的国土,在那里,在未来的时代中,世界历史将启示它的使命。”[3]86总体而言,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被禁锢在封闭的体系之中,其开放性最终也成为了僵死体系的牺牲品。
那么,如何使辩证法重获生机,如何使历史辩证法重新成为历史理解的恰当方法呢?这就需要重新复活作为黑格尔思想体系的隐性理论基础的解释学思想,并在哲学解释学的视域中重新理解辩证法。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辩证法是一种引导谈话的艺术,是以问题—回答为外在形式的思想交流,黑格尔将这种对话辩证法形式化为三段论式的自我独白,虽然其本质仍是思想的自我运动,但却丧失了对话艺术的开放性,而像先知宣布神的意旨一样从黑格尔口中流露出来。伽达默尔虽然高度评价这种辩证法,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永远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源泉”[14]3,但“辩证法必须在解释学中恢复自身。”[14]99这种“恢复自身”并不是要将某种解释学因素强加到辩证法之中,而是要将黑格尔辩证法内含的对话性重新发掘出来,“语言的进行方式是对话,甚至可说是灵魂和自己的对话,就如柏拉图对思想所描述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诠释学就是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解理论和相互理解理论。……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就已基本上包含了这种观点。”[15]这就明确地说明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内含着对话性,只是被禁锢在了先知式的独白之中,正是这种对话性发展为了哲学解释学的问答逻辑,而这就是辩证法在哲学解释学中恢复自身的成果。由此,在伽达默尔那里,辩证法与解释学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伽达默尔就自称其辩证法为“解释学辩证法”(the hermeneutical dialectic),帕尔默则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为“辩证法的解释学”(dialectical hermeneutics)。
这种问答逻辑本质上就是一种“视域融合”过程,也就是理解者自身的视域与被理解者视域之间的对话,从而使二者之间的“时间距离”得到“中介”,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相对于这种“视域融合”来说,黑格尔理解历史的两大方法各有其缺陷:历史主义的重构方法带有以历史视域取代当前视域的倾向,而解释学的综合方法则带有用当前视域取代历史视域的倾向。不可否认,黑格尔历史理解的两种方法是融合在一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从表面上看这类似于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但从根本上说,这是用一种视域取代另一种视域,因为黑格尔主张我们能够比前人获得“更好的理解”。与此不同的是,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所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更好的理解”,而是“不同的理解”,因为“视域融合”的关键并不在于用一种视域取代另一种视域,而在于视域交流融合基础上所形成的新的东西,而这种新的东西总是历史性、处境性的,即是说,总是不同的理解。
黑格尔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解释学因素,而这种解释学更多的是从赫尔德—施莱尔马赫传统继承下来的,因而其在本质上隶属于方法论解释学,但黑格尔思想中的本体论因素又使得这种解释学具有发展为本体论解释学的内在可能性,伽达默尔就肯定地说:“假如我们认识到以跟随黑格尔而不是施莱尔马赫为己任,诠释学的历史就必须有全新的着重点。”[16]从西方解释学的现代发展历程,即从黑格尔解释学思想的效果历史来看,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解释学需要在哲学解释学中重新理解自身,并在历史理解中融为一体。
四、结 语
作为一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哲学家,黑格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精神的自我理解进程,或者说,将精神的自我理解进程历史主义化了,由此,作为精神自我理解进程的方法的辩证法同样也历史主义化了,这种辩证历史主义明显地体现在世界历史的理解之中。在世界历史的理解之中,辩证法并非是纯逻辑的“本体论的辩证法”,而是“解释性的或解释学的辩证法”,由此,解释学同样构成了世界历史理解的基本方法,但与辩证法相比,解释学思想是隐性的,是作为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而起作用的。同样,作为隐性理论基础的解释学思想也必然历史主义化了。这样,在黑格尔这里,辩证法与解释学在历史主义精神中实现了统一。但是,黑格尔思辨体系的封闭性最终禁锢了辩证法本身内含的开放性,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重新恢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辩证法的开放性和对话性,并将其应用于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之中,由此,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不同视域对话、融合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辩证法是解释学的,同样,解释学也是辩证法的,并且二者共同统一于历史主义之中,但这种历史主义已经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了。
[1]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gel[M]. Edited by Frederick C. Beis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270.
[2]司退斯.黑格尔哲学[M].廖惠和,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82.
[3]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M]. Translated by J. Sibre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56.
[4]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Introduction: Reason in History[M]. Translated by H.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5]泰勒.黑格尔[M].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黑格尔.精神哲学[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 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8]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 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19.
[9]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0.
[10]安东尼.历史主义[M].黄艳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88.
[11]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gel and Nineteenth-Century Philosophy[M]. Edited by Frederick C. Beis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74.
[1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 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3]Joel C. Weinsheimer. Gadamer’s Hermeneutics: A Reading of Truth and Method[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131.
[14]Hans-Georg Gadamer. Hegel’s Dialectic: Five Hermeneutical Studies[M].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 Christopher Smith.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5]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39.
[16]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51.
(责任编辑 文 格)
The Dialectics and Hermeneutics in Hegel’s Historicism
LI Yong-gang
(InstituteofSocialDevelopmentPhilosophy,YangtzeUniversity,Jingzhou434023,Hubei,China)
The dialectics and hermeneutics are two major factors in the spirit of historicism of Hegel where the former is dominant, and the latter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egel’s speculative system. The dialectics and hermeneutics are unified in the spirit of historicism of Hegel.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major method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which are the reconstruction method of historicism and the comprehensive method of hermeneutics. But the closure of Hegel’s speculative system imprisons the openness of dialectics.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rediscovers the dialogic of the dialectics, and develops the 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 from Hegel’s monologue logic.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s the fusion of horizons, and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i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better understanding”.
Hegel;historicism;historical dialectics;hermeneutics;spirit
2016-11-22
李永刚(1981-),男,山东省青州市人,长江大学社会发展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解释学与德国哲学研究。
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思想研究”(14YJC720015)
B516.35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