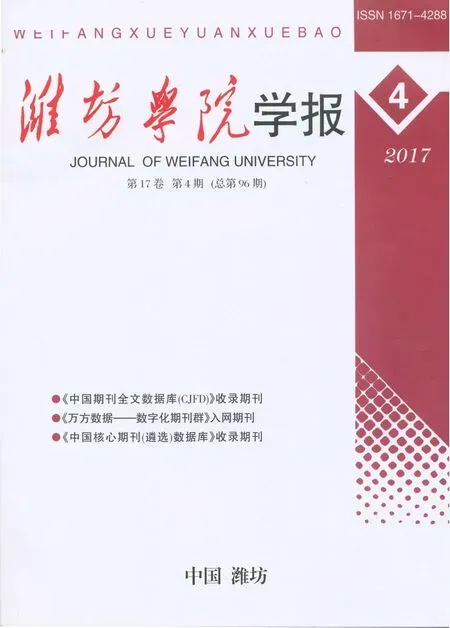秋声不“悲”
——《秋声赋》的文学性与戏剧性辩白
温雅红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秋声不“悲”
——《秋声赋》的文学性与戏剧性辩白
温雅红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秋声赋》是田汉在1944年以他真实生活为原型创作的一部五幕剧。作为一部戏剧,《秋声赋》未能与田汉伟大的艺术成就相谐,但就其文学审美性而言,却可以称得上田汉在建国前文学性最高的作品,深切表现了特殊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为田汉戏剧实验的代表作,《秋声赋》多方融汇了田汉戏剧创作的艺术追求。在戏剧史上,《秋声赋》历史意义高于其价值裂隙所带来的不足。
《秋声赋》;文学性;戏剧性
《秋声赋》是田汉为协助“新中国剧社”而到桂林创作的一部作品。田汉初到桂林时,被秀美的山川吸引,增添了不少灵感,加之当时文化界和他的家庭生活中遭逢浓浓的秋意,为打破这暮气沉沉的局面,他写作《秋声赋》一吐内心郁积多年的不快。该剧在“新中国剧社”首次演出后,卖座甚好。但随着时间推移,《秋声赋》在文坛影响日渐式微,以致未在田汉名作之列。不可否认,《秋声赋》作为田汉艺术追求的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文学性,但在戏剧史上的失势也不乏因由。因此,本文试图从三个视角切入,结合田汉的人生经历,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为《秋声赋》正名。
一、内与外:“痛苦慰藉”与“社会需要”的悖谬
与其他作品不同,《秋声赋》更像是田汉的一则内心独白,将自己感情和革命中的困境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秋声赋》是围绕知识分子徐子羽家庭和革命事业中的苦闷展开的。开篇一首主题歌奠定全剧的感情基调,“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此时的徐子羽正面临着双重的夹击。一则是文化界的寥落,他的刊物难以维持,抗战文艺界一派萧条景象,到处暮气沉沉。一则是家庭关系矛盾和感情变故,曾经支持他革命工作的妻子淑瑾日益消磨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不仅不能给予他事业上的帮助,而且两人还常常因琐事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恰逢此时昔日并肩作战的情人胡蓼红归来,誓死夺回曾经的恋人。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徐子羽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对于妻女他有作为丈夫的责任,对于曾经的情人他亦有不舍和挂念,多重困扰之下悲从中来,满目尽是秋意,呈现了知识分子在面临现实与理想、爱情与婚姻抉择时的内心冲突。
剧中的徐子羽可以说是现实中田汉的真实写照,田汉同样在妻子林维中与情人安娥之间纠缠。林维中正是剧中秦淑瑾的原型,原本大胆独立的林维中,婚后日渐消沉在“家”的小圈子里,放弃了工作,与热烈从事革命事业的安娥相比,更落后偏狭。与剧中结果不同的是,林维中几次三番大吵大闹,让田汉颜面尽失,两人关系濒临解体。因而《秋声赋》可以说是田汉现实生活窘境的反映,并且在其中倾注自己的理想,希望两个女性能联合起来一起为革命事业奋斗。田汉是个善于“移情”的作家,他将自己的生活组织进情节结构之中,个人的思想情感多在作品的人物身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显现。《秋声赋》虽也有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但主要是一部个人感奋和解脱苦闷之作,他把艺术创作看做是对生活的美化,用艺术来慰藉痛苦的灵魂。
但田汉本人的性情和艺术观念决定了他不可能将《秋声赋》写成一部大团圆式的激情澎湃的家庭革命剧。他幼时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性情中带有一种憔悴、忧郁的气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无从发泄,唯有在进入自己熟悉的领域时方能一吐为快,也许在写作过程中他也曾对这样的写法有所顾虑,但倾诉的渴望压倒写作的理性,在无意识中创作出一个带有自传性、独白性的作品,“他希望出现王尔德所云‘人生模仿艺术’的善境,也就是他企求现实的苦闷在艺术中得到解脱,或者说,用他在艺术中所营造的理想力量去化解活生生的现实矛盾。”[1]
在艺术观念上,田汉是一个文学历史功能和审美功能兼收并蓄的两元论者,他要求作品在具有社会宣传功能的同时不丧失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单纯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最大的悲哀。所以《秋声赋》中不仅大段插入欧阳修《秋声赋》的原文,而且有许多文学性的语言。如“种竹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河山”、“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还有秦淑瑾和胡蓼红分别关于“金木水火土”的解释,以及第二幕中关于皮鞋“擦不光”的暗语,有的普通观众尚且对于这些文言语句理解困难,更勿提在一闪而逝的对话中知晓这些情节设置的用意。在每一幕中都通过“风声、水声、虫声、号叫声”来渲染气氛,通过声音的重复和变化暗示主体情感的起伏,由于戏剧的关键在于“演”,这种由声音代情感的方法在舞台表演中很难引起观众的关注,正如董健所言:“在当时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特殊历史环境里,观众对戏剧演出的接受已经超出了艺术欣赏的常规。剧中哪怕处处是政治演说,观众也以极大地热情和认同感很高兴地看下去。有时演戏本身就是政治行为,台上台下一片沸腾,演员观众同声高呼政治口号。”[2]所以田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艺术观念与剧作的社会功能和呈现方式形成一个内与外的悖论,作者希望个人“痛苦的慰藉”与“社会的需要”相统一,遗憾的是,田汉的这一个理想并未实现,反而导致《秋声赋》戏剧性大大低于文学性。
二、古与今:戏剧表意性与话剧舞台性的对立
田汉的《秋声赋》发表在《文艺生活》第2卷第2期至第6期,在同期刊物上他还发表另一篇文章——《新形势与新艺术》(与众作家)座谈,在此田汉提出话剧的民族形式,反对五四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认为话剧未必新戏曲未必旧,两者都有一个新与旧的问题。“所谓民族形式的内涵,换句话说,是由内容来要求形式,问题的中心是民族的内容,没有民族的内容,也就没有民族的形式。”[3]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从内容角度分析了《秋声赋》文学性高于戏剧性的原因,本部分则从形式方面着手深入探究。
回溯田汉的求学经历,可以发现他在幼时便对传统戏曲颇感兴趣,从最初的影子戏到与梁三奶奶探讨《西厢记》,传统戏曲是引导他走上戏剧创作之路的启蒙老师,也是其血液中潜在的影响因子。成年后田汉在日本求学,深受西方戏剧和日本新剧的影响,在古与今两种戏剧的影响下,田汉对中国戏剧进行创造性的改进。他将中国戏剧千年一贯的“戏曲”一元结构改为“话剧——戏曲”二元结构,即剧中加唱的形式。第一幕中的主题歌奠定全剧凄清寥廓的感情基调,并倡导大家团结起来奋斗。第三幕的《落叶之歌》由低沉转向昂扬,表现出胡蓼红要投身救助难童的工作。据田汉的儿子田申回忆,这首主题歌在当时桂林的学生、知识青年中广为传唱。[4]第五幕中的《银河秋恋曲》将儿女私情化作家园之情,为了哭妈妈的孩子、哭哥哥的妹妹而投身革命运动,丢掉悲伤和家庭的羁绊,壮志昂扬地迎接革命。配合着第二次湘北大捷和家庭矛盾的解决,结尾有了稍显光明的影子,“秋声不悲,只会让我更加兴奋、积极。”与对白相比,唱的方式使剧作更具有抒情性、音乐美,而且唱词可以塑造人物性格,表现性格转变,具有剖白内心的作用。但是在将人物感情最大限度呈现给观众的同时削弱了情节性。《秋声赋》中最根本的在于“秋意”二字,但这也恰恰是最难表现的,与夏衍《上海屋檐下》中的“梅雨”相同,因此《秋声赋》与《上海屋檐下》都属于好的文学作品,但是要搬上舞台排演则有一定的难度。
具体而言,《秋声赋》中情节性较弱,五幕剧多由对话构成,“他的剧中人经常情不自禁地奔放出自己的情感,宛如长江流水一泻千里,因此他剧本中的台词不仅很长甚至长达七八百字,而且有些台词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独白。”[5]由此导致戏剧矛盾冲突不明。《秋声赋》故事载体是徐子羽、秦淑瑾、胡蓼红三人的情感纠葛,但却没有设计戏剧性的冲突,秦淑瑾与胡蓼红这对情敌的矛盾仅仅是造成双方不悦,以及二人间的嫉妒和不屑,并未达到剑拔弩张的不可调和。而徐子羽自始至终都游离于矛盾冲突之外,是超脱世俗的思考者形象,对于由他引起的矛盾从未介入,任由她们发展。幸运的是胡蓼红和秦淑瑾都在自我成长中达成一致,结成同盟。因而与其说《秋声赋》是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的故事,不如说是两个女性共同成长的故事,徐子羽未对她们起到指引作用,反而一直以一个犹疑、摇摆不定、感情脆弱的忧郁男子形象出现,在以母亲为代表的三个女性的保护下生长,甚至从通篇看来,所谓家庭关系的矛盾不过是徐子羽优柔寡断、矫揉造作的情感弱点导致,有故作呻吟之感。“既以对人精神状态影响最深切的爱情纠葛为主旨的载体,主人公应深入戏剧矛盾,而由主旨高远的需要,主人公又得超脱,是现实主义的败笔。”[6]对比同时期夏衍的《芳草天涯》便可明白《秋声赋》戏剧效果不高的原因,同样是知识分子情感纠葛的题材,因对矛盾的处理方式不同,戏剧效果也不同。
《秋声赋》中人物众多,除了主要人物徐子羽一家和黄志强之外,还有许多次要人物登场,且仅在某一幕中出现。如与胡蓼红相关的难童有8人,徐子羽的朋友有7人,此外还有配角11人。人物众多且又是一闪即逝,并未形成网状结构,而是呈放射状散射。加之人物性格扁平,如徐子羽的性格可以用忧郁一词概括,胡蓼红前后的转变有些生硬,仅由大纯不叫她妈妈一事便激起她要做天下孩子妈妈的转变,原本徐、胡、秦三人前后的转变是可以大做文章的,透过其挣扎、矛盾展现知识分子的心灵困境,揭露当时压抑、晦暗的时代氛围。田汉自己也在《关于“秋声赋”》一文中说:“这里面的主要人物可议之处都很多,但本质上都很善良,我仍没有把他们性格把握得更深刻。”[7]田汉自述创作该剧是为帮新中国剧社一些青年朋友们的忙,将平常所感的若干部分一吐为快,田汉的剧作经常是这样突击创作,虽然有时情节、人物刻画不周,但都是作者思想的流露。
此外,由于受传统戏曲的影响,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田汉都未遵循“三一律”的原则,地点在桂林、长沙之间切换,时间横跨1938-1941这三年的时间,由此导致故事情节采用分裂的块状结构,同样减弱了戏剧引人入胜的情节性。值得一提的是,田汉对舞台布景不重视,极少看到对舞台道具的精心设计,同样对比濮瞬卿《人间的乐园》,两位作者都将声音当做重要的表现手段,但濮瞬卿极为精心地在声音后面标注“风雨雷电可用人为……雷声只须在台上推重物似雷声就对了”[8],而田汉在全剧中都没有关注,或许在创作伊始,田汉更多地将其当做一部诗剧来写作,而不是舞台剧。
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周贻白指出:“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9]余秋雨更明确指出:“任何戏剧作品,都是为了演给由若干人组成的一群观众欣赏的,这就是戏剧作品的真正本质,这就是一个剧本存在的必须条件。”[10]在这个层面上讲,与田汉相对应,曹禺总是选择那些最能造成和加强戏剧的逼人情节、对人物的生命存在和生命追求构成严重威胁,直接撞击人物的情感与心理的紧急事件。因而《秋声赋》与《雷雨》在演出中出现两极接受反应。
三、中与西: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矛盾
田汉的话剧创作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现实斗争精神,因而现实主义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也是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作家自觉践行的创作观,但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将其创作的现实性过分拔高则过之无不及,不仅有生搬硬套的过度解读之感,而且影响了田汉作品的艺术性。田汉在日本求学时曾接触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希望“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有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窥知超感觉的世界”[11]。而且他本身又非常注重个人感受,因此《秋声赋》以现实主义的题材呈现浪漫主义的内质,彼时中国正值日寇入侵,文艺以抗战为中心,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潮,主要呈现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急处境,调动人民抗战积极性成为文学界义不容辞的民族责任,文学的载道功能压倒审美功能,《秋声赋》的审美现代性特质与当时社会唯现实主义论的氛围扞格不入。
“田汉的话剧并非侧重对现实的逼真描摹,他并不追求情节的完整一致性,而使将人物对现实的感受、事件在人物内心激起的波澜以舒缓、细腻的语调展示给观众,也就是说,他真的作品最吸引观众的不是‘事’而是由事引出的‘情’,而重视情感的直接宣泄恰恰是浪漫主义戏剧的重要标志之一。”[12]所以《秋声赋》可视作一部诗剧,从人物形象到意境营造都具有诗性的浪漫主义抒情性。
秦淑瑾是“传统女性”,属“家庭型”妻子,胡蓼红是“摩登女郎”,属“社会型”情人,前者是现实主义的,稳定如石,后者是浪漫主义的,跃动似火,这两者都是田汉所需要的。胡蓼红与安娥一般热情开放,又有一点率性,因革命是提着脑袋干的,于是把丈夫让给秦淑瑾,还为徐子羽生过一个孩子,后革命工作公开,允许有丈夫,于是毫不犹豫地回来找寻爱情,她对于自己的生活听任内心情感的诉求,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男主人公徐子羽是“感伤的漂泊者”形象,现实的“家”对于徐子羽而言更像是一个负累,三个女人对他的爱是束缚,“家庭”对于他并非“家”的真正含义,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才是其理想追求。正是这种感伤削弱了《秋声赋》的政治主题而引向一种知识分子在家庭和社会的夹缝中抑郁不得志的主题。而且剧作极重视对意境的追求,剧本中对桂林风景的描写更是平添诗意,增加戏剧的文学性,但在演出时却很难发挥其作用,舞台动作少,减少了“戏味”。作品中抒情和幻想的成分多于对于现实的如实描绘,强烈的主观抒情压倒客观叙事。
田汉的本意是想借文化工作者不肯以恋爱纠纷影响其革命工作,并且在革命工作中统一他们矛盾的故事,这样从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生活入手可以更游刃有余地驾驭材料,写得更真实、深切。事实也的确如此,《秋声赋》中那浓重的萧瑟氛围和知识分子细致入微的心理描摹,使得《秋声赋》成为田汉创作中文学性最高的文学作品之一。“文学不借人,无以表示‘性’。”“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13]但知识分子的苦闷生活对于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大众而言确实过于遥远,他们无法理解徐子羽的两难抉择和内心苦闷,整部剧作压抑、凄清的情感氛围也无法激起大众的革命热情。人民大众自古以来“喜乐不喜悲”,古代戏曲无论多么曲折,最后总会有个团圆的尾巴,以结局的团圆证明剧作意旨的正确性。而《秋声赋》中那个“光明”的尾巴却是无力的,既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也没有浪漫主义那种强烈情感的冲击力,诚然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但没能带来“戏”的深刻意蕴。[14]
结语
《秋声赋》文学价值与戏剧价值不协调,从根本而言是将其视为文学作品还是戏剧剧本看待,类别不同,审美标准自然也有差异。无疑,田汉在创作时情感诉求超越创作理性,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技巧实验、艺术追求融汇其中,而较少考虑社会功用、演出效果和时代思潮,二者的差异使《秋声赋》具有内在的分裂,相比较而言“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白毛女》,虽然因意识形态的规囿而在内容上有诸多瑕疵,但因为有效借重西方歌剧形式而具有艺术上的美感,在无产阶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次实验对于田汉而言或许并不算成功,但却标志着剧作家开始探求从传统戏剧到现代话剧的转型,并试着将二者结合,这一追求是任重而道远的,直至今天写剧和演剧仍是考验剧作家的重要命题。值得庆幸的是,在埋没将近七十年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师生将《秋声赋》重新搬上舞台,并引起轰动。在七十多年前,《秋声赋》作为一部试图融入主流的抗战革命剧未获成功,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其艺术深处的文学魅力却使它赢得诸多赞誉,这恐怕是田汉当时始料未及的。
[1][14]陈瘦竹.论田汉的话剧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80,50.
[2][6]董健.田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5,280.
[3][12]刘方政.田汉话剧创作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160,178.
[4]田申.我的父亲田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50.
[5]丁涛.戏剧三人行:重读曹禺、田汉、郭沫若[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87.
[7]田汉.田汉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484.
[8] 濮舜卿.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290.
[9][10]刘思家.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2,2.
[11]何寅泰,李达.田汉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48.
[1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32:208.
责任编辑:陈冬梅
I207.3
A
1671-4288(2017)04-0057-04
2017—05—23
温雅红(1992-),女,山西太谷人,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